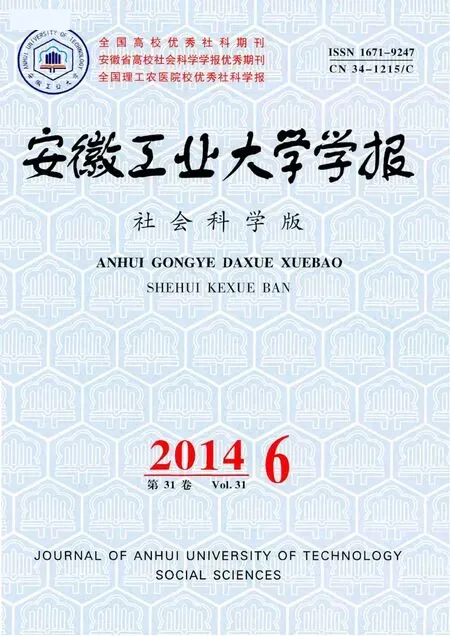《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中黑人女性尋求自我話語(yǔ)權(quán)的心路歷程
呂萬(wàn)英,徐誠(chéng)榕
(中南民族大學(xué) 外語(yǔ)學(xué)院,湖北 武漢430074)
瑪雅·安吉洛是美國(guó)當(dāng)代著名的黑人女詩(shī)人、暢銷書作家及人權(quán)活動(dòng)家。小說(shuō)《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是其撰寫的六部自傳作品中影響力最大的一部,記錄了她童年和少年時(shí)代的生活。作品將自傳與女性成長(zhǎng)小說(shuō)完美地結(jié)合起來(lái),形成了一個(gè)帶有獨(dú)特?cái)⑹嘛L(fēng)格的文體,突破了傳統(tǒng)自傳與成長(zhǎng)小說(shuō)的敘事方式,細(xì)膩而深刻地展現(xiàn)了一個(gè)黑人女性所特有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筆者擬從人格心理學(xué)的視角,針對(duì)人格面具的變換展開分析,來(lái)探究黑人女性尋求自我話語(yǔ)權(quán)的心路歷程。
一、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一詞源于演員所帶的面具,是瑞士心理學(xué)家、當(dāng)代分析心理學(xué)創(chuàng)始者卡爾·榮格集體無(wú)意識(shí)理論中原型的重要構(gòu)成之一。人格由面具所構(gòu)成,一個(gè)面具就是一個(gè)子人格,或人格的一個(gè)側(cè)面,人格就是一個(gè)人所使用過(guò)的所有面具的總和,“實(shí)際上是我們所說(shuō)的‘我’,我們所表現(xiàn)給別人看到的我們自己”。[1]榮格認(rèn)為:“人格最外層的人格面具掩蓋了真我,使人格成為一種假象,按著別人的期望行事,同他的真正人格并不一致。人可靠面具協(xié)調(diào)人與社會(huì)之間的關(guān)系,決定一個(gè)人以什么形象在社會(huì)上露面……人格面具是原型的一種象征。”[2]人格面具是一種社會(huì)產(chǎn)物,它把人際交往的方式上升到了理論層面,是個(gè)人與社會(huì)關(guān)于人應(yīng)該如何行事所達(dá)成的一種妥協(xié)。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人格面具靠我們的服飾、談吐、肢體語(yǔ)言等告訴外界“我”是誰(shuí),去表現(xiàn)理想化的“我”。此外,人格面具可以掩蓋人們因面對(duì)未知的人、事物或環(huán)境所產(chǎn)生的怯懦與恐懼,有意無(wú)意間進(jìn)行心理上的調(diào)整,從而產(chǎn)生了與真實(shí)人性不同的心境。人們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戴著人格面具,在不同的時(shí)機(jī)、場(chǎng)合使用不同的面具來(lái)表達(dá)不同的心理活動(dòng)。
二、瑪雅人格面具的變換
在小說(shuō)《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中,瑪雅3到16歲的成長(zhǎng)過(guò)程是一個(gè)持續(xù)轉(zhuǎn)換人格面具的過(guò)程:由幼年時(shí)期的幻想型人格面具,到少年時(shí)期的遠(yuǎn)離型人格面具,再到青年時(shí)期叛逆型人格面具以及對(duì)消極偽裝性人格面具的摒棄,從迷惘、困惑、痛苦到自我意識(shí)的覺(jué)醒,瑪雅迎難而上,逐漸獲得了社會(huì)大眾的認(rèn)可。
(一)幼年瑪雅的幻想型人格面具
在南北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后半個(gè)多世紀(jì)的南方,白人仍然在心理上固執(zhí)地捍衛(wèi)著自己曾經(jīng)的特權(quán),這種偏執(zhí)的心理甚至比以往更頑固、更瘋狂,致使像斯坦普斯一樣的南方小鎮(zhèn)依然籠罩在種族歧視的陰霾之中。生活在這種氛圍中,幼年瑪雅很早就察覺(jué)到自己卑微的社會(huì)地位,過(guò)早地承受屈辱、悲慘的命運(yùn)。同大多數(shù)黑人女性一樣,瑪雅的內(nèi)心極度自卑,“我的腿上涂抹著藍(lán)標(biāo)凡士林,還撲上了阿肯色紅土。經(jīng)年累月,土的顏色滲入皮膚,讓它看起來(lái)骯臟而惡心……”[3]2對(duì)于自己 “又黑又卷”的頭發(fā),“又寬又大”的腳板,有“間隙”的門牙都十分厭惡,阿媽精心為她縫制的復(fù)活節(jié)長(zhǎng)裙也不過(guò)是“白人洗舊了不要的紫色長(zhǎng)裙”。白人長(zhǎng)期的偏見(jiàn)以及白人對(duì)黑人肆無(wú)忌憚的欺凌讓瑪雅對(duì)黑人身份產(chǎn)生了錯(cuò)位感。這種以白人即美、黑人即丑的錯(cuò)位感讓瑪雅極度壓抑和痛苦,因而幻想有一天能徹底擺脫,成為有“一頭金發(fā)”和“大而迷人”、“淺藍(lán)色”眼睛的白人小姑娘。小瑪雅甚至執(zhí)著地幻想自己本有著白人的身份,只是遭邪惡的巫婆繼母嫉妒才被其施魔法“變成一個(gè)丑陋的、大碼子黑人”。這是一個(gè)生活在還帶有嚴(yán)重種族歧視色彩的美國(guó)黑人少女發(fā)自內(nèi)心的奇想。
在白人文化占主導(dǎo)地位的美國(guó),瑪雅從生活中直觀地感覺(jué)到社會(huì)對(duì)黑人的厭惡和否定。毫無(wú)疑問(wèn),幼小的瑪雅不可能深層次地去認(rèn)識(shí)和剖析生活之所以痛苦、壓抑的原因,她只能憑自己稚嫩的心靈去思考,并認(rèn)定一切是由于自己容貌的丑陋所致,從而否定自己。幼年時(shí)期的瑪雅將自己長(zhǎng)時(shí)間隱藏在一個(gè)幻想型的人格面具之后,反映了身為黑人的小瑪雅強(qiáng)烈的自卑感和錯(cuò)位感,同時(shí)也反映了她希望能像白人那樣獲得他人的尊重。
(二)少年瑪雅的遠(yuǎn)離型人格面具
少年時(shí)期的瑪雅從熟悉的南方小鎮(zhèn)被接到圣路易斯外婆家,環(huán)境的突變使瑪雅心理產(chǎn)生了很大的抗拒。門鈴、火車、汽車、巴士、抽水馬桶的噪音等各種喧囂使她意識(shí)到自己不屬于這里,因而將自己的內(nèi)心深深隱藏起來(lái)。更不堪的是,年僅八歲的她在搬到媽媽家之后不久便遭到媽媽的男友弗里曼多次騷擾和強(qiáng)暴,并被弗里曼威脅不準(zhǔn)說(shuō)出去,否則就要?dú)⒘怂钣H近的哥哥貝利。性騷擾和強(qiáng)暴以及對(duì)弗里曼的恐懼等令人心碎的事情幾乎將瑪雅推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些痛苦的經(jīng)歷使少年時(shí)期的瑪雅一度寡言少語(yǔ),刻意疏遠(yuǎn)身邊的人,包括親近的阿媽和威利叔叔,以此掩蓋痛苦的回憶,同時(shí)包裹自己,免受流言蜚語(yǔ)傷害。在將近一年的時(shí)間里,瑪雅沉默寡言,過(guò)著乏味的“像一塊過(guò)期餅干、落滿塵埃”的生活,除了哥哥貝利,瑪雅不與任何人交流:“我走進(jìn)一個(gè)房間,人們有說(shuō)有笑,他們的聲音如碎石一般撞擊著墻壁。而我只要靜靜地站著,站在這喧囂中,一兩分鐘后,寧?kù)o就會(huì)重歸此處,因?yàn)槲彝淌闪怂械穆曇簟!保?]91回到祖母身邊后,相當(dāng)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她認(rèn)為自己滿身罪惡與骯臟,變得敏感多疑,認(rèn)為威利叔叔的眼睛“滿是疏遠(yuǎn)的神色”,以至對(duì)自己的精神狀態(tài)產(chǎn)生疑慮:“所有傳到耳朵里的聲音都變得沉悶……周圍的顏色不再逼真……那完全不是我以往熟悉的斯坦普斯,人們的名字也逃離了我的記憶。”[3]91這些痛苦的經(jīng)歷使瑪雅親自為自己帶上遠(yuǎn)離型人格面具,封閉自己,縮進(jìn)了為自己織好的繭。
(三)瑪雅消極偽裝型人格面具的摒棄
對(duì)于少年的瑪雅來(lái)說(shuō),與弗勞爾斯夫人的相識(shí)改變了她的一生,弗勞爾斯夫人拋給了困境中的瑪雅一條救生索。弗勞爾斯夫人高貴優(yōu)雅,獨(dú)立自信,并善于開啟瑪雅因受傷而封閉的心靈。在瑪雅情緒低沉?xí)r,弗勞爾斯夫人借給她詩(shī)集,鼓勵(lì)她開口誦讀,讓她領(lǐng)略詩(shī)歌的魅力,認(rèn)識(shí)語(yǔ)言的神奇力量。朗誦書籍讓瑪雅打開了封閉許久的心扉,當(dāng)瑪雅讀到“我現(xiàn)在做的事,比從前要好得多得多”時(shí)終于釋懷,愿意與人交流了,摒棄了遠(yuǎn)離型面具,這是她成長(zhǎng)道路上的一個(gè)重要轉(zhuǎn)折。
在弗勞爾斯夫人的幫助下,瑪雅開始認(rèn)同自己的黑人身份,逐漸意識(shí)到了自身的存在價(jià)值以及黑人尊嚴(yán)的重要性。這表現(xiàn)在,她不愿被白人為了稱呼方便就隨意簡(jiǎn)化自己的名字,在觀看以黑人為笑料的電影時(shí)的不安和反思,同時(shí),慨嘆黑人對(duì)自己悲慘境遇麻木不仁。十歲的瑪雅在卡利南夫人家做女傭時(shí),被這位夫人隨意更改了名字,便故意打碎了白人主人心愛(ài)的盤子以示抗議,贏得了保衛(wèi)尊嚴(yán)的第一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瑪雅的反抗不僅是她個(gè)人身份意識(shí)的覺(jué)醒,也代表了全體黑人女性的抗?fàn)帯讉€(gè)世紀(jì)以來(lái)黑人總是被隨意稱呼,如“黑鬼、黑雞,臟鬼”等,這些稱呼是對(duì)黑人的侮辱,稱呼的隨意性折射出黑人作為一個(gè)種族的卑微和可有可無(wú)。瑪雅的反擊行為不僅讓其萌生了自我意識(shí),還使她走出了白人為黑人劃定的狹小生存空間,為自己是“偉大而美麗的黑人種族的一份子”而無(wú)比自豪,并極力維護(hù)著黑人的尊嚴(yán)。最終瑪雅卸下了自己幻想型人格面具,開始了獨(dú)立人格的蛻變。
(四)青年瑪雅充滿理想的有效社會(huì)人格的形成
瑪雅的青年時(shí)期除在洛杉磯停留半年,大部分時(shí)間是在舊金山度過(guò)的。瑪雅來(lái)到舊金山恰逢二戰(zhàn)剛開始不久,日本人大批逃離,大批黑人從喬治亞、密西西比等地涌進(jìn)舊金山,原先的日本人聚集區(qū)很快變成“哈萊姆”區(qū),黑人平生第一次成為生活的“主角”,他們可以付錢讓別人為自己服務(wù),這讓黑人意識(shí)到自己也“有人需要甚至欣賞”。這時(shí)的瑪雅漸漸產(chǎn)生了一種“歸屬感”,開始在心中塑造理想的自我,“希望自己長(zhǎng)大成人后友善而矜持,冷靜卻不冷漠或拒人千里,高貴但不頑固”,并且變得勇敢無(wú)畏。此時(shí)舊金山流傳著的關(guān)于黑人老兵在公汽上為尊嚴(yán)而不卑不亢地回?fù)舭兹似缫暤墓适卤砻鳎谌俗鳛槿后w對(duì)白人的歧視不再忍耐而是奮起反擊,這無(wú)疑是黑人開始身份認(rèn)同的象征。
與爸爸一同跨越邊境去墨西哥探險(xiǎn)的旅程則讓瑪雅清楚地看到了爸爸面具后的另一面:自信且游刃有余。瑪雅爸爸在墨西哥小酒吧中輕松自信的表現(xiàn)讓瑪雅再次找到歸屬感:“他是美國(guó)人,他是黑人”,這個(gè)身份足以讓“他們(墨西哥人)崇拜敬仰”。
瑪雅開始從各個(gè)方面證明自己:回家的路上,從沒(méi)開過(guò)車的瑪雅決定代替酒醉的爸爸駕駛,盡管知道稍有不慎,就會(huì)跌落山崖、車毀人亡,但這樣的挑戰(zhàn)卻讓瑪雅興奮:“我,瑪格麗特,獨(dú)自對(duì)抗著自然的偉力。”[3]243這是瑪雅自立自信的突出表現(xiàn)。隨后,從爸爸那出走,在廢舊車場(chǎng)的經(jīng)歷讓瑪雅產(chǎn)生了歸屬感。瑪雅和一群黑人、白人還有墨西哥人的流浪孩子生活了一個(gè)月,撿瓶子、修剪草坪、給店鋪跑腿等等,她敞開心扉融合到一個(gè)多種族的氛圍之中,產(chǎn)生了不分種族、不分彼此的觀念,打破了種族的藩籬。
生活在一個(gè)備受歧視的年代,黑人女性要承受來(lái)自性別、種族與階層的多重壓迫,生活給予她們的從不是甜美,而是困惑、絕望和無(wú)休止的羞辱。受“南方黑人教育”的瑪雅,和其他黑人女性一樣,深刻感受到生活的不公平和沉重的壓力。在遭受一系列不公之后的瑪雅,在與生活和種族歧視抗?fàn)幍倪^(guò)程中,越來(lái)越清晰地認(rèn)識(shí)到獨(dú)立自強(qiáng)的重要。而母親無(wú)所畏懼獨(dú)立打拼的個(gè)性也無(wú)形中影響著瑪雅。母親“自助者,上帝助之”的箴言和“沒(méi)有什么事人們做不成的”話語(yǔ)鼓舞著瑪雅。南方之行結(jié)束后,瑪雅自主的理念越發(fā)強(qiáng)烈,她立志成為舊金山電車上首位被雇的女性黑人。盡管遭受前所未有的質(zhì)疑和冷漠,瑪雅表現(xiàn)出了驚人的倔強(qiáng)和勇氣,決心打破舊金山不讓有色人種上有軌電車(工作)的限制。瑪雅通過(guò)呼吁黑人組織支持,鍥而不舍地爭(zhēng)取,最終成為舊金山電車上首位女性職員,證明了自己的存價(jià)值。
三、人格面具變換下的自我話語(yǔ)權(quán)
19世紀(jì)40年代以前,美國(guó)黑人女性在文學(xué)作品中往往都被刻畫成“單一的女傭形象:黝黑,肥胖,健壯,迷信,吃苦耐勞,毫無(wú)存在感且毫無(wú)話語(yǔ)權(quán)”。[4]19世紀(jì)后期,隨著美國(guó)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的蓬勃發(fā)展,黑人女性勇于向傳統(tǒng)社會(huì)挑戰(zhàn)、尋求自我話語(yǔ)權(quán)。《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中,作者通過(guò)細(xì)膩而深刻的筆觸,展現(xiàn)了主人公人格面具變換下坎坷的成長(zhǎng)道路和走出失語(yǔ)狀態(tài)的心路歷程,不僅為黑人女性爭(zhēng)取了平等的話語(yǔ)權(quán),也印證了福柯的論斷:強(qiáng)勢(shì)群體,即占據(jù)話語(yǔ)權(quán)的一方為了自己的主體地位,往往會(huì)施加一種壓力,抹殺他者的聲音。而被壓迫的一方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代表權(quán)力話語(yǔ)發(fā)言。[5]
(一)幻想型人格和遠(yuǎn)離型人格面具下的無(wú)語(yǔ)和失語(yǔ)
美國(guó)內(nèi)戰(zhàn)后,黑人的人權(quán)在法律上得到肯定,然而種族歧視并未隨著黑奴的解放而消失,黑人的社會(huì)生存環(huán)境依然惡劣。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幼年的瑪雅帶著幻想型面具過(guò)得自卑且壓抑,盡管她逃避現(xiàn)實(shí),幻想自己白人小女孩的身份,現(xiàn)實(shí)卻是痛苦的,當(dāng)瑪雅在教堂背不出頌歌,被牧師的妻子嘲笑且一臉憐憫地說(shuō)“愿上帝保佑這個(gè)孩子”時(shí),羞怯、屈辱的感覺(jué)在心里劇烈碰撞,瑪雅想逃離卻被絆了個(gè)趔趄,盡管她想說(shuō)些什么卻無(wú)法開口,屈辱的感覺(jué)使瑪雅失去控制而便溺。在小瑪雅眼中,阿媽的形象無(wú)疑是高大的,然而當(dāng)那些不懂禮節(jié)的白人小混混成群結(jié)隊(duì)地闖進(jìn)店里胡鬧,用奇怪的姿勢(shì)模仿、侮辱阿媽時(shí),小瑪雅除了幻想自己“抓一把黑胡椒粉撒到她們臉上,再將堿水灌進(jìn)她們的鼻子”,[3]32卻也只能在一旁哭泣,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和無(wú)能為力。稚嫩、脆弱、自卑且缺乏安全感致使瑪雅逆來(lái)順受,無(wú)法用言語(yǔ)來(lái)維護(hù)自己和家人的尊嚴(yán),此時(shí)的瑪雅毫無(wú)話語(yǔ)權(quán)可言。
以早期的小瑪雅為代表,黑人女性在種族歧視和傳統(tǒng)觀念的雙重枷鎖束縛下,無(wú)法在社會(huì)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大部分黑人女性甚至意識(shí)不到自己悲苦的命運(yùn),只是在沉重的枷鎖下渾渾噩噩地活著,她們?cè)诜N族與性別的壓迫下,在白人文化的侵蝕下,更加不敢開口說(shuō)話,長(zhǎng)期處于失語(yǔ)的狀態(tài)。
(二)叛逆型人格和有效社會(huì)人格面具下話語(yǔ)權(quán)的重建
回到斯坦普斯小鎮(zhèn)一年多后,瑪雅在弗勞爾斯夫人的開導(dǎo)下已漸漸走出難堪的過(guò)往。小說(shuō)有這樣的一個(gè)場(chǎng)景:一次阿媽帶瑪雅到鎮(zhèn)上的診所去看牙醫(yī)卻遭到白人醫(yī)生的拒絕,而且還用刻薄的語(yǔ)言侮辱她們,不得已的阿媽只好將瑪雅留在門外,自己去求醫(yī)生。門外的瑪雅卻想象著阿媽昂首闊步地走進(jìn)去揪住醫(yī)生的衣領(lǐng)痛罵道:“你是我見(jiàn)過(guò)的最‘對(duì)不起觀眾’的醫(yī)生了”、“我不想讓你當(dāng)著瑪格麗特的面道歉,因?yàn)槲也幌胱屗牢业牧α浚谴藭r(shí)此刻我要命令你,太陽(yáng)落山以前離開斯丹普斯。”[3]195盡管是想象,瑪雅卻覺(jué)得牙疼已經(jīng)減輕。可以看出,當(dāng)瑪雅面對(duì)不公平待遇時(shí),不再忍氣吞聲,雖是借由著想象中阿媽的言語(yǔ),卻是瑪雅內(nèi)心叛逆、抗?fàn)幾钣辛Φ谋憩F(xiàn)。
此外,當(dāng)瑪雅在爸爸家度假時(shí),爸爸的情人多洛雷絲卻對(duì)她心生不滿,認(rèn)為她妨礙了兩人的關(guān)系,言語(yǔ)上極盡刻薄甚至出言侮辱瑪雅的媽媽,瑪雅被激怒道:“我的媽媽,她比你強(qiáng)一百倍……”“我要扇你這個(gè)又蠢又老的賤貨”,[3]250說(shuō)罷便同她打了起來(lái)。此時(shí)的瑪雅走出了失語(yǔ)狀態(tài),重拾了自己的話語(yǔ)權(quán),語(yǔ)言上不再是被壓迫的一方。青少年時(shí)期的瑪雅積極向上,充滿理想。南方之行結(jié)束后,瑪雅立志成為舊金山電車上的售票員,盡管壓力重重,她依舊堅(jiān)持著去證明自己的存在價(jià)值,“我會(huì)得到那份工作。我要成為一名售票員,挎上一個(gè)用我的皮帶改成的鼓鼓囊囊的零錢袋。我說(shuō)道做到。”[3]273最終瑪雅成為了舊金山電車上首位被雇的女性黑人。青少年時(shí)期的經(jīng)歷也讓瑪雅學(xué)會(huì)認(rèn)識(shí)自我、直面自我,喚起了自我作為主體的力量,恢復(fù)了自我話語(yǔ)權(quán),不再是一名“需要黑人貧民窟這塊盾牌呵護(hù)的”黑人女性。
四、結(jié)語(yǔ)
借助心理學(xué)中人格面具這一理論可以看到,在《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這部自傳體小說(shuō)中,主人公瑪雅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體現(xiàn)了一個(gè)在人格面具更替下自我話語(yǔ)權(quán)恢復(fù)的過(guò)程:從沉默失聲到為話語(yǔ)權(quán)進(jìn)行抗?fàn)帲俚阶晕以捳Z(yǔ)權(quán)的恢復(fù),展現(xiàn)了黑人女性重獲自我話語(yǔ)權(quán)的艱難曲折的心路歷程。同時(shí),我們也從該作品中看到了一種全新的黑人女性性格特點(diǎn):堅(jiān)韌、執(zhí)著、自立,宛如真正沖破牢籠的鳥兒一般,自由歌唱。
[1]申荷永.榮格與分析心理學(xué)[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2.
[2]何靜靜.人格面具與自我迷失——探究長(zhǎng)日入夜行的人物悲劇性格來(lái)源[J].綏化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5):140-142.
[3]瑪雅·安吉洛.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M].于宵,王笑紅,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3.
[4]朱振武.美國(guó)小說(shuō)本土化的多元因素[M].上海:上海外語(yǔ)教育出版社,2006.
[5]Foucault,M.TheArchaeologyofKnowledge[M].Sheridan Smith A M,trans.New York:Random House,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