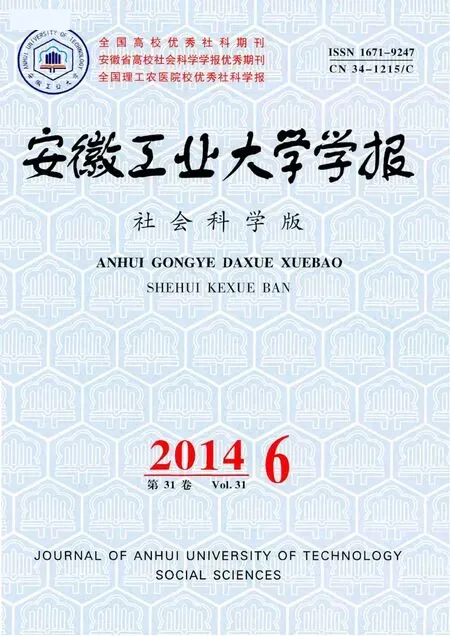從翻譯規范論評析楊憲益戴乃迭的《祝福》英譯本
李 靚,韓江洪
(合肥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9)
?
從翻譯規范論評析楊憲益戴乃迭的《祝福》英譯本
李靚,韓江洪
(合肥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運用切斯特曼翻譯規范論,對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魯迅經典小說《祝福》英譯本進行評析。研究發現,楊、戴在翻譯《祝福》中地點名詞、民俗詞、人稱頭銜詞和其他中國特色詞匯時,靈活運用了直譯、意譯、拆分法等多種翻譯策略來順應當時的翻譯規范。
關鍵詞:《祝福》;翻譯策略;翻譯規范
《中國文學》是新中國第一份、也是惟一一份向國外及時系統地譯介中國文學藝術作品的官方刊物,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平臺,許多外國讀者對新中國的了解都是從《中國文學》開始的。在發行初期,參與翻譯的譯者不多,楊憲益、戴乃迭夫婦承擔了大量作品的翻譯工作。作為優秀的翻譯家,他們的翻譯作品深受好評,譯作多以保留中國語言習慣、直譯為主注釋為輔為特點。其中,收錄在《中國文學》1961年第9期的魯迅小說《祝福》英譯本是其代表譯作之一。
《祝福》是魯迅的經典作品之一,其刻畫的祥林嫂角色入木三分,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階級對勞動婦女的摧殘與迫害。由于當時國內與國際環境的特殊性,再加上《中國文學》在外宣工作中的重要性,楊憲益、戴乃迭二人在翻譯時,需要遵循當時的翻譯規范,選擇相應的翻譯策略。
但目前的國內研究,探索《中國文學》刊登的英譯作品是如何遵循翻譯規范的甚少,為了拓展和深化對《中國文學》英譯作品及譯者風格的認識,本文將從切斯特曼的翻譯規范論角度,對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祝福》進行評析,建構當時制約譯者翻譯的翻譯規范,并探索楊戴二人在翻譯時是如何選擇翻譯策略順應當時的翻譯規范的。
一、切斯特曼翻譯規范論簡介
切斯特曼構筑的翻譯理論框架中有個不得不提到的詞——“文化基因”(meme)。文化基因最早見于多金斯(Dawkins)《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一書。按多金斯的定義,文化基因是“文化傳播的單位,或是模仿的單位”。翻譯也是文化現象之一。把文化基因運用到翻譯研究上來,是切斯特曼的一種創新。切斯特曼認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文化基因會占主導地位,強調翻譯的不同方面。而當這些占據了主導的文化基因逐漸獲得大眾認可,占據統治地位時,就形成了翻譯規范。[1]51
切斯特曼將翻譯規范分成了兩類:期待規范與專業規范。
期待規范由目標讀者對于譯文的期待建立,這種期待可能會受經濟或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權威等因素的影響。專業規范制約翻譯過程本身,其又可細分為:責任規范、交際規范和關系規范。責任規范就是要求譯者應對原作者、翻譯委托人、譯者本身以及目標讀者和有關各方忠誠。這也可以看作一條道德規范。交際規范要求譯者能隨不同場合優化翻譯涉及的各方之間的交流,即使得各方交際流暢。這也可以看作一條社會規范。關系規范要求譯者要在源語文本和目標語文本間建立并維持著合適的相關相似性,即譯作要保持與原文本的相關性,這也就從語言學的角度給予了解釋。[1]64-70
廣為人知的翻譯家嚴復的翻譯標準“信、達、雅”,正是翻譯規范的體現。這就說明,為符合翻譯標準而采用的翻譯策略其實受著翻譯規范的制約,反之,翻譯規范決定了譯者對于翻譯策略的選擇。
那么翻譯規范是否有其制約因素呢?切斯特曼給出了研究答案。四種翻譯規范其實是受四種價值觀制約的,分別是:明晰、真實、信任與理解。明晰制約期待規范,真實制約關系規范,信任制約責任規范,理解制約交際規范。因此,在翻譯過程中,當規范相對于價值觀不夠充分時,譯者可能會選擇偏離規范而不偏離價值觀。[1]172-183
二、20世紀60年代翻譯規范的重構
(一)期待規范
《中國文學》的選材取舍是基于對國外讀者需求的了解基礎上做出的:“大多數外國讀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感興趣,而西方學術界則對中國古典文學著作有很大的需求。”[2]而對于外國人來說,他們閱讀中國作品翻譯,主要是想通過文字來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普通人的感情,他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生活是怎樣的,這才是他們想要了解的主要方面。他們對于小說翻譯的藝術性要求其實是次要的。[3]因此,對于《中國文學》的編譯一直都是結合當代文學與古典文學,多方面展現當時中國的精神狀態。
《中國文學》自出版后受到鼓勵與支持頗多。印度共產黨文化部門曾寫信贊揚刊物出得及時,認為通過它不僅可以了解中國的新文學,還可以了解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進行的革命斗爭。當時許多進步作家讀完創刊號后,紛紛寫來長信,熱烈地祝賀《中國文學》的誕生并激動地談讀后感。他們認為,《中國文學》塑造了新中國新的人民形象,中國人民反壓迫、反剝削、敢于抗爭,給大家指出了一條道路。在歐洲方面,莫斯科出版的《國際文學》發表了評價這個刊物誕生的專文。[4]103由此可見,《中國文學》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讀者對《中國文學》的期待不僅包括從對中國文學的審美角度,了解中國文化與中國作品,還包括從意識形態上對中國作品展現的內容與思想進行解讀。雖然在亞非拉國家中,《中國文學》在讀者中得到了廣泛支持,但也曾受到西方讀者的反對和批評。比如,1960 年,《中國文學》第 9 期刊登了一組反美斗爭的文章,引起外國讀者強烈反應,導致刊物在國外銷售量普遍下降。[4]108由此可見,譯者在翻譯作品時,既要保留中國特色,如讀者期待的那樣展示出中國作品所反映的生活與精神狀態,又要考慮譯文發行到的國家的意識形態,這樣才算是符合了當時的期待規范。
(二)專業規范
《中國文學》以及整個外文局都是負責向國外介紹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樹立新中國的國家形象,讓國外了解中國。中國文學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連著中國人的心靈。如原中國文學出版社中文部編審徐慎貴先生所說:“就《中國文學》來說,在文革之前,陳毅副總理主管對外宣傳,他本人也十分喜歡文學。陳毅同志給我社講過兩次話,他有一次說過:你們要把中國最好的作品,藝術性最強的東西,大家真正能認可的作品介紹出去。最高的東西介紹出去,手法要潛移默化。”[5]
而當時優秀的譯者并不多,楊憲益、戴乃迭夫婦承擔了《中國文學》創作的很多翻譯工作。但是即使這樣專家級的譯者,也有許多不得已之處。“楊憲益喜歡翻譯,喜歡自己選擇翻譯并享受推敲的過程,而不愿意受人之命。有些外行,只把他當個翻譯機器。尤其大躍進時期,要趕很多任務,或者是領導需要他翻譯某個他并不熟悉但卻爆紅的作家,他固然不愿意搞應景的翻譯,但是也必須服從上級的安排。”[6]因此按照當時的責任規范,楊夫婦二人在翻譯時,不僅要對作者、讀者負責,還要忠于出版社,即對翻譯委托人負責。
縱觀《中國文學》早期的翻譯作品,整體來看,參與翻譯的中外譯者在翻譯方法上的選擇傾向于直譯為主,多數譯本比較忠實于原文。譯者力圖準確展現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風格和形象,保留中國特色,體現出當時的關系規范,與原文“保持著一種適宜的相關類似性”。
漢語重意合,英語重形合。漢語的意合一般無需借助于詞匯語法的銜接手段,僅靠詞語和句子的內涵意義的邏輯關系,便能構成連貫的語篇;而英語往往少不了詞匯句法的顯性連接,即從語言形式上把詞語句子組成語篇整體。[7]因此為了保證譯文的流暢,譯者需要對句子適當加工,保證讀者與譯文之間的交流順利,即順應交際規范。
三、對《祝福》的英譯文具體分析
(一)地點名詞的翻譯
《祝福》作為一部反映中國舊社會民間生活的小說,其中有許多地點名詞的出現,楊憲益、戴乃迭對于地點名詞的處理,采用了直譯與音譯相結合的策略,將中國式的地點名詞巧妙地轉換成了適應讀者語言習慣的表達方式,順應了當時的翻譯規范。
例如,隨著故事的發展,文中陸續出現了不同地點,如衛家山、賀家坳,楊憲益、戴乃迭對它們的處理就是以姓氏為村莊名,即分別譯成Wei Village及Ho Village。某家山、某家坳是中國民間常見的村莊名,以擁有同樣姓氏的村民為主要居民,因而衛家山的居民多姓衛,賀家坳的居民多姓賀。從切斯特曼翻譯規范論角度來看,楊、戴采用直譯的方法既忠實原文,體現了譯文與原文的相關性,又保留了中國特色,符合當時的關系規范。同時譯文又對村莊名作了處理,符合英語發音習慣,易于目的語讀者理解,體現了交際規范。
而對于故事主要發生的地點——魯鎮,他們卻采取了另一種方法,將其音譯為Luchen,而非直譯為Lu Village。首先,魯鎮并非許多姓魯的人一起居住的城鎮,因此相對于衛家山、賀家坳,需要采取另一種翻譯策略。其次,魯鎮是一個虛構的小鎮。雖然它是以魯迅的故鄉紹興作為原型,但地理上并沒有這個城鎮。然而,魯迅小說很多經典人物都出自魯鎮,如阿Q、孔乙己、楊二嫂等,它相當于一種地點象征。因此魯鎮的翻譯無須拘泥于原語的字面涵義,而可以自由地音譯為Luchen。這樣就既保留了其發音的中國特色,靠近原文,又符合讀者對于譯文的異域期待,體現了期待規范的要求。
(二)民俗詞的翻譯
《祝福》的故事發生在舊社會中國,并且是在年底迎接新年的時候,因此文中出現了大量關于中國年關民俗的描寫。此外由于故事發生在舊社會,也存在許多具有時代特色的詞匯。楊、戴對于這些詞多采用直譯法與注釋法。對于不影響讀者理解故事背景的詞匯,采用直譯,體現對作者對文本負責任的態度,并且充分保證讀者的閱讀順暢,順應了專業規范。而對于折射出中國民間風俗的詞匯,楊、戴將其以注釋形式標出,這樣滿足了讀者想要通過閱讀文學作品來了解中國的期待,順應了期待規范。
例如,《祝福》在文章中表示年終祭拜的大典,當時是典型的中國民俗。文章題為《祝福》,主要內容卻是祥林嫂的悲慘遭遇,實際上是將富人的“福”與窮人的“苦”進行對比。楊、戴將《祝福》翻譯為“Sacrifice”,而不是“wish”。從翻譯規范論的角度來看,如果譯成了“wish”就不符合原作者用意,違背了責任規范。因為“wish”僅僅表示愿望,并沒有宗教祭祀的意味。并且,全文讀完讀者會發現這是個沉重的悲慘故事,并非“wish”所蘊含的給人希望的積極意味。而“Sacrifice”,有專指供奉、祭奠之意,并且祥林嫂的形象也是舊中國封建社會對女性壓迫的犧牲品。楊、戴把《祝福》譯成“Sacrifice”,使得譯文取得與原文同等的讀者效果,很好地體現了期待與責任規范。題目中又加上“The New Year’s”以說明故事的特定時間,這樣便體現其所有的暗含意義。[8]23
“送灶”是中國傳統民俗,意為送走灶王爺,求得一年豐收平安。而在西方文化中,不僅沒有相應的習俗,也沒有相應的神。因此,如果譯者將“送灶”一詞包含的時間、背景等文化信息都翻譯出來,句子肯定冗長。楊、戴采用了直譯的方法,將“送灶”直接譯為the departure of the Hearth God。這樣雖然看似違背了期待規范,但是將原文的中國民俗簡潔又清晰地傳達出來,遵循了明晰的價值觀。
又如,祥林嫂被婆婆賣給賀家坳時,嫁給了比她年幼十歲的丈夫。而對于這一現象,譯文給了注釋:In old China it used to be common in country districts for young women to be married to boys of ten or eleven.The bride’s labour could then be exploited by her husband’s family.譯文增加了這一注釋,使得目的語讀者對于舊中國的民間陋俗有了認識,符合讀者希望讀到更多反映中國當時的生活、文化與精神狀態的作品的期待,同時,也使讀者對祥林嫂的悲慘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三)人稱頭銜詞的翻譯
《祝福》中涉及許多人稱頭銜的翻譯,如“四叔”、“祥林嫂”、“老監生”等。頭銜人稱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物之間的關系,譯者采用意譯法、拆分法等,將中國式的叫法,轉換成能夠被譯語讀者理解的叫法,同時又不違背原文的人物關系,順應當時的交際與責任規范。
例如:“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
譯文:He is a member of our clan,and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before mine,so I ought to call him “Fourth Uncle.”An old student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who went in for Neo-Confucianism.
監生一詞包括了兩個主要義素: (1)國子監; (2)學生。依據明清制度,設在京都的中央學校為國子監(明代,北京、南京都設有國子監,分別稱為北監、南監),是最高學府。因此,國子監一詞又可拆分為”國家最高級別的學府”和“學生”兩個義素。在對源語文化詞語做出準確分析、解構之后,譯者就要把這些成分轉換到目的語中去。通過這樣的拆分,監生一詞就可以譯為an old student of the imperial college,從而比較容易地在英語中找到較為恰當的表達。[8]24這樣的譯法,就可以簡明清晰地向讀者解釋“老監生”這樣的文化負載詞,同時又不影響讀者理解譯文,使得交流順暢,順應了交際規范的要求。
例如:“我回到四叔的書房里時,瓦楞上已經雪白”。
譯文:When I returned to my uncle’s study the roof of the house was already white with snow
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
譯文:In order to avoid further importunate questions,I walked off,and beat a hasty retreat to my uncle’s house
……
原文共有21處出現“四叔”的稱呼,而在譯文中,只有第一次出現“四叔”時,將其譯為Fourth Uncle,之后的20處“四叔”均譯為“my uncle”。從翻譯規范的角度來說,“fourth uncle”的處理是考慮到在文中第一次出現,原文是為了介紹四叔的位分,英語文化中并沒有將位分加以叔伯稱呼的習慣,但考慮到保留中文的特色,譯者將其譯作“fourth uncle”體現出對于原作者的負責,體現了責任規范的要求。而后,由于英語是重邏輯的語言,為了使譯文與讀者之間交流順暢,后文“四叔”出現時,譯文則根據邏輯關系,將其譯為“my uncle”。這樣一來,譯者將后面的“四叔”全都譯為“my uncle”比“fourth uncle”更符合英語讀者的語言習慣,體現了交際規范的要求。
(四)其他中國特色詞匯的翻譯處理
對于其他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楊、戴采用了意象轉換法以及意譯法等,將原文中極具中國特色的詞匯譯成了能夠被譯語讀者理解的形式,從而既達到了期待規范的要求,符合讀者期待,又能夠滿足專業規范的要求,忠實于原文。
例如:桌上放著一個荸薺式的圓籃,檐下一個小鋪蓋。
譯文:On the table she placed a round bulbshaped basket,and under the eaves a small roll of bedding.
荸薺是中國民間常見的蔬菜,中國讀者一讀便有了形象的概念。而對于外國讀者來說,他們也有相似的蔬菜叫做chufa,但是卻并不像中國的荸薺一樣普遍常見。譯者將荸薺的形象轉為bulb(燈泡),將其譯為更符合目的語讀者習慣的bulbshaped,這樣才能使目的語讀者流暢理解譯文。從翻譯規范的角度來說,這體現了交際規范的要求。同時,由于荸薺與燈泡的形狀相似,因此這樣轉換意象的處理并沒有對原文造成扭曲,體現了關系規范的要求。
白篷船在文中翻譯為a boat with a white awning。楊、戴對于這種船的處理在不同文章中是類似的。他們合譯的魯迅作品《離婚》中,也出現了烏篷船這一名稱。他們將其譯為“boats with black awnings”。這種木船的船篷比較特別:用細竹枝夾竹箬編成,呈半圓形或拱門,篷的兩頭架在船的左右舷上,一扇壓著一扇,可以拉開,也可以套攏,用來擋風雨和陽光。因船篷常用煙煤和桐油漆成黑色(紹興話稱黑色為“烏”),所以叫做“烏篷船”。[9]那么白色船篷的就叫做“白篷船”。將譯文與此船的真實面目對比可看出,楊、戴采用的意譯策略較大程度地還原了船的本來摸樣,給讀者以形象的展示。這樣的處理既體現了交際規范與關系規范,又使得文字簡潔明了,易于讀者接受。
四、結語
《中國文學》對于中國文學的譯介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座研究寶庫。雖然由于各方原因目前已經停刊,但是對于它的研究卻從未止步,多數是縱觀雜志50多年的創辦歷史的宏觀探索。本文運用切斯特曼翻譯規范論,對《中國文學》里的選文《祝福》進行評析,從微觀的角度探討了楊憲益、戴乃迭是如何充分運用直譯、意譯、注釋、拆分等翻譯策略,以順應當時的翻譯規范的。
參考文獻:
[1]Chesterman, A..MemesofTranslation[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1997.
[2]吳自選.翻譯與翻譯之外:從《中國文學》雜志談中國文學“走出去”[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2(4):86-90.
[3]吳自選. 《中國文學》雜志和中國文學的英譯——原《中國文學》副總編王明杰先生訪談錄[J]. 東方翻譯,2010(4):52-55.
[4]鄭曄.國家機構贊助下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以英文版《中國文學》(1951~2000)為個案[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2.
[5]徐慎貴,耿強. 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國家實踐——原中國文學出版社中文部編審徐慎貴先生訪談錄[J].東方翻譯,2010(2):49-53.
[6]李晶. 南京訪楊苡——憶楊憲益先生[J]. 外國文學,2010(2):147-160.
[7]許保芳,趙紅巖. 漢英人稱照應對比分析——從《祝福》漢英版本看漢英兩種語言的人稱照應差異[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77-80.
[8]李佳.漢英文化負載詞翻譯策略探討——以魯迅小說《祝福》的英譯文為例[J].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外語版),2007(4):21-24.
[9]汪寶榮,潘漢光.《離婚》中紹興方言詞翻譯規范探析[J].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7(12):68-73.
(責任編輯汪繼友)
AnAnalysisofSacrificeTranslatedbyYangHsien-yiandGladysYangfromTranslationalNormsTheory
LILiang,HANJiang-h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Anhui,China)
Abstract:The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Luxun’s novel Sacrifice which is translated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esterman’s translational norms theory shows that when dealing with the words concerning locations,titles,folklores,as well as other word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apply several 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flexibly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free translation,and splitting,in order to abide by the translational norms at that time.
Key words:Sacrifice;translational strategies;translational norms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47(2014)06-0078-03
作者簡介:李靚(1990-),女,安徽六安人,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言學院碩士研究生。 韓江洪(1967-),男,安徽霍邱人,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言學院教授,博士。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于語料庫的《中國文學》(英文版)作品英譯研究(1951~1966)(13BYY038)
收稿日期:2014-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