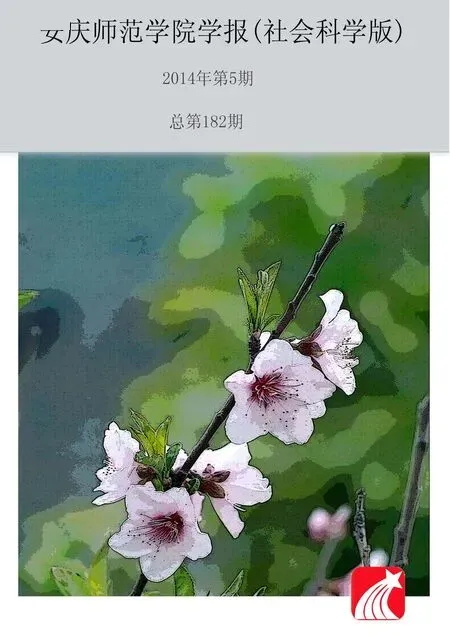論程小青偵探小說的本土化
程 海 燕
(安徽大學文學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論程小青偵探小說的本土化
程 海 燕
(安徽大學文學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程小青的偵探小說創作雖然模仿的痕跡很重,但是他對《福爾摩斯探案》的借鑒卻是經過選擇、改造和變形的。他的《霍桑探案》在主要人物形象及其思想內涵方面不同于《福爾摩斯探案》,故事的開場方式與案件發生的背景也有所不同,而且他強調的偵探小說所具有的“啟智”和“移情”兩個方面教育意義上與前者有很大的不同。他為偵探小說的本土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程小青;偵探小說;《霍桑探案》;本土化
程小青原名青心,乳名福臨,祖籍安徽省安慶市。祖上務農,家境貧寒,因為戰爭不得不全家遷往上海。他在1893年出生于上海南市的淘沙場里。1914年,他首次創作了《燈光人影》,被《新聞報》副刊《快活林》選中刊登。1916年,他與周瘦鵑等人共同翻譯了《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共12冊)。在翻譯過程中,他產生了塑造中國本土福爾摩斯的想法。1919年,他發表了以私家偵探霍桑為主角的《江南燕》。與那些“乘興而作,盡興而止”的作家不同,從1919年開始一直到解放前,他一直堅持創作偵探小說共74篇,結集為《霍桑探案》約280萬字。他是為偵探小說在文學領域爭取一席之地的“先驅”。
由于中國本土在西洋文學進入之前接近偵探小說形式的只有“公案小說”,而公案小說與偵探小說在“敘事模式、文本角色、破案方式、敘述視角”上都有很大的不同[1]。因而中國近代的偵探小說主要是吸收、借鑒國外偵探小說而形成的。程小青塑造的霍桑更有“中國福爾摩斯”的稱號,顯然是借鑒了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所以李歐梵先生在《福爾摩斯在中國》這篇評論中寫到霍桑形象時說“這個角色更接近‘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所謂的‘模擬’,即被殖民者學他的主子,外表惟妙惟肖,但獨缺膚色,而且也有主體性的問題”[2]。誠如范伯群所言,程小青“是一位模仿多于創造的偵探小說家”,但是他確實在西方偵探小說的本土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所創造的“霍桑”也絕非故作愛國,“矯枉過正”的福爾摩斯的翻版。下面通過《霍桑探案》對《福爾摩斯探案》的借鑒以及它的本土化特征兩個方面來分析程小青偵探小說的本土化。
一、本土的文化內容
要將偵探小說這種西方文學形式本土化,首先就要做到在作品中表現日常生活的真實狀態,適當揭示社會倫理情態,反映現實的本土問題。在這一點上,程小青對偵探小說的選擇是符合現實的,當時上海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并且頻頻出現各種犯罪案件。他創作中體現的本土文化內容主要是通過主要人物霍桑的形象展現的。
首先,霍桑雖具有敏銳的觀察能力,極強的邏輯思維能力,但也并非是無瑕疵的英雄,他也有普通人的缺點。比如《打賭》這篇小故事中就寫了霍桑的失敗經歷。好友孫芝年為母親過壽,霍桑也參加了,而且因為心情好,多喝了幾杯。宴會過程中,孫芝年的表嫂何氏戒指上的珍珠突然不見,于是請霍桑幫忙尋找。霍桑經過推理,認為是何氏的小兒子不小心吞食了珍珠,可是真相卻是何氏因為當時慌忙,自己將珍珠放進衣服口袋了,她在掏手巾為兒子擦眼淚時珍珠掉了出來。通過這件事,作者使讀者相信霍桑并非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物。
其次,不同于福爾摩斯對待官方警察的傲慢態度,霍桑對待官方探員的態度基本上是比較友好的。雖然有些時候也批評“他們處理疑案,還是利用著民眾們沒有教育、沒有知識,不知道保障固有的人權和自由,隨便弄到了一種證據,便威嚇動刑遍地胡亂做法”[3]。這很明顯具有進步性。但是他在很多情況下他還是選擇借助官方探員的力量來解決問題。比如在《斷指團》一案中,他就因為相信那些探員而深陷險境。而且他對一些探長是持一種肯定的態度,尤其是“汪銀林”這個人物。這些內容都說明了霍桑這個人物作為現代中國的偵探對法制的認識是有限的。他雖然認識到了當時的法律與正義是有矛盾的,但是卻不明白當時的法律不過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利用的一種工具罷了。這很符合當時上海的具體情況,私家偵探雖然被部分人接受,但是他們的權利是極為有限的,如果像福爾摩斯那樣我行我素是不可能解決案件的。而且受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影響,普通人做人做事都不會那么極端,而是會選擇比較適中的方法對待事情。
此外,他還有著明顯的“平民”思想。霍桑這個人物其實是有程小青自己的影子。程小青在11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靠幫人漿洗和縫補衣服把他和弟弟妹妹撫養長大,所以他從小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接觸的人也多是平民老百姓,因此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也有比較強的平民意識。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迎合廣大讀者的審美品位。中國傳統墨家思想中的“兼愛”思想是包含著平等的觀念的,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是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的。讀者或觀眾總希望在小說或戲劇中出現那種見義勇為、鋤強扶弱、壓制強權的英雄人物來伸張正義,因此程小青在創造霍桑的形象時就為他加入了濃厚的“平民”思想,他總是站在平民的立場來看待和處理各種案件。在《沾泥花》中,仆人施桂因為來訪的客人面貌丑陋、衣服破爛,而不愿意立刻通報,霍桑發現后便訓斥他:“你怎么忘了?我們都是平民……這里不是大人先生的府第,怎么容不得襤褸人的足跡?”
正是受到這種平民思想的影響,霍桑辦案對待罪犯的態度并非一視同仁,經常是道德戰勝了法律。在《白紗巾》一片中,霍桑說:“在正義的范圍之下,我們并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有時遇到那些因公義而犯罪的人,我們往往自由處置。因為在這漸漸趨向于物質為重心的社會之中, 法治精神既然還不能普遍實施,細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故而我們不得不本著良心權宜行事。”在《案中案》里,仆人陸全太忠實于老主人,而設計刺殺孫仲的故事感動了霍桑。為了幫助陸全,他仔細推理發現孫仲的真正死因是服用了過量的安神水,從而使其免受法律的制裁。
二、本土的藝術精神
對于本土藝術精神的體現,最突出的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傳統文學作品的重新認識。《霍桑探案》借鑒了《福爾摩斯探案》的敘事模式,采用了“單向視角”的有限制的敘事方法,不同于以往中國小說的“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作者以包朗的視角來展開敘事,這樣既能夠拉近讀者與整個案件的距離,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同時又能方便作者為情節設置各種懸念,增強大偵探的神秘感。當新文學的作家們對中國傳統文學資源加以否定,站在西方文學的視野下來審視和評價中國傳統文學時,程小青卻對傳統文學作品有了重新的認識并且借用其中的敘事技巧。
不同于《福爾摩斯探案》,《霍桑探案》在故事開場方式上借鑒了中國傳統宋元話本小說的“入話”式開場方法。“入話”是指為了等候遲到者,說書人在故事開場之前先說一首詩詞起興,或者一個簡單的故事。而這些詩詞或者故事會與后面的主要故事中的某些人物或者地點有關。可是總體上與下面的故事沒有什么強烈的聯系,而是闡述了一些對于當時社會現象的批評與思考。在《霍桑探案》中類似“入話”的故事開場方式,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以一些短小簡單的故事開場;二是關于報紙文章或者日常生活而展開的議論與批評為開場。第一類主要有《迷宮》《江南燕》等篇章。《迷宮》開頭是霍桑與包朗在火車車廂中對于私犯進行的分析,以及兩名乘客關于一件有趣的盜竊案的交談。與后面發生的失竊案并無多大的聯系。《江南燕》的故事開頭除介紹了霍桑的個人經歷以及和包朗的朋友關系外,還寫到了霍桑憑借推理得出包朗去黃天蕩劃船的事。隨后才進入了關于江南燕的珠寶盜竊案的偵探。第二類作品較多,主要有《白衣怪》《催眠術》《斷指團》等。比如《白衣怪》的故事開頭是包朗到霍桑的家中, 看到報紙上一則大學生因為爭風吃醋而殺害旅館中舞女的新聞,并且討論了當時大學生的倫理道德問題。與下面裘海峰的殺人案件并無直接聯系。《催眠術》第一部分以“扇子哲學”為題,以包朗和霍桑二人關于該不該用電扇的討論,點出霍桑厭惡國人太會享受而懶于活動的狀態。《斷指團》故事以包朗因神經衰弱和霍桑來到南京修養開始,他們在報紙上看到了關于自己的行蹤報道。批評對社會上那些捕風捉影的人,感到個人隱私的缺乏尊重。
將“入話”的方法帶入偵探小說這一緊張復雜的小說體裁中,雖然有些不協調,但是卻非常符合當時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這種開場方式比西方偵探小說的直接報道案件的小說要更有人情味,這些議論貼近讀者的實際生活,拉近與讀者的距離,能夠帶領讀者漸入佳境。關于社會現象的評論也能體現出作者本人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既增強了故事的趣味性,藝術性也有所提升。
他在語言方面,也體現了對本土傳統文化的尊重。既運用了詩歌,又有方言的使用。在《黑地牢》中,看到飛進辦公室的蜜蜂,包朗便吟了唐代詩人羅隱的《蜂》:“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為誰辛苦為誰甜?”霍桑就將最后一句改為之“為人辛苦為人甜”,原因是:“照原句的含意,憐憫蜜蜂釀成了蜜,不能自己享受,卻給不知何人享受故而對蜜蜂表示悼惜的慨嘆……這是頹廢的觀念,在這個新的時代,不但不足為訓,簡直要不得!現在我給它改一改,而且加以正面積極的解釋,就顯出這小生命的偉大性。它采花,它釀蜜,為的是人,不是為自己。生存在這個時代的人,誰也應得有這‘為人’的觀念,那末民族才得滋長繁榮,人類才得團契睦洽,世界才得安寧和平!”這樣在偵探故事中談詩歌,而且詩與案件并無關系,這只有在中國的偵探小說家筆下才能看到,這也就是傳統文學隱藏在作者筆下的所謂“趣味”。在方言的運用上主要采用的是一些鄉間理語、上海俗語,比如里弄、木作、捐客、白相人、堂信,體現了濃郁的上海風味。
本土藝術精神的另一方面就是“與本土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聯系”,作家作品對生活的表現不是膚淺的,而是飽含了作者對于本土生活的深切關注,充滿了作家的思想和感情因素。通過文學來解決“現代性”的問題曾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創作原則。“而以此為價值導向的文學具有世俗化的取向,或通常所說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就不難理解了。從五四時期開始,作家們就自覺地肩負了改造‘國民性’和救亡圖強的社會責任,幾乎所有作家都把目光投向社會的合理性問題( 社會正義) 。”[4]91程小青的創作雖然在思想深度上不及魯迅等作家,但是也為此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霍桑探案》中我們可以從他對案件發生的背景描寫中感受到他對“現代性”的思考。
《福爾摩斯探案》中最明顯對于時代的思考就體現在反對封建迷信思想上。在當時的中國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在上海這樣一個當時全中國經濟發展最快,文化進步明顯的地區,也還有很多人相信“鬼神”的存在,所以程小青在創作偵探小說時,主要考慮到的就是反對迷信的這一主題。他在《催命符》《白衣怪》等篇中都通過人物的言語制造出了一個所謂的“鬼”的形象,然后通過一步步的案件偵查證明根本不存在“鬼”,只不過是犯罪分子利用這種迷信的方法來實施犯罪罷了。《催命符》里那個能催人性命的不過是曾經被死者打過的普通醫生華濟民,《白衣怪》里死者經常看見的貌似哥哥的穿白衣的“鬼”不過是由家中老仆人方林生假扮的。
此外,《霍桑探案》中的案件主要是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大家庭生活背景下,描述的主要是子女與父母長輩之間、夫妻之間、朋友之間發生的悲劇故事。《霍桑探案》的創作時間是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這段時間由于通商口岸的開放和租界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沿海地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上海。當時的上海人口眾多,工商業十分發達,而且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眾多。而程小青對當時半殖民地的上海以及蘇州等地的“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進行了現代性的反思。在作品中霍桑和包朗曾多次提出由于現實社會物欲膨脹,金錢成為衡量所有事物的標尺,傳統儒家思想的“三綱五常”的道德戒律開始崩潰。在《活尸》中作者這樣寫道:“朋友的交情、夫妻的結合、師生的關系,一切都商品化了。”舊道德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新道德又還未建立。正如他自己所說:“在這個新舊道德青黃不接的時期,處處都暴露出反常的現象,因為傳統的倫理基礎,既然因對封建制度的崩潰,連帶地起了搖撼,新的標準還沒有建立起來,社會間失去了正軌,青年們的行動便無所適從,往往趨入歧途。”總之,《霍桑探案》中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缺乏法治思想,并且處在封建思想籠罩下的家庭中。通過的案件更加貼近生活實際,往往更能達到見微知著的效果,與那些選擇重大政治經濟事件的案件相比反而更能體現當時社會的真實面貌,在供讀者娛樂以外,還能起到一定的揭露社會矛盾與黑暗的作用。
要將西方偵探文學本土化,就要將它進行中國化的改造與交融,就要把它與中國百姓的生活融合,書寫本土生活,并深入生活:思考其中的問題,真正做到文學作品反映本土生活,這就是成功的本土化作品。程小青的創作雖然沒能做出十分深刻的人生和人性的闡釋,但是卻做到了反映本土生活的各種現象,尤其是當時上海的市民生活,并且還對其有一定的思考,這是值得肯定的。
三、融入本土生活
當時《霍桑探案》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很多讀者都曾寫信給程小青本人,大眾對霍桑這個人物的喜愛程度不亞于現在的韓劇。雖然徐念慈認為偵探小說的長處全在于“布局之曲折,探事之離奇,于章法上占長,于形式上占優,非于精神上見優者也”[6]43,讀者看偵探小說很少是為了受教育,而是為了尋找刺激,但是程小青在創作《霍桑探案》時則有著明確的“文以載道”的教育目的。這種教育主要體現在“啟智”和“移情”兩個方面。
關于“啟智”的作用是很明顯的,當時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科學”、“民主”精神,在《霍桑探案》中都可以看到。而程小青自己對這一方面也有清醒的認識,他說:“我承認偵探小說是一種化裝的通俗科學教科書,除了文藝的欣賞之外,還具有喚醒好奇和啟發智力的作用。在我們這樣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頹廢的社會里,的確用得著偵探小說來做一種摧陷廓清的對癥藥啊。”在《霍桑探案》中有《白衣怪》《催命符》《別墅之怪》《怪房客》等一系列“鬧鬼”事件,還有在《虱》中所謂的“五鬼搬運法”,霍桑都運用科學的偵探方法證實了這些并非是鬼怪在殺人,只不過是有人在犯罪罷了,破除了各種封建迷信的傳說。此外,程小青還在《從“視而不見”到偵探小說》中指出閱讀偵探小說能培養“精密的觀察力”。他在文中說:“我們天天張著眼睛,而實情所‘見’的卻實在很少很少;所以‘視而不見’除了有特殊訓練以外,委實是一般人的通病……我敢大膽地介紹一種療治‘弱視’病的膏方,那就是偵探小說。”他認為,讀者在讀偵探故事時,多數是把自己當成了一個偵探一樣,通過觀察書中所寫到的環境,人物的語言動作和細微的表情來親自推測案情的結果,犯案的過程。而把他們閱讀時的這種精密的觀察力和注意力運用到現實生活中去,那么自然能夠治療“視而不見”的社會通病,人們也就會對各種現象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成為一個關注國家和社會現實的有用的人,實現對大眾的啟發智力的教育意義。當然體現在作品中還有各種實際的科學知識的傳授,《血手印》中就介紹了一種辨別血跡的方法:用一種淡亞馬尼亞液滴在懷疑有血跡的刀面上,如果刀上的痕跡變成了綠色,那么是果汁,如果痕跡不變色,那么就是血跡。
關于“移情”的作用,《霍桑探案》通過許多的案件,對當時社會上的青年人、知識分子、普通婦女進行“勸善”的教育,引導人們要勇敢維護自己的利益,年輕人不應該沉溺于你追我趕的愛情或者各種物質享受之中,不應整日昏昏沉沉虛度光陰沒有生活的目標,而應該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知識或者財力為祖國為民族的進步和發展盡一份力。正如張碧梧所說:“偵探小說的情節大概不外乎謀殺陷害和劫財等, 讀者讀了之后……恐怕不過只在腦中留下這個惡印象罷了……我以為在這種情節當中,務必使他含蓄著勸善懲惡的意思才好。譬如說某富翁被賊黨害死, 便須附帶說明這富翁平日的吝嗇盤剝的行為;又如說某婦人被人害死,但所以會被人害死, 實固品行不端, 以致結下了仇恨。如此讀者讀完之后,必會生出 ‘自有取死之道’的感想。”[5]《白衣怪》中的裘日升不僅設計陷害自己的親哥哥,而且生活作風極不檢點,甚至對自己的養女也有非分之想,害死哥哥的事被侄兒海峰發現后,被侄兒所扮演的哥哥的“鬼魂”所嚇死,實在是一個不知廉恥的長輩,所以死有余辜。當然也可以通過這件事教育大學生們不要莽撞行事,做事要思考清楚。《青春之火》中張效琴的哥哥張有剛為了霸占妹妹的財產,想方設法破壞她和姜志廉的愛情,阻止她出嫁,甚至借著喝酒毆打她,實在是禽獸不如,最終張效琴為了擺脫這種壓迫而殺死了哥哥。讀者讀完故事都會同情這樣的殺人兇手,同時憎惡那些為了金錢而放棄親情,毫無良心的壞人。這樣,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也會友好待人,珍惜親情。這樣懲惡揚善的“移情”的目的就實現了。此外,文中還有大段關于社會現實的議論和說教的文字。當然也是因為作者懷有一顆正義愛國的熱心,希望對國家和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是受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儒家入世思想的影響。
正如陳平原先生在強調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是傳統文學和西方小說兩方面“移位”的合力時指出:“中國小說接受西洋小說刺激而發生變化是一毋庸置疑的事實;可中國小說接受的是經過選擇、改造、變形的西洋小說。不考慮這種移位過程中的‘損耗’未免低估了這一文學運動的艱難曲折。就作家心理而言,在二十世紀最初三十年,對待西洋小說的態度大體上發生過如下變化:從‘以中據西’到‘以中化西’到‘以西化中’再到‘融貫中西’。這不是四個截然分開井然有序的階段,同一個作家可能徘徊于兩種甚至三種態度之間。”[6]255很明顯,程小青的態度介于“以中化西”和“以西化中”這兩個階段中間,既希望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浸潤偵探小說中的人物,又希望以偵探小說來起到“啟智”和“移情”的教育意義。一方面程小青作為一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受到了傳統文學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他的個人經歷中可以看出他上過私塾,也閱讀過大量的中國傳統小說。而另一方面在西洋文學大量涌進的時代,他被西方文學那些新的敘事技巧、新的思想所深深吸引和影響著,所以他率先在偵探小說的創作中采用了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另外,“傳統文學更多作為一種修養、一種趣味、一種眼光,化在作家的整個文學活動中而不是落實在某一具體表現手法的運用上”[6]143,而西洋小說的影響卻恰恰表現在各種創作技巧的運用上,所以這種明顯的敘事方法往往比那些隱藏在作品中的“趣味”更容易被人發現。通過《福爾摩斯探案》與《霍桑探案》的比較,可以發現程小青在偵探小說的創作中既體現出了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趣味”,又接借鑒傳統小說的“入話”的敘事技巧。
四、結 語
“所謂文學本土化,其最基本的內涵是文學與其產生的本土現實和文化之間的關聯性,看其關聯是否密切,能否體現出本土的深刻和獨特,能否以獨特深度和個性呈現出其意義。具體說,它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內容:首先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學內容。其次是來源于本土的文學思想。它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本土文化傳統,二是與本土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聯系。最后是融入本土生活。”[7]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中主要人物以及眾多案件都是反映了本土的生活現象,在故事開場方式上程小青借鑒了中國傳統文學中“入話”的方式,并且在具體的創作中運用了許多具有傳統特色的語言。而且主要人物霍桑的思想內涵也是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平民思想,作者創作也是本著“文以載道”的教育意義,并且在描寫各種案件時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種種問題,對“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問題進行了反思。
雖然程小青在人物模式和敘事結構上借鑒了《福爾摩斯探案》的技巧,沒能對當時社會進行深入的描寫,深刻地反映人性問題,但是他筆下的偵探形象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寫霍桑,不光是為了給人取樂,做一種茶余飯后的消遣,而是為了‘剝魚肉,露骨頭’。” 他的偵探小說是深深扎根于當時中國社會的現狀以及中國傳統文學中,吸收西方偵探小說的光芒而成長起來的文學作品。
[1]任翔.文學的另一道風景——偵探小說史論[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115.
[2]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J].當代作家評論,2004(2):13-14.
[3]程小青.霍桑探案集[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156-158.
[4]楊經建.從超越性到世俗性——20世紀中國存在主義文學“本土化”表征之一 [J].天津社會科學,2009(6):91.
[5]張碧梧.偵探小說瑣話[J].偵探世界,1923(4):16.
[6]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7]賀仲明.本土化: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另一面[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2):81.
責任編校:汪孔豐
2013-12-10
程海燕,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時間:2014-10-28 14:19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4.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4
I207.42
A
1003-4730(2014)05-0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