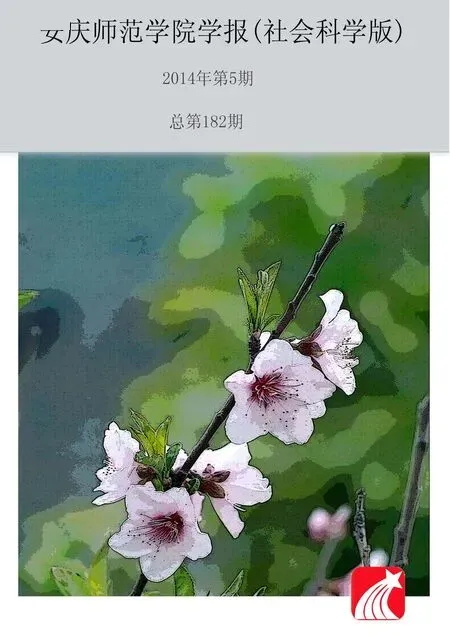從《姹紫嫣紅開遍》看傳統戲曲的當下困境
周紅兵,王蘭燕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從《姹紫嫣紅開遍》看傳統戲曲的當下困境
周紅兵,王蘭燕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項海、項憶君是滕肖瀾中篇小說《姹紫嫣紅開遍》中一對熱愛京劇的父女,他們尤其熱愛《姹紫嫣紅開遍》,也試圖將臺上的戲曲世界搬到臺下的日常生活當中,將生活也戲曲化、藝術化、虛擬化。小說通過敘寫這一對父女在工作、愛情、生活的種種遭遇,思考了傳統戲曲在當代生活中的困境,并以令人意料之外的結局表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傳統戲曲文化在當下只能存于臺上,無法活在臺下。
滕肖瀾;《姹紫嫣紅開遍》;傳統戲曲;當下困境
滕肖瀾的《姹紫嫣紅開遍》(原載于《人民文學》2007年第9期,被《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07年第10期、《小說月報》2007年第11期轉載,收入作者小說集《大城小戀》,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所引未加說明之處均引自《大城小戀》)寫了一段京劇愛好者項海與其女項憶君的生活。小說營造了一股濃濃的詩意氛圍,也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哀傷與憂愁,更借這對父女思考了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傳統文化能否在當下生存的問題。
一
這是一個現代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社會,文化上以感官、欲望為主要對象的娛樂形式占據了娛樂市場的主要份額,相對于生活節奏緩慢的農業社會,人們既沒有閑暇也難以欣賞凝結了農業社會中人們對于愛情、生活美好想象的戲曲。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偏偏有那么一部分人打心底里喜歡、熱愛那凝結了美好的戲曲,比如說被譽為國粹的京劇,重新煥發活力的昆曲以及其它一些地方曲目。他們的確是熱愛,這種熱愛不僅僅是一種業余愛好,更重要的是他們將這種熱愛化為血肉、化為魂魄,進而化為他們的生命。因此,他們也試圖將戲曲生活化,將人生藝術化,也可以說是藝術人生化、生活戲文化。這樣,一方面是急劇變動的現代社會、功利化的人際關系和以電視、電影等為主要形式的娛樂休閑文化,另一方面卻是依舊活在戲曲世界里并且將它作為自己為人處世方式的傳統堅守者、消化者,兩者之間的矛盾注定要產生一定的裂縫。
滕肖瀾的小說《姹紫嫣紅開遍》中,無論是項海還是項憶君,他們對京劇的愛好完全是發自內心深處、不沾染任何一點塵埃的,這就是康德意義上的“審美趣味”——“審美趣味是一種不憑任何利害計較而單憑快感或不快感來對一個對象或一種形象顯現方式進行判斷的能力。這樣一種快感的對象就是美的。”[1]這與小說中的其他幾人完全不一樣,他們或多或少不那么純粹。比如項海的師弟白文禮,用項海那句精辟的概括來說,二人之間的區別就是“我和他是兩種人——我只是個戲子。他卻是個人物”;白文禮心中也有戲曲的地位存在,還有一股子隱藏在心底深處的“情結”——對后來成為師嫂的師妹的暗戀,這當然不足以為外人道。但是,作為“人物”的白文禮清楚戲曲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區別,他不會將戲曲帶入自己的實際生活,他對項海的照拂一方面固然有對其技藝的承認與師兄弟情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為了“她”去世前很鄭重的那句話:“我們項海只會唱戲,別的什么都不懂,以后要靠你多照顧了。”也因此,在項海有牢騷的時候,在“這些年來,多次有人提出要停發項海的工資”的時候,他“竭力頂住了”,“反正他也不是為了他”。比如白文禮班子里的余霏霏,這是深諳娛樂圈“潛規則”之道的精明女子,在用身體獲得了白文禮的力挺從而一躍成了戲校里數一數二的年輕花旦之后,她又利用這段經歷成功地借白文禮上位,成為電影明星,戲曲在她這里完全是她走向電視、電影成為娛樂明星的墊腳石。比如為了余霏霏而學戲的毛安,學戲曲只是他接近、追求余霏霏的一個“道具”而已,雖然他也曾經深刻地領悟到戲曲的魅力,但是,那只是一剎那間的光輝,而且只有在他失戀的時候,他才深刻地進入到戲曲的世界,可以想象,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戲曲只是一道甜品或開胃菜而已,雖然好吃,但不是正餐。比如趙西林,他壓根兒就沒有喜歡過戲曲,他的娛樂方式相當市民化、世俗化甚至有些粗鄙化,就是打牌,與毛安相比,他們接近戲曲的目的都是一樣的,都只是因為追求對象與戲曲相關,而談到對戲曲的了解上,他甚至還不如毛安,毛安畢竟拜師過學習過,而且還有過一剎那間的“痛悟”,曾經進入過戲曲的世界,反觀趙西林呢,他從來只是接近沒有進入過。比如那個“吃口香糖的男生”,即便項海在他身上發現了一絲絲欣喜,但結局卻令人尷尬,他表現出來的尊敬、好學似乎是暗含了通過他接近白文禮的實際目的:“想讓項海求求白校長,看是否能讓他演個角色。”這些與項氏父女關系十分密切的人群,正構成了項氏父女熱愛戲曲的“對立面”,他們對戲曲的態度從反面襯托出了項氏父女對戲曲的愛之深、戀之切。
項海,正如他自己和他妻子對他的評價一樣:除了唱戲什么也不懂。其實也不是不懂,而是他要活在戲的世界里,用藝術的世界裝點自己的生活,讓自己的生活成為戲的現實演繹,這不是“行為藝術”,而是要踐行藝術,是要將戲曲生活化、藝術人生化。讓生活處處充滿戲曲,也就是要讓生活中處處充滿了情趣,讓自己的生命活得有滋有味。項憶君,從小耳濡目染,也發自內心深處地喜愛戲曲,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戲二代”。無論是學習、工作、戀愛,她也試圖像父親那樣,將戲曲世界里的精彩演繹到現實世界中來,從而實現戲曲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合一。但是,戲曲、藝術與現實真的可以合二為一,從而實現藝術的生活化、人生化或者說人生的藝術化,進而可以說傳統古典可以注入到現代當中來嗎?
二
正是在這里,小說文本開始出現了幾處裂變,戲曲遭遇了困境。
首先是項海。作為父親,在女兒項憶君人生的緊要關口——填報高考志愿時,第一次糾結了。項憶君是真心喜歡京劇的,因此,她在人生的緊要關口自然而然地要選擇戲曲作為自己此后的方向。但是,這個時候,舅舅適時地出現了。小說中,舅舅充當了一個“清醒者”的角色。在項海父女倆看來,項憶君選擇報考戲曲學院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然而,在舅舅看來,這完全是沒有出息的選擇,選擇戲曲帶來的實際問題就是項憶君今后的出路在哪里?這是一個不需要想都可以預見得到的未來,明白人舅舅自然不會讓自己的親外甥女跳入那個“火坑”。人生的道路,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十字路口,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這個問題盤旋在項氏父女倆那里。“那天晚上,項海沒有睡覺。房間的燈始終是亮著。關著門,煙味卻還是源源不斷地飄出來。項憶君也是一直睡不著。”煎熬了一個晚上之后,項海聽從了舅舅的建議,讓原來打算報考“戲曲學院”的項憶君把志愿改成了工商管理專業,在喜好、興趣與現實前途之間、在父親角色與票友導師之間,項海選擇了現實前途、選擇了父親的現實擔當。那個小時候想也不想就回答說要當“名角兒”的項憶君,大學畢業之后在“機場海關上班”了,在一個公務員至上的年代,這樣的工作崗位足以令很多人羨慕。
如果在項憶君填報高考志愿的問題上,項海是在作為一名父親與作為一名戲劇愛好者之間做出了違背自己內心喜好、符合現實語境的選擇的話,那么,當項海面臨羅曼娟的時候,在現實愛情與虛擬愛情之間,他會作何選擇呢?“羅曼娟的丈夫原先是京劇團的丑角,兩年前得肝癌去世了,留下一個讀初中的兒子”,項海的妻子君妍也去世有“二十三年了”,兩家是鄰居,兩人是舊相識,更重要的是,兩個人之間都有默契:“項海……心里一動,不禁朝她看去——恰恰她也在看他。目光一接,忙不迭地分開”,目光的相遇與分開是彼此的情意與心領神會,中年男女的愛情,一般是單刀直入、直奔主題的,然而,在項海那里,卻演化成纏綿悱惻、糾結浪漫,過程性取代了目的性。項海是要按照《牡丹亭》的戲文來排演自己愛情的,為此,在舞臺上飾演旦角的他給自己取了個網名——“杜麗娘”。他試圖將自己與羅曼娟的愛戀演繹成現實版的“杜麗娘”與“柳夢梅”,于是種種心照不宣的試探、雙方含蓄的眉目傳情、仿效“游園”的約會都透出一股子隱約、含蓄、欲進還退、欲罷不能的“戲風”,甚至是與羅曼娟自然而然的上床也似乎是按照“驚夢”的路子在走,項海試圖將自己的情感經歷按照戲文的模式重新現實地演繹一遍,他希望自己的生活就是戲文、自己的世界就是“牡丹亭”的世界。然而,雷同的過程卻并不必然是相同的結果:《牡丹亭》里的結局是皆大歡喜的“有情人終成眷屬”,項海版的“牡丹亭”卻令人意外:在有了實質性接觸之后,雙方本來應該會有實質性結果的,但是“好像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也沒什么鋪墊,就這么斷了”。羅曼娟以為兩人之間的那層窗戶紙已經捅破,因此等待著項海的求婚,而項海卻在猶猶豫豫,“‘驚夢’都唱完了,這出戲接下去該怎么唱呢”?脫離了既定劇本的項海心里實在沒底,于是一再延宕,終至分手。兩人分手前的告白與心理活動明白地昭示著兩人的“同床異夢”,在羅曼娟那里:“我就是想找個過日子的男人啊!”生活的邏輯是羅曼娟的邏輯,原來那一切鋪墊的根源都在這里;而在項海那里:“項海拿自己的心,去比照她的心,覺得終究不是一樣的。項海琢磨著她那名‘過日子的男人’,便有些慚愧。隱隱又有些鄙夷。”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項海夾雜著鄙夷的慚愧正說明,他并非是要尋找現實生活的愛情,而是要演繹戲文世界的愛情,當實實在在的現實邏輯碰上良辰美景的美好想象時,生活的邏輯在美好想象這里敗下陣來,這似乎寓意著想象的勝利,然而卻也可以理解為兩者的不相容,更可以解讀為美好想象的不合時宜,畢竟已經有人給羅曼娟介紹了在證券公司當會計的男人。可以說,項海和羅曼娟是錯點了的“鴛鴦譜”,一段“愛情”終于無疾而終。
其次是項憶君。作為女兒,在高考填報志愿這樣的大事件上,項憶君只能聽從父親和舅舅的安排,她是一名無法主動選擇自己的“志愿”的被動者,從而無法避免在“志愿”與現實、戲曲學院與工商管理、名角兒與公務員之間的裂變。但是,當項憶君完成了學業進入了社會成為一名能夠自主命運的成人之后,面對愛情、工作,她又將如何呢?
項憶君在機場海關工作。在一個公務員為王的時代,這個工作足以令很多人羨慕,但是職場有職場的生存法則,最重要的一點莫過于投領導之所好,一朝天子一朝臣,了解、適應并且針對了當權領導的愛好,就是為自己開啟了一道通向職場光明前景的大門。因此,最擅長跳國標舞的丁美美可以不把科長放在眼里,因為大老板喜歡跳舞,出席大場面都帶著她,丁美美也因此最受寵不過,辦公室里的同仁也都洞若觀火、無師自通。項憶君雖然熱愛京劇,但也深諳此理,因此,在她受到科長不公平批評的時候,也無來由地“有些懊悔——當初該去學跳舞呀”,當然,這也只是想想而已,機遇可遇不可求,誰能夠知道自己將來的領導喜好什么呢?然而,命運之神卻垂青于她了——新上任的譚總原來京劇唱得很棒,時來運轉,項憶君的運氣好到天花板了,這是同事的話,吹捧中不無羨慕、嫉妒甚至恨的成分。雖然有些夸張卻也并不離譜,“不久,項憶君調至總經辦”,一句偶爾的戲語迅速變成了事實,曾經無用的愛好終于派上了大用場,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就如杠桿一樣撬起了項憶君的人生,“其實依著她平常的脾性,這句話是無論如何說不出口的,那天也不知怎么了,一張嘴,便說了出來。譚總朝她看了兩眼,也笑了笑”。原本的“志愿”和“無論如何說不出口”此刻是“一張嘴,便說了出來”,古老的戲曲、曾經的矜持在此刻轟然解體、裂變,職場規則和現實人生在裂變中占據了上風。
如果說,項海的愛情多少有些因近水樓臺、情愫暗生因而有些世俗氣的話,那么,項憶君的愛情更符合《牡丹亭》的傳奇性:一次偶然的交往、兩個相遇的年輕人,或許項憶君與毛安的誤打誤撞能夠造就一段與杜麗娘、柳夢梅一樣的愛情傳奇呢?衷心喜愛戲曲的項憶君接受了對戲曲別有用心的毛安,她以投入到一場游戲中去的心情開始教毛安唱戲。明眼人都能夠看得出來,其實唱戲只是愛情的媒介,毛安固然是希望通過學習戲曲接觸余霏霏,項憶君又何嘗沒有利用戲曲創造與毛安接觸的念頭呢?純粹的愛好竟然容納了不純粹的學習,單純的戲曲當中竟然夾雜了不單純的想法,項憶君對戲曲的態度中多少也開始了裂變:突如其來的愛情的力量使然。毛安多少還是有些懂戲曲的,當然,這只是靈光乍現;趙西林就完全是一個門外漢了,這位仁兄全部的愛好只是打牌:大怪路子、八十分、斗地主、紅五星、捉豬玀等等,他都很拿手,即便是請項憶君到他家去,全部的理由與活動也是打牌,打牌與唱戲,完全是兩個極端,一個庸俗、一個高雅,完全沒有可比性,然而,這個庸俗的趙西林卻也竟然邀請她去看昆劇電影、剛剛上映的《牡丹亭》了,雖然詫異,但是項憶君還是同意了,小說一個意味盎然的結局此刻也水到渠成呈現在讀者面前:觀看電影的過程中,項憶君“悟”了:
那一瞬,項憶君忽然有些明白了——其實人人都可以唱《牡丹亭》,項海、余霏霏、毛安、白文禮,還有她自己,都可以唱。人人的《牡丹亭》卻又不盡相同。“游園”時,各人心里怎么想,“杜麗娘”便是什么樣。是良辰美景,還是斷井頹垣,只憑自己的心。又或許,這人的良辰美景,又偏是那人的斷井頹垣。
項憶君在剎那間的感悟表明,她已經意識到,《牡丹亭》也好、游園也好、杜麗娘也好,其實都已經是歷史陳跡,留存下來的只是每個人的生活態度,不同的人都可以觀看牡丹亭,不同的人擁有對牡丹亭的不同態度,因為他們本就是獨特的個體,他們本就擁有對生活的不同理解,何況世界已經變化、生活已經變遷了。項憶君從這感悟中理解到了時間的流逝、世界的變化及隨之而來的生活真諦,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有些傷感的領悟,正如詩歌“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那樣,在已逝的漫長歲月里,《牡丹亭》一如“黃鶴樓”,她依然存在,只是時過境遷,此情可待成追憶而已,“牡丹亭”內外本就是“兩個世界——臺上的世界,臺下的世界”[2],活在臺下世界的是現實中的人,如果仍然一味強求活在臺上的世界,帶給自己的恐怕最終仍然是“惘然”的“追憶”,一如她愛戀毛安而毛安終究還是沒有走入她的“牡丹亭”之“夢”中一樣,傳統在今日生活中的裂變已經不可抑制地發生了。
三
然而,事情還沒有結束,小說的精彩之處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白文禮被確診患上喉癌,住院接受治療,項海去看望白文禮,從醫院回到家時,在樓下遇到了五樓的賭博少年,這個時候,小說中最精彩的一筆出場了:
少年叫了聲“項老師”,項海“嗯”了一聲,正要上樓,少年又道:“項老師,跟您借點錢行嗎?”
項海一怔,還當自己聽錯了。回過頭看他:“什么?”
少年瘦長的臉龐浮上一絲有些狡黠的笑意。“也沒什么——這么說吧,柳夢梅想問杜麗娘借點錢。您聽明白了嗎?”
項海聽了,渾身一震。“你——”
……
項海當初有一個愛好,當他在現實中有什么事情,特別是當他與羅曼娟的“愛情”峰回路轉的時候他會借助“杜麗娘”這個虛擬的身份向同樣是虛擬的“柳夢梅”傾訴,虛擬的網絡世界,對項海來說,不僅是可以傾吐心聲的平臺,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是貼心之外又很安全的平臺,項海不需要考慮現實情境就可以向“志趣相投”的網友吐露心聲,這不禁讓人想起了那個曾經盛傳一時的網絡名言:在網上沒人會知道你是一只狗!但是,網絡畢竟是虛擬的,當它與現實相遇時,就像易碎的瓷器跌落堅硬的地面一樣,那個靠網線構建起來的美好世界瞬間土崩瓦解了。原來那個貌似“志趣相投”、可以無話不談的“柳夢梅”,竟然是五樓那個不爭氣的、迷戀賭博的不良少年,他假扮了“柳夢梅”這一角色與自己交談,此刻出來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兩人的聊天記錄敲詐三萬元錢。虛擬與現實一旦接觸,這個脆弱的瓷器在強烈的碰撞下便開始四處開裂!善解人意的“柳夢梅”現身為敲詐勒索的惡魔,這是一個多么讓人無法接受的事實啊。然而,這確確實實地發生在項海身上,不難想象,這對一向活在戲曲與虛擬世界里的項海,是多么巨大的打擊,一時之間,項海的惶恐、震驚、無法相信與失魂落魄齊齊展現:“項海聽了,渾身一震”,“項海只覺得渾身的血一下子溢到頭頂。眼前一黑,差點要暈過去”,“項海說不下去,牙齒在發抖,整個身子都在發抖。他驚恐地望著少年,簡直不敢相信”,“項海怔怔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整個人傻了似的”。
這是整篇小說最精彩的地方。從小說結構上來說,前面不斷出現的五樓不良少年,在整個小說的前半部沒有參與故事中任何情節的發展,似乎就是一處閑筆。但是,這個時候,卻奇峰突起,屢次提及的不良少年從閑筆一躍而為一處高明的伏筆,貌似游離于整個故事之外的不良少年在這里開始牽出翻江倒海的情節,在技術上這是一處高明的設計。而最高明的是,借不良少年的自我現身與自我闡述,以一種完全世俗的眼光將項海一直構建的戲曲世界、藝術世界、虛擬世界揭了個底朝天。
少年又是一笑。“三萬塊錢也不是很多啊,你女兒在海關工作,效益一定不錯——項老師,我聽說樓下那個女的要結婚了,是吧?其實我老早就曉得您不會和她來真的。您是當自己在戲臺上呢,您看那些才子佳人,一到成親結婚,戲就結束了,所以您也結束了。那女的和您不是一路人。要是放在過去,您就是風流才子、老克勒,那女的只不過是弄堂里的大媽——我下午還有事,您現在能不能告訴我,什么時候給我,啊?我要現鈔,別轉賬什么的。”少年笑瞇瞇地望著他。
小說中至少四處提到了少年的“笑”,這是洞察了別人秘密之后的狡黠的笑,這是掌握了別人弱點的勝利者姿態的笑,這也是將項海看得明明白白的笑。項海是一個活在雙重虛擬中的人物,京劇與網絡就是這雙重虛擬。更重要的是,項海力圖將自己的世界也戲文化、藝術化與虛擬化,與羅曼娟的交往、化身“杜麗娘”、到戲曲學校上課、對女兒項憶君的理解,無不表明,他幾乎已經混淆了現實世界與戲曲世界、虛擬世界。他也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這是一種堅守,即便為了女兒的前途這份堅守出現了短暫的裂縫,但是,在涉及自身的時候,他完全是投入到其中去的。然而,他的堅守在不良少年的眼里竟然是那么的幼稚、可笑甚至無聊,古老戲曲中的氤氳世界無法在現實世界里復制,原來如此美好的世界竟然是如此的不堪一擊。作者借不良少年完全將戲曲、藝術與虛擬與現實的裂縫撕開,從而向人們昭示:當下生活有其現實邏輯,它已經無法容忍古典式的生活,即便你可以“獨善其身”,安然守著自己的小天地。但是,社會作為一種無孔不入的勢力,終究會將小天地撕開一道口子,讓你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那么的透徹。
四
不良少年從“柳夢梅”到真實身份的轉變,項憶君不經意間向領導說的那句“那您就把我調到機關來呀”,以及小說結尾處糅合了古典戲曲與現代城市的雙重空間:“一時間,這座城市的上空都回落著幽婉凄轉的唱腔,像層薄薄的紗,籠罩著整座城市”,似乎都在表明了一種文化的尷尬。的確,古典戲曲的式微已經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如果說,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里古典戲曲曾一度成為文化娛樂的主要形式,那么,進入到現代之后,隨著中國社會從古代向現代的轉型,隨著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日益推進,即使京劇曾在梅蘭芳那里盛極一時,在現代樣板戲那里曇花一現,在“國粹”的名義下年年登上春晚的舞臺,但是大勢所趨,以京劇為代表的古典戲曲終究還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了,它們逐漸在社會轉型這個龐大的背景下耗盡了自己的能量,漸漸淡出了文化的主舞臺,古典戲曲的根脈在中國傳統文化,古典戲曲的衰落因此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式微的表征。《姹紫嫣紅開遍》中,項海被不良少年敲詐勒索、項憶君屈從于舅舅的壓力將高考志愿由戲曲學院改為工商管理以及項憶君利用領導對京劇的喜好將自己調至機關等等,都已經表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戲曲已經被生活阻隔于現實之外,項氏父女倆也無法徹底生活在一個自造的神話當中。沒有人可以否認項氏父女對京劇發自內心的喜好,同樣也沒有人能夠否認,當古老的戲曲、傳統文化意欲凌駕于“業余愛好”之上,進入到人們日常生活的腠理之下的時候,傳統與現代、藝術與生活的裂變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無論這多么令人惋惜。
[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353.
[2]滕肖瀾.創作談[J].北京文學,2007(10):80.
責任編校:汪孔豐
OntheContemporaryDilemmaofTraditionalOperas:ACaseStudyofFlowersGlitterBrightlyintheAir
ZHOU Hong-bing, WANG Lan-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XIANG Hai and his daughter XIANG Yi-jun are Peking Opera lovers inFlowersGlitterBrightlyintheAir, a novella by TENG Xiao-lan. They have an ardent love forFlowersGlitterBrightlyintheAir, and try to put the dramatic stage into their daily life, making life dramatic, artistic and virtual. By narrating experiences of the father and the daughter in their work, love and life, the novella reflects on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operas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 surprising end reveals that traditional opera culture as a life style does not exist in real life and only appears at the stage.
TENG Xiao-lan;FlowersGlitterBrightlyintheAir; traditional opera; contemporary dilemma
2014-04-29
周紅兵,男,安徽桐城人,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王蘭燕,女,山西壽陽人,安慶師范學院傳媒學院講師,文學碩士。
時間:2014-10-28 14:19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7.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7
I207.42
A
1003-4730(2014)05-0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