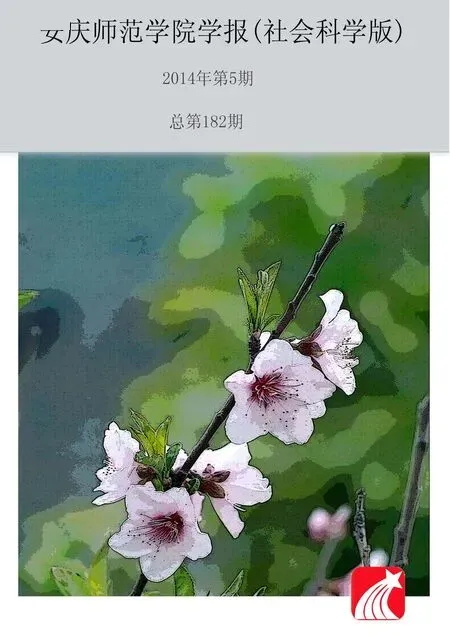魏明倫劇作的“中國化”改編與“世界性”眼光
吳 彬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魏明倫劇作的“中國化”改編與“世界性”眼光
吳 彬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民族身份的自我認同和世界戲劇的理想建構,這是魏明倫劇作的重要價值。“中國化”改編與“世界性”眼光,是他在改編過程中的基本立場。《潘金蓮》從創作技巧上自覺與世界戲劇潮流接近,但又不失中國味兒;《中國公主杜蘭朵》通過對西方文化霸權的還擊,表達了作家對中國文化的深刻認知;《好女人·壞女人》是在現代派技巧非常嫻熟地操作下對人類共同本質的自如應答。魏明倫以其創作實績達到了與世界的對話,顯示了他對民族戲劇的自信。
魏明倫;中國化;世界性
民族性和現代性一直是中國戲劇所面臨的偉大課題。作為中國當代最負盛名的劇作家,魏明倫的劇作在民族性和現代性探索過程中做出了有益嘗試,并取得了重要收獲。民族身份的自我認同和世界戲劇的理想建構,這是魏明倫劇作的重要價值。“中國化”改編與“世界性”眼光,是他在改編過程中的基本立場。
一、現代戲劇的創新實驗
何謂現代戲劇?戲劇史家董健認為:“基本內涵有三條:第一,它的核心精神必須是充分現代的;第二,它的話語系統必須與‘現代人’的思維模式相一致;第三,它的藝術表現的物質外殼和符號系統及其升華出來的‘神韻’必須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追求。”[1]8一言以蔽之,現代戲劇“就是在現代化的舞臺上表現現代人的生活體驗、生命意識與審美愉悅的戲劇,它是人在精神領域里的‘對話’,不管它的題材多么古老,多么‘非現實’,它的‘精神內涵’中必然閃耀著‘現代’之‘光’。”[1]83
中國的現代性是從20世紀初期開始的。“現代性作為一項社會規劃工程,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現代民族主義意識的生成。這在思想文化領域和審美領域表現出來,就是民族性追求、自我認同”[2]。董健認為:“此一階段的核心思想是求新求變”,就戲劇而言,就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用西方戲劇的藝術價值觀念來改造戲曲的結構模式”[1]5。稍后,因為戰爭的需要,救亡壓倒啟蒙。所謂的民族性最終只是落實到了爭取民族獨立、避免亡國滅種的政體層面,而文化層面的現代性則被擱置。1949年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由于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抬頭,對西方采取敵視態度,所謂的現代性被視為毒草,只是片面夸大民族性,致使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橋梁被拆斷。真正把這座橋梁重新搭建起來是在20世紀80年代。就戲劇而言,“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從更加‘形而上’的層面上重估與認同古典戲曲的美學價值。戲曲表現生活的‘寫意性’,結構的‘開放性’,表演和唱腔的‘程式化’,舞臺觀眾的‘直線溝通’等等這些千百年延續的藝術特征,均被從美學精神的高度加以總結、重估與認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甚至“有人將這些‘遺產’與西方現代主義戲劇掛上了鉤,試圖使其獲得世界意義”[1]5-6。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了一批帶有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色彩的‘探索劇’(或曰‘實驗劇’),結束了單一的寫實主義的統治,從而把中國戲劇的現代化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為中國戲劇與世界戲劇的‘接軌’與‘對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25。川劇作家魏明倫便是在這一時期,以其劇作鮮明的現代性而在戲曲界首領風騷的。正如余秋雨所言:作為“二十世紀晚期中國傳統藝術與現代社會和國際社會深度斡旋的活躍性因素”,魏明倫打通了中西戲劇溝通的橋梁,解答了“中國文化如何面對國際,傳統藝術如何面對現代”的問題[3]6。
荒誕川戲《潘金蓮》發表于1985年底,是魏氏的第一部探索之作。《潘金蓮》的題材,在中國戲劇中早已有之,川劇中有《武松殺嫂》,話劇中有《潘金蓮》,魏明倫的創作,實乃“舊戲新編”。董健認為:這一時期的戲劇家們“更多地從藝術的角度并以世界眼光看戲劇,不但不反對中國傳統戲曲,而且試圖從一個更高的美學層面上尋找西方現代主義戲劇與中國傳統戲曲藝術特征的接軌點”,“他們是站在戲劇觀念的現代化的高度來審視傳統的”[1]35。魏氏的《潘金蓮》雖標名為“荒誕”,但已經遠離西方戲劇界對“荒誕”一詞的內在規定性。“荒誕”一詞本來源于西方,講的是本體意義上人的存在世界的虛無。但在魏明倫這里,只是取了荒誕的形式,其內核還是對婚姻、對愛情、對封建倫理道德等社會問題的嚴肅思考,也正是因為魏明倫取了“荒誕”之形而舍其“實”,結果招致“堅持西方正統‘荒誕派’概念純潔性的人的批評”。但是,正如學者呂效平所言,“魏明倫在《潘金蓮》里的成功”,不在于它是不是采用了荒誕的形式,而在于“他使戲曲超越了傳統上倫理的奴仆的地位,寫出了真實的人性和我們觀照自己的人性時的永久的困惑”[4]。這種“真實的人性”正是現代戲劇的應有之義,因為“中國戲劇現代化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在戲劇舞臺上表現‘現代人’的覺醒意識與理想追求”[1]253。其實,魏明倫的“荒誕川戲”之所以別異于西方的“荒誕派”戲劇,正是他在改編過程中有意為之的基本策略,那就是把中國戲曲放在世界戲劇的大背景中進行考查,精神上與西方思想接近,技術上又盡可能使之“中國化”,具有濃重的中國味兒。這是由中國戲曲觀眾強大的欣賞慣性所支配和決定的。
很明顯,就《潘金蓮》的創作而言,魏明倫是采取了一種“中體西用”的策略,劇作在立意、主題、思想、內容等方面都是有關本土社會的,它是植根于中國文化這個大背景中的,但在形式上卻借鑒了西方的技巧,而這種借鑒又不是一味地模仿,而是為我所用,為自己的創作目的服務,使之盡量“中國化”。在觀眾看來,雖然名為荒誕劇,但還是地地道道的川戲,里面有川音川味兒,川劇的唱腔、川劇的表演、川劇的幫腔等都保留完好。譬如在楔子部分,一開場,先是四句幫腔:“才子編野史,戲臺塑武松。靈堂刀光閃,血濺孝衣紅。”這是中國古典戲曲慣常使用的敘事手法,正戲開始之前,先由“引戲”對劇情加以介紹或解說,使觀眾大致明了這出戲的主要內容,以便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對演員技藝的關注上。然后,“大幕徐啟,燈光漸明,映出一組雕像——‘武松殺嫂’場面”。這又是中國戲曲開場時的一種旨在吸引觀眾注意力的亮相手法。接下來,“幫腔一止,群雕即活。”群眾場面出現,各個角色形態畢現:
王婆怪叫一聲,奪門欲逃,被士兵拖回,“托舉”奔下。
鄰居紛紛做鳥獸散,下。
武松殺嫂,按傳統戲招式,刀光與水發飛舞,輕功隨椅技翻滾。武松口含短刀,撕開潘金蓮孝衣領襟,對準胸膛一刀捅去,潘金蓮慘叫撫胸,身如落葉徐徐飄落。
切光,四周黑暗,只留潘金蓮“臥魚”合目于血泊,漸隱沒。
這里,中國傳統戲曲的多種身段和技藝得以展現,有步法,有發功,有身法,有腰功,還有椅技和軟僵尸,極具觀賞性。在《潘金蓮》這個戲里,魏明倫既表達了對傳統戲曲“技藝”的充分肯定,又顯示出對現代戲劇“理念”的追求和對新的“表現”形式的熱情。他是既放眼世界,又立足本土。
二、“中國化”語境前設
如果說《潘金蓮》還只是通過對中國傳統戲曲故事的改編使之帶上了“洋味兒”,從而達到與世界戲劇的對話,那么,《中國公主杜蘭朵》則是通過對外國劇本的改編使之中國化,從而表達作家對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在與世界戲劇對話的同時,彰顯出他對民族話語的充分自信。
《中國公主杜蘭朵》是1993年創作演出的川劇。同年,該劇在北京和張藝謀導演的意大利歌劇《圖蘭多》同時上演。對于張藝謀執導的歌劇《圖蘭多》,當時的評論界就有人指出其中所攜帶的后殖民話語,盡管張藝謀在歌劇的外部包裝上盡量中國化,甚至采用中國京劇里的服裝和動作,但內核還是西方的。魏氏的川劇《杜蘭朵》卻是真正具有中國味兒的戲劇,達到了真正的“中國化、戲曲化、川劇化”[3]240。“杜蘭朵”本是“外國人臆想的中國故事”,它最早見于流傳在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日》中的《杜蘭鐸的三個謎》。這個“流傳西方的題材”曾備受西方人欣賞,席勒、戈齊等先后寫過多個劇本演繹這個美麗的愛情故事。不管是席勒,還是普契尼,他們都未曾到過中國,都是憑著自己的臆想來猜測這個“中國故事”,都或多或少地烙上了西方人思想觀念的印記。歌劇《圖蘭多》和川劇《杜蘭朵》“表面上一個是‘外國人臆想的中國故事’,一個是‘中國人再創的外國傳說’,但在這兩出戲背后所反映的,卻是關于詮釋中國與中國人的話語權的爭奪”[3]345。《圖蘭多》講的是一個中國公主為了拒絕向她求婚的男子,設下毒計,凡是求婚者必須回答她的三個謎語,答錯的就要被殺。韃靼王子卡拉夫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終于答對謎底,并用真情感動了冷酷的圖蘭多公主。最后,二人結為夫妻,“大團圓”結局。魏氏的《杜蘭朵》即取材于這一故事。但是,在原有情節框架上進行了新的改寫,從而,使之更加具有中華民族的本土特征。
(一)公主與王子相遇場面的改寫
在歌劇《圖蘭多》中,圖蘭多與王子卡拉夫的相遇是因為一支送葬的隊伍。圖蘭多出題擇婿,波斯王子考驗失敗,被送往刑場。圖蘭多站在陽臺上觀看,恰巧被卡拉夫王子見到。由于圖蘭多公主的天姿國色,卡拉夫頃刻為之傾倒,精神恍惚,并且不顧一切要把她弄到手。于是,便有了以后卡拉夫求婚的情節。在川劇《杜蘭朵》中,這一情節被改寫了。在該劇中,是說無名氏(即《圖蘭多》中的卡拉夫王子)隱居荒島,因偶然的機會看到了使女柳兒手中的公主畫像,遂被畫中公主的美麗所吸引:“看一眼心馳神往”,“看兩眼走火入魔”,“看三眼墮入愛河”。這種“見畫生情”是中國文學中常見的愛情模式,它與《牡丹亭》中柳夢梅“因畫生情”的故事異曲同工。前者是一種“陽臺”模式,它的愛情特征是熱烈、奔放;后者是一種“花園”模式,它的愛情特征是羞澀、含蓄。男女之間縱然相遇也只是在花園這種幽靜之所,而且是偷偷進行的。“花園相會,私定終身”,這是中國傳統戲曲中“才子佳人”題材的創作套路,如《西廂記》和《賣水記》等。魏氏的這一改動更符合中國文化的倫理型特征。
(二)三個謎語的改寫
杜蘭朵公主設下的三個謎語,在不同的作家筆下是不同的。《杜蘭鐸的三個謎》中其謎底分別是眼睛、犁頭、彩虹。在戈齊的劇本里分別是太陽、白晝和黑夜、亞得里亞雄獅。在席勒的改編本中則為日歷、眼睛和犁。到了歌劇《圖蘭多》中,則成了希望、熱血、圖蘭多。其實,不管是上述哪個謎底,都明顯帶有西方人的思辨特征。其原型則是古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與紐芬克斯之間的一場猜謎較量。這種智力型的猜謎是西方思辨型社會的產物,在中國很難找到共同的話語。
在魏明倫這里,對考驗無名氏的難題進行了重新改寫與設計。三道難題分別是測試對方的體力、智力和體智結合的武藝水平。在中國的民間傳說中,比武招親的故事比比皆是,這種測試方式更能滿足中國觀眾的欣賞期待,更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
(三)公主要殺死求婚者原因的改寫
在《杜蘭鐸的三個謎》中,杜蘭鐸要殺死求婚者是因為父皇要她嫁給一個配不上她的西藏王子。為了反抗這種包辦婚姻,她定下擇偶標準:“凡是答不上我三個謎語的求婚者,你要用鎖鏈把他鎖起來,拉到刑場上去”。在歌劇《圖蘭多》中,圖蘭多殺死求婚者的原因則被解釋為復仇。因為自己的先祖中曾有一位公主被一個外國侵略者欺凌而死。為了復仇,她便使出這套考驗男人的方法。
在《中國公主杜蘭朵》中,魏氏把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情況,進行了大膽改動。他從變態心理學的角度對杜蘭朵的心理進行了深入解讀。他剝去了公主嗜殺成性的復仇面紗,從少女青春期性心理的發展變化細致入微地分析了杜蘭朵的矛盾心理,把一個殘酷的、性格單一的、簡單化、臉譜化、符號化的女性從既定的形象中解放出來,恢復了她作為女性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進而從人性的深處發現人格的二重性和復雜性。在川劇《杜蘭朵》中,杜蘭朵公主長期生長在宮闈深處,所見的都是太監這些“去了勢”的男人。生長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里,自然會對性愛產生錯覺和抵觸心理。所以,在她看來,男子皆是“須眉濁物”。由于對男子并不了解,她本能地以為男性都是粗野的:“一想到異性粗野就害怕”。然而,作為青春少女,她和其他女性一樣思春、懷春,甚至為之長夜失眠。她一想到男女間的事情也害羞,她也需要愛情。不過,由于愛面子,放不下“公主威儀”,她的虛榮心被扭曲。加以對性愛懷有恐懼心理,這時,她的被扭曲的虛榮心已經不僅僅是女性常有的驕矜,而是暴戾。她試圖以冷酷殘殺求婚者,但其內心還是渴望求婚者。正如杜蘭朵所唱:“有人求婚,我怒哇,怒氣大”,“無人問津,我愁哇,愁更加”。這種由愛而恨,愛恨交織的矛盾心理,這種對男性世界懷著集體仇視的變態心理是具有普遍性的。
“無人問津我太煩悶,有人求婚我又驕矜。少女心情有矛盾,且看來者是何人?”一語“且看”,足見杜蘭朵對異性還是有所期待的。無名氏出場,按先前的慣例,求婚者面見公主,公主都要以“香羅遮面”,為的是“遮去須眉臭味”,但無名氏卻例外。在公主看來,“此人似乎沒有男子濁氣”。杜蘭朵這一細微的行動轉變(不用遮面旗),其實,是她大的行動轉變的端倪,是對男性態度的開始轉變,對男性的強硬立場的開始和緩。當公主和無名氏乍一照面,雙雙心中都動了漣漪。公主由外表美開始追問無名氏的內心美,她所需要的就是外表美和內心美相統一的真正的男性。這個時候,她內心的情緒反應是“乍暖還寒難穩定”。
魏氏的這一改動,從根本上消除了因文化隔膜造成的對中國公主的曲解。這種性心理的變態反應,不但有了科學的根據,而且在文化特征上找到了自己的“母題”和身份。
(四)求婚者被殺結果的改寫
由于歌劇《圖蘭多》基于“復仇”這一內核,所以,一開場就是波斯王子考驗失敗,被押赴刑場,準備砍頭的血腥場面。這為的是突出公主的殘酷,但它卻是對中國歷史的誤讀。中國的歷代皇朝中,確實不乏驕橫跋扈的公主,如東漢之湖陽公主、唐代之太平公主,但嗜殺成性卻是罕見。歌劇《圖蘭多》更大的偏狹在于,“把傳說中的‘中國公主’上升做一種象征,而不是當作實有其人的地道的中國公主”,“并不在中國味兒上做文章”[5]308。蘇叔陽認為,普契尼的這種做法是“高明的”,但正是因為這種所謂的“高明的”“象征”,使得杜蘭朵不具有具體的指證性,而成了一個能指很寬泛的符號。進而把杜蘭朵一個人的存在作為中國歷代公主的代表,由杜蘭朵的殘酷進而指證整個中國文化,把中國與中國人視為愚昧、殘酷、落后的象征。基于西方人的這種文化錯覺和敘述策略,魏氏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他也“將‘公主’模糊化,而不坐實該公主究系何朝何代第幾位皇帝的女兒,是嫡出還是庶出抑或是私生女”[5]308-309,也以象征的手法,擴大“公主”的能指范圍,從具體細節的修改上下功夫,進行文化上的還擊。
(五)“大團圓”結局的改動
從本體論的角度來講,中國傳統戲曲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悲劇,有的只是以“大團圓”為結局的苦戲。或許是為了更加適應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在普契尼筆下,卡拉夫最后入贅駙馬,與公主結為百年好合。雖然這種結尾更接近中國傳統的戲曲模式,但這種形式上的“大團圓”頗有牽強之感,有悖于中國文化的倫理型特征。當一直深愛著卡拉夫的侍女劉(柳兒),為了保護自己的心愛之人自殺之后,卡拉夫卻立即用自己的“長吻”溶化了公主冰冷的心,贏得了公主的愛,在對“愛情”的禮贊中以“大團圓”結局。這種行為舉止在以倫理為本位的中國是絕對不可能也不容許發生的。
卡拉夫為追尋愛情而來,試圖以愛情感化公主,使其擺脫復仇心理。《圖蘭多》極力宣揚的“愛能征服一切”的理念代表的是西方人的優越感和自信,其最終指向是通過“對中國公主施以人性救贖和愛情感化,使其擺脫復仇心理,服膺西方文明”[6]255。倒是魏明倫的改動,更加人情化。在魏氏筆下,無名氏目睹柳兒的癡情和犧牲,幡然悔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最終拒絕了入贅駙馬,駕舟而去。這不僅僅是道義上的負責(為柳兒的真情和犧牲負責),它更是道家“無為”、“自然”思想的徹悟。這種從山水之間來(無名氏在川劇中只是孤島一隱士),又到山水之間去的隱逸思想,是典型的中國山林隱士思想,它與西方的探險精神是相背的。杜蘭朵最終追隨無名氏而去,也是自我在徹悟之后,對這種隱逸思想的認同和踐行。由歌劇中的“卡拉夫王子”到川劇中的“無名氏”,這一名字的改動充分說明文本指證已經由具體的所指擴展到了無限大的能指。無名氏已非一個簡單的具體的隱逸之士,他成了一種符號,成了道家文化的代表,成了中國本土文化最明顯的標志。劇末柳兒、公主合二為一,杜蘭朵棄權勢追隨無名氏回歸自然,“升入至善至美境界”,“這個主題不僅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而且也與當今時代人類文明進程的總體趨勢相契合”[6]254。通過對既有文本的改寫,魏氏最終將這個“外國人臆想的中國故事”還原成了“中國人再創的外國傳說”。在它的背后,不但是話語權的爭奪,更是一種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確認。
三、“世界性”的終極關懷
在《中國公主杜蘭朵》中,作家只是從話語權的爭奪與反擊中顯示了本民族戲劇真實的一面,對西方人的誤解予以澄清,它所關注的只是中國這個局部區域中人的生存面貌和由之反映出的文化特征,而《好女人·壞女人》則是把視野放大到了全人類。它已經“無法取信于一種具體的真實性”,“它屬于人類生活的整體”[7]。作家從人性的深層,從人的內在的對立、統一中對人的靈魂(人的本質)進行了偉大的拷問。在人性中始終伴隨著“天使”和“魔鬼”的雙重較量,這是人類共通的,沒有地域之限、國家之別、種族之分。
川劇《好女人·壞女人》改編自魏氏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四川好女人》。《四川好女人》取材于布萊希特的譬喻劇《四川一好人》。布氏的《四川一好人》只是借“四川”這個地方,以社會底層人物為依托,來表達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人的異化,揭示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好人做不成,為了生存,只好做壞人”的社會現實[8]。布萊希特創作該劇的時候,中國尚是一個農業古國,工業還不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所謂的“人的異化”現象也并未發生。而布氏選擇四川,這個農業文明深厚,又遠離工業文明的內陸省份,本身就是對中國的陌生和不了解。雖然,“四川”只是一個象征的抽象世界,是一個概念的存在。但是,由于對中國社會特征的盲視,布氏的劇作很大程度上顯示了他對中國的誤解。這種把自己臆想的“當然”當作一個理想的國度的“實然”,其本身就有一種文化霸權的味道。在布氏的《四川一好人》里邊,除了劇名是四川,以及劇中人名采用了漢民族的稱呼以外,我們很難再看到它有什么中國特征。
由于民族意識的自覺,魏明倫在改編電影文學劇本《四川好女人》時便有意識地使之中國化了。雖然,他仍舊是把四川作為一個能指很寬的地域,但在他的筆下,四川并不僅僅是一個符號。它既有自己的能指范圍,又有自己的所指范圍。在這里,不但有四川的袍哥、川西壩、峨眉山、大佛,還有小販子、妓女、警察、城門、茶館、酒肆、煙店、當鋪、作坊、商行、法庭、汽車和飛機等,應有盡有。既有古裝、清裝、民國服裝,又有洋裝,真是古今中外雜糅。它既像四川,又不像四川,既像中國,又像外國。它已經不是確指哪個地域,而是指向了全人類。更為明顯的是三位神仙。在布氏筆下,三位神仙的來歷都不甚明了,分別是神仙甲、神仙乙和神仙丙。而在電影本《四川好女人》中,魏氏對三位神仙進行了拼貼。老神仙“裝若南極壽星與圣誕老人的混合”,女神仙“好像觀音菩薩與圣母瑪利亞的嫁接”,洋神仙“十足老外,全盤西化,希臘神話原裝貨”,并且還設計了女神仙和洋神仙的打賭。但是,人類究竟是好是壞的爭論最終也沒有個明確的結果。因為人性中存在著“天使”和“魔鬼”,簡單的“好”、“壞”二元對立判斷是不行的,只能寄希望于天使多多出現,魔鬼少來打擾。
在川劇《好女人·壞女人》中,劇作家使這部本來具有象征意味的譬喻劇更加象征化、中國化、川味兒化了。三個神仙都是外星人,他們下凡之后分別化作了財神、進寶女、招財童——這純正的中國貨,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特征。但是,劇作的主題并未改變,仍是對人性二重性的探討。很顯然,作家是立足本土,以放眼全球的目光,來看取人性的。他雖站在民族身份自我認同的立場,但其視角已經伸向了世界。
從《潘金蓮》到《中國公主杜蘭朵》,再到《好女人·壞女人》,魏明倫的創作思想是非常明確的。由對西方創作技巧的模仿,到對中國文化的深刻解讀,再到中西文化的和融,魏明倫以其創作實績達到了與世界的對話,表達了他對民族戲劇的自信。
[1]董健.戲劇與時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2]譚好哲,任傳霞,韓書堂.現代性與民族性:中國文學理論的雙重追求[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8.
[3]魏明倫.魏明倫劇作精品集[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
[4]呂效平.戲曲本質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366.
[5]魏明倫.戲海弄潮[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
[6]居其宏.讓東方精神回歸東方——從川劇《中國公主杜蘭朵》想起的[C]//魏明倫.好女人與壞女人——魏明倫女性劇作選.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7]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229.
[8]布萊希特.四川一好人[M].黃永凡,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1.
責任編校:汪孔豐
2014-06-09
吳彬,男,河南許昌人。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時間:2014-10-28 14:19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8.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8
I207.36
A
1003-4730(2014)05-00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