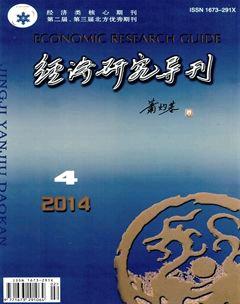保安處分借鑒與中國違法行為矯正制度構建
蔡景華
摘 要:勞動教養制度是指中國對有嚴重違法行為,但尚未構成刑事處罰標準的嚴重違法人員采取的一種以限制人身自由為手段的強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保安處分是對具有社會危險性的特殊違法行為人進行強制性思想矯正的法律制度的總稱。中國勞動教養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存在諸多明顯缺陷。因此有必要構建中國違法行為矯正制度,在制度設計上可以借鑒西方保安處分的相關制度。
關鍵詞:勞動教養;保安處分;違法行為矯正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4-0299-02
勞動教養制度是指中國對有嚴重違法行為,但尚未構成刑事處罰標準的嚴重違法人員采取的一種以限制人身自由為手段的強制性教育改造措施。自20世紀50年代中國開始創立勞動教養制度以來,這項制度對挽救嚴重違法人員,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發展,現行勞動教養制度的運行機制越來越不適應當前社會的需要。對中國勞動教養制度進行徹底改革已經成為共識,但對其未來的改革方向和具體制度設計的討論,則應建立在勞動教養制度功能定位的基礎上,我們應當首先回答的問題是什么是勞動教養,建立勞動教養制度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是什么,在明確了勞動教養制度的功能定位后再進行相關的制度設計。
一、勞動教養制度概述
中國學界對勞動教養制度性質的觀點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行政強制說,另一種是行政處罰說。行政強制說認為勞動教養是一種旨在改造人、教育人,從思想上徹底改造違法人員的強制性教育措施,限制自由和集體勞動只是進行教育的手段;行政處罰說認為勞動教養是一種對嚴重違法但尚不構成犯罪的違法人員的一種處罰行為,限制人身自由本身即是目的。筆者認為現行勞動教養制度同時具備了上述兩個特點,但這也是造成問題的根源,而行政性強制教育措施才是勞動教養制度的理論定位。
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是在在建國初期特定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是尚不夠刑事處分標準的嚴重違法分子,并且要具有“屢教不改”和“生活無出路”的特點。由此可見,勞動教養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對具有嚴重“社會危險性”的嚴重違法人員進行強制性教育,使其在思想上受到徹底改造,并且具有自食其力能力的行政性強制教育措施。所謂“社會危險性”是與主體“再度侵害社會的現實可能性”具有相同含義,這一表述與含義相近的“人身危險性”有以下區別:(1)“人身危險性”一般含義是“犯罪主體再度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性”;“社會危險性”的一般含義是指“主體再度實施侵害社會行為的現實可能性”;(2)“人身危險性”是中國刑法理論用語,它通常用來表示犯罪主體的人身特征,必須以主體已經實施了犯罪行為為前提;而“社會危險性”是法律規范用語,它通常用來表示侵害社會行為主體的特征,不以主體已經實施犯罪行為為前提;(3)作為評價對象時,“人身危險性”以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為成立要件;而“社會危險性”則必須以“再度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現實可能性”,即真正意義上的現實的危險性為成立要件。
但自1982年公安部制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后,對于勞動教養的六種適用對象,除對犯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的違法分子有“屢教不改”的要求外,其他五種適用對象均不再將“屢教不改”作為勞動教養的必要條件。這一規定實際上已經動搖了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價值基礎。因為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是建立在預防“社會危險性”基礎上,即對“再次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現實可能性”的違法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屢教不改”是被教養對象的主要特征,勞動教養制度的期限和措施也是和被教養對象“屢教不改”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的。去除“屢教不改”這一必要條件后的勞動教養制度,只能以相對人實施的違法行為嚴重程度作為決定對其進行勞動教養的根據,“社會危險性”不再是必要根據。這樣本應是針對相對人的“社會危險性”采取的強制性教育改造措施,在實際運行中就不可避免地轉變成為一種針對相對人實施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這也導致了相對人嚴重但不構成犯罪的違法行為與過長的限制自由期限之間的矛盾。
因此,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應當回歸制度建立的初衷,充分發揮作為對具有較大“社會危險性”違法人員的強制性教育改造措施的作用,而不是一種行政處罰措施。只有這樣,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根基。
二、西方保安處分制度概述
保安處分是指以特殊預防為目的,以違法行為人的社會危險性為適用基礎,通過實施強制性矯正、教育、感化、醫療等手段,對具有社會危險性的特殊違法行為人進行強制性思想矯正的法律制度的總稱。保安處分制度建立的目的是為了克服傳統報應主義刑法理論的缺陷。報應主義理論是基于道義責任論,對犯罪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客觀犯罪行為,進行罪責刑相適應的刑事處罰的一種刑法理論。由于其注重行為人客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輕視行為人主觀的社會危險性,因此對于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社會危險性較大但不夠刑事處罰標準的累犯、慣犯,以及客觀行為嚴重但主觀惡性較低的未成年犯,只科處與行為人外在行為而不是與其主觀惡性相適應的道義責任,已經無法對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大量新型社會問題引起的違法犯罪活動起到防衛社會、預防犯罪的目的。
在此基礎上,西方國家提出建立保安處分制度,通過對違法犯罪行為人的主觀社會危險性進行矯正,以達到防衛社會、預防犯罪的目的。保安處分的適用對象包括少年人、精神病人、吸毒者、酗酒者、常業和常習慣犯和累犯等,主要方式包括對于常業和常習慣犯進行預防性監禁;對于無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吸毒者、酗酒者等進行強制性隔離治療;對于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對于厭惡勞動的職業乞丐、常習性流浪者處以強制勞動;以及保護觀察等對危害較小的犯罪人所采取的監督與改造的措施等各種社會性矯正措施。
三、構建中國違法行為矯正制度
通過兩者比較可知,西方保安處分制度和中國勞動教養制度在改造行為人主觀社會危險性上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但在運行中中國勞動教養制度存在諸多缺陷。由于改造行為人主觀社會危險性的需要,因此有必要構建違法行為矯正制度,并可借鑒西方保安處分的相關制度。立法上,中國應制定一部《違法行為矯治法》,建立完備的違法行為矯治制度,取代現行法律依據雜亂且有違反人權保障之嫌的勞動教養制度,并在適用機關、對象、原則和執行方式等方面作出規定。
首先,在適用機關上,應由行政機關來決定適用,這是基于行為人的各種違法行為是屬于不應受刑罰處罰的一般違法行為,可以由行政機關決定適用《違法行為矯治法》的相關條文,但為了保護行為人的合法權益,應當賦予其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具體可由地市級違法行為矯治委員會來決定適用,組成人員可包括民政、司法、公安人員等;在適用對象上,未來的違法行為矯治的適用對象應當包括實施嚴重違法行為但尚不夠刑事處罰標準的違法行為人、屢教不改但尚不夠刑事處罰標準的常習犯、多次賣淫嫖娼者、作為強制醫療對象的患有性病的賣淫嫖娼者、吸毒者、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精神病人、以及作為強制教育對象的未成年違法犯罪人等;在適用原則和條件上,應當將行為人的主觀社會危險性作為判斷的主要標準,行為人的客觀違法行為可以作為程序適用啟動條件但不作為主要判斷標準,綜合考慮違法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再犯可能性。
在執行期限、方式和機關上,應當基于行為人的主觀社會危險性程度,決定對違法行為人實施強制矯治的期限和不同方式。在期限上,不應設置一個絕對期限,而應當根據違法行為人的主觀矯治進程而適用不同期限;在方式上,除強制醫療和未成年人強制教育外,對于嚴重違法但不構成刑事處罰標準的違法行為人、屢教不改的實施違法的常習犯,可以采取多種思想矯治措施。如可以由慈善機構、社會團體等承擔監護責任,通過社會力量對觀察對象進行監督改造,通過采取比較和緩的方法,對受處分者不予拘禁,依靠社會力量對受處分者進行教育,以改善其生活環境,排除自新障礙,促使其健康地重返正常的社會生活。在保護觀察期間,如其無悔改表現,可延長期間或改處其他更合適的矯正措施;在執行機關上,可由各違法行為矯治機構實施(由原勞動教養執行機構轉化而來),根據不同執行方式選擇不同執行機構,如需要監禁性處分的可在封閉式場所實施;需要強制醫療和教育的可在專門性場所進行,如在戒毒所、精神病院和少年學校等;需要社會矯治的可以在敬老院、孤兒院、社區醫院等公益性機構進行。
中國勞動教養制度在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取得了公認的成就,也造成了侵犯人權等惡果,改革已經是大勢所趨。西方保安處分基于其與中國勞動教養制度具有相類似的目的和制度上的合理性,可以作為構建違法行為矯正制度的借鑒對象,但必須考慮中國自身國情,切忌盲目照搬,以最終實現中國維護社會安全和人權保障的雙重目的。
參考文獻:
[1] 全理其.英國的保安處分[J].現代法學,1984,(2).
[2] 張小虎.論中國保安處分制度的建構[J].政治與法律,2010,(10).
[3] 劉仁文.治安拘留和勞動教養納入刑法的思考[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0,(1).
[4] 薛暢宇,劉國祥.論改革和完善收容教養制度[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04,(4).
[5] 胡衛列.勞動教養制度應予廢除[J].行政法學研究,2002,(1).
[6] 屈學武.保安處分與中國刑法改革[J].法學研究,1996,(5).
[7] 喻偉.保安處分刑事立法化——中國刑法改革上的重大議題[J].法學評論,1996,(5).
[8] 周水清.對收容審查立法問題的探討[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90,(6).
[9] 陳忠林.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困境、價值危機與改革[J].法學家,2004,(4).[責任編輯 陳 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