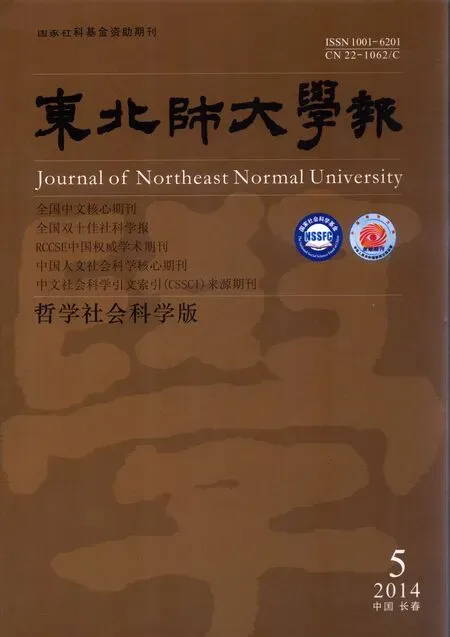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批評理論之探究
王 翠
(1.吉林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2.北華大學 外語學院,吉林 吉林 132013)
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批評理論之探究
王 翠1,2
(1.吉林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2.北華大學 外語學院,吉林 吉林 132013)
1991到1992年期間,洛奇在《星期日獨立報》上發表了50篇短文,并于1992年結集出版,取名為《小說的藝術》(TheArtofFiction)。本文試圖通過對《小說的藝術》的解讀,來了解英國批評家戴維·洛奇分析小說文本時所采用的批評方法,并探討文學史知識對文學創作的潛在影響,以及批評理論與創作實踐的關系等問題,以欣賞這部獨特的小說詩學。
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批評理論;批評方法;文學史;批評與創作
在學術界,戴維·洛奇這個名字并不陌生。他既是一位享譽世界的小說家,也是一位別具一格的文學批評家。自從其第一本批評著作《小說的語言》(LanguageofFiction,1966)問世之后,洛奇相繼出版了十幾本批評論著或文集。1991年初,洛奇應邀在《星期日獨立報》的文學專欄上,每周撰寫一篇關于散文小說內容的文章。洛奇共在這個專欄上發表了50篇文章,由于受報紙版面的限制,篇幅較短。后來,在1992年結集出版前夕,洛奇將這些文章進行了修改和完善,基本將原篇幅的長度都增加了1/3左右。
雖然《小說的藝術》第一篇名為“開頭”,最后一篇名為“結束”,但正如洛奇自己所述:“自從1987年提早在大學退休以后,我發現我不再打算專為學術界寫作;但仍然感到對小說的藝術和小說的歷史意猶未盡,而這兩點對于更加廣闊的讀者大眾而言,可能他們會更感興趣”[1]9,本書的假想讀者并非學術圈的教授學者們,而是普通讀者大眾。因此,洛奇并沒有賦予《小說的藝術》一個系統、循序漸進的理論體系。此外,由于洛奇在伯明翰大學任教時曾教授過《小說的形式》這門課,使洛奇在《小說的藝術》中,對文本的駕馭和分析能力,得到了極好的發揮。通過詳盡的闡釋和細致的分析,使讀者了解作家的寫作特色及修辭技巧。
縱觀全書,可以看出一些標題存在著彼此緊密的聯系,如:“開頭”、“書名”、“章節”、“敘事結構”、“結尾”;而另一些標題則聯系得不夠緊密或沒有聯系,如:“神秘”、“構想未來”、“電話”、“清單”。此外,讀者也可以發現,還有一些題目是可以寫成一篇學術論文的,例如:“象征”、“動機”、“視角”、“諷喻”、“互文性”等。然而,洛奇并沒有這樣做。既然這些文章是為了使讀者大眾能饒有興趣地進行閱讀,以“提高讀者對散文小說的理解和欣賞能力,向他們表明新的閱讀的可能”[1]11,自然就不用寫得像學術論文一樣深奧。但如同“要是沒有恰當的工具,就無法拆開發動機”[1]10一樣,洛奇在談到很多問題時,也會用到一些概念或術語,并追溯詞源或進行前后梳理,引入相關文學史知識,進而展開討論。
不可忽視的是,洛奇在論述某些問題時,會時而引述自己的作品片段或自身的寫作體驗,把批評理論與文學創作結合起來,說明寫作技巧該如何運用等問題。洛奇這樣做,理由很充分,因為他“一向將小說的本質視為一種修辭的藝術。即:在閱讀體驗中,小說家或短篇小說的作者勸慰我們去分享某一種世界觀。如果成功了,就使讀者沉醉在想象的現實之中。正如梵·高在他的油畫‘小說讀者’中讓人著迷那樣。甚至那些故意打破這一魅力的小說家,也會為了他們的藝術目的,而不得不首先運用它。”[1]10
一、洛奇的批評方法
自古以來,文學的藝術價值與魅力,就在于不斷地對作品進行重新解讀和評估,在這一過程中,會提高同時代人對自我的認知能力,也會滿足人類不斷變化的精神需求。早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就曾將悲劇藝術分為6個要素——形象、性格、情節、言詞、歌曲與思想來加以討論[2]。而自小說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以來,談論小說的藝術的著作相繼問世。E·M·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將小說從以下6個方面進行了細致分析:故事、人物、情節、幻想、預言和結構與模式[3]。此外,亨利·詹姆斯的《小說的藝術》、盧卡奇的《小說理論》、伊恩·瓦特的《小說的興起》、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的藝術》等,也都是小說詩學中的重要著作。
然而,集作家和批評家于一身的戴維·洛奇,在《小說的藝術》中向讀者展示了50個小說詩學的話題。洛奇不但引領讀者賞玩小說的藝術之美,向讀者展示了不同類型的小說,如“少年侃”、“書信體小說”、“意識流”、“實驗小說”、“喜劇小說”、“魔幻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非虛構小說”和“元小說”等。同時,洛奇還在分析文本時,談及了許多小說的寫作手法和技巧,如:“懸念”、“陌生化”、“止于表面”、“展示與講述”、“以不同的口吻講述”、“頓悟”、“巧合”、“諷喻”、“暗示”、“天氣”等等。
洛奇在所論述的每個話題的開端,首先援引一兩段英美作家的小說片段。在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我們所熟知的,如簡·奧斯丁的《愛瑪》、查爾斯·狄更斯的《荒涼山莊》、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知道什么》、弗吉尼亞·伍爾芙的《達洛維夫人》等;也有一些是我們完全陌生的作品,如保羅·奧斯特爾的《玻璃城》、R·吉卜林的《巴瑟斯特太太》、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的《告別柏林》、蕾奧諾拉·卡靈頓的《助聽器》等。洛奇借助這些作品文本來分析問題,循序漸進地展開討論。此外,洛奇有時故意避開偉大作家的經典之作,而是引述他的一部不知名的作品,來分析一個問題。比如,《苔絲》一直被國內學術界認為是哈代的經典之作,而洛奇偏偏援引哈代的另一部小說《一雙藍眼睛》作為討論“懸念”的文本,使讀者更加了解了這一寫作技巧對情節推動的重要意義。可以說,洛奇所舉例子如此恰到好處,讓人不得不折服。
洛奇援引作品范圍如此之廣,并沒有影響其作為一個批評家有序、深入的分析。以“概念小說”為例,首先,洛奇指出這種小說有時也被稱為“主題小說”,即有論點的小說。同時,洛奇給出了“概念小說”的定義:一般指敘事性不強的作品,小說中的人物反復商討哲學問題,而吃、喝、調情等則異常簡短。這個詞源自法國,而這類小說在歐洲大陸的發展比英國更興旺。洛奇指出,柏拉圖的《對話集》就是概念小說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在英國的歷史上,只有D·H·勞倫斯的《戀愛中的女人》接近“概念小說”,但這里的概念是非常個人的、怪異的,不同于歐洲大陸的思想。洛奇分析,這可能與英國自17世紀以來沒有經過任何形式的革命有關,產生不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馬斯·曼、羅伯特·穆齊爾、讓-保羅·薩特等那樣偉大的作家。接著,為了更加明確這一問題,洛奇指出任何小說都有概念,產生概念并用概念來討論。但“概念小說”是指作品的能量來源是概念,產生、形成和維持敘事動力,而不是感情、道德選擇、個人關系或人類命運的輾轉等因素[1]198。通過這樣的分析,洛奇使讀者明白了何為“概念小說”,也清楚了其前因后果。
洛奇既是他所援引的片段精辟的分析者,也在分析的同時,涉及和談論了很多寫作技巧。例如,互文性是一個很古老的寫作技巧,一個文本可以用多種方式來指涉另一個文本:戲仿、拼貼、呼應、引用典故、直接引語及結構平行。洛奇與許多文論家有相同的看法,認為互文性是文學的存在形式,所有的文本都是用另一些文本的素材編織而成,不管作者是否意識到這一點[1]98-99。讀過柯勒律治《古舟子詠》的人不難看出,約瑟夫·康拉德的《影線》與其有互文性;讀過《奧德賽》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便取材于此。而洛奇的小說《大英博物館的倒塌》的靈感則來自于《尤利西斯》,所有的行動都發生在一天之內。另一部小說《小世界》則取材于亞瑟王與他的圓桌騎士及他們尋找圣杯的故事,來突出小說中的學術界人物飛來飛去,在國際會議上職業和性愛的競爭。
在談到“視角”的時候,洛奇援引的例子是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知道什么》,來說明一部小說在同一問題上可以提供不同的視角,但一次只能采用一種視角。即使采用“全知”的敘述方法,從上帝的角度來報道一切行為,也只能限于一到兩種可能的視角[1]26。限制敘述的視角,只用一個人稱來敘述,可以獲得一種強烈和直接的效果,這點同亨利·詹姆斯的看法不謀而合。洛奇指出,一個懶惰的或者是沒有經驗的作家的最常見的一個標志,就是在把握視角時的不一致性。雖然在視角的轉換上沒有規定,但洛奇認為,我們要根據一些審美計劃和原則,如果不這樣做,讀者投入故事的程度和對文本意義的“解讀”,將都會被打亂[1]28。
雖為學院派學者,但洛奇能深入淺出,不茍于深奧的學術術語,以實例為基礎進行細致有序的分析,使得洛奇的批評文章既能迎合大眾讀者的閱讀趣味,又不缺乏深度。雖然必須承認,不論什么作品,一旦產生,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都會超出作家原初的意識,正如“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每一篇文本放在自己的面前,讀者都會有不同的反應和思考。作品意義的構建,有賴于讀者對作家的理解和自己的意識如何投射到作品上,進而獲得一種審美活動,獲得一種享受或快感。然而,戴維·洛奇帶領我們進入的是更專業、更有序、更深刻的一種思考。我們不能滿足于淺嘗輒止,只停留在故事的情節。我們要變被動的讀者為主動的參與者,與洛奇一起,對作品進行分析、理解和批評,這樣才能深刻理解作品想要表達的意義,避免浮泛地閱讀作品。難怪戴維·洛奇有如此的美譽,《小說的藝術》被稱為是“自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以來,最出色的面向大眾的小說研究作品。”[4]6
二、“隱含的”文學史
韋勒克曾經說過,文學史對于文學批評是極其重要的,“因為文學批評必須超越單憑個人好惡的最主觀的判斷。一個批評家倘若滿足于無視所有文學史上的關系,便會常常發生判斷的錯誤。他將會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創新的,哪些是師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歷史上的情況,他將常常誤解許多具體的文學藝術作品。”如果一個批評家缺乏或全然不懂文學史,那很可能馬馬虎虎、胡亂推測、或沾沾自喜于描述自己“在名著中的歷險記”了[5]。與許多其他文學理論著作相比,洛奇并沒有直接強調作為一個讀者或作家,應該掌握更多的文學史知識。然而,我們閱讀《小說的藝術》時會發現,在這50個章節之內,很多都涉及了相關的文學史知識。洛奇對西方文學史精準的把握,使讀者在閱讀《小說的藝術》時,對該論題的發展脈絡有了詳盡的了解。此外,在談及一些術語時,洛奇往往會追根溯源,將其演變發展的歷程,向讀者交代。
例如:在談及“超現實主義”時,洛奇首先進行了追溯,指出超現實主義在視覺藝術中比在文學中更加被人知曉,也更容易定義。達利、杜尚、馬格利特和恩斯特都是現代藝術史上的杰出人物。接下來,為了進一步澄清什么是“超現實主義”,洛奇用了對比的方法,對“超現實主義”和“魔幻現實主義”進行了區分。首先,它們有明顯的親緣性。然而,在魔幻現實主義中,在現實和幻想之間總是有一種緊密的聯系:不可能的事件是對現代歷史的極其自相矛盾的一種隱喻。而在“超現實主義”中,隱喻變成了真實的,擦去了這個世界的理性和常識。超現實主義者喜歡把他們的藝術用夢來類比。舉例來說,第一部在英語語言中的超現實主義小說是一個夢境中的故事:《愛麗斯漫游仙境》。在這樣的敘述之后,洛奇再來詳細分析其所舉的例子——莉歐諾拉·卡林頓的《助聽器》,來說明這個老人的種種幻覺與現實相混淆的情景,也許就十分容易理解,并使人感到極為輕松愉快了。通過這樣的寫作手法,洛奇不但使讀者了解了“超現實主義”這一寫作技巧,更讓讀者了解其淵源,并明晰了“超現實主義”和“魔幻現實主義”的差異,使所討論問題更加清楚明白。這一切,都離不開洛奇扎實的文學史功底。
在談到標題時,洛奇認為標題是文本的一部分,因此對讀者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和影響。最早期的英語小說的標題都是中心人物的名字,如《摩爾·弗蘭德斯》、《湯姆·瓊斯》、《克拉麗莎》等,而有時小說會以自傳的形式出現,來掩蓋自己的虛構身份。之后,小說家意識到標題也能暗示主題,如《理智與情感》;標題也可以暗示神秘,如《白衣女人》;有時標題也能提供一種場景和氛圍,如《呼嘯山莊》。到了19世紀的某個時期,小說家開始引經據典,這一傳統一直沿襲到20世紀,如《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一捧塵土》、《喪鐘為誰而鳴》等。最偉大的現代主義小說家開始用象征和隱喻為標題,如《黑暗的中心》、《尤利西斯》、《虹》等。而近期的小說家更喜歡用怪誕的、謎似的、不合拍的標題,如《麥田里的守望者》、《獻給因彩虹足以慰藉而意圖自殺的非白人女孩》。除了上述翔實的介紹,使讀者對這一論題了解極為透徹之外,洛奇強調不能忽視一個問題:小說既是一件藝術品,更是一件商品,商業的考慮會影響標題,或者使標題改變。例如,福特·馬道克斯·福特的《好兵》原初的題目是《最悲慘的故事》,但由于它是在大戰期間產生的,出版商勸作者把題目改成一個不太傷感并愛國的標題。
在《小說的藝術》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章節”、“時間跨度”、“結尾”、“非虛構小說”、“暗示”、“異域風情”、“頓悟”、“諷喻”、“歷史感”、“實驗小說”、“華麗散文體”、“天氣”等等問題的論述,都涉及了相關的文學史知識。正如洛奇所述,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文學史一直在尋找他們共同的傳統、策略、和技巧,因而把這些文學作品分成“時期”、“流派”或“運動”用以來概括或對文學作品進行分類[6]。只有懂得了什么是傳統,才能明白如何應對非傳統。洛奇的批評實踐告訴我們,只有深入了解文學史,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運用寫作技巧,創造出更加優秀的作品。從《小說的藝術》中,我們看到洛奇對西方文學史及其發展脈絡掌握得如此嫻熟,不僅為文學批評開辟了寬闊的道路,更為他的小說創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三、批評理論與文學創作
在西方文學批評史上,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一個人既可以是創作中的能手,同時也可以是一位極有影響力的批評家。例如,華茲華斯、托爾斯泰、波德萊爾、歌德、愛倫·坡等,不僅其詩歌或小說讓人奉為經典,他們的批評理論在西方文學批評史上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任何研究西方文學批評史的人,都不能隨意繞過他們。在當代英國學者中,戴維·洛奇的學術地位,十分顯赫。隨著2011年《有才能的人》的出版,洛奇所創作的長篇小說已達15部之多,其中以校園三部曲《換位》、《小世界》和《好工作》而享譽全球。而這些作品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并非光靠曲折的情節或細致的人物刻畫,洛奇的批評實踐,為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良好的構思,促使這些小說極具感染力。
在《小說的藝術》中,洛奇多次談到了傳統的敘事方式對自己創作的影響。比如,在《你能走多遠》這部小說中,洛奇用了概括敘述的方法。因為概括的方法似乎十分適合現代人的節奏,及追求簡潔和冷嘲熱諷的口味。洛奇指出,概括的方法尤其對處理大量的人物和一個很長的故事十分有效,避免了傳統古典小說中的慢節奏和細節過多的弊端。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一定要避免在概述時的詞匯和句法的單一化。舉例來說,費·威爾頓的很多小說,雖然大量地運用了概述,但其敘述的節奏和活潑的文筆反倒使作品十分著名[1]126。
談到“巧合”時,洛奇認為它的使用頻率因小說類型和時期不同而變化。同時,它也和作家本人認為適合與否有關。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洛奇援引了自己的寫作經驗,來說明這一問題。與《好工作》相比,洛奇感到《小世界》中運用巧合更加愜意,不受抑制,因為它的題目就表明了這一現象。洛奇指出,《小世界》是一部喜劇小說,而喜劇的讀者由于喜劇所產生出來的愉悅,會接受一種看似不太可能的巧合[1]151-152。《小世界》刻意模仿中世紀騎士傳奇里交錯的情節,為了達到喜劇效果,故事中運用了多重巧合。洛奇承認,雖然在寫作的過程中某種巧合有時似乎不太可能發生,但小說發展到了這一階段,越是巧合,越會使人感到愉悅,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違反常規。此外,洛奇指出,有時巧合也受情節需要的制約。比如,在《好工作》中,也有喜劇和互文性元素,但它是一部更嚴肅、現實的小說。洛奇意識到在這部小說中,必須謹慎運用巧合。戴維·洛奇并沒有肯定自己處理巧合的方法是否成功,但他的用意,就是向讀者展示作者是如何處理巧合,并如何打消人們的質疑的。
洛奇在“結尾”中,以《換位》為例,指出小說的結尾要考慮多重因素,如視角、懸念、驚訝詫異、互文性、止于表面、書名題目和章節、元小說等。首先,因為《換位》這部小說高度對稱,甚至讀者可以預料到情節,所以在文本的層面上,洛奇提供了某種變化和意外,在寫作時,洛奇刻意采用了不同的風格和形式。其次,在寫作的過程中,洛奇已經意識到了結尾的處理很棘手。因為那不僅是“換妻”的問題,在這背后是文化的認同與背離等社會問題,洛奇不想做出選擇,但他又不喜歡后現代的沒有結尾或不確定的收場。最后,經過斟酌,洛奇把最后一章寫成了電影腳本,解決了所有的問題。洛奇既不用在這“四人方塊舞”中做出評判,也可以以“非正常”小說語體創造敘述高潮的構想。并且,洛奇為自己這樣做找了一個更加合適的借口,那就是他在構思下一部小說《小世界》時,可以繼續利用這些主人公,自由地編寫他們的生活故事。洛奇最后指出,一部小說的各個細部考量都不是憑空、單獨地決定出來的;小說創作的任何一個方面的考慮都會影響到其他方面,也受到它們的影響[1]229-230。單純片面地只考慮一種因素,對作品的創作是不利的。
在寫“章節”時,洛奇回顧了自己的創作過程。他意外地發現,在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自己的創作過程竟然有一些自己都未察覺到的明顯變化。如果不是因為在《小說的藝術》中討論“章節”,洛奇自己都忽略了這一點。
由此看來,由于批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使洛奇的文學創作在不經意間改變著。洛奇自己曾說:“因為我本人是個學院派批評家,……(所以)我是個自覺意識很強的小說家。在我創作時,我對自己文本的要求,與我在批評其他作家的文本時所提的要求完全相同。小說的每一部分,每一個事件、人物,甚至每個單詞,都必須服從整個文本的同一構思。”[4]2
四、結 語
洛奇曾經這樣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是一種游戲,一種至少需要兩個人玩的游戲:一位讀者,一位作者。作者企圖在文本本身之外控制和指導讀者的反應,就像一個玩牌者不時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繞過桌子去看對家的牌,指點他該出哪一張。但愿我尚未因這樣的錯誤而掃了讀者的興。”[4]3-4也許,正如洛奇所說,散文小說的黃金法則就是沒有規則——除非每個作家為自己規定。重復和簡潔通常是海明威的藝術目的;變化和裝飾是納博科夫的藝術宗旨(尤其在《洛麗塔》中)[1]94。如果每個讀者或有志成為作家的人能從洛奇的解讀和分析中獲得智思,那將是最大的收獲。
戴維·洛奇的一生都在從事文學創作和批評。對于文學創作而言,很少有作家能夠或愿意用平白的語言來表述自己的寫作過程,當他們談論自己的作品時,往往非常迷茫;而另一些作家則不愿意透漏自己的寫作秘密,防御心理非常強。洛奇輕松、實際地描述自己的寫作經歷,并結合理論來談寫作實踐是本書最大的一個亮點。對于文學批評而言,洛奇善于發現藝術的長處。加之擁有深邃的文學史知識,透過精湛的解讀和批評分析,戴維·洛奇使文學作品的生命遠遠超越了本書所舉的實例,它擁有了另一種生生不息的生存空間。
[1] Lodge,D.TheArtofFiction[M].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92.
[2] 亞里斯多德.詩學[M].羅念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21.
[3] E·M·福斯特.小說面面觀[M].馮濤,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1.
[4] 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M].王峻巖,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5] 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M].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39.
[6] Lodge,D.AfterBaktin[M].London:Routledge,1990: 25.
[責任編輯:張樹武]
On David Lodge’sTheArtofFictionCritical Theory
WANG Cui1,2
(1.College of Literature,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Beihua University,Jilin 132013,China)
From 1991—1992,David Lodge wrote 50 articles about prose fiction for a weekly column ofTheIndependentonSunday,which were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in 1992,entitledTheArtofFic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TheArtofFictionand learn the critical method adopted by David Lodge when he analyses the fictional texts,and simultaneously,discusses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on literary crea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creative practice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distinct fiction poetics.
David Lodge;TheArtofFiction;Critical Theory;Critical Method;History of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Creation
2014-03-22
吉林省教育廳“十二五”社會科學研究立項(吉教科文合字[2014]第 168 號)。
王翠(1978-),女,吉林農安人,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北華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I106
A
1001-6201(2014)05-01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