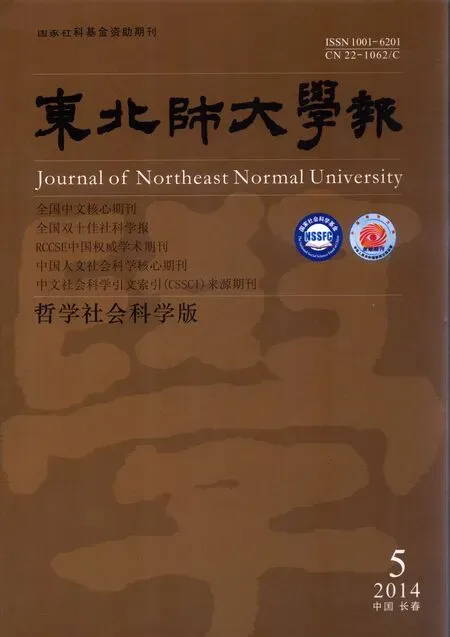武則天形象的嬗變及其性別文化意蘊(yùn)
韓 林
(大連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部,遼寧 大連 116622)
武則天形象的嬗變及其性別文化意蘊(yùn)
韓 林
(大連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部,遼寧 大連 116622)
從武則天故事的發(fā)展演變軌跡,可以看出敘事者的立場(chǎng)經(jīng)歷了三個(gè)階段:唐、五代基本符合事實(shí);宋、元時(shí)加入主觀(guān)因素;明、清時(shí)則被妖魔化。故事的重點(diǎn)從一個(gè)政治問(wèn)題,轉(zhuǎn)移到民族國(guó)家問(wèn)題,最后演變成性別問(wèn)題。明清小說(shuō)對(duì)武則天進(jìn)行暴力改造,包括執(zhí)政能力平庸化,情感生活艷情化,子孫后代妖怪化等。這種變化是封建社會(huì)性別哲學(xué)泛化到政治學(xué)領(lǐng)域的結(jié)果;是男性“個(gè)體自戀”上升到“群體自戀”的產(chǎn)物;男權(quán)文化體系完全剝奪了作品中女性的話(huà)語(yǔ)權(quán)。
性別;武則天;妖魔化;
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M.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 Gubar)合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婦女作家與19世紀(jì)文學(xué)想象》一書(shū)是20世紀(jì)女性主義文論史上的代表作之一。在這本書(shū)中,她們提出女性作家由于“作者身份焦慮”,創(chuàng)作出兩種完全相反的女性形象,一種是集眾美于一身的“天使”,她們漂亮、溫柔、無(wú)私,善良,如圣母、簡(jiǎn)·愛(ài)等;另一種則是集萬(wàn)惡于一身的“魔鬼”,她們丑陋、粗暴、自私、兇狠,如瘋女人、女巫等。前者是女性遵守和屈從于父權(quán)家長(zhǎng)制的結(jié)果,后者則是女性潛意識(shí)中對(duì)父權(quán)家長(zhǎng)制叛逆心理投射的結(jié)果。這個(gè)觀(guān)點(diǎn)是針對(duì)女作家而言的,但“天使”與“魔鬼”兩種形象并不只是女作家的專(zhuān)利,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同樣也存在,只不過(guò)別有深意。在男性掌握話(huà)語(yǔ)權(quán)的社會(huì),文學(xué)是他們教育女性的方式之一,為了維護(hù)男性的統(tǒng)治地位,為了防止女性自我意識(shí)的覺(jué)醒,女性便被定位成兩種極端的形象——“天使”與“魔鬼”。一方面他們要塑造一種盡善盡美的“天使”形象,作為正面典型,為廣大女性樹(shù)立光輝的榜樣;另一方面,要塑造出惡貫滿(mǎn)盈的“魔鬼”形象,作為反面典型,讓所有的女性都知道“越軌”的下場(chǎng)。由于武則天以女性的身份做皇帝,將夫家的天下改朝換代,觸犯了男權(quán)文化體系,因而被人為地塑造成“魔鬼”。
一、武則天形象從歷史到文學(xué)的移位
總體看來(lái),武則天故事經(jīng)歷了從歷史到文學(xué)的移位過(guò)程。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武則天的形象呈現(xiàn)出每況愈下的狀態(tài)。唐代的文本承認(rèn)武則天執(zhí)政,相對(duì)客觀(guān)地展現(xiàn)了武則天的功過(guò);宋元時(shí)期,文人士大夫的主觀(guān)意識(shí)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人們借武則天表達(dá)自己的思想;明清時(shí)期,人們惡意歪曲武則天形象,把她妖魔化。武則天故事總體上可以分為三個(gè)發(fā)展階段:發(fā)軔期、沿承期和繁榮期。
唐、五代是武則天故事的發(fā)軔期,人們對(duì)武則天采取相對(duì)客觀(guān)的態(tài)度。劉餗的《隋唐嘉話(huà)》、劉肅的《大唐新語(yǔ)》、張鷟的《朝野僉載》、段成式的《酉陽(yáng)雜俎》、牛肅的《紀(jì)聞》等大多是擷取當(dāng)時(shí)的朝野傳聞,對(duì)武則天的描寫(xiě)多屬于片段式的呈現(xiàn),并沒(méi)有形成完整的故事。部分作品如陳翰《異聞集》中的《韋安道》,鐘輅《感定錄》中的《袁天綱》、《貞觀(guān)秘記》等,逐漸形成有情節(jié)的小故事。牛肅《紀(jì)聞·裴伷先》、薛用弱《集異記·集翠裘》兩則故事比較有代表性,引起了后人的關(guān)注,出現(xiàn)了一系列相關(guān)作品,貫穿了整個(gè)武則天故事系統(tǒng)。這一時(shí)期,關(guān)于武則天的記載比較分散,多是片斷性的、獨(dú)立的小故事,內(nèi)容涉及各個(gè)方面,為后世文學(xué)作品提供了敘述的藍(lán)本和撰寫(xiě)起點(diǎn):這一時(shí)期的文獻(xiàn)總體上有以下幾個(gè)特點(diǎn):在體裁上,主要集中于史學(xué)類(lèi)著作,包括正史、野史及筆記雜記;在篇幅上,除了正史中的傳記類(lèi)作品比較長(zhǎng)外,野史筆記中多是只言片語(yǔ),或是簡(jiǎn)短的小故事,長(zhǎng)篇作品比較少見(jiàn);在內(nèi)容上,大體是關(guān)于武則天的出身經(jīng)歷、言論行為、施政措施、朝野佚事的記載,接近武則天的真實(shí)面貌;在藝術(shù)手法上,這一時(shí)期的作品大多數(shù)采取客觀(guān)敘述的筆法,即使小說(shuō)也是實(shí)錄風(fēng)格,比較客觀(guān)。
宋、元是武則天故事的沿承期,也是無(wú)顧忌地評(píng)價(jià)武則天的開(kāi)始,這一時(shí)期的作品帶有明顯的主觀(guān)因素,但并沒(méi)有完全背離史實(shí)。正史如《新唐書(shū)》、《資治通鑒》等書(shū),受以歐陽(yáng)修、司馬光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觀(guān)念的影響,把武則天放在正統(tǒng)的框架內(nèi)來(lái)評(píng)價(jià),難免有失偏頗,這種官方言論很容易左右人們的思想。金、元時(shí)期的戲曲豐富了武則天故事的體裁,使人物形象的展現(xiàn)形式更加多樣化。與前代相比,這一時(shí)期的作品有以下特點(diǎn):首先,受史學(xué)家正統(tǒng)觀(guān)念的影響,武則天故事介于史學(xué)與文學(xué)之間,界限比較模糊。唐、五代時(shí),武則天故事大部分都是由史學(xué)類(lèi)作品記錄下來(lái)的,很難區(qū)分哪些是歷史,哪些是文學(xué)。宋代掀起編纂唐史的熱潮,大量史書(shū)出現(xiàn),如《新唐書(shū)》、《資治通鑒》、《唐會(huì)要》等,這些編撰者的正統(tǒng)意識(shí),對(duì)武則天故事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其次,出現(xiàn)了大量類(lèi)書(shū),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cè)府元龜》、《彤管懿范》、《重廣會(huì)史》等。雖然類(lèi)書(shū)的內(nèi)容是分類(lèi)收集編撰前代的故事,但卻無(wú)法抹煞其時(shí)代色彩。再次,這一時(shí)期是新體裁出現(xiàn)的高峰期。散曲、金院本、元雜劇等都是全新的,這是元代出現(xiàn)的一個(gè)新領(lǐng)域。但由于通俗文學(xué)作品難登大雅之堂,許多作品已經(jīng)散佚,難以窺其全貌。這是一個(gè)整合前代素材,生成新故事的時(shí)期。
宋代是修撰唐史的高峰期,集中于正史的重寫(xiě)。除了野史筆記外,文人的別集中也常能看到對(duì)武則天的評(píng)論,如由宋入元的鄭思肖在其文中說(shuō)“呂后稱(chēng)制八年,武后稱(chēng)制廿一年,牝雞司晨,俱惡逆事,書(shū)法同前;但仍書(shū)曰呂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當(dāng)以后書(shū)之”[1]。他以正統(tǒng)觀(guān)念來(lái)評(píng)價(jià)武則天,把她與呂后并列,甚至認(rèn)為她連呂后都不如。史書(shū)中用“武后”稱(chēng)之是高抬了她。宋詞和元代的散曲中也出現(xiàn)了武則天的身影,如薛昂夫的[中呂·朝天曲]中,“則天,改元,雌鳥(niǎo)長(zhǎng)朝殿。昌宗出入二十年,懷義陰功健。四海淫風(fēng),滿(mǎn)朝窯變,《關(guān)睢》無(wú)此篇。弄權(quán),妒賢,卻聽(tīng)梁公勸。”對(duì)武則天的私生活大加鞭笞。此外,還擴(kuò)展到了類(lèi)書(shū)、小說(shuō)和戲曲中。篇幅上則從短篇的記錄,發(fā)展成為長(zhǎng)篇故事。如關(guān)于武則天與王皇后和蕭淑妃的故事,在唐代的記錄僅百余字,而在元代則出現(xiàn)了戲劇,如《武則天肉醉王皇后》(劇本)、《武則天》(劇本佚)等,都是長(zhǎng)篇作品。內(nèi)容上與唐代相比更加豐富,將原來(lái)的零星記錄整合到一起,按照因果關(guān)系加以排列,再完善細(xì)節(jié),使分散的史料變成連綴的故事。從藝術(shù)手法上看,增添了部分史籍中原本沒(méi)有的內(nèi)容,運(yùn)用文學(xué)手段稍加修飾,但總體上沒(méi)有偏離史書(shū)的記載。
明、清是武則天故事的繁榮期,人們對(duì)武則天進(jìn)行暴力改造,很多內(nèi)容完全是杜撰出來(lái)的。這一時(shí)期武則天的形象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此前的武則天故事是基于史實(shí)之上的描繪,但明代受新思潮及商品經(jīng)濟(jì)的影響,顛覆了傳統(tǒng)的武則天形象,小說(shuō)和戲曲中出現(xiàn)了刻意貶損,惡意歪曲武則天的傾向。體裁上從以前偏重于歷史記載轉(zhuǎn)向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面來(lái),這一時(shí)期的武則天已經(jīng)退出了史書(shū)的舞臺(tái),在文人士大夫的政論、文集中頻頻出現(xiàn)。明代時(shí),描寫(xiě)武則天的作品可以說(shuō)是眾體兼?zhèn)洌宕谶@一基礎(chǔ)之上把各方面又向前推進(jìn)了一步,出現(xiàn)了新體裁如彈詞等,這一時(shí)期的武則天故事主要集中于小說(shuō)和戲曲。篇幅上則出現(xiàn)了以武則天為主人公的中篇和長(zhǎng)篇小說(shuō),此前的小說(shuō)多是文言,明清時(shí)期,白話(huà)小說(shuō)占主體。戲曲也有數(shù)部,長(zhǎng)篇作品大量出現(xiàn)。明清時(shí)期不僅繼承之前的故事形成精彩的單篇小說(shuō),還出現(xiàn)了系列小說(shuō),與前代的作品一起構(gòu)成了“說(shuō)唐系列”與“公案系列”等。內(nèi)容上不再局限于史實(shí),加入了很多杜撰的內(nèi)容,尤其是歪曲、詆毀武則天的內(nèi)容。這一時(shí)期武則天出現(xiàn)了艷情化的傾向。藝術(shù)手法上則與以前的“實(shí)錄”風(fēng)格不同,虛構(gòu)的手段大量運(yùn)用,想象、夸張等許多文學(xué)手法都加入進(jìn)來(lái)。
唐朝時(shí),武則天故事只是一個(gè)政治問(wèn)題;宋元時(shí)期,武則天故事轉(zhuǎn)變?yōu)槊褡寮皣?guó)家問(wèn)題;明清時(shí)期武則天故事的重點(diǎn)轉(zhuǎn)變成性別問(wèn)題。從武則天故事的演變軌跡可以看出作品的敘事立場(chǎng)一直在發(fā)生變化:唐五代時(shí)期基本符合客觀(guān)歷史事實(shí),宋元時(shí)期人們按照自己的需要加入了主觀(guān)見(jiàn)解,明清時(shí)期則對(duì)武則天進(jìn)行暴力改造,惡意丑化武則天。唐代時(shí),統(tǒng)治者可以說(shuō)都是武則天的后代,武則天是唐代統(tǒng)治集團(tuán)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維護(hù)武則天的形象,就是維護(hù)統(tǒng)治者自身的形象。宋元時(shí)期,民族矛盾突出,或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或處于異族統(tǒng)治之下,故民族矛盾、國(guó)家問(wèn)題成為人們生活的重心,人們把反對(duì)武則天執(zhí)政,擴(kuò)大到反對(duì)異族統(tǒng)治,武則天故事自然而然地表現(xiàn)出人們的情感取向。明清時(shí)期,理學(xué)興盛,禮教的禁錮使人們對(duì)女性的言語(yǔ)行為提出嚴(yán)格的要求,武則天成為文人士大夫發(fā)揮說(shuō)教特長(zhǎng)的反面教材。
二、明清小說(shuō)對(duì)武則天的暴力改造
明清時(shí)期,封建禮教對(duì)女性限制較多,武則天的所作所為使她成為一個(gè)“異類(lèi)”。官方文化對(duì)武則天進(jìn)行暴力改造,把武則天塑造成一個(gè)“靶子”,成為眾矢之的。明清時(shí)期的文本專(zhuān)門(mén)樹(shù)立了一系列的忠臣形象,以便弱化武則天的執(zhí)政能力,同時(shí)在生活上把她刻畫(huà)成一個(gè)不知廉恥的蕩婦。武則天政治行為中閃光的一面被男權(quán)文化排擠出去,而陰暗面則被無(wú)限放大。
首先,執(zhí)政能力平庸化。歷史上的武則天具有一定的執(zhí)政能力,從歷史到文學(xué)的移位過(guò)程中,武則天的執(zhí)政能力越來(lái)越差。唐宋時(shí)史書(shū)中所記載的武則天的政績(jī),被弱化或抹殺,基本上被排斥出文學(xué)領(lǐng)域。史書(shū)中所記載的與之相關(guān)的一些大臣的事跡,被后人挖掘出來(lái),不斷演繹夸大,其中,有四個(gè)人物的故事形成系列作品:一是駱賓王,相關(guān)作品有唐代張鷟《朝野僉載》、劉肅《大唐新語(yǔ)》、段成式《酉陽(yáng)雜俎》、孟棨等《本事詩(shī)》、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清代古吳墨浪子《西湖佳話(huà)》、李汝珍《鏡花緣》、佚名《綠牡丹》等;二是安金藏,相關(guān)作品有唐代劉肅《大唐新語(yǔ)》、李冗《獨(dú)異志》、明姚子翼《上林春》、鐘惺《混唐后傳》、中都逸叟《異說(shuō)征西演義全傳》、褚人耯《隋唐演義》、如蓮居士《反唐演義》、佚名《武則天四大奇案》等;三是裴伷先,相關(guān)作品有唐代牛肅《紀(jì)聞》、明代王翃的傳奇《詞苑春秋》(又名《留生氣》,劇本已佚)、許三階《節(jié)俠記》、許自昌據(jù)許三階作品改訂的《節(jié)俠記》;四是狄仁杰,相關(guān)作品有唐代劉肅的《大唐新語(yǔ)》、戴孚《廣異記》、薛用弱《集異記》、佚名《梁公九諫》、祝穆的類(lèi)書(shū)《事文類(lèi)聚》、金元時(shí)期佚名的傳奇《狄梁公》(劇本佚)、關(guān)漢卿雜劇《風(fēng)雪狄梁公》(劇本佚)、于伯淵雜劇《狄梁公智斬武三思》(劇本佚)、佚名雜劇《張昌宗雙陸博貂裘》(劇本佚)、明代李贄的《藏書(shū)》、馮夢(mèng)龍的《情史》、王士貞的《艷異編》、程文修的《望云記》、金懷玉的《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記》、清代余懷的傳奇《集翠裘》、裘璉的雜劇《集翠裘》等。這四個(gè)人物形象在后世被無(wú)限拔高,形成一個(gè)忠臣系列群像,與武則天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文學(xué)家通過(guò)塑造這些人物,來(lái)反襯武則天,其潛臺(tái)詞是武則天當(dāng)政時(shí)之所以沒(méi)有造成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慘狀,并不是因?yàn)樗齻€(gè)人有能力,而是有這些股肱之臣做后盾。“男性歷史學(xué)家和男性政治學(xué)研究者,極力將女性排斥在政治史和政治學(xué)之外,可以理解為兩個(gè)原因:一方面,男性學(xué)者將男性經(jīng)驗(yàn)視為唯一標(biāo)準(zhǔn)和普遍經(jīng)驗(yàn),難免會(huì)以偏概全,女性經(jīng)驗(yàn)和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被忽略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男性學(xué)者或多或少對(duì)女性介入政治領(lǐng)域的現(xiàn)象產(chǎn)生了恐懼,似乎感覺(jué)到了男性群體這一傳統(tǒng)文化賦予的權(quán)利被女性蠶食著,似乎覺(jué)得如果政治權(quán)力中心的性別秩序被打亂,將會(huì)危及整個(gè)政治權(quán)力系統(tǒng)的安全。所以,他們對(duì)女性參與公共政治領(lǐng)域是如臨大敵,并且選擇在政治史和政治學(xué)文本中遺忘女性的存在,即使有些婦女被提及,也往往是作為一個(gè)‘?huà)D女干政’的反面教材。”[2]
在“說(shuō)唐”系列小說(shuō)中,武則天成為一個(gè)毫無(wú)政治才能,禍國(guó)殃民的典型的“禍水”形象。羅貫中的《隋唐兩朝志傳》、鐘惺的《混唐后傳》、中都逸叟的《異說(shuō)征西演義全傳》(六卷四十回)及《征西說(shuō)唐三傳》(十卷八十八回)、褚人耯的《隋唐演義》、如蓮居士的《反唐演義》等都有所涉及。唐太宗在世時(shí),她是一個(gè)狐媚成性的人,千方百計(jì)勾引唐太宗,并與太子李治私相授受。太宗死后,武則天抓住唐高宗寺廟進(jìn)香的機(jī)會(huì)迷惑君王,終于再度入宮。高宗在位時(shí),武則天背著高宗與一些面首及大臣私通。為了面首,在高宗面前屢進(jìn)讒言,殘害功臣。薛氏一門(mén)三百余口被滿(mǎn)門(mén)抄斬,引出薛剛?cè)馈拌F丘墳”的故事。晚年當(dāng)上皇帝的武則天縱情享樂(lè)。這個(gè)文學(xué)形象生動(dòng)地演繹了駱賓王在《代李敬業(yè)討武氏檄》中的描述。“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shí)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jié),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后房之嬖。入門(mén)見(jiàn)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fù)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ài)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3]唐高宗時(shí)她妖言惑“君”,高宗死后她妖言惑“眾”。在用人上寵幸奸佞、任用酷吏;在私生活上,大興土木,勞民傷財(cái);寵幸面首甚于忠臣良將,以致冤殺忠臣,血流成河。文學(xué)領(lǐng)域的武則天毫無(wú)政績(jī)可言。
其次,情感生活艷情化。明清時(shí)期出現(xiàn)了一大批關(guān)于武則天的艷情小說(shuō),如徐昌齡《如意君傳》、餐花主人《濃情快史》、西泠狂者《載花船》、袁枚《控鶴監(jiān)秘記二則》、不奇生《武則天外史》、佚名《唐宮春武則天》等。這些艷情小說(shuō)不僅描寫(xiě)武則天與面首的故事,還把唐太宗和唐高宗拉到小說(shuō)中來(lái)。這兩位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形象完全被打破,二人的語(yǔ)言行為與面首的界限并不是很分明。“明代艷情小說(shuō)的目的是摧毀武則天的正面形象,所以她所有的陰暗面都被挖掘出來(lái),尤其是與男寵生活。唐太宗也被拉入了男寵的行列,成為寫(xiě)作對(duì)象。”[4]這些作品中的武則天僅采用武則天這個(gè)人物的名字及少量歷史,大部分內(nèi)容都是杜撰出來(lái)的,武則天只是一個(gè)被物化了的女性符號(hào)。
在傳統(tǒng)文化中,性對(duì)男女有著截然相反的意義。男人與性聯(lián)系在一起,表現(xiàn)的是男人的魅力和氣概。這是彰顯自我,肯定自我的方式之一。當(dāng)年邁回首時(shí)可以說(shuō)是年少輕狂,后來(lái)浪子回頭,折節(jié)向賢。對(duì)男性的道德不僅沒(méi)有影響,有時(shí)還會(huì)成為男性自夸的資本。而女性如果與性聯(lián)系在一起,就變得萬(wàn)劫不復(fù),臭名昭著。所以打擊女性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她與性聯(lián)系在一起。男性在政治事業(yè)上的失敗常常會(huì)在感情上尋求發(fā)泄。凱特·米利特認(rèn)為“這不過(guò)是貪欲沖動(dòng)由一個(gè)對(duì)象向另一個(gè)對(duì)象的轉(zhuǎn)移。通過(guò)將女人視為商品,他也就有機(jī)會(huì)體會(huì)‘成功’的歡樂(lè)。如果不能賺錢(qián),他至少可以賺女人——如果賺錢(qián)還需要用借來(lái)的錢(qián)做本錢(qián),那就做一筆大大的無(wú)本生意吧”[5]462。男性通過(guò)征服女人來(lái)維護(hù)自身的尊嚴(yán)。“出人頭地的其他途徑也都似乎全都向他關(guān)了門(mén),公共生活中的權(quán)力已經(jīng)成泡影,剩下的只有性的權(quán)利”[5]877。男性把政治上的失敗轉(zhuǎn)移到兩性生活中,用虛構(gòu)的情節(jié)臆想男性的勝利,尋求一種心理的平衡與解脫。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奧秘》一書(shū)中指出,女性的性行為與智商成反比,也就是說(shuō),性行為能力越高,智商越低。無(wú)限夸大武則天的情愛(ài)生活,客觀(guān)上產(chǎn)生了貶低她智商的效果,進(jìn)而達(dá)到貶低武則天的目的。
在歷史發(fā)展中,選擇此類(lèi)題材來(lái)丑化武則天,具有一定的社會(huì)文化原因。無(wú)論在哪個(gè)時(shí)代,這類(lèi)作品都是文化的一個(gè)組成部分。西方哲學(xué)常常把女性與身體聯(lián)系在一起,福柯認(rèn)為,身體是被權(quán)利、文化、經(jīng)濟(jì)等霸權(quán)所建構(gòu)的,沒(méi)有絕對(duì)自由的個(gè)人。“身體之所以可以強(qiáng)有力的反映文化,并成為社會(huì)控制的中心,是因?yàn)榭梢詿o(wú)窮無(wú)盡地被操縱——重新塑造、設(shè)計(jì)與改建,可以靈活的變遷,以符合時(shí)下的風(fēng)尚與文化價(jià)值。身體的靈活性使得它與社會(huì)文化的發(fā)展緊密相連,甚至走在前面。”[6]利用武則天的形象,重塑武則天的形象,可以“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這比直白的說(shuō)教更加深入人心。
再次,子孫后代妖怪化。武則天的女性身份使其在中國(guó)的帝王系列中空前絕后,帝王與女性的雙重身份使其處在歷史的風(fēng)口浪尖上。這個(gè)男權(quán)文化的侵略者、踐踏者,令所有的男性包括恪守封建道德的女性恨不得饑食其肉、渴飲其血。于是人們把所有的臟水都潑向了武則天。前人已經(jīng)從武則天的政治能力、情感生活的角度丑化武則天,這些方面難以找到新的增長(zhǎng)點(diǎn),于是人們便別出心裁地開(kāi)發(fā)出丑化武則天后代的新思路。歷史上所明確記載的武則天的后代包括四個(gè)兒子李弘、李賢、李顯、李旦以及女兒太平公主(關(guān)于是否有一女兒被武則天扼死以陷害王皇后,史學(xué)界仍有爭(zhēng)議)都是武則天與丈夫李治所生,這些人都是皇室血統(tǒng),不可以被玷污,故丑化武則天后代就只能丑化她的私生子,即與面首所生的孩子。于是,“驢(騾)頭太子”形象便誕生了,《征西說(shuō)唐三傳》和《反唐演義全傳》等說(shuō)唐系列小說(shuō)中都塑造了這個(gè)形象。小說(shuō)描述武則天與面首薛敖曹生了一個(gè)兒子,這個(gè)孩子生下來(lái)時(shí)就是一副怪模樣,雖然身體與常人無(wú)異,但卻長(zhǎng)著一個(gè)驢頭,有的小說(shuō)描述成騾頭。這副模樣嚇壞了武則天,令她羞愧萬(wàn)分,不敢讓他見(jiàn)人,便把他拋進(jìn)河里。這個(gè)孩子后來(lái)被一位久居深山的怪人救走并傳授武藝。后來(lái),武則天與薛家后代兩軍對(duì)峙時(shí),驢(騾)頭太子被師傅派下山幫助母親作戰(zhàn),在陣前被樊梨花劈成兩半兒。無(wú)論是“驢頭”還是“騾頭”,都是罵人話(huà)。在民間文化中,騾是一種雜交動(dòng)物,被視為“雜種”,而且很難有后代。無(wú)論這個(gè)孩子是驢頭還是騾頭,結(jié)論都一樣,即武則天與面首的后代——不是人,而且斷子絕孫。
三、男權(quán)話(huà)語(yǔ)下的武則天形象
武則天之所以成為官方文化著意“妖魔化”的對(duì)象,原因在于她以女性的身份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這是對(duì)男權(quán)文化體系的公然挑戰(zhàn),必然會(huì)受到扼殺。武則天形象的嬗變是菲勒斯中心主義在文本中的體現(xiàn),是典型的男權(quán)話(huà)語(yǔ)模式。
武則天形象的命運(yùn)是封建社會(huì)性別哲學(xué)泛化到政治學(xué)領(lǐng)域的結(jié)果。武則天最大的罪名是“牝雞司晨”、“女子干政”,這兩個(gè)詞都帶有貶義色彩。封建社會(huì)把女性的生活局限于家庭,與政治無(wú)緣,只有宮廷中的女性由于家國(guó)同構(gòu)的原因在特殊的歷史時(shí)期有機(jī)會(huì)參與政治。女子干政,一個(gè)“干”字表明這并非女子的本分,而是僭越之舉,否定了女性所有政治行為的合法性。宋代大儒程頤在解釋坤卦時(shí)說(shuō)“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yàn)槿犴槪驗(yàn)槲拿鳎驗(yàn)榘等酰辉诶ぃ瑒t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huà)z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7]。男尊女卑,這種定位是人類(lèi)社會(huì)后天形成的,是男權(quán)社會(huì)刻意塑造的。恰如西蒙·波伏瓦所說(shuō)“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變成的。”武則天“以女、以妻、以陰、以地的命定屬性,卻打破這樣的命定屬性,而敢于直取以男、以夫、以陽(yáng)、以天的命定屬性才能占據(jù)的地位”[8],這是對(duì)男權(quán)文化體系的公然挑釁,在男權(quán)社會(huì),武則天的行為必然會(huì)遭受打壓。唐代的《則天實(shí)錄》失傳也有這方面的原因。馬端臨在《文獻(xiàn)通考》中寫(xiě)到《唐則天實(shí)錄》時(shí)說(shuō):“陳氏曰:按《志》魏元忠等撰,劉知幾、吳兢刪正,今惟題兢撰。武氏罪大惡極,固不應(yīng)復(fù)入唐廟,而題主猶有圣帝之稱(chēng),至開(kāi)元中,禮官有言,乃去之。武氏不應(yīng)有實(shí)錄,猶正史之不應(yīng)有本紀(jì),皆沿襲《史》、《漢》呂后例,惟沈既濟(jì)之論為正,而范氏《唐鑒》用之”[9]。在這種情況下,《則天實(shí)錄》失傳是預(yù)料之中的事,女性參與政治從一個(gè)正常現(xiàn)象變成了一個(gè)反常現(xiàn)象,女性被人為地“踹”出了政治領(lǐng)域。武則天因?yàn)橐耘缘纳矸輩⑴c政治,同時(shí)又做出了改朝易姓的舉動(dòng),致使她的政治生涯貼上了徹頭徹尾被“反對(duì)”的標(biāo)簽。武則天的政治行為奠定了她在歷史坐標(biāo)中的位置,決定了她的文化形象。
武則天的文化命運(yùn)是“個(gè)體自戀”擴(kuò)大到“群體自戀”的結(jié)果,是菲勒斯中心主義的表現(xiàn)。弗洛伊德提出了“自戀”的概念,弗洛姆在《人之心》中專(zhuān)門(mén)討論了這個(gè)問(wèn)題。弗洛姆指出,個(gè)體自戀在某些情況下會(huì)轉(zhuǎn)變?yōu)槿后w自戀。男性作家在某些時(shí)候,會(huì)把個(gè)人的思想通過(guò)文學(xué)等途徑轉(zhuǎn)變成集體意識(shí)。“從任何想要維持生存的有組織的群體的立場(chǎng)來(lái)看,把其成員的自戀動(dòng)力變?yōu)槿后w自戀的動(dòng)力是非常主要的。群體的幸存在某種程度上要依賴(lài)于這樣的事實(shí),即其成員要認(rèn)識(shí)到群體生存的自戀,比他們個(gè)體的生存的自戀同等重要或還要重要得多,進(jìn)而認(rèn)為自己的群體與其他的群體比較,要更堅(jiān)信正義和更有優(yōu)越性。如果沒(méi)有對(duì)于群體的自戀的專(zhuān)注,那么推動(dòng)這個(gè)群體活動(dòng)所必須的動(dòng)力甚至為其做出巨大的犧牲,就要大大地減少”[10]。男性只有把個(gè)體自戀上升為群體自戀,通過(guò)群體自戀,堂而皇之地確定自我群體的優(yōu)越地位,才能名正言順地確立有利于自我群體的統(tǒng)治秩序。“群體自戀”是“個(gè)人自戀”的高級(jí)形式,反過(guò)來(lái)又在一個(gè)更高的層次上強(qiáng)化“個(gè)體自戀”。把男性個(gè)體自戀情緒上升到整個(gè)男性集體的自戀是男性在社會(huì)中的生存方式。這種自戀導(dǎo)致男性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性別優(yōu)越感,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不斷建構(gòu)、完善,把它發(fā)揮到極致。“女性一旦不僅在社會(huì)職能而且在男性想象中成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物品,便獲得了某種秩序內(nèi)的安頓,因?yàn)榻璐税言竞茈y把握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生理上的異己固定在一個(gè)可以把握的位置上,把未來(lái)也許是不可理喻的異性群體幻化為一種不必理喻的對(duì)象。父子們的欲望起始于對(duì)女性的恐懼的終結(jié)。繼而,能否消除這種恐懼,又成了欲望獲得象征滿(mǎn)足的標(biāo)準(zhǔn)”[11]。這種思維使武則天的故事中處處顯示出男權(quán)文化的烙印。
男權(quán)文化體系剝奪了小說(shuō)中的女性話(huà)語(yǔ)權(quán),武則天處于完全失語(yǔ)的狀態(tài)。話(huà)語(yǔ)權(quán)本來(lái)應(yīng)該是“一種人人都享有的為了充分表達(dá)思想,進(jìn)行言語(yǔ)交際而獲得和擁有說(shuō)話(huà)機(jī)會(huì)的權(quán)利”[12]。但整個(gè)武則天的故事史,我們聽(tīng)不到武則天的聲音,即使有,也早已在男權(quán)話(huà)語(yǔ)的口水之下銷(xiāo)聲匿跡。男權(quán)文化為女性設(shè)定了一系列規(guī)章制度,并且小心翼翼地戒備著,一旦有女人偏離了他們所設(shè)定好的軌道,就會(huì)利用話(huà)語(yǔ)霸權(quán)給她們扣上了“魔鬼”、“蕩婦”的帽子,把她們鞭撻掘尸,讓女人引以為戒。在小說(shuō)中則表現(xiàn)為把武則天完全物化。歷史上的武則天縱橫捭闔、多姿多彩。為女兒聰慧多才,嫵媚迷人;為妻妾溫柔多情,爭(zhēng)寵狠毒;為君主芟夷斬伐,安邦定國(guó)。武則天的故事應(yīng)該是豐富生動(dòng),趣味橫生的。但明清艷情小說(shuō)用大量篇幅鋪陳武則天與面首之間的生活。似乎在武則天的生命中,沒(méi)有其他事情可做。突出強(qiáng)化武則天主觀(guān)行為上的敗壞,孤立地描寫(xiě)性,剝離了附著于其上的情感道德因素。小說(shuō)家對(duì)她人生所承載的所有光輝都不屑一顧,甚至是故意隱瞞,刻意丑化,使她的行為顯得墮落不堪,塑造出了徹頭徹尾的蕩婦形象。所有這一切描寫(xiě)都成為作者具有虐她性質(zhì)的個(gè)人意志的伸張。這樣描繪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hù)幾千年來(lái)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級(jí)秩序,鞏固男性對(duì)女性的統(tǒng)治。
女性被物化成觀(guān)賞的對(duì)象。小說(shuō)中所展示的武則天是一個(gè)被看者、被凝視者,永遠(yuǎn)處在被人觀(guān)賞、被人評(píng)價(jià)的位置上。安·卡柏蘭認(rèn)為男性的凝視并不單是將女性性欲化或?qū)ο蠡八€可以被設(shè)計(jì)為消滅女性的威脅,其中一種方式便是將女性物化,……把作為對(duì)象的女性美化為觀(guān)賞的實(shí)物”[13]。男性不愿意被觀(guān)看、被窺視,但掌握話(huà)語(yǔ)權(quán)的他們卻可以根據(jù)男性的口味和欲望,把武則天塑造成一個(gè)被窺視的對(duì)象。武則天在男權(quán)語(yǔ)境的壓迫下失了聲,無(wú)力表達(dá)自己的思想。小說(shuō)把武則天與活生生的人對(duì)立起來(lái),物化成一個(gè)符號(hào),使武則天成了一個(gè)被沉默化了的“他者”,在話(huà)語(yǔ)場(chǎng)中成為一個(gè)無(wú)意義的空洞能指。“蕩婦強(qiáng)烈地刺激了男性的心理,又找不出合理的理由來(lái)解釋?zhuān)缓冒阉齻儚呐说男辛兄星宄踔翉娜祟?lèi)的行列中清除,于是采取了非人化、超常化、妖魔化的手段。這樣不僅可以使她們遠(yuǎn)離正常人群,還可以名正言順地詛咒、打壓甚至絞殺。”[14]
在男權(quán)文化體系中,如果不能成為“天使”,那么就必須成為“魔鬼”。武則天文化形象的塑造正是男權(quán)文化與正統(tǒng)意識(shí)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1] 鄭思肖.鄭思肖集[M].陳福康,校點(diǎn).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32.
[2] 蘇紅.多重視角下的社會(huì)性別觀(guān)[M].上海:上海大學(xué)出版社,2004:89-90.
[3] 駱賓王.代李敬業(yè)討武氏檄[A].董誥,等.全唐文2[C].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3:2096.
[4] 韓林.武則天故事中唐太宗形象的文本演變及文化內(nèi)涵[J].天中學(xué)刊,2012(4):126.
[5] [美]凱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鐘良明,譯.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1999.
[6] 沈奕斐.被建構(gòu)的女性——當(dāng)代社會(huì)性別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1.
[7] 程頤,鄭汝.伊川易傳·易翼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
[8] 林丹婭.當(dāng)代中國(guó)女性文學(xué)史論[M].廈門(mén):廈門(mén)大學(xué)出版社,2003:51.
[9] 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6:1641.
[10] [美]弗洛姆.人之心:愛(ài)欲的破壞性?xún)A向[M].都本偉,趙桂琴,譯.沈陽(yáng):遼寧大學(xué)出版社,1988:64.
[11]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xiàn)代婦女文學(xué)研究[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15.
[12] 馮廣藝.論話(huà)語(yǔ)權(quán)[J].福建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4):54.
[13] 文潔華.奇女子狄娜:20世紀(jì)70年代香港情色電影個(gè)案研究[A].荒林.中國(guó)女性主義4[C].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204.
[14] 周力,丁月玲,張容.女性與文學(xué)藝術(shù)[M].沈陽(yáng):遼寧畫(huà)報(bào)出版社,2000:124.
[責(zé)任編輯:張樹(shù)武]
Evolution of Wu Zetian’s Image and Its Gender Culture Connotation
HAN Lin
(Faculty of Humanities,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The two images “angel” and “devil” usually appeared in literary works.Wu Zetian offend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system,are portrayed as “the devil”.The narrator’s stand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the Tang and Five periods Dynasties basically accord with the facts;adding subjective factors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demonized.The point of the story from a political issue,transfer to a national problem,finally evolved into a gender issues.The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iolently transformed Wu Zetian,including the reduction of ruling ability;eroticize her love;demonized her posterity etc..This change is the generalization resulting from gender philosophy to political field in feudal society;the product of male “individual narcissism” going up to “group narcissism”;patriarchal system completely deprived of the women’s right to speak in works.
Gender;Wu Zetian;Demonization
2014-02-22
大連大學(xué)2012年度博士啟動(dòng)基金項(xiàng)目。
韓林(1978-),女,遼寧大連人,大連大學(xué)人文學(xué)部講師,文學(xué)博士。
I206
A
1001-6201(2014)03-01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