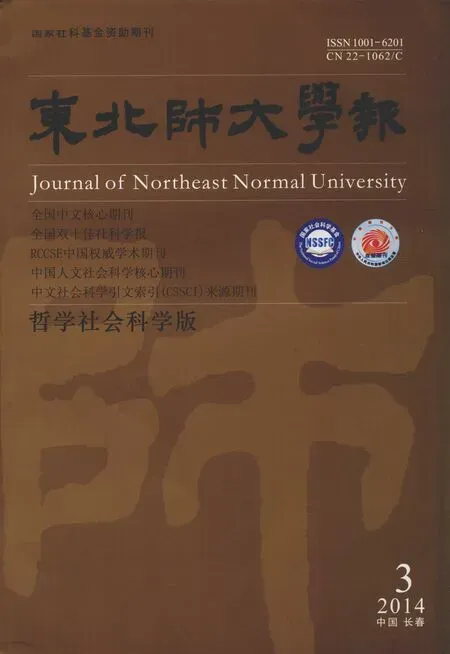農村權力結構嬗變與農民權利實現的互動關聯
楊 郁,劉 彤
(1.東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吉林 長春130117;2.白城師范學院 政法學院,吉林 白城137000)
權力是政治的一個永恒話題,它有著自身的結構和運行邏輯,這種結構一旦形成,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當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發生大的變革時,權力結構也會適時地分化、整合。就農村社會而言,權力結構的動態變化對農民的權利實現所產生的效力不盡相同,其作用方式也并不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從中國農村變遷的漫長歷史過程來看,每一次權力結構的調整都對農民的權利實現產生了或隱性或顯性的影響。當今農村存在的諸多矛盾與問題,歸結起來,根源就在于現存的權力結構與農民權利的訴求之間未達成契合,使力與利失去了相對的均衡。事實上,農村權力結構與農民權利相互依存。農村權力結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需要得到權利主體即農民的認同,而獲得認同的前提就是權力對農民權利的保障與實現程度。農民權利的確認與維護同樣離不開權力結構,在現代法治國家中,只有被權力主體界定后的權利,才有被維護的可能。因此在農村權力結構的嬗變與農民權利實現之間必定存在著某種深刻的互動關聯,這種內在互動關聯成為構筑均衡的農村權力與權利關系的邏輯根基。
一、農村權力結構嬗變緣于國家權力與農民權利的反復博弈
相比國家權力,部分學者認為,權利似乎更具先驗性,是人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一部分。尤其在自然權利學說當中,明確提出權利先于國家權力產生的特質,認為先有了人的自然權利,之后才逐步形成了國家權力。馬克思批判了這種觀點,否認了權利的自發性,認為二者都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無論權利與國家權力產生的先后順序具體為何,人類歷史的發展始終交織著權力與權利的博弈與沖突調適。農村權力結構的嬗變可以說就是國家權力與農民權利反復博弈的結果,是矛盾運動后的整合和理性選擇。
(一)農民的權利訴求對傳統權力結構的沖擊
傳統中國農村的權力結構建立在王權至上的集權模式之上,社會分裂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廣大的農民是當然的后者,沒有與國家權力對抗、主張自身權利的能力和機會。農民本身具有分散性,零散的、弱小的個體權利在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意之前,往往會被強勢力量所壓制[1]。國家權力即王權以其神性權威,借助宗族、鄉紳的統治中介,支配和消解著農民的權利,將權力變成了自己的階級特權。
權力與權利的矛盾運動有其特定的張力,當權力的行使嚴重背離權利訴求的方向或當權利主體的能力和民主意識漸趨增強時,必將改良或誕生新的權力結構模式,恢復社會的基本平衡。傳統農村權力結構中對權利的長期忽視和壓制所積蓄的反抗心理最終以革命的形式爆發出來,重新取得被權力所承認的權利地位。“如果農村處于反對地位角色,那么制度和政府都有被推翻的風險。”[2]革命勝利后的中國農村權力結構發生了本質變化,但沒有停止嬗變的歷程。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分工愈發細化,農村權力主體的單一化越來越無法回應農民的多元需求,基于農民權利實現的必然性和緊迫性,傳統的權力結構在村民自治應運而生后開始了進一步向權利復歸的步伐。
(二)國家權力滲透與農村自治傳統的碰撞與整合
中國的農村社會內含著自治的傳統,在傳統中央集權的體制下,王權擁有絕對的統治權,但在實際權力運作中考慮到行政成本等因素,王權的觸角并未深入到每個分散而具體的村莊,農民的微觀生活更多的是自給和封閉的。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事實上,正式的皇權統轄只施行于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出了城墻之外,統轄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3]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自治傳統存在的經濟前提,根深蒂固的家族倫理文化為其提供了生長土壤。但專制體制下的自治實際上是一種鄉紳治理,普通農民并不具有平等的自治地位。鄉紳與國家權力相互借重,從對方提取自身所需的權威資源,鄉村自治由此變相地成為國家權力在農村的統治延伸[4]。此時的自治嚴格意義上只能說有了某些自治的因素,但并不等同于現代法定的自治權。
新中國成立后的國家權力滲透,其本質已有別于傳統專制國家,但農民自身的分散性、封閉性和組織弱化并沒有隨著主人翁地位的被賦予而根本改觀。在這種情況下,運用一定的國家權力整合農村社會是必要的。當然由于初期制度的不完備和操作的不規范,出現了國家權力對自治權的剝奪,農民的權利受到了嚴重影響。但隨著國家整體法治化與民主化程度的加深,農村社會的境況引起了人們的反思,特別是中共領導層,意識到計劃時期的農村權力結構對農民積極性的壓抑,亟待還權于農、恢復農民自治的主體地位。到1988年我國共建立村民委員會882 564個[5]。自治在被國家權力自上而下的認同后,再一次活躍于農村社會,也加速了權力結構的再次變遷。
二、農村權力結構嬗變對農民權利實現產生的影響效應分析
權力結構歸根到底是要解決權力的配置與運用的問題,權力作為一種具有強制性的支配力量,總是要把權力主體的意志加諸在權力客體上,迫使客體服從主體,實現對客體的控制。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實踐上來講,權力的分配與運作模式的變化都將對客體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一)農村權力結構嬗變促使農民權利關系的重組
權利關系的分立、沖突、調和顯示著權力主體對權利的側重、界定的變化,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它受制于權力,是被權力塑造和影響的對象之一。農民的權利關系與相關的利益各方有緊密的關聯,是在利益各方的互動中逐步形成的。按照農民權利關涉的主要利益相關方,農民權利關系體現在三個方面:農民與農民、農民與國家、農民與市場。
首先,體現在農民與農民的關系上。傳統農村權力結構中,國家權力為了達到既節省行政成本、又能有效控制農村社會的目的,把農民中經濟較為富足的鄉紳階層的地位突顯了出來,使其成為傳統農村實際上的主導力量。農民與特殊農民階層即鄉紳的關系是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農村權力結構注重階級成分,鄉紳成為農民中的底層,喪失了土地、以往的地位和聲望。貧下中農翻身享有了民主權利,并且具有明顯的階級優勢,農民的地位和權利關系被重新確立。村民自治建構起了更趨民主的權力結構,進一步改變了農民間的權利關系,一方面使農民對利益的追求有了更為寬松的政治環境,催生了不同的農民階層。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在權力結構中所形成的新型委托—代理關系,引發了農村內部各階層地位與角色的變化。按照各階層擁有的資源和影響他人的能力,可分為精英階層、治理階層、普通村民。這些階層因占有資源的多寡在權利主張能力上也存在差異,形成了復雜的權利關系。
其次,體現在農民與國家的關系上。農村權力結構基于一定國家政權形式而建立,建立后的農村權力結構反過來會作用和影響農民與國家的關系。傳統農村社會中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是疏離、冷漠的,征收賦稅是二者最主要的交集。國家對農民盡的責任和義務幾乎沒有,農民傾其所有換取的也并不是國家對其利益的保護,而是更沉重的壓榨和剝削。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不對等關系滋生了更進一步的反抗,激化了深層次的矛盾。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推翻了壓迫,徹底摧毀了傳統的權力結構,在農民與國家之間形成了新的聯系。新型權力結構中農民作為主人受到了應有的重視,這種農村權力結構為農村土地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農民權利有了來自國家的承認和庇護。雖然人民公社體制曾抑制了農民權利的實現,但村民自治扭轉了農民和國家一度偏差的關系定位。國家既是權力的所有者,又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農民權利的維護者,自上而下的提供政策支持,并在農民權利的實現中不斷獲得權力主體的合法化資源。農民作為權利的主體,同時也是國家權力的服從者,它的權利實現不能超越權力界定的限度。二者的關系隨著自治結構的運作更加成熟和明朗。
最后,體現在農民與市場的關系上。傳統小農經濟在很長一段時期保持了高度穩定,它具有的內在調節機制在自由競爭的市場面前卻顯得極為脆弱。而傳統農村權力結構由于只具有統治職能,缺失公共服務職能,無力在市場的沖擊中給予農民任何幫助和支持,消極作為的權力主體加速了農民的日趨貧困和小農的普遍破產。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市場與社會主義性質相悖的觀念使農民長時期地只需面對國家,與市場的關系被擱置和遮蔽起來。人民公社解體后,中國龐大的農民群體再次面對市場,不同的是這次與市場的遭遇是權力主體的主動選擇。在這次市場化面向中,農民在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政策支持下贏得了在市場立足的動力源泉,作為農村權力結構核心的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也充當起“代理人和當家人的雙重角色”[6],幫助農民在市場中正確選擇。相對獨立的自治空間,維護了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和對自身勞動力的自由支配權,使農民在市場中的權利實現得以可能。
(二)農村權力結構嬗變引發農民權利實現方式的變革
傳統權力結構支配下的農村社會,缺乏權利觀念,被專制統治壓迫的農民只有維持基本生存的樸素愿望。但即使是這些最為基本甚至低微的生存權利主要還是依靠農民的自我救助來實現,傳統的權力結構并不承擔保護農民權利的責任。當農民連最基本的生活都難以保障,自我救助也無濟于事時,一般來講,依照侵犯權利的主體不同,農民會采取不同的維權途徑。若對農民權利的侵犯來自其他農民,那么首先會求助于父母兄弟、親朋好友,其次是有威望的鄉紳、宗族族長,如果都未能解決而又忍無可忍時,最后農民會告到官府,由地方官裁決。若對農民權利的侵犯來自當權者,即官府,農民一般會選擇忍受。如果到了無法容忍的程度,對于地方官員的欺壓,會向上一級官府檢舉、上告,而對于整個政權體系的苛政,走投無路時也會鋌而走險,揭竿起義[7]113。由于農民不可能在制度法律的框架內尋求到自身權利的位置,最基本的權利實現往往也需要采取最極端的方式,而且效果并不理想。
村民自治時期的農村權力結構變革了傳統的根基,理性自覺與民主法治構筑起了農民自治的平臺,廣大農民贏得了權利的主體性地位和制度化的權利保障。事實表明,缺少一個反映農民權利相對平衡的權力結構,是自古以來農民權利得不到實現、農民利益受到損害的重要原因。新時期的農村社會利益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各不相同的利益主體實現權利的方式和渠道大致分為兩種,“一是政府保護,二是自我保護(農民自我維權)”[7]114。政府保護一方面來自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在體察民情、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制定和出臺相應惠農利農的政策和法律法規,在制度上確保農民擁有同等的權利實現機會,“把擴大和保障公民權利視為自己執政興國的重要任務”[8]。另一方面基于政府行為的保護,具體指政府對法律、政策的執行及對自身行為的規范,也就是明確作為與不作為各自的界限。就農民的自我保護而言,可以通過村民直選、定期換屆、參政議政等方式維護自身權益,也可以通過法律渠道對侵犯權利的行為依法進行反抗。在新的權力框架內農民獲得了更多與權力對話、調適的機會,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向渠道的開辟拓寬了農民的權利生長空間,權利實現正逐步向自覺的政治行為轉軌。
(三)農村權力結構嬗變推動權利保障的制度設計與供給路徑的更新
伴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權力與權利的博弈,在制度層面衍生出了逐漸趨向合理的制度設計,即尋求對權力的行使與對權利的保障達到某種均衡。著名政治學家羅爾斯在其論著《正義論》中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第一美德一樣。”[9]正義的制度平等地待人,不歧視、不剝奪社會成員應有的權利,其中內含著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農民作為弱勢群體的一部分,保障他們權利的制度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艱難形成過程,而權力結構的嬗變催生了關于權利的不同制度選擇。
傳統國家權力通過對各個地方的控制來體現權威,控制和權力滲透是傳統權力結構設立的初衷,也成為其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如果說從傳統專制社會的制度安排中能解讀出農民權利保障的內容,那么傳統社會農民的權利恐怕只限于繳納沉重賦稅交換來的短暫安寧和利益被侵犯時得到官府無法確保公正性的裁決。這種制度的實行路徑是單向的,只有制度由國家向農村社會的輸出過程,而不存在執行效果反饋的輸入過程,這也直接導致了政策制定者言路閉塞。集權式的國家主導或鄉紳主導式的權力結構對農民權利的制度設計必然是缺位的。隨著新中國成立后農民主體地位的確立,權力來源、權力主體性質的根本變革建構了新的農村權力格局,農民具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在法律和政策制定上發生了異于傳統的轉向。特別是經過集體化的洗禮,農民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漸強,村民自治形成了更為民主、均衡的權力結構,而制度上的相對滯后日益暴露,影響著自治的效果和農民權利訴求的滿足。作為農村利益的凝練整合體,權力結構通過制度制定、推行和反饋方式的革新,實現制度供給由單向向雙向的轉變。一部分制度來自國家權力,由國家權力部門制定和傳達,另一部分來自農村公共管理機構,由農村公共機構在國家法律界限內制定切合本地實際的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在自治的權力框架內兩種供給方式相互補充,構成農民權利實現的制度保障。
農村的主體是農民,農民問題的關鍵在于權利實現。農民權利實現與農村權力結構嬗變之間存在緊密的邏輯關聯,農村權力結構嬗變緣于國家權力與農民權利的反復博弈,農民權利實現又深受農村權力結構嬗變的影響。要解決當下農民權利實現的問題不能不考慮權力結構如何構建,農村權力結構嬗變與農民權利實現的互動性表明:在權力與權利的博弈中,沒有真正的輸家和贏家,二者必須找到互贏的均衡點。在權力結構的構建中,改變權力至上的傳統觀念,擺正農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關系,打下維護權利的思想與行為根基,進而使其“超越自身的觀點和利益的局限,考慮到公共利益”[10]。在權利的實現中,增強農民自身的主動性和自覺性,監督權力的法治化運行,遏制其惡性膨脹。以權力均衡促權利平等,將權力變成權利的屏障。
[1]曲婧.網絡問政:權力保障下的權利實踐[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205.
[2][美]亨廷頓.變遷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聯書店,1988:267.
[3][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110.
[4]金太軍.村莊治理與權力結構[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25-30.
[5]盧福營.沖突與協調:鄉村治理中的博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4.
[6]徐勇.徐勇自選集[M].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275-280.
[7]朱新山.中國農民權益保護與鄉村組織建構[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1.
[8]劉彤,張等文.論中國共產黨民本思想對傳統民本思想的傳承與超越[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12):108.
[9][美]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
[10]張等文,劉彤.西方學者視域中的協商民主:理念、價值與限度[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