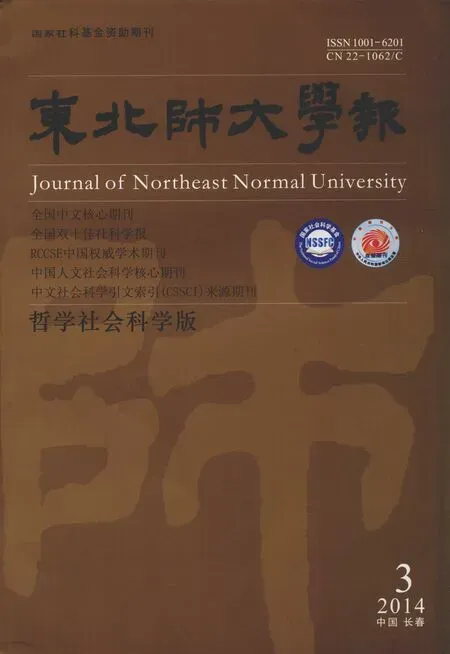阿爾都塞歷史無主體論的譜系背景與獨特張力
李 賽,韓秋紅
(1.東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部,吉林 長春130024;2.長春工程學院 人文社科部,吉林 長春130000)
“歷史無主體”既是阿爾都塞對《資本論》歷史觀的一項獨特解讀,又是阿爾都塞本人所堅定堅持的歷史觀。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多從“歷史無主體”是阿爾都塞獨創觀點的表象出發,忽視了將之歸入到整個歷史無主體論的大范疇中予以思考的必要性;另有學者雖然分析了阿爾都塞與普列漢諾夫、蘇聯哲學教科書在歷史無主體論傾向上的一致性,但卻對之采取了武斷拒斥的態度,未能真正釋放出隱匿在這種歷史觀中的思想活力。所以,我們就從哲學史和對歷史無主體論的誤判這兩個基點出發,試澄清阿爾都塞的是非功過,為推進唯物史觀基礎理論研究探索某種可能富有價值的路徑。
一、統觀歷史無主體論的哲學陣營:從黑格爾到阿爾都塞
“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1]47在阿爾都塞之前,并沒有人明確作出“歷史無主體”的判斷,但阿爾都塞石破天驚的旗幟性話語,卻激活了雖未正名、然早已存在的歷史無主體論思想庫。通過對較近的哲學家阿爾都塞進行“人體解剖”,我們能夠獲得“解剖”較遠的哲學家黑格爾、普列漢諾夫以及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的歷史無主體思想的鑰匙(限于篇幅,本文僅選取上述幾種與馬克思歷史觀最為密切的觀點作為分析對象)。
《資本論》中對現實個人的主體地位被抽象資本所架空的科學判斷,直接源于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解密。黑格爾認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2]8至于肉身的個人,其“欲望、興趣和活動,便是世界精神為完成它的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2]25由于非人身的“理性”才是歷史的主體,因此黑格爾的觀點實際上就是歷史無主體(無現實的個人作為主體)論。對于這種歷史觀,人們多以一句“神秘主義”拒之,這就閹割了黑格爾思想的重要發問意義,對此我們稍后再分析。
第二國家理論家所通行的經濟決定論,是另一種形式的歷史無主體論。如普列漢諾夫認為,盡管杰出人物可以決定歷史的個別面目,但“事變的總的方向……是由別的力量決定的”[3]166,它就是“生產力及其所決定的社會關系”[3]170。不可否認,普列漢諾夫關于歷史主體或者說歷史動力的這種闡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基本命題的正面解讀;但普列漢諾夫忽視了馬克思更深層的個體解放情懷——馬克思揭示現實歷史的這種運動規律的根本目的,不是要承諾、相反是要取消它的現實權力。
發源于普列漢諾夫闡釋模式,而又為蘇聯模式計劃經濟服務的哲學原理教科書,進一步強化了歷史無主體論的思想傾向。有學者指出:“哲學教科書雖然沒有這樣明說,但是把歷史規律夸大為自然必然性,長期忽視對人的研究……也隱含著這種傾向”[4]220,“因而歷史往往被理解為一種無主體的過程。”[4]44但教科書的無主體論成因又有其獨特性。由于高度集權的管理模式需要,每一個個體被抽象化為人民群眾、人民群眾被抽象化為革命領袖、革命領袖被抽象化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規律貫徹者,就成為意識形態上的必然要求。
與前三者不同,阿爾都塞直接斷言“歷史無主體”。《讀〈資本論〉》寫到:“真正的主體不是……‘具體的個體’,‘現實的人’,而是……這些規定者和分配者:生產關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識的社會關系)。但是,由于這是一些‘關系’,我們不能把它們設想為主體的范疇。”[5]164阿爾都塞強烈反對以“現實的人”作為馬克思學說闡釋基點的做法,而認為只有用社會結構解釋歷史發展才是唯一科學的路徑。阿爾都塞的觀點具有極大的思想張力,它使馬克思關于歷史科學與人類解放二者關系的復雜思想突顯出來。
二、反思對歷史無主體論的答非所問式批評:“忽視個人能動性”等原因并非阿爾都塞等論者的癥結所在
如果概括一下上述四種歷史無主體論的共同點,可以認為“個人在歷史中沒有任何地位”是其要義。在黑格爾那里,即使拿破侖這樣的個人也不過是“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在普列漢諾夫和蘇聯哲學教科書那里,具體的個人在鐵一樣冰冷的生產方式中無足輕重;在阿爾都塞那里,先驗的社會結構支配著一切歷史活動。
由此觀之,歷史無主體論是足以泯滅普通人的自尊心與能動性的學說,它告訴我們:如果作為草根的我的活動符合了或“理性”、或“歷史規律”、或“社會結構”的目的要求,那么我的活動結果不過是證實了它(們)的必然性而已;如果我的活動不符合其目的要求,那么我的活動必將失敗,從而在反向證明它(們)的必然性。“地球沒了誰都照轉。”作為世俗生活中的小老百姓,一方面我對這種無我的歷史理論感到氣憤,另一方面卻又無奈地看到,這種理論所描述的情形活像一面鏡子那樣逼真。這種矛盾性,應引發我們對歷史無主體論進行冷靜的思考,而首先要反思的就是以往對之的不冷靜思考。
不冷靜的思考之一,是用一句“神秘主義”的謾罵拒斥掉黑格爾的歷史無主體論。在對黑格爾歷史哲學乃至整個哲學的理解中,許多人一上來就是“唯心主義”、“神秘主義”、“醉醺醺的思辨”、“幻覺”之類的指責,而馬克思最為重視的造成黑格爾幻覺的根源,反倒被遺漏了。實際上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是“為歷史的運動找到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表達”[6],他以最抽象的形式表達了人類最現實的生存狀況。所謂個人成為理性的工具,被馬克思唯物主義地翻譯過來,也就是“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7]287。可見,與其說黑格爾歷史無主體論是唯心主義的胡說,不如說它敏銳地提出了時代性課題:為什么活生生的個人反倒不是真實的歷史活動主體?
不冷靜的思考之二,是用“忽視個人能動性”作為病因,來看待普列漢諾夫、蘇聯哲學教科書和阿爾都塞等人歷史無主體論的提出。由于阿爾都塞等人只談社會結構、不談具體個人,于是許多研究者就堅持認定其理論缺陷正是源自對個人能動性的忽視。這種批評實在是答非所問。前面我們已經分析到,從黑格爾開始的歷史無主體論,其真實意義不僅在于描述現實個體被剝離的歷史現象,而且也在于向這種現象的產生根源發出提問。但持“忽視個人能動性”式批評的研究者們卻說:“只有社會中的活生生的個體才是推進歷史進步、導致社會關系變革的真正主體”,“把社會夸大為獨立主體,完全忽視個體的地位和作用是錯誤的……這也正是普列漢諾夫、阿爾都塞忽視人的主體地位的原因”[4]221;再如,有學者認為黑格爾歷史觀的不足,也是低估了個體的作用[8]。這不是對癥結的診斷,而是對問題的不解。阿爾都塞等論者的真實意義在于發問:為什么現實個人失去了主體地位?而上述反駁者卻說:因為你忽視了個人的能動性。按這種邏輯,仿佛只要阿爾都塞“重視”了個人,他所揭露的關于現實個體被抽象資本所無情支配的現象就消失了。可見,對歷史無主體論的“忽視個人能動性”、“神秘主義”等批評,并未切中阿爾都塞等論者的要害。
三、阿爾都塞歷史無主體論的特殊意義:對《資本論》“社會結構具有支配地位”之科學發現的彰顯
歷史無主體論指的是個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的空場,它確實揭露了資本主義條件下最真實的生存狀況,而這正是馬克思歷史理論所要挑戰的對象。在理解這一點上,阿爾都塞既有很大的理論貢獻,又有很大的理論失誤。
首先,作為結構主義者,阿爾都塞明確指出社會結構超越于現實個人,支配著現實個人,而被人本學唯物主義所體認的人、人的關系等等,統統屬于非科學的幻想。這就用一種極端化的方式,將馬克思對社會結構具有支配地位的重要發現彰顯了出來。對于站在普通經驗立場和抽象人道主義立場上,將現實生活中的“人”作為歷史發展主體的觀點,阿爾都塞大加鞭撻:“真正的‘主體’(即構成過程的主體)并不是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職能的執行者。同一切表面現象相反,真正的主體不是天真的人類學的‘既定存在’的事實,不是‘具體的個體’,‘現實的人’,而是這些地位和職能的規定和分配。所以說,真正的‘主體’是這些規定者和分配者:生產關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識的社會關系)。”[5]164
阿爾都塞強調的是,《資本論》反對讓具體的個人向歷史運動負責,因為具體的個人被牢牢綁定在生產關系、社會結構的鐵鏈之中。如果用黑格爾的術語再表述一遍,就是肉體化的人成為“理性的狡計”的工具。這樣,阿爾都塞就成為理解黑格爾——馬克思理論傳承關系的一把鑰匙。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中明確提示到:“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9]10阿爾都塞在解讀《資本論》的過程中,將馬克思的思想又進行了重新的發揮演繹,不僅將個人,而且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范疇也剔除出他所體認的歷史科學之中,而直接作出了“歷史無主體”的結論。
《讀〈資本論〉》寫到:“由于這是一些‘關系’,我們不能把它們設想為主體的范疇。如果任何人偶然想要把這些生產關系還原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還原為‘人的關系’,他就是在褻瀆馬克思的思想,因為只要我們對馬克思的少數模糊不清的提法持真正的批判態度,我們就可以看到,馬克思極其深刻地指出,生產關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社會關系)不能還原為任何人類學意義上的主體間的關系”[5]164。由此,阿爾都塞“矯枉過正”地警示人們,馬克思歷史科學中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人際交往,而是隱匿在這些行為背后支配這些行為的社會結構。由于社會結構脫離于個人而單獨自在,因此它既與個人無關,也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無關。總之,“人”構不成歷史運動的主體,歷史沒有主體。
下面,我們聯系《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相關論述,來從正面認知阿爾都塞的歷史無主體思想。前面提到,關于“歷史無主體”現象,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表述是“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又從原因與結果兩個維度考察了這一歷史現象。在原因方面,商品、貨幣、資本等物格代替人格運動從而造成“歷史無主體”的假象,是因為生產商品的勞動分裂為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個人勞動只有通過自身的異化才表現為抽象一般的勞動”[10],從而使得人與人的關系(勞動交換)表現為了物與物(商品交換)的關系,最后物的邏輯代替人而成為歷史運動的主詞。在結果方面,個人日益喪失存在感:“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生產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9]487,資本主義“奪去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9]487由此造成一種令人眩暈的現象:明明是由一個個活人所構成的歷史,卻死寂得仿佛沒有主體一般。從這個理論層面來看,阿爾都塞以“社會結構”范疇為基礎,將馬克思區別于人本學唯物主義的思想精華提煉得非常精彩[11]。
四、阿爾都塞歷史無主體論的根本局限:對《資本論》人類解放學說之真實含義的遮蔽
但是,阿爾都塞在突顯馬克思科學發現的時候,因為極度突顯此一維度,而又走向了對彼一維度的遮蔽。阿爾都塞對馬克思有一項“恨鐵不成鋼”式的批評:“因為只要我們對馬克思的少數模糊不清的提法持真正的批判態度,我們就可以看到……生產關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社會關系)不能還原為任何人類學意義上的主體間的關系”[5]164。這就是說,他埋怨馬克思對于“人與人的關系”范疇清除得不徹底,馬克思尚存在“少數模糊不清的提法”,而我們應當對馬克思的這種曖昧做法“持真正的批判態度”。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這一解讀,恰恰暴露了阿本人歷史無主體論的根本局限:它完全曲解了馬克思的原意,把馬克思恢復人與人之間的直接關系的終極追求,看成了“模糊不清”的筆誤,從而遮蔽了《資本論》解放學說的真實含義。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阿爾都塞歷史無主體論的成功基點在于“社會結構”范疇,失敗基點也在于“社會結構”范疇。實際上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結構”不僅不是對人與人之間的人類學關系的拒斥,反而正是圍繞這種人類學關系而展開的[12]。“人與人的關系”非但不是阿爾都塞所說的根本無意義的“馬克思的少數模糊不清的提法”,反而是一個包含著深刻價值追求、哲學性與科學性二位一體的范疇,是真正理解社會結構和歷史無主體假象的鑰匙。
首先,與阿爾都塞特別反感的人類學態度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始終重視對人與人關系的人類學考察。從早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到晚期的《人類學筆記》、《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恩一直在鉆研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發生、發展、演化、趨向。他們的研究揭示到,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并不是斯密、李嘉圖所幻想的亙古不變的東西,而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從起源來說,社會關系發生于原始社會“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13]的事實。不是黑格爾的“理性”、阿爾都塞的“結構”走在了人類社會發生之前,而是相反,最初的實踐活動構成了被哲學家們抽象成“理性”、“結構”等等“歷史目的”或“歷史規律”的現實基礎。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由對社會關系的人類學考察,進入對其最新異化形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專門考察。社會關系最初表現為群體生存所要求結成的人與人的直接性聯系,但進入私有制階段后,則異化為統治人(特別是勞動階級)的抽象力量,“最初作為促進生產的手段出現的東西,成了一種對生產者來說是異己的關系”[1]95。這就是歷史無主體現象(生產者被異己的關系所支配)的根源。歷史無主體是一個逼真的假象。表面看來,商品、貨幣、資本所代表的社會結構凌駕于個人之上而大行其道,造成“人們信賴的是物(貨幣),而不是作為人的自身”[1]110,“但為什么人們信賴物呢?……貨幣所以能擁有社會的屬性,只是因為各個人讓自己的社會關系作為對象同他們相異化。”[1]110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只有轉化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能實現自身,也就是活生生的個別必須服從抽象化的一般。因此馬克思揭示到:“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地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己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7]85-86,這就造成了一種歷史無(個體)主體的表象。阿爾都塞只關注馬克思對資本控制個人的表象揭示維度,而忽視了馬克思對這種控制機制的本質揭示維度。
最后,與斯密、李嘉圖等“國民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采取永恒肯定的立場相反,馬克思認為控制活生生的個體的既有社會關系,在歷史科學的意義上只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現象,在價值批判的意義上應當被新型的人與人的關系所揚棄。商品、貨幣、資本及其造成的各種拜物教,終歸必然和應當消亡,個人將取得把握自身的自由、作為實實在在的歷史主體而存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7]294。顯然,這正是“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9]97,也就是被阿爾都塞誤認為是“馬克思的少數模糊不清的提法”(見上文)的人類學關系。正因如此,阿爾都塞怎么也不能理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也是一種人道主義。
綜上可見,阿爾都塞的元范疇即“社會結構”[14],在馬克思眼中只是次生范疇,是起源于人類學的原初社會關系、異化于人類學的現代社會關系、必將要演進為人類學的未來社會關系的范疇。使社會結構(社會關系)與現實個人的從屬關系顛倒過來,使個人真正作為歷史主體而確立起來,正是馬克思解放論的立足點。阿爾都塞緊緊盯著《資本論》在分析過程中對抽象資本統治個體這一事實的科學描述,卻沒有體認到馬克思時時刻刻操持的價值批判,進而遮蔽了《資本論》最終訴諸個體解放的根本意蘊。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3][俄]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讀本[M].王蔭庭,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4]孫承叔.真正的馬克思——《資本論》三大手稿的當代意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法]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8.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西方馬克思主義卷:上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21.
[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75.
[11]韓秋紅,史巍.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的雙重維度[J].江蘇社會科學,2010(1):46-50.
[12]賈麗民.反思達致真理:馬克思《資本論》的思維方式意涵[J].學習與實踐,2013(4):120-126.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6.
[14]劉宇蘭,雷有壽.論早期阿爾都賽的主體思想[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