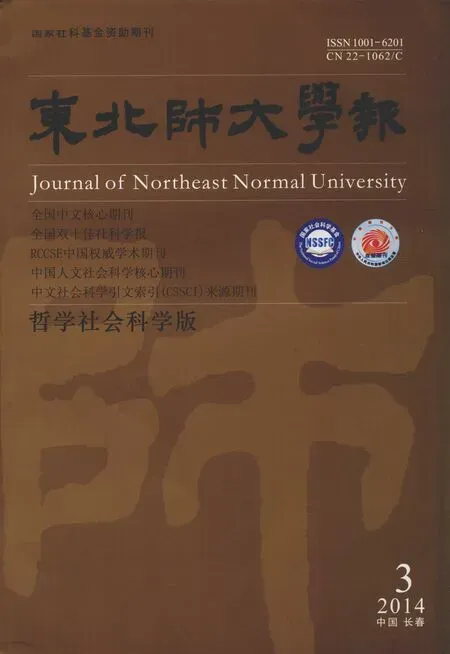福克納與美國南方“圣經地帶”
(吉林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一個偉人的成長和成功離不開其生長環境的影響,一個偉大的作家更是如此。而偉大文學家所鑄就的文學作品都與其所成長的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無論他對此種文化有意識的繼承還是刻意的反叛,其個人思想和藝術作品也或多或少地打上那個文化的烙印。美國現當代著名小說家威廉·福克納成長于美國的“南方圣經地帶”,這里受圣經文化的影響比較大,而福克納就是在這樣的宗教文化環境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所以,他的成長經歷、性格品質都打上了“圣經地帶”的烙印。重要的是,他的很多著作中也明顯可以看出圣經的烙印。
一、美國南方宗教文化概述
宗教是美國文化中非常顯著的一部分。與歐洲宗教衰落的情況不同,宗教人口在美國建國后持續增長:1776年去教堂的人數只占全國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到1850年則接近全國人口的一半,而到了20世紀初期超過一半,現在已經占到了3/5。
美國到底有多少種宗教,學者們意見紛紜,有人說近300種,有人說有900種,《新興宗教運動》一書中則說有1 200種,有的書還提出有1 900種。這是由于人們對宗教和教派的理解不同造成的。主張近300種的是指較大的、在美國社會中得到公認的宗教派別,主張1 200種或更多的人是把各種新興宗教包括在內,這些新興宗教也許只有幾十或幾百名信徒,在美國社會中影響不大。不管用哪種統計方法,每個踏上美國國土的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會發現美國的宗教派別和教堂之多確實令人瞠目。一位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在課堂上對學生說,他去德留學時見到德國人填宗教信仰這一欄時只列三項:路德派、天主教、其他。這種表格要拿到美國則完全不適用,因為美國的宗教信仰實在太多太雜,以致沒有一種或兩種教派能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教派,他的說法是符合實際的。世界上沒有—個國家像美國那樣有如此眾多的宗教派別和宗教組織。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多種,但其中有兩點較為重要。一是美國本身是個移民組成的國家,各國移民在移居美國的同時將其母國的宗教信仰也帶到了美國,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來移民的成分越來越復雜,使美國的宗教愈益多元化;二是美國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實施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早在美國1789年立國時,美國的締造者們便確立了這一政策,1791年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正式宣布美國不設任何國教,聯邦政府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不歧視也不特別支持某種宗教。這一修正案至少在法律形式上為各種宗教創造了公平競爭的條件,促進了形形色色的宗教滋生和繁榮。
由于美國宗教帶有濃厚的移民色彩及某些歷史原因,致使各宗教教派在地理分布上相對集中在東部和南部地區,南部地區也形成了獨特的南方宗教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人口流動性大為增加,這一特點在許多教派中已不明顯,但在某些教派中仍可見到。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蘇達州就有許多路德派教堂,因為來自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移民及其后裔在這些州人數相對較多。在猶他州,則到處可見摩門教堂,因為該州是摩門教的基地。美國天主教則主要集中在西海岸、西南部和東北部,西南部是墨西哥移民集中地,東北部是愛爾蘭、波蘭、意大利等歐洲移民集中地。至于東方宗教,如伊斯蘭教和佛教則大部集中在西海岸加州一帶,這是由于亞洲移民在該地相對集中之故。
由于移民抵達美國時間先后不同,故各種宗教傳入美國時間也有先后。一位美國天主教神學院教授在上課時問學生“誰發現了新大陸?”大家回答說是哥倫布。他幽默地說,應該回答說是天主教徒。盡管他是在說笑話,但也有一定道理,因為哥倫布是天主教徒,由于他發現了新大陸,使西班牙人在16世紀首先將天主教帶到美洲。至今在加州還保留著一些有數百年歷史的老天主教堂,這些教堂都是早期西班牙傳教士向印第安人傳教的見證。繼西班牙人之后是英國、北歐、法國人進入北美。17世紀初英國在弗吉尼亞建立殖民地,新教圣公會傳入北美,以后隨歐洲新移民的到來,新教各派陸續涌入北美。18、19世紀美國發起了兩次大覺醒運動,產生了不少新的基督教派別,使美國的新教各派派系更加林立。除了新教教派外,猶太教也是最早傳入北美大陸的宗教之一。北美第一個猶太社團正式建立在1654年,至于猶太人進入北美的時間則更早,哥倫布的船只上就有數名猶太水手。非基督教傳統的宗教如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傳入美國的時間都是在19世紀末葉,這些宗教至今在美國文化中不占主導地位。
在美國南方,參加同一教堂的會眾,都是由階級地位、社會地位相當、思想意識相近、有共同信仰的人組成。到美國教堂去參加禮拜,雖然事前往往并不了解這些教堂的背景,但一到那里馬上可以根據人們的汽車、服飾、談吐、教堂音樂和氣氛判斷出該教堂屬于哪一階層。圣巴巴拉流傳著“富人住山上,窮人住山下”的說法,也就是富人都買能俯瞰大海和城市的山上住房,而窮人只能擠住在平地。在芝加哥則是“富人住郊區,窮人住市內”,往往郊區教堂是中、上階層的信徒集中之地,而市內的教堂就成為窮人教堂。有時整個社區居民成分發生變化,教堂也隨之興衰。例如在芝加哥大學校區附近有一座原屬基督教科學派的大教堂,一度曾十分興旺,但60年代后期該社區中原有的白人中產階級陸續搬離,黑人居民陸續搬入,該教堂失去大量信徒,最終因經濟困難不得不將大教堂賣掉,搬進附近較小的居民樓內。這種興衰情況在美國不少教會都發生過。較明顯的是美國天主教會,原信徒大多屬中、下階層,集中住在大都市市區內,二次大戰后,美國天主教徒經濟地位上升很快,大都躋入中產階級行列,大批信徒由市區遷往郊區,致使許多市區教堂衰落,而郊區則新建了不少新堂。
二、南方宗教文化與福克納的成長環境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人類的發展以及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在大部分的西方社會中,社會現代化的結果之一必然是宗教活動的大大減少,但是美國卻一直保持著它非同尋常的宗教特質。這樣的宗教特質在20世紀的美國也就是福克納所生活的時代顯得尤其明顯。顯而易見,美國南部地區的文化形式是多種多樣并且是由不同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在該地區占主導地位的還是新教,它對美國南部地區的社會、政治、文化以及經濟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同時,它也對美國南部地區的種族主義以及奴隸制有著支撐性的作用,并且也限制著當地民眾的思想和生活,對人和人之間的行為準則也有一定的規范作用,所以對美國南方地區的人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該地區被人們稱之為美國南部“圣經地帶”。而福克納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并且進行日后的文學創作,所以其文學作品與圣經文化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另外,早期乘坐“五月花號”不遠萬里移民到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嚴格意義上的清教徒。他們此行的目的不光是為了逃避原居地區的迫害,更重要的是對個人宗教信仰的一種追求。因此在起始階段加爾文主義就存在著一定的影響力,而后來該種宗教思想在移民浪潮的帶動下才在美國南部地區扎根。該種相對于其他宗教而言保守的宗教形式能在該地區迅速蔓延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它對南方的種族主義和奴隸制的支持。另一方面,南部地區在內戰中失敗對新教在此地的迅猛發展有著極大的刺激作用。當然,當時戰爭失敗的南部的人們對戰爭所帶來的衰敗以及社會的不公無法接受,同時他們對可否依靠自身的能力解救自己產生了質疑,所以他們開始尊崇最原始的信仰,這樣的目的無非是能讓神對其有所幫助,從而自己形成一種心理上安慰[1]134。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所產生的結果是異常明顯的:新教各種教會形式在南方如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起來。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新教逐漸在南方占據了無可爭議的頭把交椅。
盡管南方地區的教會形式相對繁雜,但是多數人都對與加爾文主義相關聯的宗教形式情有獨鐘,而加爾文主義的根本教義是相信上帝對人類事務的絕對主權,按上帝的旨意行事是他們的首要責任。根據原罪教義,人類祖先亞當被創造為純潔的人,他能按上帝的意愿行事。但是亞當的原罪導致全人類從純潔的狀態中墮落。因此,所有人都是“完全敗壞”,只會犯罪,而不能去行善。所以所有人都承受上帝公義的定罪。同時他們認為主耶穌基督的死是為有限的少數人而不是全人類贖罪。有限的少數人,被稱作“揀選之人”,可以得救。根據加爾文最廣為人知的教義——救贖預定論,上帝決定揀選之人得永生,其他的人則是永遠被定罪或棄絕。根據“不可抗拒的恩典”教義,上帝揀選的人被他的恩典救贖,對于這種恩典,人不能拒絕。在加爾文主義中,《圣經》成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權威。因此當時在加爾文主義的橫行之下,南方的劇院被關閉,酒吧被禁止,講授進化論的教師被接二連三的拉出去審判。生活中的享受被等同于罪惡,生活成了人們“自己把自己不斷釘在十字架上的過程”[2]。
而福克納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度過了他的大部分時光。他的家庭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基督教家庭。其祖父曾是當地的一位傳奇人物,出身異常貧窮,靠勤勉來持家,后來擁有了私人鐵路和自己的莊園,并且當上了州議員。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作為騎兵挺進隊上校的祖父也曾立下了汗馬功勞。不幸的是,他后來死于合伙人之手。到了父親這一輩時,家庭逐漸衰敗下來。在福克納五歲時,跟隨家人搬到了設有州立大學的牛津鎮,父親當時以經營馬車出租為業,家境并不富有。因此,福克納從小便對種植園世家由盛轉衰過程中的種種際遇非常熟悉,他尤其關注的是自己所在區域民眾的精神萎縮現象,他將此稱為“人的愿望無法實現的歷史過程中的整個重負”。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主要內容都與自己家庭生活的各種感受和印象密不可分。在其首部作品中,福克納在自己“像郵票那樣大的土地上”開始建立起屬于自己精神世界的宏偉藍圖——約克那帕塔法世系小說。這一世系小說活脫脫是一部美國南部的歷史,也是一個具體而又細微透視西方文學世界的一扇窗口。
在1956年的一次訪談中,被問及“你引用《圣經》,怎么會這樣熟悉?”福克納回憶了這樣一種特殊的家庭傳統:“我的太公默里,是一個溫厚而和善的人,至少在我們小孩子看來是這樣。就是說,他雖是個蘇格蘭人,卻并不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也從不聲色俱厲;他不過有他的一套道德原則,堅決不可動搖。他有一條原則就是,每天早上大家坐下來吃早飯時,在座的從小孩子起直到每一個成年人,都得準備好一節《圣經》的經文,要背得爛熟,馬上就能脫口而出。誰要是講不出來,就不許吃早飯,可以讓你到外邊去趕緊啃一段,好歹要背熟了才能回來。背誦的經文可一定得有根有據、準確無誤。起初我們年紀還小,只要有一節經文獲得通過,就可以天天早上來這一節;后來年紀稍稍大了一點,遲早就會有那么一個早上(此時你這一節經文已經可以倒背如流,你就有口無心地匆匆念完,因為你早已等了好大一會兒了,火腿、牛排、炸子雞和麥片、甘薯、花色熱面包等等早已擺滿在你面前了)你會突然發覺太公的一雙眼睛盯在你的身上——他的眼睛是藏藍藏藍的,目光很溫厚很和善,即便在此刻也并不嚴厲,然而卻是一副寸步不讓的神氣;于是到第二天早上,你自然就換上了一節新的經文了。可以這么說吧,到那時你也發現自己的童年時代已經過了;你已經不是個小孩子了,已經開始懂得人世間的事了。”[3]由于生長在這樣的社會和家庭生活之下,基督教對他的影響肯定是非常明顯的。除了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以及家庭因素,福克納自己對圣經的興趣也是異常濃厚的。他多次在訪談或者個人的文學作品中提及《圣經》,特別是舊約是他最為喜歡并且反復研讀的作品之一。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南方的宗教文化是美國大部分南方州郡中所盛行的一種集體主義精神。塞繆爾·S·希爾曾經說過:“南方是基督教國家中唯一福音派教徒占大多數的地區。”南方地區的人對待宗教是非常認真的,民眾們都被鼓勵或者會直接被要求參與教會的活動,而參與到宗教團體生活中信教的南方人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這些人群經常每星期參加三次或者三次以上的活動。眾所周知,福克納就曾經經歷過南方宗教文化特有的一面,至少在他幼年時是這樣的,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以及自己的家庭成員就參加了新奧爾巴尼衛理公會教堂的主日學校。直到1904年,他們開始減少參與次數,因為福克納的母親明顯厭煩強迫自己的子女去參加這樣的宗教活動。在他12歲之后,他似乎更愿意呆在父親的馬車租賃中心,追求的活動內容都是更具有南方男子氣概的特有形式,比如打獵。據說福克納本人也給他的妻子讀過雅歌中的詩文,這也一定程度上說明他在幼年時就已經學習過《圣經》中的一些內容,即便是出于其詩學價值也罷。
三、南方宗教文化與福克納的精神世界
1957年在弗吉尼亞大學接受采訪時,他被直接問到他個人的宗教信仰問題,福克納給出的答案卻含糊不清。以下就是一次這樣的交談:“問:福克納先生,除了其他頭銜,你還曾被稱為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不知道你是否能告訴我對于你和基督教的關系,你是怎么看的?答:基督教于我無害。我希望我也不曾于它有害。我有過教區基督教教育的背景,當然很可能,人們對此會想當然地不多加思考。我認為我可以算是,至少在我自己看來,我是一個好基督徒,這是否符合其他人的標準,我就不知道了。”[4]
乍一看,這似乎是個誠實的答案。它以一種不那么直接的方式來回答問題,而且充滿了典型的福克納式的智慧。不過我們可以想像,福克納是在有意識的情況下對南方宗教文化產生興趣的。當被問及他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宗教典故和明顯表現出宗教思想時,他回答說:“基督教的傳說是每一個基督徒”,特別是像他那樣的“南方下鄉小孩的背景的一部分”,“我在其中長大,在不知不覺中將其消化吸收,它就在我身上,這與我究竟對它相信多少毫無關系。”[5]86所以毫不奇怪,福克納在美國南方圣經地帶這樣的大環境下逐漸形成了他的精神世界。而我們所熟知的詩人和作家都是通過文字來表現出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在他日后的文學創作中都不同程度的反映出以上所提及的精神內容。福克納自己也曾經說過,他的小說中約克納帕塔法這個地方正是美國南部地區人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優秀品質的發源地。同時,從另一方面來講,福克納文學作品中是對南方精神的凸現,也是對人類可貴精神財富的贊頌。
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歷史因素,美國南部地區的人們對南方圣經地帶有著特殊的感情。他們以自身的勤勞來構建自己的家園。長期的農業生產活動使得他們意識到自然以及土地的重要性,這些因素嚴格意義上來說都對南方人的精神面貌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對大自然以及土地的熱愛是美國南方精神中最為核心的部分。
在福克納生活的時期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比如說美國南北戰爭,南方戰敗,新南方成立以及后來的一戰和二戰,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對南方地區存有重大的影響力。原本南方地區傳統的生產方式以及長久存在的奴隸制度不復存在。換句話說,南方地區是在歷史車輪的壓制之下才進入到現代社會的。社會轉型的同時,帶動的是南部地區的生產方式以及生活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當然,南北方的這些碰撞也帶來了各式各樣的矛盾和沖突,南方地區固有的保守傳統和北方文明社會的巨大進步顯得格格不入。在這樣一種大的歷史背景之下,這就好像一個人來到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般,面臨著一個重大的轉折。北方的先進文明逐漸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進入到南方社會,因而南方地區原來所存在的那種方式就顯得異常落后。當然,這樣的沖突對南部地區所存在的原有的勞動觀念勢必會形成沖擊,而這一切的根源源自殖民地時期,當時南方地區以傳統的種植園經濟為主,是不折不扣的傳統農業社會。甚至到20世紀30年代,大部分人仍然從事繁重的與體力相關的農業活動,而且傳統守舊依然是他們生活方式的代名詞。這樣的傳統生活方式以及保守主義深深地根植于南方人民的心中。而保守主義的長期存在使南方地區的人們對現代化的文明本來就心存反感,更為嚴重的是對新的思想或者宗教形式心存害怕和仇視。卡什認為:“對新思想的懷疑是南方固有的毛病之一。”[1]439更讓人意想不到的竟然是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南方地區還存在禁止進化論在學校講授這樣的法案,時不時的會發生因為有人講授而入獄這樣的事情。新思想在南方地區各個階層所造成的影響都或多或少地給當地的人們造成憤怒和恐懼。[1]336也正是由于南方社會中這種保守主義的存在,當一戰后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化蔓延到南方地區的時候,它在南方地區中所造成的震撼比美國的任何一個地區都要強烈,而南方文藝復興正是對此種震撼所做出的反映。
此外,奴隸制以及趨于嚴苛的種族主義是南方地區的另外一個顯著特征。南北戰爭之前,美國南方地區留存黑人奴隸數量大約是南方地區總人數的1/3。而在美國的南部地區,奴隸制以種植園經濟為依托。雖然美國南北戰爭過后,奴隸制表面上已經不復存在,但是,黑人這個被眾人所歧視的群體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觀。種族問題一直是南方社會的根本問題。不僅如此,南北方地區的長期沖突也源于奴隸制和未徹底解決的種族問題,而南北戰爭更是影響了南方地區的發展,當然,文學也因此處于滯后的尷尬境地。美國南方地區遠遠落后于其他地區,以致羅斯福在位時對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很頭疼。另外,由于早期的移民具有一定的開拓精神并且趨于接近大自然的種植園經濟,因而他們的性格中本身就留存有一種浪漫主義情懷,而同北方地區的長久鏖戰致使他們把自己所居的南方地區浪漫化。尤其是在留存已久的奴隸制問題上,南方民眾總是覺得自己處于社會譴責的風口浪尖。所以他們不管在哪個方面都想為自己所存在的地區進行辯護,從而創造出了自己內心世界的神話。在這樣的狀況下,奴隸主們都以一種仁慈形象被呈現出來,當然他們就會像慈父一樣照顧著奴隸們,而奴隸們肯定都會對他們心存感激并且忠心耿耿。在種植園里奴隸們過著舒服、高雅、悠閑的生活,宛若歐洲中世紀時期的貴族們一般。內戰的失利不但沒有終結他們對南方地區的美化,沒有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所生活的地區的罪惡和弊端,他們也沒有對自己的戰敗做出深刻檢討。相反,在戰爭這種催化劑之下,南部地區民眾的浪漫情結再次被點燃。所以在美國南部地區的故事和文學作品中,浪漫和甜蜜成為它們的代名詞。
四、南方“圣經地帶”對福克納文學創作的影響
基督教與西方文學的關系源遠流長,與當代西方文學的關系仍然十分密切。基督教歷來是西方作家重要的精神資源,千百年來,它對西方作家的思維方式、價值判斷、藝術理念等產生了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在20世紀,傳統信仰崩潰,旋即就是宗教信仰的回歸,眾多西方作家仍然不僅從《圣經》中汲取創作素材、結構框架和意象典故,更表現出濃厚的宗教情懷。任何事物總是存在著多面性,西方作家在自覺或被動地吸納和接受基督教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的同時,也有對后者的主動拒斥和反叛。西方文學對基督教的各種觀念或接受、宣揚,或批判、否定,或改造、發展而為己所用,對基督教各種觀念的堅持或動搖、反叛或復歸貫穿西方文學的始終,直至今日。
基督教經典《圣經》以其神學特質和文學原型模式影響西方文學。信仰學說是基督教神學的基礎。在西方文學中,信仰首先是一種信念,但也可以作為旗幟、工具或武器。基督教的盼望與神的國(天國)連為一體。文學中盼望既仰望來世又俯視現世,盼望一直與天堂、與上帝之城、與理想國密切相關。在20世紀,盼望轉向了空無。基督教的愛及其延展:仁慈、博愛、忍耐、寬恕、憐憫是西方文學大師尊奉的圭臬,是他們消除罪惡與貧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法寶。基督教禁欲主義要求世人棄絕現世的一切欲望和利益,基督教的禁欲理論與人的自然天性格格不入。基于對人的本能、人的生理屬性的肯定,歷代西方文學對合理滿足人的生理本能、欲望持肯定的態度,對人貪得無厭的權力欲,橫流的物欲,泛濫的情欲、性欲給予尖銳的批判和否定。20世紀,在進一步彰顯人性、人權的社會思潮的推動下,文學中對情欲、性欲肯定與褒揚的聲勢日益壯大,文學橫掃否定性欲的基督教禁欲主義,但也不乏基督教禁欲主義的偶爾回歸。
在福克納《高大的人們》中,麥卡勒姆一家人不但勇敢而且獨立自主,他們不接受政府所派發的津貼,當然也拒絕政府影響他們獨立自主的生活方式。政府的行為與他們一家人原來的生活以及生產方式互相抵觸,而使他們陷入這樣尷尬境地的原因便是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經濟制度矛盾所造成的。從政治方面看,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水火不容。福克納的成名作《喧嘩與騷動》中也或多或少體現了這樣的內容。福克納在后來描寫南北戰爭的小說中也明顯的表現了這一點,此篇小說充分展現了南方地區種植園主對內戰的態度。
福克納生于南方,長于南方,他對南方地區的種種也異常熟悉,南方地區這個存有圣經符號的地區,對于他來說,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曾在一次講演中說道:“作家必須從他的背景出發進行寫作,必須寫自己知道的東西,而基督教傳說是任何一位基督徒背景的一部分。我的生活以及童年是在密西西比的一個小鎮上度過的,那就是我背景中的一部分。我在這種環境中長大,同時我也消化了它,不知不覺吸收了它。”[5]868圣經和基督教的精神教義作為長時期形成的一種文化積淀澆鑄了福克納多半人生。因此,在其后來的文學作品中,濃重的宗教悲劇意識貫穿其中,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幾乎都以悲劇收場。這是因為這些人無法擺脫傳統思想和世俗觀念的層層束縛,他們因而喪失了對自身存在和對自然反應的機會。美國內戰之后,故鄉的淪陷以及南方地區固有文明的不復存在在福克納的心中濃縮成一種讓他無所適從的情感,其內心深處一直處于痛苦的彷徨之中。情感上,他對傳統南方地區有一種依戀,但是理智上,又對罪惡的舊南方心存厭惡。他自己也曾經說過他既愛南方也恨南方,因為那里是他的故鄉,無論故鄉有多少令人痛心的缺憾,他都不離不棄。所以他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南方地區現實生活中人物的真實寫照。他把現實與想像交織于其文學作品中,平凡的南方地區被賦予了一種全新的面貌,因而形成了不平凡的文學藝術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他追溯過去。在他看來,“人類心靈與自己沖突”才是宇宙永久的主題[6]。
著名學者肖明翰在《美國南方文藝復興的動因》一文中指出:“縱觀整個人類的歷史,我們發現那些最為輝煌的文化和文學繁榮幾乎都發生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抑或是社會的轉型期,并且他們都為社會的變革和當時的文化繁榮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7]
[1]W.J.Cash.The Mind of the South[M].Vintage:Vintage Books Press,1941.
[2]Edmond Volpe.A Reader’s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M].New York:The Noonday Press,1964:162.
[3]李文俊.福克納評論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58.
[4]William Faulkner,University of Virginia.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class confer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1957—1958[M].Charla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59:203.
[5]Gwynn,Frederick,Blotner,Joseph,eds.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M].Charlattesville: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59.
[6]吳偉仁.美國文學史及選讀學習指南:第2冊[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55.
[7]肖明翰.美國南方文藝復興的動因[J].美國研究,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