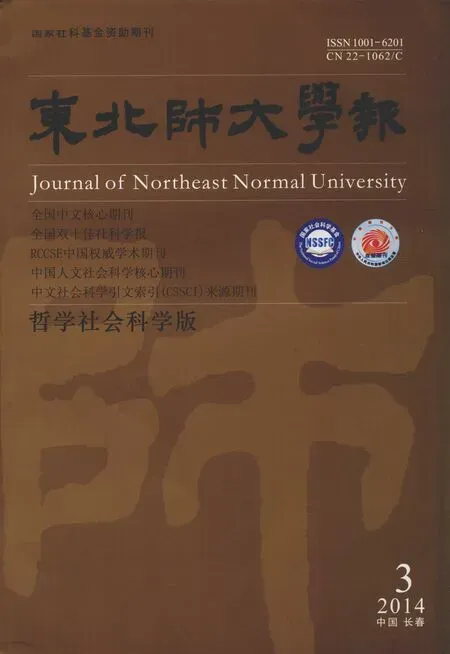“為何”與“何為”: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的政府責任論析
羅紅艷
(1.河南師范大學教育與教師發展學院,河南新鄉453007;2.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北武漢430074)
“為何”與“何為”: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的政府責任論析
羅紅艷1,2
(1.河南師范大學教育與教師發展學院,河南新鄉453007;2.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北武漢430074)
弱勢群體貧困性、劣勢性與底層性等群體特征決定了政府必須在其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充分履責。這可以從弱勢群體發生學、政府能力屬性以及公共教育職能等方面尋求學理根基。但政府在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的責任并非無限責任,而是有限責任。其責任邊界可以從市場社會語境中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多元救助體系中政府責任的地位以及由各級教育屬性不同所導致的政府責任差異等維度來予以廓清與限定。
弱勢群體;教育權益;政府責任;限度
弱勢群體,也叫社會弱勢者、困難群體、脆弱者群體、社會脆弱群體、底層社會群體等,在英文中稱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弱勢群體是指由于自然的或者自身的某些原因及社會結構性因素或者制度上的安排,導致在經濟、政治、社會競爭中處于不利處境,而需要政府給予特別援助的特殊人群。弱勢群體經濟上的“貧困性”,政治上的“劣勢性”,文化上的“底層性”,使得其子女的教育權益保護成為政府教育治理的重要責任。但為何要關注政府責任以及政府責任邊界在哪里,則需要從學理上進行論析。
一、“為何”:政府在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履責的理論依據
政府在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需要履行責任,政府責任主體的角色可以從弱勢群體發生學、政府能力屬性以及公共教育職能等角度獲得確證。
(一)弱勢群體發生學的視角
從弱勢群體發生學的角度來看,關于弱勢群體的形成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爭論:一種是“個人責任論”;一種是“社會責任論”。前者認為個人原因是造成某些成員淪落為弱勢群體的根本原因。他們從個人特殊性的角度提出問題,為什么別人沒有落到這種地步?其潛臺詞是,這些人淪為弱勢群體是由當事人個人及其家庭因素造成的。但是20世紀中葉以來,“社會責任論”開始成為主流的觀點。此種觀點認為弱勢群體是由于壟斷和信息不對稱等市場不完全競爭造成的,是社會變遷、利益分化重組使他們失去了機會而被邊緣化,是政府的政策偏向強者而拋棄了后來成為弱勢群體的人們。說到底他們是社會資源(包括教育資源)不平等分配的受害者,是貧困循環的產物,所以責任在政府。因此,“政府負有減輕貧困的責任——或者是向窮人提供收入保障,或者是改善產生貧困的條件”[1]。
對我國弱勢群體做發生學維度的分析,也需要從“個人責任論”向“社會責任論”做思考轉向。除了生理性弱勢群體之外,社會性弱勢群體已經成為我國弱勢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仔細分析起來,我國現有的社會性弱勢群體大體上包括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城市下崗工人等。從發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對應形成的城市中心資源配置模式造成了農民利益的長期缺失;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鎮化、工業化戰略轉型必然帶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遷徙,進城務工人員為社會文明做出了貢獻,但自身也成為弱勢群體;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型帶來經濟領域的結構性調整,造成了國有企業職工的大規模下崗,城市下崗工人成為又一新的弱勢群體。可見,為推進現代化進程我國所實行的制度轉型與調整是不可避免造成弱勢群體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作為制度安排與政策供給責任主體的政府,理所當然要通過建立新的制度與政策來緩解與消除弱勢群體的弱勢地位與不利處境。
(二)政府能力屬性的視角
政府能力是政府為實現自身的目標與任務而擁有的可以將自己的意志轉化為現實,進而有效治理社會的能量與力量的總和。在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過程中之所以要強調政府責任,與政府能力屬性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
首先,政府是公共暴力合法使用的壟斷者,對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予以保護有利于增強其壟斷公共暴力的合法性。資源相對稀缺與人的欲望無限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類從原本上看充滿矛盾與沖突,這使得政府公共暴力具有合法性,但其合法性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是公正的,不會偏袒任何一方。然而,轉型期社會制度與變革的偏差致使社會性弱勢群體的廣泛產生,生理性弱勢群體的生存、發展機會也大打折扣,以至于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公平的缺失,使得弱勢群體容易滋生相對剝奪感,對廣泛的社會秩序構成了潛在的危機,這直接影響到政府的合法性與公信力。因此,對弱勢群體,尤其是對其子女進行教育救助,是政府當然的責任。
其次,政府有汲取公共資源的能力,對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予以保護需要社會公共資源強有力的支撐。在現代國家背景下,政府是一個不能生產財富的公共組織,政府必須從社會中汲取公共資源來維持自身運轉。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講,現代人將政府的公共財政視為國家的血液和政府的神經。公共資源的汲取,是政府存在的基礎,是政府施政的前提條件。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的保護最直接的就是教育機會的創設、教育條件保障、優質師資的配備,而這些教育權益各個要素環節均需要有國家公共資源做后盾。政府汲取社會公共資源的能力屬性恰恰滿足了這一條件。
再次,政府有政治動員的能力,對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的保護需要全社會的一致認同與形成共識。社會弱勢群體保護,必須依賴政府的政治動員能力。社會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的首要前提是,必須讓所有社會成員認識到保護社會弱勢群體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為了促使社會成員就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達成共識,政府必須發揮其政治動員能力,使自身對社會弱勢群體實施保護的行為正當化,使社會公眾支持政府的救助行為,減少在沒有共識的基礎上所必然出現的阻力。另外,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的保護也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它需要全社會的統一行動,共同救助。因此,政府動員也有利于喚起全社會共同投身到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的保護中來。
(三)公共教育職能的視角
從公共教育職能的視角看,政府也應當承擔起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的責任。近代以來,教育已不再是少數特權階級實現其所屬階級地位復制與再生產的途徑;不再是純粹宗教力量傳遞教義、誦讀經典的工具;也不再僅僅是少數人附庸風雅、顯示高貴的一己私事。教育開始從特權走向大眾、從宗教走向世俗、從私己走向公共,教育開始成為全社會人們的事情,開始承載著越來越多的社會職能與公共價值。
首先,教育承載著促進個體社會化的職能。每個人都包含了“個體我”與“社會我”兩個部分,而公共教育價值越來越多地體現在促進人的社會性發展,實現和完成“社會我”的塑造上。“教育是年長的幾代人對社會生活方面尚未成熟的幾代人所施加的影響。其目的在于,使兒童的身體、智力和道德狀況都得到某些激勵與發展,以適應整個社會在總體上對兒童的要求,并適應兒童將來所處的特定環境要求。”由此,進一步得出的結論是,教育的功能就在于我們“怎樣才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達到這一目的”,使教育者成為適應社會生活的“社會我”[2]。政府通過對社會成員,尤其是對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的廣泛保護,把普遍認可的核心觀念與價值準則傳輸給每個社會成員,以形成公共意見,有利于消除社會分歧,增進社會理解,達成規則共識,從而獲得一種消除社會懷疑、增進社會穩定的力量。
其次,教育充當了向上社會流動篩選器的角色。隨著我國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長期以來的依靠身份屬性的社會分層機制已經逐步轉向能力本位的社會流動制度。而社會個體接受教育的類型、層級以及與此相應所獲得的學歷則成為個體能力水平的基本的憑證與依據。社會學研究表明,個體在突破階層壁壘向上流動的過程中,教育是最為重要的促進機制。通過改進貧困階層后代的受教育狀況,進而使他們在未來的勞動力市場上找到一個合適的職業位置、獲得較好的社會生活機會,是改變貧困階層代際世襲模式的主要方式[3]。一方面,教育在弱勢群體子女向上社會流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權力資本、經濟資本以及文化資本上的劣勢地位,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的享有方面勢必處于劣勢,在這種情況下,就特別需要作為社會利益調節閥的政府有所作為,通過政府行為對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做專門的、補償性的保護以使其子女擺脫弱勢累積與代際傳遞的困境,最終實現向上社會流動。
二、何為: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政府責任的限度
如前所述,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需要政府履責,但政府應該履行完全責任,還是有限責任?政府責任體現在哪些方面?等等,均需進行分析。
(一)市場社會中教育、政府之間關系的重塑:基于政府職能定位的分析
首先,要重新審視政府與教育之間的關系。建國之初,我國以蘇聯模式為榜樣,建立起了計劃經濟背景下以高度集權為特征的教育管理體制。政府既當“掌舵者”,又當“劃槳者”。隨著社會發展日趨加速、社會關系日益復雜以及社會轉型深入推進,這種全能政府的教育管理模式不僅束縛了教育活力,也不利于教育公平的有效實現。誠如美國學者E.S.薩瓦斯所言,“政府這個詞的詞根來自希臘文,意思是‘操舵’。即政府的職責是掌舵而不是劃槳。”[4]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政府與教育之間的關系也得以重新塑造。讓渡“劃槳者”角色,充分履行“掌舵者”責任,確立基于市場社會的政府教育責任體系構成了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政府責任的理論基礎與價值前提。
其次,要厘清政府在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的責任邊界。在市場語境中,政府教育活動中“掌舵者”角色主要體現在教育制度安排與法規政策供給方面。這在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中也不例外。其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教育規章的制定責任。市場經濟時代亦即法治時代,政府對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的保護應主要從依靠行政手段轉向以依靠法制手段為主。通過法律法規的制定,使對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的保護從道德上的呼吁轉變為法律上硬性規定,有法可依是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得以保障的首要條件;第二,教育法規的執行責任。政府是教育法規的執行者,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要從潛在的紙上權益轉變為現實的實際權益,需要政府充分履行其義務,利用其公共暴力壟斷者、公共資源汲取者、政治行為動員者的地位嚴格執法,使教育法規成為弱者教育權利保障的利器。第三,對學校主體進行監督與評估的責任。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的落實歸根結底要落實到學校教育的微觀層面。貧困大學生的資助政策、城市流動兒童的入學政策等弱勢群體子女的教育權益保護最終還得落實到學校層面。而政府應該成為學校履責狀況的監督者與評估者。
(二)政府責任與社會救助、自我維權的關系:基于救助途徑的分析
從保護途徑來看,要想真正實現對弱勢群體子女的教育救助,必須建立政府、社會以及弱勢群體自身多元救助的立體模式。政府在立體化的多元救助中發揮主導作用。
首先,態度與價值上的主導責任。態度決定行為,價值引導實踐,政府應該樹立正確的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保護觀,以政府態度主導全社會態度。目前,社會上關于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救助方面存在兩種誤區:一是無需救助觀。弱勢群體之所以會陷入弱勢困境,是因為他們自身的能力不足或者勤奮不夠,如果對弱勢群體子女進行特別的教育救助,實際上是縱容了懶惰行為的發生,這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公正。二是無需教育救助觀。由于教育具有遲效性與模糊性,對弱勢群體子女進行教育救助不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對弱勢群體進行經濟援助比對其子女進行教育救助更為緊迫,也更加重要。如前所述,走出無需救助的誤區需要政府實現從個人責任向社會責任的價值轉向,走出無需教育救助的誤區則需要政府實現從補償性的社會救助向發展性的教育支持的態度轉向。除此之外,還需要明確的是,對弱勢群體的教育救助是全社會的責任,尤其是政府的責任。由于政府態度與行為在社會中具有宣示與導向的作用,政府應該在教育救助中形成明確的態度以及做出行為上的表率。
其次,財政與經濟上的主導責任。經濟上的貧困是造成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難以保障的瓶頸性因素之一。2004年全國高校在校貧困生的比例為20%,有的高校貧困生高達30%左右,個別高校甚至達到60%[5]。即便是在國家政治經濟中心的北京,此種現象也普遍存在。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市參加2005年夏季高考的考生中,貧困生比例占11.8%;其中逾七成家庭年收入低于6 000元,近四成教育支出超過6 000元,近四成家庭負債上萬元[6]。可以說,幫助弱勢群體子女走出經濟困境是保障其教育權益的基礎,也是關鍵。對弱勢群體子女進行經濟救助的途徑可以多元化,比如,鼓勵各界愛心人士捐資、集資;在有條件的地方建立教育基金會;幫助弱勢群體實現充分就業,從輸血式救助變為造血式救助,等等。但社會救助畢竟不能強制,需充分自愿,因而不具有廣泛的救助意義,自我救助則因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而不能解決當下的教育困境。因此,政府通過公共財政的傾斜性與補償性安排,以從根本上解決弱勢群體子女教育上的貧困處境在多元經濟救助途徑中具有主導的作用,因為“國家公共財政是興辦帶有公益性質的各項社會事業的最強有力的保障。”[7]
再次,程序與實體上的主導責任。歧視是造成弱勢群體子女教育權益得不到保障的重要原因。“歧視一般通過正式制度的方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方式來實現。前者指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層面上以法律、法規、條例、政策的形式將含有歧視性的內容予以制度化,后者指以某種社會風氣、價值觀念、習慣的方式對某些人群進行排斥和限制”[8]。破除對弱勢群體及其子女的制度性歧視,需要政府在制度安排與政策供給的程序公正與實體權益兩個方面發揮主導責任。從前者而言,要疏通渠道,健全制度,充分保障弱勢群體教育利益表達的途徑與機會,充分尊重弱勢群體在其子女教育權益方面合理的權利主張與利益訴求,以程序公正保障實體權益。從后者來看,政府應該通過理性的制度設計保障弱勢群體子女享有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機會,為保障其成才提供同等的資源、創造同等的條件,保障包含經濟權益在內的實體教育權益。
(三)各級教育屬性及其與政府責任的關系:基于教育屬性的分析
根據教育的“級”上差異,可以將教育大體分為“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由于兩者的屬性不同,政府在弱勢群體子女接受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中的責任及程度是有區別的。
首先,在義務教育階段,政府承擔完全責任。從本質屬性上看,“義務教育作為法律規定實施的強迫教育,其實質是一種贈與性機會。”[9]這種機會是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而且應該平等享有的,不應該因為經濟、政治、地域、城鄉、父母的身份等因素而有所區別。政府在弱勢群體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平等方面承擔完全責任。具體來說,第一,利用法律與政策供給保障弱勢群體子女享有受教育機會,使每個弱勢群體子女的受教育權成為法定權利;第二,在經費上的完全保障責任。切實履行《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真正做到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并且給予弱勢群體子女接受教育的特別經費保障;第三,健全有利于弱勢群體子女義務教育權益享有的辦學機制。政府應該采取措施促進學校標準化建設,促進學校均衡發展;取消重點學校制度,嚴禁學校分設重點班與非重點班,杜絕教育中的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把教育公平作為義務教育的首要辦學價值;第四,建構弱勢群群體子女義務教育權益保護的政府責任履行督導機制與問責機制。
其次,在非義務教育階段,政府承擔充分責任。如果以產品性質為依據將產品進行分類的話,可以把產品分為純公共產品與純私人產品,而非義務教育則屬于介于兩者之間的準公共產品,比如學前教育、高中教育等。一方面,公民接受非義務教育可以增強國民素質,提高社會整體的文化與文明程度,具有公共性;另一方面,對非義務教育的享有可以給受教育者帶來個體收益,比如,良好的職業、體面的工作、豐裕的收入等。因此,非義務教育也具有私益性。由于它的公共性,政府需要承擔責任;由于它的個體收益性,受教育者本人也理應支付一定的教育成本。當然,弱勢群體子女也不例外。但是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公共資源十分緊缺,政府把有限的資源注入義務教育,致使對非義務教育總體投入嚴重不足。經濟資源的匱乏與社會支持的不足使弱勢群體子女處于明顯的不利處境,其教育權益的切實保障需要政府承擔充分責任:第一,非義務教育準公共產品屬性的特征要求政府必須承擔責任。而且隨著非義務教育的逐步普及化,其公共性較私益性的成分日益增多,政府履責必要性也逐步增強。第二,弱勢群體的弱勢處境決定了政府在其權益實現過程中要承擔比其他的社會群體更多的保障責任。非義務教育不能“錦上添花”,而應該“雪中送炭”。第三,對弱勢群體子女非義務教育權益的保障應該通過補償原則來實現。“補償原則認為,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的機會,社會必須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較不利社會地位的人們。”[10]
[1]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288.
[2]張人杰.國外教育社會學基本文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9-23.
[3]劉精明,楊江華.關注貧困兒童的教育公平問題[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2):120.
[4][美]戴維·奧斯本,特德·蓋布勒.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著公營部門[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1.
[5]陳至立.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C].在教育部直屬高校工作咨詢委員會第十五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05-01-10.
[6]新京報.貧困高考生沒錢上大學資助貧困考生行動今啟動[EB/OL].[2005-07-12].http://news.sohu.cocom/20050712/n226271565.shtml.
[7]吳華.國家教育公平政策的思路、問題與對策[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2):154.
[8]吳忠民.歧視與中國現階段的歧視[J].江海學刊,2003(1):100.
[9]姚本先,劉世清.論弱勢群體子女的教育公平[J].教育發展研究,2003(8):57-59.
[10]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01.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Its Limits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ducation for Children of Vulnerable Groups
LUO Hong-yan1,2
(1.Education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Colleg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2.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Huazhong University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It is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such as disadvantage,the fragility and need help that the government claims responsibility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ducation for children of vulnerable groups.It can get academic explanation from ontogeny of vulnerable education phenomenon,attributes about th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ttribute of public education.Yet the government has not the unlimited liability;but has limited liability.Responsibility border of the government can be clarified and limited from the new fixed position of governmental func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society,the rol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in multiple assistance system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caused by attribute of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Children of Vulnerable Groups;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ducation;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Limits
G40
A
1001-6201(2014)03-0196-05
[責任編輯:何宏儉]
2014-02-19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11JYC880075)。
羅紅艷(1974-),男,湖南洞口人,河南師范大學教育與教師發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