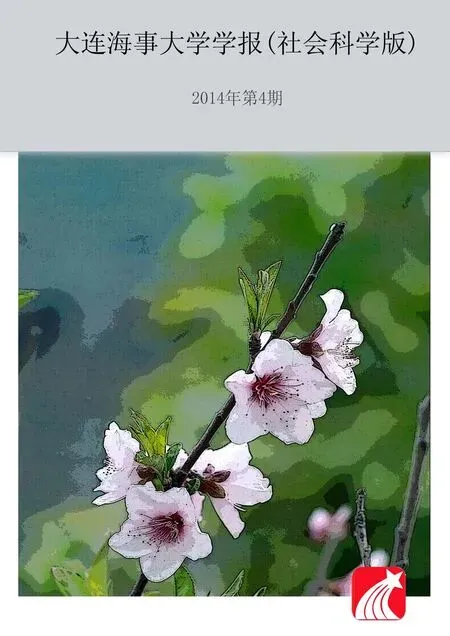創傷記憶與赫塔·米勒的文學創作
胡冰霞,谷 珵
(1.武漢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武漢 430062; 2.新金融文化傳媒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天津 300000)
作為歷史上第12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女性獲獎者,赫塔·米勒這個名字也許還并不廣為人知。她的作品真實地描繪出了齊奧賽斯庫獨裁統治時期羅馬尼亞的生活圖景,語言詩性而犀利。對于米勒來講,集權政治下的創傷記憶構成了她創作的主要基調與思想源泉,深刻地影響了作家的審美觀照與藝術表現,賦予其作品獨特的風貌。赫塔·米勒秉持著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在對自身創傷記憶的不斷梳理與重新構建的文學創作中,叩問著人類生存困境中的人性與尊嚴。
一、創傷的源頭:集權統治下的鄉村記憶
“創傷”(trauma)一詞本源于希臘語,到了19世紀末期被普遍應用于心理學領域。弗洛伊德對此進行了這樣的定義:“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1]對于誕生在齊奧賽斯庫統治時期的赫塔·米勒而言,集權統治的創傷記憶深深烙印在她的人生履歷中,與她的文學創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米勒自己就坦言道:“我的寫作必須停留在我受傷最深的地方,否則我不需要寫作。”[2]150她的作品根植于集權統治下的社會經歷,展示出一幅在獨裁政治籠罩下從鄉村到城市的落后貧瘠、恐怖彌漫的畫卷,以大角度蘊含了整個國家與民族的孤獨。
赫塔·米勒出生在羅馬尼亞蒂米什縣的一個偏遠落后的小山村,是個遠離城市卻沒有遠離政治的地方,屬于羅馬尼亞的德意志少數族裔,二戰時期曾支持納粹德國,米勒一家也包含在內。這種獨特的民族屬性決定了她在齊奧賽斯庫當政時期所受到的待遇。米勒的外婆是虔誠的宗教徒,每晚睡前都要唱贊美詩作為米勒的催眠曲。但小米勒覺得既然那些愿望無法達成,贊美詩就都是陳詞濫調。父親酗酒,母親終日為勞作操心,為自己嫁給酒鬼的命運哭泣,沒有太多剩余的精力關照子女的情感。米勒非常渴望得到親人的關愛,每天早上出門前,都要等母親詢問帶沒帶手絹,以此獲得不會直接表達感情的母親的關心。可以說,赫塔·米勒就是這樣一個早慧的女孩,擁有著敏感而豐富的內心,從幼年便顯現出與他人的不同。
隨著年齡的增長與價值觀的逐步形成,米勒更加體驗到鄉村閉塞狹隘、愚昧停滯的生活和濃重的政治陰影,并將這些記憶反映在日后的文學創作中。她的處女作《低地》是這一類型作品的典型代表,以一個孩子的眼光敘述出集權統治下落后的鄉村風貌。《施瓦本浴》中,米勒用相同的句式不斷反復,描寫一個鄉村家庭祖孫三代在同一缸水中洗澡,最后,祖父從身上搓下的泥垢與祖母、父親、母親和女兒的污垢混合在一起,遺留在排水口的上方。《鄉村紀事》里,教師組織學生分成兩個民族,進行暴力與混戰的游戲。小說《人是世界上的大野雞》(以下簡稱《人》)則從另一個側面體現出鄉村的愚昧:村民之間流傳著蘋果樹會吃自己的果實,于是集體將蘋果樹焚燒了,盲從與迷信占據了每個人的頭腦。狹隘的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更加劇了村落的封閉,凝滯的氛圍難以被打破。
而在落后鄉村背后發揮作用的,是充滿迫害、腐朽沒落的集權統治。在極權統治下的生活環境里,酗酒、貪污、死亡等現象司空見慣。米勒筆下多次出現的屠宰場和死獸園意象就是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羅馬尼亞的社會現實的象征。在集權的暴力之下,恐懼彌漫在每個角落。從年幼時代,米勒就已經將恐懼的感覺深入腦海。《人》是一個隨著死亡事件而進行的故事,通過等死、死亡、葬禮將小說從時間上串聯起來,死亡的腳步如影隨形。
在這樣的環境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充滿猜忌和敵對。米勒筆下從未有過牧歌般的田園生活與淳樸的人際關系,取而代之的是秘密警察的肆意活動、普通人之間互相的窺探與傾軋。《人》里,神甫利用職務之便,占那些想辦理移民手續的婦女的便宜,將法衣室用來干骯臟的勾當。《心獸》中,同伴對一個寢室的蘿拉的死亡抱著漠然視之的態度。身邊的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是情報機構安插的眼線,即便在酒館,也要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議論政治。
這種踏著他人向上爬的毀滅性已經成為集體遺傳基因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個體,即使是在一家人之間,也無法輕易彼此理解。“父親只能獨自承擔他酗酒的生活……母親沉湎于丈夫酗酒的痛苦,將自己的孩子棄之不顧。外公獨自守著他的發票表格,外婆手里永遠舉著陣亡兒子的照片和經書。”[2]65米勒的整個家庭都沉浸在這份孤獨與隔絕之中,每個人都無法幫助他人走出深淵,每個人都無法自救。
帶著這份沉重的孤獨,米勒來到一心向往的城市,然而城市的生活卻并不能令人滿意。伴隨著從封閉的德語農村到多語混雜的城市的空間轉換,語言和價值觀念的變化都對她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我痛苦地認識到,村里‘精英’們的自視甚高都是自以為是的幻覺,他們的理念在離村子只有三十公里的城市全部成為廢話,一文不值。”[2]133周圍是羅馬尼亞令人窒息的社會氣氛和肅殺的文化環境,思戀故土的情緒開始攀升。城市中物資匱乏,全國大的商店中僅有為數不多的幾樣商品,服裝店里的衣服樣式、材質和顏色都是相同的,生活必需品只能通過“黑市”上的交易得到。《心獸》中主人公在城市四處游蕩時里看到的是乞丐、殘疾人、每個城區的瘋子,并一語道破這貧瘠背后的真相:“獨裁者治下不會有真正的城市,因為監視著,什么都大不起來。”[4]
在大學階段,米勒加入了一個德裔青年作家組織——“巴納特行動小組”,他們抗議齊奧塞斯庫的統治,追求創作自由。畢業后,精通兩門語言的米勒在一家機械制造廠擔任科技翻譯。1979年她拒絕為國家安全部門充當秘密線人,此后不斷受到秘密部門的審問和騷擾。卡如斯認為,所謂“精神創傷”就是“受害人在毫無準備和極其恐懼的狀態下遭遇某一驚人事件所產生的復雜情感,先前的知識結構無法為它作好準備”[5]。這種創傷記憶一旦形成,就會在日后的生活里不斷往復地出現在當事人的意識中,成為“自我重復的固置形式”[6]。可以說,這段突發的往事影響了米勒一生的軌跡,是其創傷記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并反復投射在她的文學創作中。《心獸》里的每個主人公也都有著被審問的記憶。情報部門總是會威脅主人公要制造各種看似意外事件來解決掉異己,在主人公的生活圈子內散布謠言使之被排擠到孤立的位置。不僅如此,秘密警察還時常造訪主人公的家中進行搜查。《狐貍那時已是獵人》中的阿迪娜,每天下班回家都會發現掛在臥室的狐貍尾巴短了一截;《心獸》里,“我”和朋友們用放置頭發來檢測房間里是否來過情報人員,信件是否被拆開過。頭發在赫塔·米勒的文學世界中總是與權力聯系在一起。
情報機構的刁難使米勒不堪其擾,更打擊她的是身邊朋友的背叛。米勒有一名女友,被安全部門買通來刺探她的生活。這一往事對米勒的創傷深重,被多次在作品中書寫,《心獸》中的苔蕾莎就是以女友為原型塑造的。來自鄉村的“我”與城市姑娘苔蕾莎成為朋友,盡管兩人的性格愛好相去甚遠,但漂亮單純的苔蕾莎依舊取得了“我”的信任。但是,這份信任終究落空,“她承認是秘密警察讓她來的”。秘密警察的騷擾和生活的絕望使米勒一度想在河里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在口袋里塞滿大石塊正欲投河時,她認出了原來石塊放置的地點,改變了初衷。后來她這樣描述了這段經歷:“死神在向我招手,我做好了起跑的準備,在幾乎得手之際,細小的地方卻不愿配合。或許那就是心獸。”[2]78
死里逃生的米勒,以更加冷峻的目光審視著獨裁統治下的羅馬尼亞。正如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談到的,極權主義的統治是以恐懼作為行動原則的,“統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統治者”[7]210。恐懼的情緒蠶食著生命的自我,充斥在日常生活中。作者洞察著集權恐怖下的人的本性,“仇恨允許踐踏,允許毀滅。親密無間的人允許割愛”[2]67。米勒在記錄這種恐懼的同時,也透視出恐懼背后的希望。人們用幽默的笑話、諷刺挖苦以及自嘲來緩解恐懼的氣氛,幻想著政權的解體,也在其中尋找著生命的存在感。而就是憑借著這種生命欲望,赫塔·米勒將這些集權統治下的創傷記憶投注到寫作中,并于1987年離開了飽受政治鐵蹄踐踏的羅馬尼亞,移居德國。
二、記憶的綿延:流亡異鄉中的創傷心靈
盡管離開了創傷之地,但昔日的記憶與受創的心靈并未遠離作家,并在新的環境中被觸發和延伸開來。雙重身份使米勒在德國遭遇了尷尬的處境,體驗到異化社會中人與人的陌生感,也促使她審視著德國的歷史與現實,繼續著對權力的反抗。同時,她從未放棄對羅馬尼亞的關注,并以高度的道德責任感揭露了羅馬尼亞歷史上一段不為人道的黑暗記憶,探尋著困境中人類的尊嚴。
初到德國的赫塔·米勒并不順遂。投奔德國的初衷是因為對母語國度和自由以及生存空間的向往,然而迎接她的卻只有失望。多年之后,她在文章中這樣形容自己的處境:“遠走他鄉的樹像背井離鄉的人,在恰當的時刻離開了危險的地方,找到一塊不很恰當的土地,在其中一個錯誤的地方停下來,再也下不了決心繼續走下去。”[2]9
作為擁有雙重身份的米勒——在羅馬尼亞,她是少數民族作家;在德國,則被視為移民作家,被邊緣化的處境和政治流亡的困境使之在德國這片新土壤上備受冷遇,境地尷尬。小說《獨腿旅行的人》是作家這一時期經歷的生動寫照。[8]政治逃難的伊蓮娜從東歐抵達德國,充滿了移居后的孤獨與迷茫。
資本主義的異化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異常陌生,充滿隔閡。小說中,海邊的男子可以每天在黑暗的夜晚對著陌生女子自瀆,卻不能演變為一場光天化日下的愛情。在街頭接吻的情侶,“連彼此的手都不碰一下……沒有激情,就連戲里的那種輕浮都沒有”[3]。伊蓮娜在德國的第一個落腳點——臨時難民收容所位于一條死胡同里,象征她在這里同樣沒有出路。伊蓮娜尾隨著兩個陌生人偷聽他們談話,只是渴望與人交流。她總是在給情人弗蘭茨寫卡片,如同寫在虛空中,而施特凡總是對著她滔滔不絕地表白自我,每個人都在自說自話。正是這種異化感加劇了“獨腿旅行”的疏離與孤獨,作者用詩意的清淡的語言勾勒出人與人之間遙不可及的距離感。
盡管米勒遠離故土,但是舊日的創傷記憶并未從她的思想中淡出,相反還在新的環境下得到進一步的觸發。弗洛伊德曾提出“重復強迫”的概念來解釋創傷的再現。他指出,創傷記憶會作為一種體驗強行出現在受害人的生活中。當米勒于街頭看到一則踩著男人的手的高跟鞋廣告,就會難以避免地由畫面中暴力的復制與傳承聯想到獨裁統治。在《一顆熱土豆就是一張溫馨的床》(以下簡稱《一顆》)中,她犀利而準確地指出德國的優越感意識和平庸思想都是導致納粹的原因。納粹的模式與獨裁、集權有異曲同工之勢,是不能被遺忘的。納粹給普通人造成的傷害沒有結束,使德國人“失去了房屋和家園,他們的民歌和習俗也被用來為這場戰爭服務……他們拼命做苦工,為了逃避這滿目瘡痍的一切”[9]40。米勒所表現出的,是對歷史的尊重與對遺忘的抗爭。
對于曾經的祖國,米勒本人從不輕易表達對故土的懷戀。“當我離開羅馬尼亞時,把離開戲稱為‘變換地方’。我拒絕所有感性的詞。正如我從未提及過‘家鄉’或‘鄉思’之類的概念。”[9]271但是,羅馬尼亞發生的一舉一動都深深牽動著米勒的心。在米勒看來,齊奧賽斯庫政權被推翻后,羅馬尼亞卻并沒有從集權、暴力、殘害人權中解放出來。以前的政治課被現在的“民主”課取代了,教師依然是當年的教師,新的情報機構被安插在舊的情報機構辦公的地方。政府沒有發放革命中致殘者的撫恤金,“又開始按照老模式監聽電話,閱讀信件、威脅和策劃車禍”[9]136,焚燒吉普賽人的住處這類對邊緣群體的排擠事件仍然存在。“和平只提供了一個具有意義的轉折點”[7]12,羅馬尼亞仍舊處在權力的鉗制與思想的狹隘中。在這樣的情況下,米勒將自己的創作眼光投放到羅馬尼亞德國后裔在蘇俄時代的遭遇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關于這段往事,米勒其實從幼年就已經有了相關的記憶。米勒的母親在二戰后曾經與許多德裔羅馬尼亞人一樣,被羅馬尼亞政府流放到蘇聯,在烏克蘭的一個勞動營里接受了五年的勞動改造。米勒的母親并不是村中的個例,幾乎所有那一輩的人都遭到過流放。年幼的米勒就一直聽說關于蘇聯的消息,日后就自然而然地萌生出創作這一題材的想法。早在米勒先前的文學作品中,就已經隱約有了關于這段歷史的折射。《人》中,溫迪施的老婆就是被流放俄國人群中的一個,在條件惡劣的勞動營中只能靠與不同男人發生關系來換取食物和生活基本保障。《一顆》則記錄了一個在二戰期間沒有加入黨衛隊的羅馬尼亞德裔人被改造的真實經歷。2001年,米勒開始著手記錄下村里以前被流放者的訪談,并通過對當時也在流放隊伍中的作家奧斯卡·帕斯提奧的采訪最終鑄就了小說《呼吸秋千》。
《呼吸秋千》以奧斯卡·帕斯提奧為原型,以一個17歲男孩的視角書寫了勞動營的記憶。主人公雷奧因為同性戀罪而被流放,在最初離開家庭的時候,他絲毫沒有感覺到恐懼,反而慶幸自己離開了連“石頭都長著眼睛”[10]2的小城,對降臨的噩運全然無知。然而,自踏往俄國的那一刻,噩夢便開始了。在去往俄國勞動營的途中,所有人被迫集體在月夜下的雪地脫褲子方便。在勞動營中,人失去了最基本的價值與尊嚴,他們在生活基本需要都難以滿足的條件下被迫從事著鏟雪、修復鐵路、運煤、挖樹洞、清理糞池、春秋大掃除、粉刷街道等各種體力活動。而對他們折磨最深的,卻是發了瘋一般的饑餓。當同伴因饑餓或者疾病死去時,埋葬他們的人要將死者的衣物扒下來,以抵御刺骨的嚴寒,尋找活下去的機會。生存成為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標,人的價值體系完全顛覆,發揮著本能像動物一樣生活。
雷奧在一次賣煤的過程中,饑餓難忍,想用一塊煤換點吃的。當他敲開了一扇門,一位俄國老媽媽出現在門口,并讓他進屋給他熱湯。當她看見他匆忙吃得連鼻尖上都是湯汁的時候,遞給他一塊有格紋花邊、刺繡精密的白色手絹。手絹既顯示出安慰,又映襯出他遠離人類文明的窘境。勞動營的可怕不僅在于對人生命的威脅,更在于它對人價值的質疑與思想的鉗制。米勒書寫的不僅是羅馬尼亞德裔的放逐歷史,更探討了個人在極權社會中的真切體驗。
然而,米勒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她不放棄對人類尊嚴的找尋。盡管在勞動營中人性本能的陰暗與丑態百出,但人們還是努力維持著人之為人的內涵。小說中設置了一個特殊的角色——白癡巡夜人卡蒂。她天生智力低下,不知何故也到了流放者的隊伍中。和勞動營的每個人都不一樣,“她不做選擇,只做最簡單的事,隨遇而安”[10]94。她不受制度的指揮,暴力和強權對她絲毫不起作用。作者借一個白癡的形象揭示了權力的虛妄。勞動營中的人都以格外寬厚的標準對待卡蒂,如果有人偷了卡蒂的食物,會遭到集體教訓。這名白癡的存在,使勞動營的人感到還有善良的存在與人性的微光。
三、結 語
在談到記憶的時候,米勒這樣寫道:“神經被摧殘后無法復原,它在以后的歲月中會永遠處于緊張狀態,甚至會追溯到從前,它改變著后面的,也改變著前面的事物。”[2]76集權統治時代的創傷記憶在米勒心中是難以消解的,這種精神的創傷通過她的寫作表達出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秘書長彼得·恩隆德說:“當我讀到她的書時,我的內心受到強烈的震撼……完全逼真地講述了歷史,具有難以想象的深度。”[11]她以高度的道德責任感追溯著歷史的記憶,持久地反抗著遺忘,在卑微之處尋找人的尊嚴。創傷記憶是孤獨的,卻也賦予了她獨特的文學秉志。照片上的赫塔·米勒,總是一襲黑衣,警覺的雙眼洞穿著人性的黑暗,唇角緊閉著下垂,仿佛所有言說的途徑都被封閉,唯有見諸筆端的才是真實。
參考文獻: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217.
[2]米勒.國王鞠躬,國王殺人[M].李貽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3]米勒.人是世界上的大野雞[M].陳民,安尼,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134.
[4]米勒.心獸[M].鐘慧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33.
[5]衛嶺.奧尼爾的創傷記憶與悲劇創作[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3.
[6]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5.
[7]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M].林驤華,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8]安尼,谷裕.《獨腿旅行的人》與對赫塔·米勒小說的非政治性闡釋[J].長江學術,2011(1):24-28.
[9]米勒.鏡中惡魔[M].丁娜,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10]米勒.呼吸秋千[M].余楊,吳文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11]張帆.赫塔·米勒:一個被“放逐者”的邊緣寫作與詩意抵抗[J].譯林,201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