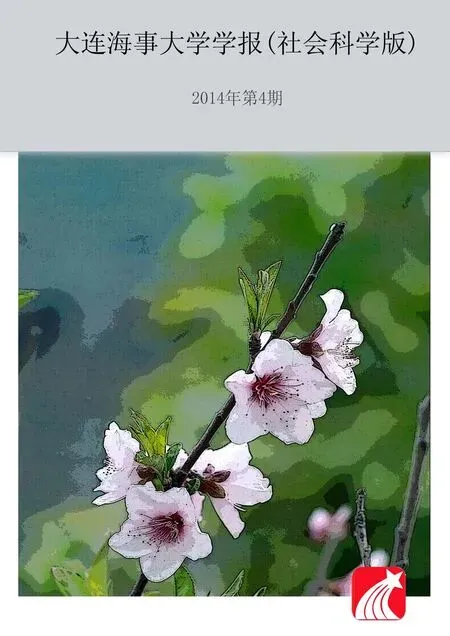文學翻譯的文本、系統與折射
胡小倩
(大連醫科大學 外語教研部,遼寧 大連 116044)
20世紀70年代后期,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界異軍突起,并成為時代的主流。與此同時,翻譯理論也受到該種思潮的影響,呈現出一派多元化的景象,其中最為耀眼的莫過于“翻譯研究派”的興起。該派學者主要探討的是“譯文在什么樣的文化背景下產生,以及譯文與目的語的文學規范和文化規范的關系”,他們更加“注重考察政治、歷史、經濟和社會制度等因素對翻譯的影響”[1]156,因此又被稱作“文化學派”。本文所探討的勒菲弗爾的翻譯思想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1944—1996),著名的旅美比利時學者,生平撰寫過多部專著,發表論文百余篇,在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領域均享有盛譽。他的關于文學翻譯的文化理論在西方翻譯界更是備受關注,該理論的雛形最早見于其在1982年發表的評論文章——《大膽媽媽的黃瓜:文學理論的文本、系統和折射》中。本文在對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追根溯源的基礎之上,欲以文學文本為依托,對其作更深入的探討,旨在為文學翻譯提供一個多元化的視角。
一、勒菲弗爾關于文學翻譯的文化理論
勒菲弗爾在吸收了佐哈(Zohar)和圖里(Toury)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文學系統的概念和標準作了重新定義。他指出,“翻譯、批評、評論、歷史文集、文學選集和戲劇等都是一種‘折射’”[2]235,翻譯就是“把文學文本從一個系統折射到另一個系統”,“并且由贊助人、詩學和意識形態所決定”[2]217。
在《文學理論的文本、系統和折射》一文中,勒菲弗爾選取了德國著名戲劇大師——布萊希特*布萊希特(Bertlt Brecht,1898—1956),德國著名戲劇家兼詩人。早年參加過德國革命,信奉馬克思主義。1933年希特勒篡權后,他流亡國外。其間創作了包括《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伽利略傳》《高加索灰闌記》等在內的多部代表作。的名篇——《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以下簡稱《大膽媽媽》)*《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是布萊希特的一部敘事劇作,通過描述一位潑辣、狡猾、想靠戰爭發財的大膽媽媽和她的三個子女在戰爭中凄慘、辛酸的經歷,再現了戰爭的殘酷,從而喚醒人民爭取和平的信念。該劇先后由海斯(H.R.Hays)、本特里(Eric Bentley)和曼海姆(Manheim)三人譯成英語,其中以本特里的版本最為廣泛流傳。的三個英譯本作為藍本,闡述了他關于文學理論中的文本、系統以及折射的觀點。
文章開篇,勒菲弗爾列舉了三個譯本的一些翻譯片斷。在最早的譯本中,海斯將原文(德語)大膽媽媽的一句對白“Da ist ein ganzes Messbuch dabei,aus Alt?tting, zum Einschlagen von Gurken.”(這里有一整本阿爾特丁的彌撒書,包黃瓜用的。)[3]譯成“There’s a whole ledger from Alt?tting to the storming of Gurken.”[4]在這句譯文中,“彌撒書(Messbuch)”被譯成了“賬本(ledger)”,而無辜的“黃瓜(Gurken)”也變成了想象中的城鎮——Gurken。類似的誤譯現象在其他兩個譯本中也均有出現。然而,勒菲弗爾所關注的卻并非這些誤譯的句子本身,而是將著眼點放在了現象背后的本質——原著為大眾所接受是通過譯本實現的,人們所看到的只是一種對原文的“折射”。“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總是帶著某種意圖或目的,折射就是要調整文學作品,使之適應不同的讀者。”[2]235布萊希特在美國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完全是基于本特里的功勞。因此,“折射影響了作品及作者的聲譽”[2]235。
“折射”始終伴隨著文學作品,但卻常常被人們忽視。正是勒菲弗爾將“折射”這一概念引入到文學理論中。他認為:“文學是包含在某一文化或社會環境中的系統,這是一個人為的系統,因為它由文本和作者、折射者和讀者組成。但同時又是隨機的。”[2]235文學系統是從屬于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翻譯就是由一個文學子系統向另一個文學子系統折射的過程。這其中要受到來自詩學、意識形態、贊助人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約。
1.詩學與折射
詩學“一方面是指文學要素,包括流派、象征、人物及原型地位等;另一方面是指文學在社會系統中所起的作用”[2]236。一種文學系統的詩學不一定適合另一種文學系統的詩學。文學文本的詩學經常與接受系統讀者的詩學迥然不同,這就需要譯者,即折射者在兩種詩學中作出妥協。為了迎合讀者,妥協的結果往往傾向于目的語的詩學。
在原版的《大膽媽媽》中,隨處可見布萊希特挑戰傳統詩學的身影。但在不同的英譯本中,譯者卻分別采取了加詞、添句、重新分布對白次序等方式來接近讀者的詩學。海斯甚至還按照接受系統的詩學將劇本的幕次和場景重新劃分,本特里也在其譯本的章節前添加了小標題。而在我國翻譯界,此種現象也不勝枚舉。“譯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外國文學作品大都披上了章回小說的外衣”[5]40,如蘇曼殊和陳獨秀合譯的《悲慘世界》等,因為這樣做符合了當時中國的詩學傳統和讀者的閱讀習慣。
2.意識形態與折射
“意識形態”是指在特定文化語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系統,即某一階級或社會集團的世界觀或普遍觀念。勒菲弗爾認為:“翻譯并非在兩種語言的真空中進行,而是在兩種文學傳統的語境下進行的。”[1]162原語文本與譯入語文本均受控于各自的意識形態,因此,譯者還必須在目的語的意識形態與其自身的意識形態之間作出妥協。
在《大膽媽媽》的翻譯折射過程中,海斯和本特里刪減了許多布萊希特帶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容。海斯一直堅持反對進攻性和平主義,于是他將原作中一整段的相關演說內容全部刪除。綜觀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所走過的歷程,不難尋出這樣一條規律:期間的每個歷史時期所引入的外國文學作品無一不顯示著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盡管《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部超越國界、產生過世界性影響的鴻篇巨著,但直到1989年,最完整的俄文版本才得以問世,補全了20世紀30年代后期被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所唾棄的內容,如布爾什維克黨同托洛茨基派的斗爭。而其中文譯本也在隨著意識形態的變革日臻完善。
3.贊助人與折射
意識形態和詩學對文學折射的具體操縱是要通過另一制約因素,即贊助人的力量實現的。所謂“贊助人”,是指足以促進或阻礙文學的閱讀、書寫或折射的力量。他可以是“個人、團體或是協會”[1]236,包括教會、黨派、貴族、地區政府和傳媒機構等。贊助人通過其自身的意識形態、經濟和社會地位來影響文學系統的折射,但“這種影響并非直接的”[1]236。他要依靠折射者,即職業的翻譯工作者來完成。一般來說,“贊助人更重視文學文本的意識形態,而不是文學的詩學”[1]162。這樣,譯者在其翻譯過程中就難免要受到贊助人的意識形態的操縱。
此外,在《文學理論的文本、系統和折射》中,勒菲弗爾還從語法和語用兩個角度論述了關于“自然語言”對文學文本折射的作用。他認為:“不同語言反映不同的社會文化,譯作應該試圖歸化不同的文化,使其適應不同的讀者環境。”[1]236-237例如,本特里將《大膽媽媽》中的“K?s aufs Weissbrot(加了奶酪的白面包)”譯成“Cheese on pumpernickel”。這是因為,在美國的社會文化中,人們更傾向于接受德國人將奶酪加在裸麥粉粗面包上的習慣。
與此同時,經濟因素也同樣不可忽視。經濟利益與文學系統活動息息相關,《大膽媽媽》就是通過百老匯的舞臺展現在美國觀眾面前的。為了遵循經濟規則,百老匯劇組對原作進行了一定的刪減,以此來提高經濟利潤。而這一做法絲毫沒有影響《大膽媽媽》在觀眾中的反響。
綜觀全篇,勒菲弗爾所要表現的主旨就是“折射使得文學文本得以生存和發展”[2]247,而其中的制約因素又是多元的,但最根本的是意識形態和詩學。事實上,對于那些毫不關心文本本身的讀者來說,折射就是原作。通過折射,原文本確立了它在目的語文學系統中的地位。
二、勒菲弗爾的文化翻譯理論之創新與貢獻
首先,該理論打破了“長期以來盛行于西方文學理論中的忽視翻譯研究的浪漫主義詩學”傳統。其研究方法別具一格,“通過闡述目的語的文化規則和文化傳統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全新的文學翻譯研究法則”[2]217,同時也使翻譯研究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20世紀70年代之前,翻譯一直被視作一種交流的工具,其學術地位往往不為人所重視。正是勒菲弗爾扭轉了這一尷尬局面,使文學翻譯研究能夠以文化學這一嶄新的視角呈現于世人面前。
其次,勒菲弗爾的折射理論和文化三要素理論把翻譯從語義層面的微觀世界擴展到了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強調歷史意識和文化觀點。他所代表的文化學派的主要貢獻在于突破了語言學和傳統美學的研究范疇。[1]161與結構主義尋求文本深層的等值因素不同,勒菲弗爾將目光放在了文本表層,并從社會文化角度入手,對其進行細致深刻的分析。在對文學文本的評譯上,勒菲弗爾也有別于傳統的那種介于“空泛的贊賞”和“集中評錯”[5]7之間的做法。在他看來,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翻譯評判標準,任何翻譯文本都是一定社會文化的產物,從屬于一定的社會群體。
該理論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和當代西方社會的學術思潮密切結合。與其他翻譯理論相比較,勒菲弗爾的文學翻譯的文化學理論可以說是更直接地建立在后結構主義的基礎之上。他更多地吸收和采納了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的理論,利用它們對文學翻譯本體進行重新審視,指導具體的翻譯研究,開創了文學翻譯研究的新局面。
三、勒菲弗爾的文化翻譯理論之局限性
然而,勒菲弗爾的文化翻譯理論也并非完美。他在《文學理論的文本、系統和折射》一文中所說的“折射(refraction)”也就是他后來在1990年出版的《翻譯、歷史與文化》[6]和1992年出版的《翻譯、改寫及文學名聲的擺布》中所用的“改寫(rewrite)”[7]。“折射”與“改寫”兩詞,后者比前者更加大膽激進。“改寫”一詞更能體現勒菲弗爾試圖將譯文本從原文本的影子中脫離出來的思想,有種將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絕對化的傾向。他認為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無處不在,隨時都會影響和左右譯者的思維和行文。在對《大膽媽媽》的譯文作評介時,勒菲弗爾完全無視其中的誤譯現象,這無疑會將文學翻譯帶向另一個可怕的極端。
在某種程度上說,勒菲弗爾過于強調改寫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而完全拋棄了文本層面上的“忠實”,忽視了原作本身的價值對譯入語文學和社會的影響。他認為翻譯研究的中心不是考慮詞語的對等,而是要考慮社會歷史、文化意識等因素,把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放到了與譯入語文化圈內的文學創作等同的地位上予以考慮,這也表明了他過于強調譯作的地位。此外,由于過度強調譯者受意識形態、詩學及贊助人等文化因素的控制,而忽視了譯者本身的主觀能動性和反操控能力。該理論很少對譯者這個翻譯的真正實踐者進行關注。譯者雖然受到這些制約因素的控制,但同時也具有主觀能動性去打破這些控制因素,在某種程度上,譯者是會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翻譯的。
因此,如果將文學翻譯的文化學派觀點過分絕對化,那就可能導致否定翻譯學基礎體系的另一個極端。在不斷擴大翻譯研究范疇的同時,把翻譯研究帶入一個漫無邊際、雜亂無章的境地。
四、結 語
的確沒有哪個翻譯理論是完美無瑕的,翻譯理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如果將勒菲弗爾關于文學翻譯的文化理論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審視,它無疑是承前啟后的一筆。勒菲弗爾對翻譯所進行的反思的確給傳統的翻譯理論帶來深刻變化。他將文學翻譯研究從語言層面延伸到文化層面,從微觀的技法探討上升到宏觀的理論研究,這些都無疑有助于翻譯研究融入西方學術研究的主流。同時,在勒菲弗爾的文化翻譯理論的關照下,文學翻譯理論和實踐也出現了多元化的視角,而非傳統的單一的語言學傾向,其意義尤為深遠。深入探討該理論勢必會給文學翻譯和評譯工作開辟更廣闊的天地。
參考文獻:
[1]郭建中.當代美國翻譯理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VENUTI L.Mother courage’s cucumber:Text,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M].London:Routledge,2000.
[3]王宏志.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7-40.
[4]BENTLEY E.Mother courage[M].London:Methuen,1967:9-12.
[5]孫鳳城.布萊希特戲劇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6]BASSNETT S,LEFEVERE A.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M].2nd ed.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7]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2nd ed.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