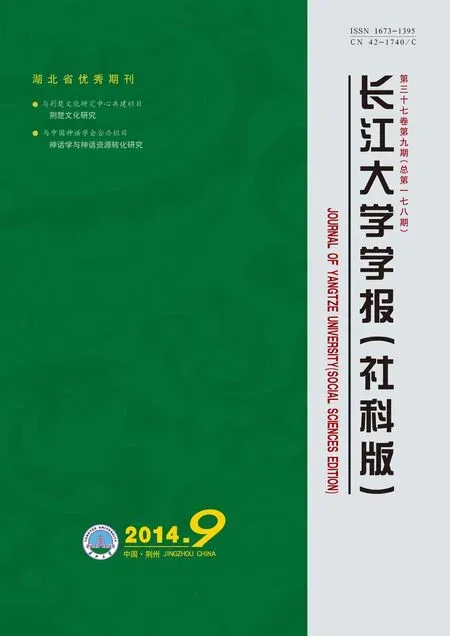歌劇《尤利烏斯·凱撒在埃及》中阿奇拉角色探析
李健
(湛江師范學院 基礎教育學院,廣東 湛江 524300)
歌劇《尤利烏斯·凱撒在埃及》沿襲了亨德爾歌劇選材的一貫風格,仍然采用歷史題材。主要內容是羅馬共和國獨裁官凱撒與埃及女王克列奧帕特拉七世在埃及發生的愛情故事和與埃及王托洛梅奧的政治、軍事斗爭。由于亨德爾歌劇的唱段以獨唱為主,這部歌劇產生了多首膾炙人口的詠嘆調。莊嚴樸實的樂曲旋律和宏偉壯闊的樂隊音樂,都與詠嘆調和劇情相互襯托,描繪了巴洛克時期最優美的音樂線條。[4]男中音角色阿奇拉在整部歌劇中只能排名“男四號”,但該角色無論是戲劇形象還是音樂形象都非常完整,且擁有三首詠嘆調,在劇情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一、阿奇拉戲劇形象與性格
阿奇拉在劇中雖然只是配角,但其在劇中多次扮演著戲劇沖突激發點的角色,使劇情得以完善并增強了角色的戲劇性,三首帶有抒情性質的詠嘆調也使阿奇拉的人物性格得以明確化。
(一)真實的阿基拉斯與劇中的阿奇拉
歌劇《尤利烏斯·凱撒在埃及》中的阿奇拉(Achilla)角色是有歷史原型的,他是埃及王國托勒密王朝國王托勒密十二世時期的將領和托勒密十三世的顧命大臣,是埃及的軍事統帥。一般譯為阿基拉斯。公元前48年羅馬內戰,龐培被凱撒追擊到埃及亞歷山大港,卻被阿基拉斯下令處死。之后阿基拉斯與另一位顧命大臣伯迪努斯一起率軍反抗凱撒,并殺死了前來和談的凱撒使者,攻入亞歷山大港。同時埃及女王克列奧帕特拉七世的妹妹阿爾西諾伊四世逃到阿基拉斯占領區域,卻因意見不合于公元前47年將其處死。
阿基拉斯對埃及歷史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是一位有勇有謀的軍事將領。但歌劇《尤利烏斯·凱撒在埃及》賦予了他更加細膩、豐滿的人物性格。全劇阿奇拉共出場六次(后文仍使用歌劇中的意大利語譯名“阿奇拉”)。
第一幕出場三次,包括阿奇拉向凱撒獻上龐培的頭顱,卻被凱撒訓斥的場景;阿奇拉偷聽到克列奧巴特拉與凱撒的談話后向托洛梅奧告密并渴望得到科內莉亞的場景;阿奇拉與托洛梅奧設計暗殺凱撒和企圖強行占有科內莉亞的場景。包括第一首詠嘆調《你是我心中的心》;第二幕出場一次,是阿奇拉告訴托洛梅奧在與凱撒的戰斗中將其擊敗,并仍然對科內莉亞表達愛意的場景。包括第二首詠嘆調《如果你殘忍的對待我》;第三幕出場兩次,包括阿奇拉與托洛梅奧因科內莉亞而反目并戰斗的場景。包括第三首詠嘆調《在森森的刀光下》;阿奇拉臨終前將軍權交給塞斯托的場景。六次出場從多角度塑造了一個完整的阿奇拉角色。
(二)抒情性的戲劇詠嘆調明確阿奇拉人物性格
阿奇拉的第一首詠嘆調《你是我心中的心》一開始就反復吟唱著“你是我心中的心,是我的愛,不要生氣”直接表達對科內莉亞的愛。而到了中部,仍然用“我向往你的愛,但不要求很多”這樣的近乎乞求的語氣向其表白。這首詠嘆調旋律抑揚頓挫,情緒忽高忽低,深刻表現了阿奇拉想要強行占有科內莉亞卻猶豫不決的矛盾心理;第二首詠嘆調《如果你殘忍的對待我》則出現在他的軍隊擊敗凱撒之后,剛剛獲得勝利的阿奇拉信心倍增,唱出“如果你殘忍的對待我,我的心依然忠誠于你”,雖然對科內莉亞仍然充滿著渴求,但到了中段則話鋒一轉:“但如果你不改變,我的脾氣會更加暴躁,將會嚴厲的對待你”。這首詠嘆調的旋律比前一首要平和得多,但歌詞語氣也要強硬得多,突出了阿奇拉得不到心愛的人而焦躁不安的情緒。[2]兩首詠嘆調都是唱給科內莉亞,唱段中的旋律和歌詞或抒情、或強硬、或乞求、或威脅,賦予了阿奇拉角色高度的抒情性。
第三首詠嘆調《在森森的刀光下》則完善了阿奇拉的人物性格。托洛梅奧的擊敗凱撒即把科內莉亞的允諾完全沒有實現,而托洛梅奧自身也想得到科內莉亞。國王的背信,使阿奇拉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羞辱,從而直接促使他與托洛梅奧反目成仇。這首詠嘆調就是阿奇拉在極度憤怒的情緒下唱出的,短短的幾句歌詞就可以看出他的心理活動:“森森的刀光下,在羞辱一顆邪惡的心;不能遭受他的侮辱還捍衛他的王國。”抒發了阿奇拉在得知國王的背信棄義和心愛的人被奪走時的激憤心情,也預示著他將對托洛梅奧采取行動,奮起反抗[3]。使原本塑造的有些奴顏婢膝和狡猾陰險的阿奇拉形象加入了“英雄末路”的成分。這首詠嘆調使阿奇拉角色的抒情性達到了新高。
(三)沖突的矛盾激發點賦予阿奇拉立體的戲劇形象
阿奇拉的形象塑造主要是通過與三位角色發生緊張的劇情沖突而完成的。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配角,卻與劇中主要角色的關系緊密相連,促使劇情全面發展,而使歌劇顯得更加張弛有度。當然,當代音樂界對該部歌劇的劇情完整性采用懷疑的態度,是為見仁見智。
在歌劇中第一幕開場不久阿奇拉就向剛剛得勝的凱撒進獻了龐培的頭顱,他自信滿滿,原以為凱撒會因為自己為其消滅了勁敵而得到好處。結果卻適得其反,凱撒勃然大怒,一首《日落前我要公布你的罪行》使阿奇拉敢怒不敢言。使這一個討好不成卻激怒入侵者而又怒又怕的政客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劇中阿奇拉與托洛梅奧的關系最為微妙,也是歌劇情節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當阿奇拉偷聽到克列奧巴特拉與凱撒即將聯合的談話后,趕緊通知了托洛梅奧讓其早做準備暗殺凱撒。作為埃及王國的大臣和將領,這種忠君行為無可厚非。但隨即提出的條件卻暴露了他的私心,他要在事成之后占有科內莉亞。這種大敵當前仍要滿足自己私欲的行為將阿奇拉的人物形象刻畫得更加細膩。
這個角色最具戲劇性的人物沖突,主要體現在與科內莉亞的渴求上。全劇中阿奇拉與科內莉亞的戲劇沖突最為激烈,也是這部歌劇的重要脈絡之一。從向托洛梅奧講條件索要科內莉亞,到直接向科內莉亞表達愛意的詠嘆調《你是我心中的心》、《如果你殘忍的對待我》,再到為科內莉亞而與托洛梅奧反目而被殺。無不將阿奇拉好色、多情甚至“沖冠一怒為紅顏”的“情種英雄”性格表現到極致。
二、阿奇拉的音樂形象塑造
(一)典型的亨德爾式詠嘆調塑造典型的正歌劇音樂形象
亨德爾大型聲樂作品中的詠嘆調一般有五種類型,包括勝利型詠嘆調(如《參孫》中的《天使在歌唱》)、憂郁型詠嘆調(如《里納爾多》中的《讓我痛哭吧》)、田園型詠嘆調(如《賽爾斯》中的《綠樹成蔭》)、詼諧型詠嘆調(如《賽墨勒》中的《我喜歡自己》)以及戲劇型詠嘆調(如《尤利烏斯·凱撒在埃及》中的《你如此無情》)。
阿奇拉的三首詠嘆調中,《在森森的刀光下》和《如果你殘忍的對待我》結構縝密,大量使用切分音,用突出的強拍和強音和急促的伴奏音型預示戲劇矛盾。A段使用大調式,B段則使用關系小調。而《你是我心中的心》除A段小調B段關系大調外,創作手法基本與《在森森的刀光下》一致。兩段力度成鮮明對比,花腔長句中的多個十六分音符(一般為四組)塑造了音樂的緊張感。因此,三首詠嘆調應屬于戲劇型詠嘆調,所不同的是《如果你殘忍的對待我》和《你是我心中的心》更偏重于抒情性。
兩首帶有浪漫色彩卻不失莊嚴的詠嘆調《你是我心中的心》、《如果你殘忍的對待我》旋律優美,節奏鮮明,抒情性明顯;另一首詠嘆調《在森森的刀光下》也體現了正歌劇的莊重與典雅,雖然表達的是強烈的憤怒和恥辱感,卻在憤怒中充滿平靜,用宏偉的平和音調和有力的莊嚴節奏突出角色的激憤情緒。
(二)高度歌唱性的敘事宣敘調強化角色的音樂性格
宣敘調在歌劇中是一種以語言音調為主,強調敘述式、朗誦式的自然音調變化,有時用在詠嘆調之前作為鋪墊,與詠嘆調形成鮮明對比以將戲劇結構完整化。阿奇拉角色在歌劇中也有大量的宣敘調,根據劇情和旋律的不同發展階段分別具有以下幾點功能。
其一,為即將開始的詠嘆調做準備。第一幕阿奇拉與托洛梅奧商議刺殺凱撒后,捕獲了潛入王宮的科內莉亞母子。在這一場景,阿奇拉對科內莉亞、塞斯托演唱了抒情性的一小段宣敘調。“科內莉亞,你的燈光照亮我的心,如果你的愛轉向清晰的邊緣,你們母子都會得到自由”。在被科內莉亞拒絕和受到塞斯托的訓斥后,氣急敗壞的阿奇拉開始對塞斯托咆哮并將其擊倒,但隨即平靜下來,對科內莉亞唱道:“如果你珍惜我的愛,你仍然可以保留你的想法”。在宣敘調的末尾節奏明顯放慢,調性也更趨于d小調,與后面詠嘆調《你是我心中的心》主題性旋律構成了鮮明對比,突出了角色旋律的標志性動機。
其二,表達與其他角色沖突的對立思想。這一功能在阿奇拉與托洛梅奧從爭論到反目中更加凸顯,先是阿奇拉把擊敗凱撒的消息告訴托洛梅奧,托洛梅奧對其大加贊賞,而后阿奇拉請求托洛梅奧兌現承諾希望得到科內莉亞,但卻遭到背信的拒絕,最后阿奇拉用宣敘調的形式唱出內心獨白:“誰沒有信仰,你不應該這樣”,清晰地表達了兩個角色從合作到分裂的過程,將兩人的沖突明確化。
其三,增強劇情緊張度的敘說功能。阿奇拉最后一次出場是在與托洛梅奧的戰斗后,臨終前與凱撒、塞斯托和尼雷諾的對話性宣敘調。這一段宣敘調旋律和節奏使這個角色聽起來非常虛弱無力,但瀕死的阿奇拉仍然摘下統帥軍隊的戒指交給塞斯托,鼓勵塞斯托與凱撒一起反攻托洛梅奧的唱段,無比精煉地勾畫出阿奇拉最后僅存的一絲英雄形象。這段宣敘調是他的臨終遺言,死前的平靜與大氣也使劇情沖突更具有壓迫感和緊張感。
三、阿奇拉詠嘆調的曲式結構與伴奏特點
(一)巴洛克歌劇常見的返始曲式結構
18世紀意大利正歌劇最典型的詠嘆調結構就是返始詠嘆調,這種由ABA形式逐漸發展為“da capo”形式的詠嘆調被巴洛克中后期的歌劇作曲家們廣泛采用[4]。在亨德爾的早期歌劇作品中,絕大多數詠嘆調都是這種形式。
阿奇拉的全部詠嘆調都是返始詠嘆調,亨德爾賦予了這個角色三首“da capo”三部曲式的返始詠嘆調。從曲式結構上看,這三首詠嘆調以段落為單位形成塊狀對比,中段篇幅短小,從調式、音高、速度、力度上看都是對比性的樂段。這種音樂布局使人物情感的表達得到了升華和回歸,把再現部分交給歌唱者以裝飾性變化的形式將情感推向高潮。
(二)“花腔”式的器樂伴奏
阿奇拉三首詠嘆調充分地體現了亨德爾歌劇的旋律與伴奏創作特征。
聲樂與器樂旋律交替出現是亨德爾歌劇詠嘆調的一大特征。特別是在快板詠嘆調中,如《在森森的刀光下》前奏中,在低音提琴部分出現了一段四組十六分音符的連續組合,到了43-46小節,在人聲聲部也出現了同樣的旋律,所不同的僅僅添加了歌詞。事實上,前奏還包含了很多后面的人聲歌唱部分,有些在小提琴部分,有些在低音提琴部分,其特點是保留人聲旋律主干音,將復雜的節奏簡略化。[5]遺憾的是,這三首詠嘆調并沒有出現著名的亨德爾式“格言主題開始法。”
(三)簡單而有效的配器
由于時代的限制,巴洛克時期的樂器種類并不多,也沒有形成系統的配器學理論。亨德爾也必然受到這種時代的束縛,三首詠嘆調除了在《你是我心中的心》的37-40小節使用了大管之外,全部僅僅用了小提琴和低音提琴兩種樂器[6~7]。但是僅有的三種樂器,卻勾畫出一幅完整的音樂畫面而絲毫不給人單調感,不能不說這是巴洛克時期的奇跡。
參考文獻:
[1]于潤洋.西方音樂通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
[2]吳素芹.亨德爾在聲樂藝術發展史上的貢獻[D].首都師范大學,2002.
[3]葉松榮.試析亨德爾歌劇盛衰之史因[J].人民音樂,1985(5).
[4]李秀軍.從音樂風格發展的角度簡述亨德爾的歌劇創作——兼談學習《音樂學分析》的點滴感想.[J].中國音樂,1997(4).
[5]張繼紅.18世紀上半葉意大利正歌劇詠嘆調研究[D].上海音樂學院,2006.
[6]尚家驤.歐洲聲樂發展史[M].北京:華樂出版社,2003.
[7]管謹義.西方聲樂藝術史[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