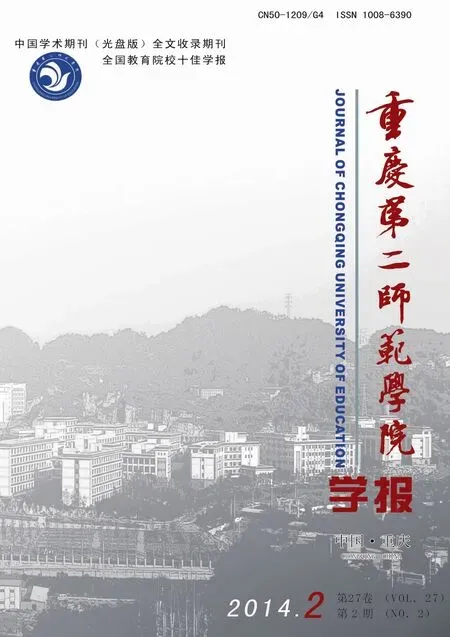召喚結構視角下的《寵兒》解讀
昌 楊,何江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6)
德國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沃爾夫岡·伊瑟爾認為,文學文本中存在著意義“空白”和“不確定性”,其各級語義單位之間存在著連接的“空缺”,而當文本對讀者習慣視界進行“否定”時,就會引起讀者心理上的“空白”。所有這些空白、空缺、否定因素就組成文學文本的否定性結構,成為激發、誘導讀者進行創造性填補和想象性連接的基本驅動力,這就是文學文本的“召喚結構”。[1]伊瑟爾還指出:“任何文學閱讀都是對文本的一種期待,但各種期待幾乎從來不曾在真的文學文本中實現,否則就是一種缺陷。好的文學文本在喚起讀者期待的同時更應否定它、打破它,而不是去證實它、實現它。”[2]
美國非裔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第五部長篇小說《寵兒》(Beloved)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新的里程碑,在文學界和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并于1988年獲得普利策文學獎。該小說以“驚心動魄的情節和無與倫比的敘事”深受讀者的喜愛,1993年莫里森憑借這部代表作榮獲諾貝爾文學獎。[3]該小說的現有研究多集中在小說的敘事風格、精神分析角度、女性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寫作手法、種族歧視等方面,本文擬通過探討該小說中存在的召喚結構,分析作者在小說中為讀者提供的各種形式的接受、審美空間以及作者是如何利用這些空間召喚讀者進行文本提示、填補空白、更新視域的創造性閱讀,進而發現文本本身的藝術價值和藝術生命力。
一、文本提示——寵兒的身份
在與文本的交流過程中,讀者一直都在不停地思考,不斷地向文本提問,同時作品也在不斷地用自己的文學手段來指引提示讀者,回答讀者的問題。文本的提示或回答有時候會否定讀者原先對作品的認識,正是在這種不斷的提問和回答過程中,讀者的認識在不斷深化,閱讀在不同階段的不完整性和未完成性激發讀者強烈的閱讀欲望,進而推動閱讀的行進。
《寵兒》講述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故事,黑奴塞絲(Sethe)在攜女逃亡途中遭到追捕,為了不使自己的女兒重新淪為奴隸,她毅然扼殺了自己的幼女。18年后,被她殺死的女嬰還魂歸來,以自己的出現日夜懲罰母親當年的行為。在創作時,作者大膽地運用了當時盛行于美國的讀者反應批評理論,處處留下了讀者參與的空間,召喚著讀者全方位地體味和感悟 “白人文化沖擊下的黑人心靈”。[4]
在小說的開篇,讀者就接受了一種特殊的提示:“124號惡意充斥。充斥著一個嬰兒的怨毒。”[5]3接下來作者并沒有指出這個嬰兒的身份,只是暗示著它帶著恨與怨,為日后124號一家人原本有序的生活被這個嬰兒打亂做了鋪墊。讀者接受到作者的提示后,內心難免產生疑問:為何一個嬰兒會有“怨毒”?這便喚起讀者的強烈探尋欲望。隨后,塞絲的124號家便開始發生一些奇怪而詭異的事情:怪異的聲音、奇異的燈光、物體莫名其妙的移動或振動,這些描述都是在為寵兒的出場做鋪墊。作者在暗示寵兒的身份,試圖讓讀者將寵兒與這個嬰兒聯系起來。當寵兒出現在塞絲家并和她們生活在一起之后,作者時不時提示讀者寵兒的行為舉止極像塞絲多年前親手殺死的女兒。當丹芙和寵兒去棚屋拿蘋果汁時,二人進了黑乎乎的屋子,寵兒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而當年塞絲就是在這個屋子里殺死自己女兒的。丹芙感到害怕,哭了起來,此時寵兒又神秘地出現在她面前。直到后來連塞絲自己也堅信寵兒就是當年死去的女兒轉世還魂,“寵兒,她是我的女兒。她是我的。看哪,她自己心甘情愿地回到我身邊了,而我什么都不用解釋”。[5]239而寵兒也把塞絲認作是自己的母親,兩人關系特別親密,如同母女,整天形影不離。塞絲早上出去打工,寵兒天不亮就起來到廚房等她,下午又到路上去接塞絲。回到家里,寵兒跟著塞絲,形影不離。她對丹芙說:“留在這兒。我屬于這兒。”[5]89小說中類似對寵兒的身份的提示性話語讓讀者的閱讀始終處于一種設想、期待和發現的運動過程。這正是現代小說家所期待的讀者反應,因為敘述中無法擺脫的一個悖論就是:“雖然敘述作品寫出來,就是要使自己被閱讀、被理解,但是另一方面為了使讀者能夠耐心地讀到最后一頁,敘述者又必須有意識地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設置種種困難和障礙,以便延長讀者的理解。”[6]
二、填補空白——開放性結尾
波蘭哲學家羅曼·英伽登提出:“由于文學作品是一個充滿不確定的圖示化的存在,在具體化過程中,必然要求讀者對不定點給以填充或確定,這樣,‘具體化’過程就成了文學作品與讀者之間交流的過程。”[7]伊瑟爾贊同英伽登的看法,并指出空白本身就是文本召喚讀者閱讀的結構機制,文本的意義恰恰是產生于讀者與文本的交流過程。空白是一種動力因素,是“一種尋求缺失的連接的無言的邀請”。[8]文學作品不是物理存在,而是文本和讀者想象相遇的結晶。作者要尊重讀者的地位和作用,善于有意地保留一些信息,使文本充滿空白與省略,讓讀者自己在填補空白的同時參與到作品的創作中。在《寵兒》中,小說的開放式結尾便是空白的一種形式。這種開放式結尾不同于傳統小說的單一結尾,而是給出了多種可能性,把原本一種結尾所賦予的確定性變為不確定性,從而調動了讀者的思維力和想象力,共同挖掘小說文本的宗旨,以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小說的第一個結尾是圍繞塞絲和保羅兩人的愛情歸宿為主線。保羅在得知寵兒的鬼魂被驅趕走了,又重新回到了塞絲的身邊。但是莫里森在小說中并沒有明確指出保羅回到塞絲身邊的動機和目的。此時,讀者需要通過自己的想象和猜測去填補文本之外的空白,以求閱讀的完整性。這種似乎圓滿的大結局還是讓讀者內心產生這樣的疑問:這個家庭能否從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他們的未來又會怎樣?黑人的生活就此改變了嗎?
小說的另一個結尾同樣讓人捉摸不定,這便是寵兒的消失和去向。寵兒的離去和她的到來一樣是一個謎,充滿了懸念,讓人遐想。在小說結束時,寵兒的命運被賦予了不同的斷言,使得小說的結尾處于開放的、不確定的狀態。
因此,《寵兒》的結尾不能簡單地概括為:塞絲被治愈,寵兒被放回了原處。這種結尾體現的空白構成了潛在的文本,激發了讀者的想象力和連續建構過程。文本意義的不確定性來自于它開放的內在結構,文學作品是一個“過渡客體”,一個“潛在空間”,閱讀就是讀者靠自己的想象與經驗來填補完善文本中的不確定的空白與間隙。[9]莫里森曾經說過:“我不想循規蹈矩,我要打破傳統小說的條條框框,寫出真正有價值的小說來,在我的小說里給讀者留有更多的空間,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去感受、去理解,我不想關閉我的小說,打斷讀者的想象,讓我的讀者憑自己的理解完善我的小說。”[10]由此可見,莫里森意識到了讀者的存在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文本的建構作用,于是她竭力邀請讀者來加入她的小說創作。如果說“敘述的開端是一個問題的拋出,那么其結尾便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并非所有的結局都只是一種期待的落空,那種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結尾本身就具有接受魅力”。[11]
三、更新視域——多重敘述視角
伊瑟爾由于受到伽達默爾“視域融合”學說的啟示,指出文本的“否定性”是一種召喚讀者閱讀的結構性機制。文學文本不斷喚起讀者基于既有視域的閱讀期待,但喚起它是為了打破它,使讀者獲得新的視域。[12]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經常會按照自己已有的經驗來預想并期待故事情節的發展,但這種舊視界常常會被文本打破,即否定。當文本在集中講述某個人的故事時,突然插進一段新的故事或另一個人物的故事,這時,原來的情節線索被打斷,此時的讀者需要通過進一步閱讀獲得新的視點,改變舊有的視界。多重敘述視角的敘述方法使得讀者在片段性的、零亂的、不連續的描述中去拼湊故事情節,不斷更新視域。
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員朱迪絲·瑟曼在《紐約人》雜志上討論莫里森的創作手法時指出:“她把這玻璃打碎, 然后以互不相連、令人迷惑的現代形式將其重新組合。”[13]在《寵兒》中,對于塞絲背上因白人奴隸主毒打而造成的巨大傷疤的描寫,莫里森就采用了多重敘事視角的敘述方法不斷更新讀者的視域,讓讀者逐步了解疤痕的來源。透過三個敘述者——塞絲本人、女兒丹芙和保羅的描述,疤痕在讀者面前呈現不同的形象。塞絲是當事人,也是受害者,丹芙和保羅都是不知情者。小說第一次對塞絲背后的傷疤描述只用了一句話“我后背上有棵樹”,[5]18這是塞絲對保羅說的。在這里,敘述者并沒有透露原因,她點到即止。這是塞絲過去的個人經歷和深切的痛苦,她是不愿意提及的,因為塞絲日常的“嚴肅工作”就是“擊退過去”的記憶。[5]86所以,塞絲在敘述時簡單地一筆帶過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作為讀者,他的心理反應和保羅一樣,對這話摸不著頭腦,此時的讀者視域便是“一棵樹”,可是又怎么會有一棵樹呢?讀者心中產生疑問,塞絲的簡單一句話就給讀者留下了懸念。讀者只能追隨小說中其他人物的眼睛,一點一點地揭開秘密,不斷更新讀者內心對傷疤的認識。塞絲背上的傷疤就是通過不同人物的回憶、不同人物看到的景象呈現在讀者眼前的。讀者之前對塞絲后背上的“樹”的舊視域接著便被保羅的描述所打破,透過保羅,看到“她后背變成的雕塑,簡直就像一個鐵匠心愛得不愿示人的工藝品”。[5]21從讀者反應批評理論來看,這樣的句子的優點恰恰在于它并沒有告訴讀者什么。具體地說,讀者并不可能期望得到任何一個事實來回答心中的疑團。讀者雖然明白她背上并非什么樹,而是長了一個什么東西,但懸念繼續存在。只有白人女孩愛彌·丹芙對塞絲傷痕的描述才真正揭開了事情的真相,讀者的視域再次被打破,形成了新的視域:
是棵樹,露。一棵苦櫻桃樹。看哪,這是樹干——通紅通紅的,朝外翻開,盡是汁兒。從這兒分叉。你有好多好多的樹枝,好像還有樹葉,還有這些,要不是花才怪呢。小小的櫻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整棵樹。正開花呢。我納悶上帝是怎么想的。我也挨過鞭子,可從來沒有過這種樣子。[5]93
莫里森從不同人物的角度來描寫這個讓人心痛、不愿回憶起的傷疤,促使讀者自己去揣摩和研究,不斷否定讀者原先的視域,展現新的視域。“每人雖然講的都是同一事件,但都不是完整故事,而是從不同層面為故事提供和積累了互為補充的信息”。[14]多重視角的轉換通過敘述者的眼光選擇來突出某些因素,同時也淡化乃至排除了另外一些因素,就會造成文本的某些地方給讀者留下懸念,否定讀者原先的視域,進而達到更新讀者視域的目的。
綜上所述,莫里森遵循以讀者為中心的現代創作理念,并將這一理念融入她的小說創作中。在《寵兒》中,莫里森召喚讀者進行文本提示、填補空白、更新視域的創造性閱讀,制造了種種懸疑,需要讀者通過自己的想象、內化、破譯,才能捕捉到潛在的隱蔽的信息,挖掘出游離于字里行間的、疊加在語義上的美學內涵。《寵兒》的出版曾經在美國轟動一時,它的故事情節取材于當時的真實的歷史事件。作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為了激發讀者對黑人悲慘生活的同情,揭示并批判奴隸制的慘無人道,莫里森以其超人的智慧、嫻熟的寫作技巧以及敢于冒最大風險的創新精神構筑了一個個誘人的結構、情節和語言迷宮,召喚著讀者的參與、領悟、創造和思考,給讀者提供了各種形式的審美空間,激發和調動了讀者進行創造性的填補和想象性的連接的“再創造”。小說的廣受歡迎從某種意義上應歸功于小說文本所蘊藏的召喚性。
參考文獻:
[1]朱立元.略論文學作品的召喚結構[J].學術月刊,1988,(8):43-49.
[2]伊瑟爾.閱讀行為[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296.
[3]王家湘.20世紀美國黑人小說史[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446.
[4][14]王守仁,吳新云.性別·種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6.134.
[5]Morrison, Toni著.潘岳,雷格 譯.寵兒[Z].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9.
[6]羅鋼.敘述學導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55.
[7]蔣濟永.羅曼·英伽登對讀者接受理論的影響[J].外國文學研究,2001,(1):7-11.
[8]伊瑟爾.本文與讀者的交互作用[A].張廷琛 編,接受理論[C].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52.
[9]Gates, H. L., Jr. and K. A. Appiah, eds.ToniMorrison:CriticalPerspectivesPastandPresent[M]. New York: Amistad Press, 1993.396.
[10]Christian, Barabara.TheContemporaryFablesofToniMorrison[A].BlackWomenNovelists:TheDevelopmentofATradition, 1892- 1976[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74:177.
[11]蓋利肖.小說寫作技巧十二講[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312.
[12]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295.
[13]Chatman, S.B.StoryandDiscourse:NarrativeStructureinFictionandFilm[M]. London: Routledge, 197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