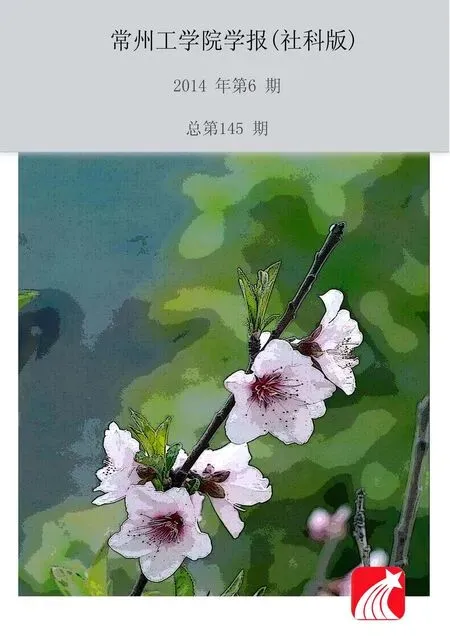新時期影視服飾色彩對傳統文化的傳播誤區
——以新版《紅樓夢》為例
花俊蘋
(江西服裝學院,江西南昌330201)
新時期影視服飾色彩對傳統文化的傳播誤區
——以新版《紅樓夢》為例
花俊蘋
(江西服裝學院,江西南昌330201)
《紅樓夢》原著對服飾描寫精致、美妙、和諧,體現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服飾文化。2010年新版《紅樓夢》卻引來了諸多爭議,尤其是劇中服飾色彩搭配以及妝容設計。文章從中國傳統色彩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新版《紅樓夢》服飾色彩對傳統文化的傳播誤區,指出影視劇組應該秉承中國傳統文化,以嚴謹的態度為廣大觀眾創作優秀的、有文化價值的影視作品。
傳統色彩文化;《紅樓夢》;額妝;服飾色彩
中國是世界上很早就懂得使用色彩的國家之一,遠古時期就以“青、赤、白、黑、黃”五色定位“正色”,并與五行中“金、木、土、水、火”相聯系,把中國人關于哲學、倫理、自然等觀念融合到色彩中,從而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傳統色彩文化,并在禮教、政治、生活中融匯貫通。然而,目前中國播出的電影電視中卻往往把古代服裝色彩的身份搞錯,使觀眾對傳統文化產生誤解,這對學習服裝歷史有一定的影響。
一、傳統色彩文化概念及特點
一是傳統色彩文化。“五行說”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比較深遠的,傳統色彩文化與“五行學”有著密切的聯系。“五色觀”由“青、赤、白、黑、黃”組成五色。有關色彩記載的文獻中提到殷商時期祭祀選擇牲口會根據色彩的變化來進行。中國古代五色誕生之初被賦予獨特的象征含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將五色象征身份貴賤,將制服用色彩來劃分等級,倡導以禮教為代表的“五色”法制。同時,“五色”又被稱為“正色”,通常在禮教中為身份尊貴的正室穿著;五色相混合得到的間色“綠、橙、騮、碧、紫”,這是妾室穿著的色彩。據傳衛莊公帶著心愛的妾氏出門,妾氏穿著黃色衣裙,衛莊公被大家嘲笑不守尊卑嫡長的禮法。“黃”是正色,為正室之色,妾只能穿其間色“綠”。可見我國傳統禮教之嚴厲。
二是傳統色彩文化的審美特點。在中國傳統的服裝禮教觀念中,色彩一直被看作地位和權利的象征,中國也被稱為禮儀之邦,遵從禮教治國。孔子極力維護“五色說”,他賦予了正色與間色的貴賤尊卑之區別,不僅是服飾色彩,五色還涉及祭祀、房屋、器皿等等方面。《詩經》里有“綠衣黃里”的說法,代表的含義是“于禮不合”。如果從字面來理解只能體會到膚淺的含義,然而從傳統色彩文化中不難看出,黃為正色、綠為間色,而這里黃色為輔料,綠色為主面料,間色高于正色的配置方式是不合適的。中國古代統治者們把色彩作了等級劃分,例如代表中央力量的黃色只能是皇帝的服裝色彩,烏紗帽和紅頂子是官員的服飾色彩,皂色與素縞是老百姓的服裝色彩。
同時,民間的服裝也是大多數質樸思想和藝術語言的體現,在“陰陽五行學”中與“土、木、火、水、金”對應的是“黃、青、赤、黑、白”。古時皇帝的服裝有四時衣“夏朱、春青、秋黃、冬黑”,這種穿衣方式一直流傳到民間。三國時,孫權弟兄在秦淮河邊設軍營,軍人服色全部為黑,當時稱為“黑衣巷”,之后一些紈绔子弟相仿穿著黑色,一時間黑色成了貴族的象征。民間色彩依照風俗習慣漸漸完善,在婚嫁、生育、祭祀、喪葬、慶壽、節日等民俗活動中,對服裝色彩都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紅色的運用最為講究,因為紅色在中國代表女子,象征幸福、吉祥。婚禮中以穿紅色來代表喜慶。同時,正紅代表正妻,妾氏穿紅得穿粉紅。
二、新版《紅樓夢》的色彩傳播誤區
曹雪芹所寫的《紅樓夢》可謂百科全書,書中涉及的文化極為豐富,其中對服飾色彩的描述非常多,為后人的影視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但影視劇作品中有時為了追求畫面效果往往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禮教因素。由李少紅導演的2010版電視劇《紅樓夢》,戲劇化的造型,打破了服飾色彩搭配傳統,引起了廣大觀眾的注意,但在挑戰傳統的同時,在色彩方面存在傳播誤區。
一是額妝色彩方面的傳播誤區。新版《紅樓夢》中引起廣泛爭議的是十二釵們的戲曲造型“額妝”。額妝是視覺沖擊力非常強的美學符號,體現了電視劇創作團隊寫意化美學的追求,也是一次大膽、新穎的嘗試。“額妝”是指對鬢或額的修飾,加上臉頰大塊的胭脂與濃厚刻意拉長眼線的處理,以及“貼片”發型的處理,令人感到油彩撲面的厚重感。“額妝”又稱“佛妝”,主要在魏晉南北朝流行起來,開始只是在額間點一個紅丹點,之后出現各種花式圖案,最著名的有梅花妝。至宋元清時期轉變為“額帕”,就是將額發盤起成云朵狀橫在眉間,再在上面綴上珠寶,這個妝容當時只有貴族女子使用。新版《紅樓夢》濃墨重彩地把頭發做成多個“貼片”,臉上又如戲劇一樣做花旦妝,這的確充滿創意,但過于接近的妝容導致人物的對比太弱,很多經典人物區分度過小,有人稱50集電視劇看完后都沒分清楚誰是迎春、誰是惜春。
二是服飾色彩設計方面的傳播誤區。我國封建社會服裝色彩除了有審美功能之外還蘊含著等級貴賤的劃分,并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隨著歷史的變遷,印染價值便宜的黑、白逐漸從正色轉為平民小吏等下層階級常用色,而難以印染的紫色上升為高貴的象征,唐朝官服二品以上著紫袍,黑色白色為貧民布衣,青、綠為妓女、婢女等身份低賤之人所著之色。
在新版《紅樓夢》中比較有爭議的一個人物是秦可卿,書中描寫她是賈家寧國府比較有身份的孫媳婦,身份位同賈寶玉的妻子,我們看過薛寶釵是怎么被精挑細選才當上這個孫媳婦的就知道秦可卿身份之尊貴了。書中還提到秦可卿極講究禮數,即使在病中也要穿戴整齊來見看望她的人。然而這樣一位講究的貴婦,卻在第一次賈府家宴的時候著一身黑色出席。黑色不是吉祥的色彩,給人嚴肅、寂靜、悲哀的感覺,古代通常是喪葬或寡居的人著的服裝色彩。秦可卿的丈夫賈榮在世怎么會穿一身黑呢?也許新版《紅樓夢》為了打破傳統,想以黑色來象征秦可卿悲劇性的命運,但這一身黑色的著裝加上綠色眼影、鮮紅嘴唇和勾人的眼神,讓觀眾感受到她完全沒有了貴族婦人該有的貴氣,卻有一種女鬼般的驚悚。
在中國傳統色彩文化中“白色”是正色,同時與黑一樣都是“喪葬”色彩,看見白色往往令人想到的是悲涼。新版《紅樓夢》中薛寶釵始終以一襲白衣示人,令人莫名驚異。薛寶釵是一個為人淡泊,不喜粉黛釵環,懂得揣度長輩心思,知書達理、崇尚簡潔的女子。寶釵恪守閨閣之禮,在服裝上也必然體現一個大家閨秀應有的審美情趣。雖然書中說她從小吃用白梅花、白荷花、白牡丹花蕊等制成的“冷香丸”,雖然在黛玉的綠、寶玉的紅中,她的白是一種適時的調和;但同時書中也把她比為牡丹,是“艷冠群芳”“任是無情也動人”的貴族少女,不可能整日一身素服出入賈府。飾演寶釵的演員臉上永遠淡淡的笑容,可能想表現的是寶釵喜怒不形于色的內斂,可加上這件白衣讓人感到的卻是單調、乏味,像一個沒有感情的生命,即使經典的“寶釵撲蝶”也毫不生動。
再說林黛玉,87版的《紅樓夢》中黛玉常以藕色、月白、粉紅、淺藍凸顯其清麗婉轉而不清寒的“世外仙妹”之感。新版《紅樓夢》中的黛玉幾乎都著一襲綠色衣裙。“綠色”在色彩觀中是妾氏之色,尤其是身份卑賤的婢女之服裝色彩。林黛玉生性敏感多疑、纖弱嬌美,是曹雪芹筆下的女詩人,她喜歡瀟湘館的綠竹,書中描寫她把鸚鵡掛在半月形月洞底下賞玩足以見其具有較高的藝術審美情趣。同時,黛玉自小父母雙亡,雖然賈母百般疼愛,但寄人籬下一直是她心中的隱痛。湘云無意中說出小旦長得像黛玉,使黛玉大發脾氣。然而新版《紅樓夢》中的黛玉毫不忌諱的天天一襲綠衣,穿著婢女之色招搖于賈府,這與她孤傲的性格南轅北轍。小說中說黛玉“行動時如弱柳扶風”,陳曉旭版的黛玉常常穿著粉藍色棉布衣裙,走起路來搖搖擺擺,柔弱之態油然而生;而新版的黛玉臉色紅潤,走路穩穩似有彈性沒半點病態,厚重的綠色衣裙重重地壓在身上沒半點飄逸之美。
書中最有身份的女人就是老壽星賈母,這位聚集了各種福氣的老太太享盡了榮華富貴,原著中賈母代表了享樂、家世、地位、財富。她作為賈府最尊貴的人最大的任務就是窮奢極欲地玩樂,她最喜歡的就是和這些孫子孫女們在一起說說笑笑。書中描寫她看見寶釵的衡蕪院陳設過于簡單,發出“年輕的姑娘們,房里這樣素凈,也忌諱”這樣的不滿。可見賈母是一位有品位,有童心,很好玩的人。這樣有福氣的人在新版《紅樓夢》中卻骨瘦如柴,天天著一身黑色繡滿祥瑞圖案的服裝端坐正堂,看不見可愛可親,卻見猶如擺設一般沉重而沒有朝氣,甚至不如劉姥姥來得福氣延綿。新版中的賈母還非常西派,無奈時常常像西方人那樣聳聳肩。在賈元春省親的場景中,賈母穿了一品誥命夫人服,一身黑色服裝左右胸口繡著仙鶴,這格局完全是一品文官的紋樣,而傳統服飾中黑色從來不會出現在官員服飾色彩中,更不可能出現在誥命夫人服飾中。這么歡喜得臉的場面,賈母作為賈家大家長穿黑色是極度失儀的。
然而,當賈府里這么一眾奶奶小姐都身穿黑色、白色、綠色的時候,襲人這個屈居寶玉妾氏的通房大丫頭,一出場就是一身正紅色的衣服,正紅是正室之色,在那個時代嚴重逾規,尤其在賈府這樣一個世代官宦的大戶人家更是所出不合。襲人在丫頭中是最懂禮數的,她甚至去向王夫人告狀說寶玉和大觀園的女人太接近、太失去禮數,那么她自己怎么可能這么不懂禮節穿出正室服色呢?這些都令觀眾感覺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在這里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新版《紅樓夢》里有很多妾氏逾規現象,像探春之母趙姨娘,通身一件紫袍,高貴挺拔。她的身份在書中連小輩王熙鳳都敢厲言斥責她,紫色為正色,古代一品官員著紫袍可見顯赫的地位,她作為一個沒家底的妾氏怎么可以穿著高貴的紫色呢?
《紅樓夢》原著對服飾色彩的描寫非常精致、美妙、和諧,體現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服飾文化。在87版《紅樓夢》中有一場戲,服裝色彩十分有趣。是鳳姐發現賈璉在外包養尤二姐而去接尤二姐回家那場,賈璉和鳳姐的服飾是夫妻裝,并且都是孝服。尤二姐穿的是喜氣洋洋的淡粉與橙色的衣服,這個是典型的小妾服,小妾是不能穿正紅色的,這與鳳姐、賈璉的孝服藍白對比強烈,很明顯可以看出尤二姐的不合時宜。王熙鳳雖然衣服顏色低調,但發型卻是飛揚跋扈的飛仙髻,那種自信和張揚,將低眉順眼的尤二姐的悲慘結局,已經照映得清清楚楚。同是這場戲,新版《紅樓夢》中的王熙鳳穿著淡黃色的衣服,正妻的身份在這個“黃色”上已一目了然。賈璉穿著一件灰色衣袍滿臉堆笑地站在旁邊,顯示了他看似聽話但陽奉陰違的個性。然而,尤二姐穿著一件鮮紅色衣裙,這個時候正妻在側,小妾是不能穿這么艷的紅色的。這些嚴重違背了中國傳統服裝色彩在文化、禮教上的嚴格劃分規制。
其實在原著中作者對很多人物都有非常細致的服裝配色描寫,然而新版《紅樓夢》的造型總監葉錦添背離了曹雪芹的原意,而用一種奇裝異飾的手法來隱喻人物悲慘命運,這的確有他的用意,但這種背離中國傳統的審美顛覆了小說本有的美學情趣,也令很多初讀《紅樓夢》的人產生了誤解,不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和傳播。
三、產生誤區的原因分析
一是“經典代讀”導致文化底蘊下降。所謂“經典代讀”原本是指名著的講解者通過繪聲繪色的方式說書,把經典說給聽眾聽,代替“讀”的一種方式。隨著電子時代的蓬勃發展,代讀的方式越來越多,例如有聲小說、電影、電視等,這些方式都涉及改編問題。有改編就有編寫者自我的理解,就涉及編寫者文化修養層次的問題。大家習慣將新版《紅樓夢》與87版的《紅樓夢》對比,87版開拍前選出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大多讀過原著,而新版開拍前的“紅樓夢中人”吸引了近40萬人參加,但他們大多沒有讀過原著。連導演李少紅也坦言,在接到拍攝《紅樓夢》這個任務之前還是個“紅盲”。兩部《紅樓夢》對比凸顯一個重要問題:在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和浮躁的心態之下,優秀經典漸漸退出人們視野,人們沒有耐心和時間來閱讀經典,但社會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很多人又需要從經典中獲取心理安慰,這個時候“經典代讀”成為了文化消費方式。《紅樓夢》原汁原味的文化內涵囊括了太多的經典,而現在這種娛樂至上的消費方式顯得與傳統文化背道而馳。新版《紅樓夢》中服飾色彩帶有一定的主觀文學理解,轉述給觀眾(特別是沒有讀過原著的觀眾)的信息是,為什么林黛玉這么喜歡穿綠色,為什么薛寶釵這么喜歡穿白色,難道她們衣柜里只有這個色的衣服嗎?還是古代的貴族少女只能穿這個顏色?拍攝一部經典巨著到底是為了傳承經典開啟觀眾的心靈,還是抑制觀眾的思維活力?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二是商業炒作超越文化傳承。日益強化的商業文化充斥這個社會,像《紅樓夢》這樣的經典巨著也一樣逃避不了商業的炒作。“紅樓夢中人”角色選秀活動,對書中主要人物林黛玉、薛寶釵、賈寶玉等人進行了海選。然而最后出演時換人不斷,例如姚笛最初演寶釵,后傳演黛玉,最后為王熙鳳,這樣三個性格迥異的人物能同時在姚笛身上找到影子嗎?白冰是觀眾認為最適合寶釵的人選,也是寶釵組的冠軍,可最后只在后半部戲份不多時出現。回頭去看當初的選秀似乎并不是在挑選合適的演員,只是為了提高收視率鼓噪的“預熱”而已。服裝造型總監葉錦添是一位來自香港的優秀的影視服裝設計師,然而或許是受西方文化影響太深以及對本土服飾不夠了解,或許是太偏愛寫意表現,千篇一律的銅錢頭造型忽視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固定的服飾色彩弱化了豐富的貴族生活,讓新一代紅迷分不清《紅樓夢》中上百個人物的性格區別,更別說欣賞了。像這樣不從內涵和原著中下功夫,僅通過商業炒作來渴望一夜成名的方式,很難吻合經典慢慢熏陶的接受原則。相比2010年熱播的《甄嬛傳》,作者流瀲紫坦言書中很多創作點來自《紅樓夢》,例如人物說話的方式、生活方式、服飾描寫等。當2010年“宮斗劇”十分蓬勃并流于形式的時候,《甄嬛傳》一改慣用的討好方式,尊重原著的拍攝手法博得一致好評。
四、結語
《紅樓夢》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的文化精粹,它每一個細節都精心雕琢。曹雪芹雖然沒有說出書中所處的時代,但書中描寫的衣食住行基本符合明清特色。87版的《紅樓夢》尊重原著,擔任服裝設計的史廷芹由于精通中國傳統服裝的流變,為了盡量還原那個時代做了2 700多套服裝,并得到廣大民俗學家和紅學家的認可。葉錦添擔任服裝設計的新版《紅樓夢》超出了經典翻拍的基本底線,只是追求視覺效果而不尊重原著使得惡評如潮。這也告訴我們,影視劇應該秉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使命,以嚴謹的態度為廣大觀眾創作專業的、有文化價值的藝術作品。
[1]曹雪芹.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2]王朝聞.美學概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劉心武.劉心武續紅樓夢[M].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4]王慧.影視新版《紅樓夢》的服飾美學淺析[J].大舞臺,2013 (2):277-278.
[5]袁學敏.新版《紅樓夢》電視劇觀感之角色與服飾[J].攀枝花學院學報,2011(5):54-57.
責任編輯:莊亞華
J91
A
1673-0887(2014)06-0061-04
10.3969/j.issn.1673-0887.2014.06.014
2014-09-24
花俊蘋(1978—),女,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