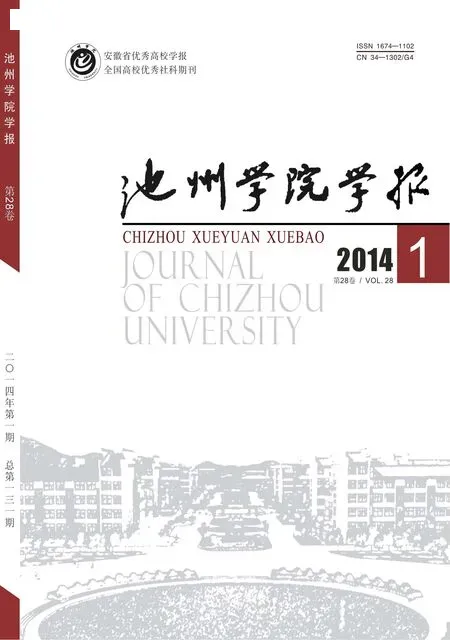從民國報刊史料看李鴻章形象
李發(fā)根
(安徽大學 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從民國報刊史料看李鴻章形象
李發(fā)根
(安徽大學 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民國時期,現(xiàn)代傳媒在宣傳人物形象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許多歷史人物的形象正是通過報紙媒體的形式呈現(xiàn)在大眾面前。文章主要從塵封已久的民國報刊史料入手,管窺當時李鴻章在人們眼中的功過是非,呈現(xiàn)李鴻章在民國報刊輿論中的不同形象,并探索這些不同形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李鴻章形象。
李鴻章;李鴻章形象;報刊史料;影響因素
民國時期,中國的紙媒業(yè)發(fā)展迅速,各種報刊雜志如雨后春筍。這些報刊史料中有大量歷史人物的記載,作為晚清重臣的李鴻章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客體,而此時的李鴻章已經(jīng)從過去的清廷重臣進入了塵封的歷史。這些報刊中有大量關于李鴻章的信息記載,涉及面非常廣,幾乎涵蓋了其一生中所有重大事跡,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眾說紛紜,從報刊史料來看,主要塑造了三種形象:“功臣”形象,“罪人”形象和“時代”形象。
1 “功臣”形象
這一方面的報刊主要是回顧李鴻章一生為清廷所辦的一系列有利于“國家民族”的大事上去探討其人生功業(yè),稱之為“功臣”,“他活了七十八歲,代我們干了不少艱難的事業(yè)”[1]62,死后贈太傅,封一等肅毅侯,由其子李經(jīng)述襲其爵位,入祀賢良祠,以此來表彰其一生為清廷所做的巨大貢獻。以至于“那是歐洲人只知東方有個了不得的人物李鴻章,而往往不知中國的國名”[2]29。
首先,是贊其在軍事、辦洋務上之功。李鴻章出仕正值太平天國運動之時,而后又暴發(fā)北方捻軍起義,在清廷內(nèi)憂外患之時,李鴻章回鄉(xiāng)辦團練,助曾國藩平叛亂,而后建立淮軍,“練淮軍助曾國藩破洪、楊之亂后,克復蘇、常也是清代史上的功績……平捻之功,李鴻章實是功臣中之個可紀念的人物……治軍練將是清代諸將中的上將”[2]29這里主要是從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農(nóng)民起義、捻軍起義以及在創(chuàng)辦淮軍管理兵將上對清廷所做的功績?nèi)ピu價他的,而這也一舉奠定其“咸同中興”功臣之重要地位。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后,作為當時變法圖強的“先知先覺者”,“鴻章出其全力苦心倡辦洋務”[2]57。有輿論認為這是其眼光方面的過人之處,光緒九年,李鴻章和曾國藩聯(lián)名上奏派遣留學生出國留學,“特別在軍事學識上尤注意造就人才”[3]30-31,這里民國學者們主要在探討李鴻章在清末國際大潮已進入西方工業(yè)時代,民族危機漸深之時,辦洋務;向西方學習新式武器制造法、新式練軍法、派遣留學生等一系列具有近代性質(zhì)的舉動符合當時時代的發(fā)展潮流,符合近代化的發(fā)展方向。這方面也當是李鴻章為“國家民族”所作的一大貢獻。同時認為其所辦洋務對后來的民國也是意義重大的“民國初年的西洋物質(zhì)文明的一切,都是李氏維新事業(yè)的遺跡”[4]18。
其次,在外交方面之功。李鴻章的后半生幾乎都與中國當時的外交事件緊密相連,他所辦的外交似乎就像當時中國的一個縮影。“天津教案”、《煙臺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交涉和條約的訂立無不經(jīng)李鴻章之手,其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而這一時期民國的一些報刊傳媒對于李鴻章在中國外交史上之地位以及他的外交才能給予了一定的肯定,清朝后期的中國所經(jīng)“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自鴉片戰(zhàn)爭,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隨著列強的紛紛侵入,“交涉事務因此日漸加多,清室乃專任李鴻章去辦理,故清末的外交,無論大小都是經(jīng)過李鴻章之手的。”,以至于時有輿論[5]420稱之為當時“滿清唯一的外交人才”[6]48時人有稱“李鴻章為一位大的外交家,以為當時列強很想瓜分中國,而中國所以能夠依舊生存下去,頗有賴于李鴻章的力量”[5]420。把李鴻章的外交才干與國家存亡相連,突出其外交政策對于維系清廷統(tǒng)治的重要性。當時的著名學者左舜生對當時有些人妄議李鴻章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李鴻章“以一身當國家對外之沖,論才氣、論資望、論聲名流傳之廣遠、論耿耿謀國之孤忠,似尚無一人及李鴻章者”[4]23。足見當時部分學者,報刊輿論對李鴻章外交才識的贊賞。
再次,在政治才能方面。李鴻章以翰林起家,歷任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協(xié)力大學生等顯赫官位。足見其政治能力在當時的水準。當年與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的俄國財政大臣維特回憶說“李鴻章之風度,卻使余所得印象特深,此次真可稱為一位大政治家”[4]34。當時西方很多學者稱李鴻章為“中國的俾仕麥(俾斯麥)”。從中亦可看出當時的一些社會人士對李鴻章政治才能的肯定,正是這方面的政治才能使他在維系清廷的統(tǒng)治得以延續(xù),挽救民族國家的危亡上起到很大作用。已對當事民國政局混亂,軍閥割據(jù)現(xiàn)狀的痛心和對強有力政治人物的一種呼喚。
最后,在經(jīng)濟方面的才能。李鴻章一生中很大一部分光陰都與洋務緊密相連,從十九世紀60年代到世紀之末,在創(chuàng)辦軍事工業(yè)的同時,他也創(chuàng)辦了一系列近代企業(yè),以及當時他爭取的一些有利于近代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對當時以至后來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近代化起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作為當時維新運動的重要部分,李鴻章以其當時的地位,影響力去創(chuàng)辦洋務,時人有言“清代維新運動,倡之者非一人,而以合肥李鴻章晚年主之最力,鴻章位隆望重,其言論遂為朝野中外所注目”[7]52時人有稱之為“中國近代企業(yè)創(chuàng)始者第一人”[6]48從中亦可看出當時的輿論對李鴻章之于中國經(jīng)濟以及中國近代化進程的重要作用。
在這種“功臣”形象的背后,我們認為有著深刻的時代因素影響著當時報刊輿論對這種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民國的中國依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軍閥割據(jù),政局混亂,民族危機,矛盾有增無減,而此時宣揚李鴻章之“功”,無疑是為了啟迪當下,尤其是近代化問題,那是民國學者們關注的重點,而李鴻章作為近代化先知先覺者,“中國近代化的第一人”,他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所作出的種種自覺或者不自覺的舉動,在當時社會無疑都具有與一種啟迪作用,值得社會的反思與研究。另一方面;近代思想的傳入,和各種新式學校建立培養(yǎng)了一大批“新式”人才,隨著時代的變化,他們的思考社會,分析人物漸漸全面,不在片面的以表面成敗作為評價的唯一標準。
2 “罪人”形象
這一方面的報刊主要是詬病李鴻章在近代中國一系列對外戰(zhàn)爭中的失敗和外交方面的喪權辱國去塑造他的“罪人”形象。
軍政方面;當時的輿論有言“淮軍二十余年訓練,毫無成績可言”[8]4平定太平軍時,克復蘇,常實屬“僥幸”,認為他在軍事上的勝利“大都是坐收人之利”[8]4,而中法戰(zhàn)爭“不敗而敗”的結局,甲午中日戰(zhàn)爭,作為當時主持北洋軍務者李鴻章“無論事前事后,都要負著極嚴重的責任”[9]36;而其性格上的某些缺陷也是被看作他無法挽救中國的原因之一,當時有報紙輿論認為“鴻章略具梟雄氣概,而缺乏駕馭群倫之鐵腕,在彼靈魂中猶不免存有婦人之仁”[10]6;有人言李鴻章雖然致力于洋務,但沒真正看清西方強國的強國本源之所在,“徒知效法西洋物質(zhì)建設,而不明西洋所以富強之本源”[10]5;清末世界潮流已形成以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為主導的世界格局,世界早已連成一個整體,要想在國際競爭中避免潰敗,國際性的視角與外交手段都是不可缺少的,而導致這一系列軍事上失敗反映在現(xiàn)實中則歸罪于李鴻章“李鴻章近視眼的政治精神與態(tài)度”[11]17,目光短淺,看不清世界發(fā)展形勢,“如果李鴻章是一個眼光遠大的政治家,應該勵精圖治,痛除私弊……但李鴻章則不然,對于內(nèi)政一點也不過問,專門在外交上玩弄花樣”[5]422。最后換的個“以夷制夷終為夷所制”[4]17的悲涼結局。同時當時的部分報刊輿論認為李鴻章麻木不仁,魚肉百姓以博取最高統(tǒng)治者的歡心,民國三十六年(1947)《寧波晨報》一篇題為《李鴻章政治學》就報道過這樣一件事,大意是說李鴻章當年出訪歐洲時和俄國外交大臣說自己在任北洋大臣時,當時直隸省發(fā)生瘟疫,每天死幾百人,但他依然會向朝廷報告“庶民無恙”,此外民國八年(1919)年第11期的《廣益雜志》載有一篇《李鴻章督粵論》的文章,言李鴻章當年任兩廣總督在廣州“打黑”時,所殺“盜匪”多為平民。以博取統(tǒng)治者歡心和提升名望。
外交方面:由于近代中國已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身為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幾乎親手辦理或經(jīng)手晚清中國所有外交事務的李鴻章自然是當時很多批評者口誅筆伐的對象。“論者多以李氏亡清當國,搆約喪權,割地賠款,辱國誤民”[11]94;有言“李鴻章是陷中國于次殖民地的大罪人”[3]32。可見當時有部分輿論將中國之敗、之恥、之辱皆歸罪于當時主辦外交的李鴻章。即使有認識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而李鴻章的外交政策也不能辭其咎”[5]420。首先;擁有近代思想的部分學者認為“外交政策的第一要義貴能洞悉當時之國際環(huán)境,并利用各國的矛盾以求達利我之目的……李鴻章尚未能也”[5]420。“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為當時國際社會中慣用的外交手段,而“李鴻章用之,除了中法越南之役外,沒有一次不是失敗的……昧于國際公法,李鴻章就是因為不知道國際公法所以起了中日大戰(zhàn)”[5]420。而訪歐期間與俄國所訂的《中俄密約》在當時有輿論認為“種下后來幾十年的禍根”。從方法手段和效果全面否認李鴻章的外交政策。
這種“罪人”形象的塑造亦有著深深的時代烙印,一方面;延續(xù)了將晚清一系列辱國戰(zhàn)爭,條約歸罪于李鴻章的傳統(tǒng)式評價,給其貼上“國賊”,“民賊”等標簽。另一方方面;由于當時的中國國情日趨惡化,中日民族矛盾不斷加深,國難當頭,而李鴻章尤為時人所唾棄莫以甲午中日戰(zhàn)爭為最,借以批評當時國民政府“不重視海防,乃海寇肆掠至此,國幾不國,無政府對于海防之認識,迄未有所表現(xiàn)者”[9]94,以古論今,警示國民與政府。
3 “時代”形象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說過“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當時部分輿論看法類似于梁啟超,有的報刊就直接指出了當時批評李鴻章的很多學者大部分是“在封建基礎上,建立著西洋文明的態(tài)度”[4]17,片面的將當代思維模式強加進李鴻章所處時代。這一方面的報刊主要是結合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和中國的國情去較客觀的分析和塑造李鴻章形象。
軍政方面;當時的民國報刊中也有很多從李鴻章所處時代特征去評價李鴻章,而不是從一些表象去給他蓋棺定論,有言認為他是“太平天國和英法聯(lián)軍的產(chǎn)物”[12]173,“是一個被動的英雄,一是時勢所造的英雄”,有言李鴻章“竭力提倡新式軍器和新式練軍法,只是清廷的王公大臣腦筋頑固,皇太后又晏于安樂,以海軍費大修頤和園,結果在歷史上造成無限侮辱”[3]31認為洋務運動與外交的失敗根本不在李鴻章,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完全由于各省割據(jù)已形成,中央徒擁虛名,而無實力,德高望重如李鴻章亦莫能挽回頽運于萬一”[7]54,當時李鴻章雖位極人臣,而實際掌權者上有慈禧太后,滿族貴戚,此外所辦洋務需大量資金,而當時的資金大量源于各省海關,可各省官員實力較大,中央很難完全管制,而李鴻章“直接所轄區(qū)域僅直隸一省,戶部不足靠”[12]176,所以李鴻章處在這樣的時代環(huán)境下“習于保守,憚于振作,自然不能有作用”[13]29;這些報刊輿論從當時的政治背景,經(jīng)濟條件等因素分析了李鴻章所辦洋務自強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罪不在李鴻章之身,他也是那個時代的“犧牲品”,集“無耐”,“悲劇”于一身。李鴻章處在那樣一個復雜的環(huán)境下也應了后人為他所寫的同情之聯(lián):“言戰(zhàn)言和兩不支,可憐一代中興將”[14]36。一定程度表達了民國時輿論對其所處環(huán)境導致的一系列“失敗辱國”的一種原諒吧。
外交方面;李鴻章后半生主要致力于外交事業(yè)上,時人常以成敗論英雄,但也有很多報紙輿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關于李鴻章所辦的外交,“我認為是沒有成功的,但我承認這也不是李鴻章個人的完全失敗,因為當時清廷的腐敗,士大夫又頑固不堪而自大妄尊……不知者以為是李鴻章誤國”[3]30-31。外交上的失敗很多源自于未看透國際形勢,而對于這方面的感悟,也是大部分中國人后來才“被迫”知道的事實,有言認為“不應該拿來作為批評的根據(jù),在當時他還有一個政策,別人則袖手無策,他還有半知,別人則全不知,李鴻章不能救國,他人無須說”[12]18。他一生所辦外交無數(shù),“雖均失敗,但弱國無外交,外交的失敗,豈能歸罪于一人”[3]30。1896年,李鴻章出訪歐洲,開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環(huán)球之旅”,同時也是唯一一次,身為傳統(tǒng)的中國士大夫,由于國情風俗的不同,而鬧出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的笑話,但民國的報紙輿論也有不同的看法,有言“這是外國人向來看輕中國人而不尊重中國習俗的緣故”[15]1242。
這種“時代”形象的塑造,我們認為是部分學者結合當時的國情,世情所做的一個反思,在肯定李鴻章對中國歷史的客觀貢獻后,開始反思是什么導致了近代中國的一系列悲劇,洋務運動和外交的失敗不是李鴻章一人之失敗,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衰敗,只有擁有一個清明的政府,一個富強的國家,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同時這也折射出當時部分學者對國家民族未來的擔憂。
4 結語
歷史上對人物的評價“唯才唯德”,蓋棺定論,而處于近代中國大轉(zhuǎn)型時代的李鴻章因其在復雜時代背景下的復雜經(jīng)歷,成為近代中國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對他的評價從來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觀點。伴隨著當時西方近代思想的傳入,在打破傳統(tǒng)儒家思想“一統(tǒng)天下”局面的同時也帶來了社會思想的多元化,正是這種多元化也導致了輿論界在不同思想指導下,不同政治背景下,不同階級立場上對李鴻章的評價形成很大的差別,從而把李鴻章塑造成“功臣”、“罪人”、“時代形象”這三種形象。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時期對于李鴻章的評價隨著社會的進步相對準確全面了,但不同形象的塑造還是有失偏頗,尚未達到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去全面分析和評價李鴻章的功過是非,去塑造一個客觀的形象。
[1]史奇生.李鴻章:拙編清代名人評傳第五章[J].江蘇學生,1934(2-3).
[2]李季谷.李鴻章與俾士麥[J].宇宙文摘,1947(6).
[3]劉鶴德.中國外交史上的李鴻章[J].復旦實中季刊,1927(3).
[4]劉廣惠.評李鴻章[J].史地社會論文摘要,1935(11).
[5]周霞.論李鴻章的外交政策[J].上海周報,1941(13-21).
[6]黃紀聲.李鴻章與近代中國企業(yè)[J].中國工業(yè),1943(2).
[7]德昌.李鴻章之維新運動[J].清華周刊,1931(2).
[8]李季谷.李鴻章與俾士麥[J].讀書通訊,1947(129).
[9]張健甫.談甲午戰(zhàn)爭的李鴻章[J].前鋒,1940(1).
[10]羅爾綱.李鴻章評傳[J].文史雜志,1944(3-4).
[11]李鴻章對于國防之認識[J].海事月刊,1933(10).
[12]蔣廷韍.李鴻章—三十年后的評論[J].政治學論叢,1931年創(chuàng)刊號.
[13]將星德:總理上李鴻章書的分析研究[J].三民主義半月刊,1945(11)
[14]耐煩.詠清宮外史人物:李鴻章[J].臺糖通訊,1947(21).
[15]左舜生.中日外交史上之李鴻章[J].外交評論,1936(3).
[責任編輯:章建文]
K26
A
1674-1104(2014)01-0092-04
10.13420/j.cnki.jczu.2014.01.023
2013-10-27
安徽省政府專項”新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項目(05100915)。
李發(fā)根(1989-)男,安徽肥東人,安徽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xiàn)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