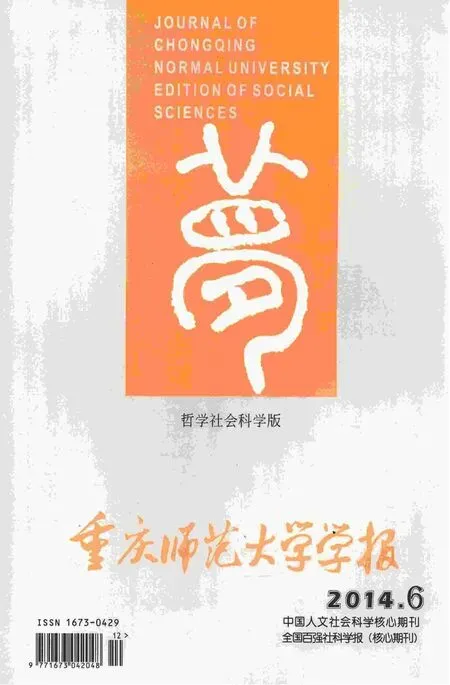公眾參與對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影響的理論分析
官永彬
(重慶師范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重慶400047)
一、引 言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走過三十余年的歷程,在經濟方面所取得的顯著成就為世人所公認。然而相對于經濟的快速增長,基礎教育、醫療衛生以及社會保障等與民生高度關聯的公共服務的發展卻比較滯后。這種以國富與民生關系失調為本質特征的增長失衡(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6),促使中國各級黨政部門的施政理念做出了順應時代要求的調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200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進一步指出要“堅持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等社會事業發展和改革,積極解決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與黨政高層的施政理念一致,承擔多重任務的地方政府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也逐漸擴大了公共財政支出,但實施效果并不明顯。《小康》研究中心(2008)公共服務滿意度調查顯示,接近70%的受訪者表示不滿意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整體供給情況。[1]此結果說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擴大公共產品的財政投入也可能無法帶來居民公共服務滿意度水平的顯著提升。這就意味著,我們有必要從公共服務需求者即公眾的視角探究公共服務滿意度的影響機制,以此為相關的民生改革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參考。
受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論思潮影響,各國政府逐漸意識到政府并不是公共生活中的唯一主體,市場、公民個人以及公民社會組織也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喬治·弗雷德里克森(2003)所言,公共生活與政府相互依賴,政府只是公共生活的一種表現。[2]46市場、公民個人以及公民社會組織參與公共生活治理,正成為公共生活“民主性”的主要標志,也將成為推動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從應然走向實然的重要力量。對于我國來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中多元化社會主體的培育,公眾的權利意識和民主參與意識也在不斷增強,這勢必要求政府部門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為公眾的強烈參與提供暢通的參與渠道和建構有效的參與機制。為此,《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首次提出:“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引導人民群眾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制定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原則上要公開聽取意見”。隨后,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拓寬范圍和途徑,豐富內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制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從上述政策宣示中可以看出,公眾參與承載著推動政府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加快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以及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多重功能,這必然對政府民生類公共服務的滿意度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然而,公眾參與與政府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關系的理論研究一直以來備受忽視。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從理論上梳理和詮釋公眾參與對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的可能影響機制,以此探尋民生改善的有效路徑。本文余下的結構安排是,第二部分厘清本文的核心概念,第三部分揭示公眾參與與公共服務滿意度的關系,最后是研究結論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公眾參與與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的概念界定
民生類公共服務。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s)屬于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范疇。公共物品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研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薩繆爾森(1954)認為,公共物品是指所有成員集體享用的消費品,社會全體成員可以同時享用該物品;而每個社會成員對該物品的消費都不會減少其他人對該物品的消費。由此可知,相對于私人物品來說,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以及受益的非排他性三個重要特征。因此,公共物品在市場上存在嚴重的“搭便車”問題,無法利用價格機制進行有效的供給,出現了所謂的“市場失靈”。這就意味著,政府理應成為公共物品的當然供給主體。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物品由政府供給并不代表由政府生產,為了提高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實踐中也采取了民營化的配置機制與模式,即公共物品由私人部門來組織生產。
根據公共物品的供給主體和溢出效應的范圍,我們可以將公共物品分為全國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前者由中央政府提供,比如國防、法律等,此類公共物品的地域性差別不大,全國的均等化程度較高;后者由地方政府提供,包括基礎設施、環境治理、市容衛生、教育、醫療、文化等,其供給水平主要取決于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和支出偏好。本文研究的公共服務一般都是指地方性公共物品或服務。此外,根據公共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水平,我們還可將公共服務分為基本公共服務和非基本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政府為保障社會全體成員基本的福利水平而向全體居民提供的大致均等的基礎性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而非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為滿足更高層次的社會公共需求而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服務,如高于社會保險水平的高福利等等。本文分析的公共服務,主要指的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即民生類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滿意度。公共服務滿意度(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最早從市場營銷學和企業管理學中的顧客滿意度概念借鑒而來。一般來說,顧客滿意度是實際績效與期望值之間差異的函數。正如Oliver(1980)所指出,顧客滿意度是一種心理狀態,是由預期感知不一致產生的情緒和顧客購買前的感受結合在一起的結果。[3]從這個角度來看,公共服務滿意度是指轄區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預期效用與實際感受的差距的認知,或轄區居民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滿足自身需要程度的一種判斷。公共服務滿意度是居民在體驗公共服務的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心理反應。當居民的實際感受與預期效用一致時,居民將產生肯定、愉悅、滿足的積極心態(Osborne&Gaebler,1992)。[4]在居民滿意度的衡量構面上,Czepoel(1974)認為民眾滿意度可以看作是一種整體的評估反應。[5]事實上,轄區居民享受著多元化而非單一性的公共服務,所以本文研究的公共服務滿意度是轄區居民對其感知到的公共服務的總體評價。考慮到居民對政府公共服務效果整體績效的主觀評價并沒有明晰的差異臨界點,為此,我們在問卷調查中按照滿意程度設計出“很不滿意”、“不滿意”、“一般”、“滿意”以及“非常滿意”五個級次。
公眾參與。公眾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指的是在公共服務供給決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公眾以合法的形式和渠道表達切身利益訴求和需求意愿,并影響公共服務供給決策過程和結果的行為。根據參與主體的不同,公眾參與既包括公民個人身份參與的個體性參與和私營企業、公民社會組織等利益群體參與的組織性參與。而從參與形式來看,公眾參與不僅僅體現在投票、選舉等政治參與上,還體現在聽證、座談等行政參與上。公眾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的核心內容,也是優化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決策、實現公共生活民主性和公共性的重要途徑。但在公共權力主導公眾參與的背景下,有效的公眾參與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信息公開。信息公開是公眾民主參與公共服務供給決策的基礎條件和內在要求,因為信息公開保障了公眾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而知情權不僅影響公眾參與的意愿和能力,也影響公眾參與的實際成效。二是過程參與。私營企業、公民個人以及公民社會組織等多元治理主體全面參與到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之中,是公眾參與制度的核心和本質要義。三是政府回應。政府積極回應和滿足公眾多樣化的利益訴求與需求偏好是保障公眾參與有效性的關鍵。
三、公眾參與對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的影響機制
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是公眾基于自身感知的主觀評價。從理論層面上說,這種主觀評價既受到政府行為因素,也受到環境特征、地區特征和個體特征等諸多潛在外生因素的影響。本文主要考察公眾參與對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的影響。接下來,我們從理論層面上梳理和詮釋公眾參與對公共服務滿意度的可能影響機制。
第一,公眾參與通過影響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偏好,進而影響民生類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諾思(Douglass C.North,1981)指出,制度就是為約束謀求財富或效用最大化的個人行為而制定的一組規章、依循程序和倫理道德行為準則。[6]也就是說,理性的個體總是在一定制度框架或環境的約束和誘導下做出某種行為,從這個層面看,新制度經濟學便為理解個體的行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邏輯。在新政治經濟學看來,政治市場上政府主體的行為與經濟市場上經濟主體的行為一樣,總能放置于各種約束其行為的制度環境中加以動態理解。在現行的政府垂直治理體制中,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考評制度將決定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和行為方式。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促進地方經濟增長進而推動全國經濟發展的要求,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的選拔和晉升的標準由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的政治績效為主轉變為經濟績效為主。因此,在中國現行以經濟績效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框架下,相對于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中央政府來說,承擔多重任務的地方政府將會選擇性地配置財政資源,亦即傾向于帶來短期增長績效的生產性支出項目而忽視與民生關聯的福利性支出項目。正如Prudhomme(1995)所指出,財政分權體制下擁有自身目標函數的地方政府不會天然地對本轄區居民的福利需求偏好作出積極回應(responsiveness)。[7]Demurger(2001)的研究也發現,地方政府為了推動本地區經濟增長,把過多的財政資源配置到生產性投資之中而忽視了社會性公共物品的建設。[8]國內學者龔峰、盧洪友(2009)構建了教育支出等7類公共支出的供需匹配指數,實證發現,隨著政府公共資源配置權力的擴大,地方政府具有不顧轄區居民實際需求而膨脹行政成本和擴張基建支出的雙重傾向。[9]尹恒、朱虹(2011)的實證研究同樣表明,中國縣級政府決策者主要對上級負責,追求盡可能高的經濟增長率,而非居民福利最大化,導致其財政決策偏向生產性支出。[10]而作為民主制度核心內容的公眾參與將有效重塑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偏好,激勵地方政府從增長導向的發展型政府向民生導向的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從而增強地方政府對教育、醫療、社會保證等民生需求的敏感性和回應性,進而提供社會合意的公共服務,改善轄區居民的公共服務滿意度。正如Oates(2005)所指出,民主參與制度較之于專制集權體制更能滿足選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11]這是因為制度化的公眾民主參與可以給地方政府施加一種橫向問責(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的壓力。對于中國的民主體制來說,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司法體系等橫向問責機制是用以引導、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的關鍵性制度安排(郁建興,高翔,2012)。[12]這種以人民代表和政治協商為途徑的民主參與制度可以削弱因基礎建設擴張導致的公共支出結構扭曲,使地方政府支出行為更加趨向于與民生關聯的公共品供給(趙永亮、楊子暉,2012)。[13]因此,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框架下,通過公眾參與對具有多重利益目標的地方政府施加問責壓力,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決策和執行過程中更加反映民生訴求,提供更加優質化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
第二,公眾參與通過影響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決策,進而影響民生類公共服務的滿意度。由于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公共文化等優效品和服務(merit goods and services)以及社會保障和福利等市場機制無法有效供給,所以,這類與民生高度關聯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應該納入政府的職責范圍。但是,政府的角色也會由于信息約束而受到限制(吉恩·西瑞克斯、加雷思·D.邁爾斯,2011)。[14]212因為,在公共物品供給決策中,導致政府無法做出有效率決策的一個因素是政府缺少消費者的偏好與公共物品支付意愿的信息(吉恩·西瑞克斯、加雷思·D.邁爾斯,2011)。[14]212速水佑次郎(2003)也指出政府往往不具備準確掌握基層公共物品需求結構的能力。[15]200從物品的需求來看,私人物品可以通過消費者的貨幣投票直接傳遞出消費者的偏好,而公共物品卻無法從消費者強制性的稅收支付中判斷其真實偏好。這是源于公共物品的供求決策是通過政治制度而非市場制度實現的,并且不存在可以輕松進行公共物品供求分析的競爭性秩序的對應物(詹姆斯·M.布坎南,2009)。[16]5更為重要的是,公共物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以及受益的非排他性,導致其供給過程中面臨著搭便車(free rider)問題,使得公共物品和服務的偏好顯示出現扭曲。因此,由轄區內所有潛在公共物品受益者組成的集體消費單位需要建立一種替代性的價格機制,來表達和傳遞其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邁克爾·麥金尼斯,2000)。[17]109-110經濟學家蒂伯特(Tiebout,1956)、威克里、克拉克(Clark,1971)等基于不同假設提出了公共物品的偏好顯示機制(preference revelation mechanisms),但都難以契合中國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背景。鑒于民生類公共服務的范圍、屬性和特征,以及不同區域、不同階層居民公共服務需求異質性的事實,帕累托最優的選擇是引入公眾參與機制,讓擁有更多知識和信息的公共服務需求者參與到公共服務供給決策中。公眾參與的過程也是公共服務供給者與需求者即地方政府與轄區居民之間的雙向溝通和信息流動的過程。在這互動的過程中,一方面,轄區居民可以真實表達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意愿和利益主張,避免信息的扭曲和漏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準確識別轄區居民的公共服務需求偏好,減少信息搜尋成本。可以說,公眾參與機制在公共服務供給者與公共服務需求者之間架起了一座信息溝通的橋梁,促進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進而有助于改善轄區居民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鄧佑文(2011)認為公眾參與可以有效彌補行政領導和決策專家認識理性的有限性,實現行政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18]呂建華、郭玲玲(2008)也認為公眾參與減少了信息扭曲的概率,擴大了政策資源的提取范圍,減少了政府行為和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從而有助于提高政府績效。[19]趙永亮、趙德余(2012)的實證研究表明民主參與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減少公共物品供給與民眾需求偏好之間的差距。[20]
第三,公眾參與通過影響公眾對地方政府的信任,進而影響民生類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政府信任是建立在公眾對政府的合理期待以及政府回應基礎上的一種互動、合作關系(張成福、孟慶存,2003)。[21]它是公眾對政府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種政治心理(上官酒瑞,2011)。[22]從歷史形態演變的視角,政府信任可以劃分為“習俗型信任”、“契約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種類型的信任關系(張康之,2005)。[23]對于現代民主國家政府來說,政府信任構成了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基礎(Easton,1965)[24]273,因而對于政府的順利運作和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胡榮等,2011)[25]。但是,“信任是內生而不是外生的,信任取決于制度的供應”[26]259,因為“制度提供人類在其中相互影響的框架,使協作和競爭的關系得以確定,從而構成一個社會特別是構成了一種經濟秩序”[27]195。而公眾參與制度正好保障了公眾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政治權利和合法渠道,促進了公眾與政府間在更廣的范圍內和更深的層次上的良性互動,形塑出一種新型的公共服務多中心合作治理格局,進而在公眾與政府之間逐漸培育和內生出持久和穩定的合作型信任關系。由是觀之,制度化的公眾參與可以提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朱國瑋等(2005)認為公眾參與政策制定過程有助于消除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隔閡從而改善政府信任。[28]胡榮等(2011)則運用廈門市居民的問卷調查數據實證分析表明,城市居民公共事務參與對城市居民政府信任存在積極正面的效應。[25]也有部分學者從公眾參與政府績效評價活動的視角考察了公眾參與對政府信任的正向影響(吳建南等,2007)。[29]高水平的政府信任一方面可以改進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減少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和效果,進而有助于回應和滿足公眾對公共服務的迫切期待和利益訴求。Grimes(2008)認為高的政府信任促進了公眾對行政決策的認同[30],并支持政府行動去實現政策目標(Chanley et al.,2000)[31]。章延杰(2007)指出政府信任在某種程度上防止了政府權力的濫用,從而減少了社會資源的浪費,確保了政府提供較高水平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最終促進社會福利。[32]81此外,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高度關聯(Schyns&Koop,2010)[33],政府信任有利于社會信任的生成(Hudson,2006)[34],而社會信任作為一種社會資本可以提高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速水佑次郎,2003)[15]288。另一方面,高水平的政府信任可以促進公眾形成穩定和樂觀的預期(Hudson,2006)[34],并相信政府未來能夠動用更多的公共資源以持續改善居民的福利狀況,進而影響公眾對現在公共服務供給績效的主觀評價。
上述理論分析表明,公眾參與可能通過多種傳導機制或路徑影響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且這些傳導機制或路徑對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的影響方向都是一致的。這就意味著,在控制其他外生變量的情形下,公眾參與可能是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的重要促增因素,擴大公眾參與能提高居民對民生類公共服務的滿意度。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的理論分析發現,公眾參與對民生類公共服務滿意度的影響渠道可能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公眾參與矯正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偏向,增強了地方政府對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關聯公共服務的敏感性和回應性,促進了地方政府從經濟增長為導向的發展型政府向民生需求為導向的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進而可能改善了居民公共服務滿意度;二是公眾參與優化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決策,克服了地方政府與轄區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促進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進而可能增加了居民公共服務滿意度;三是公眾參與通過地方政府與轄區公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培育出了一種持久和穩定的合作型信任關系,該信任關系不僅提高了公共服務供給效率,而且促進了公眾樂觀和穩定預期的生成,進而可能提升了居民公共服務滿意度。總之,地方政府在民生關聯的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擴大公眾參與的程度,將顯著提升轄區居民對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水平。這對于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轉變政府職能,改善國家-社會關系,實現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私營企業、公民個人以及公民社會組織等多元化主體參與公共生活治理是公共生活“民主性”的主要標志,也是實現公共生活“公共性”的重要途徑。本文的理論分析表明,公眾參與可能是居民公共服務滿意度的主要來源。因此,為了有效發揮公眾參與對公共服務滿意度的促增效應,強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效果績效,改善民生福利水平,我們的政策著力點應放置于如何從體制機制層面上保障私營企業、公民個人以及各類社會組織有序參與公共生活治理的有效性和持續性。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公共事務信息公開制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決策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其次,拓寬公眾參與公共生活治理的制度化渠道,真正賦權于公眾,使各種利益相關者都能通過多元化的途徑或形式(如民主投票、聽證會、咨詢會等)參與公共服務供給決策,合法表達自身公共訴求和利益主張;最后,構建和完善地方政府回應機制,公共服務供給是自下而上的民意獲取和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相結合的過程,在整個供給過程中應該始終堅持民生需求為導向,有效滿足轄區居民普遍性和差異性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需求,以此保障和改善民生。
[1]《小康》研究中心.轉型期的公共服務2008中國公共服務小康指數:67.2[J].小康,2008,(3).
[2]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L.A.Oliver Richard.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0,(17).
[4] Osborne David and Gaebler Ted.,Reinventing Government—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M].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2.
[5]Czepiel J A.,Perspective on consumer satisfaction[C].Chicago:AMA Conference Proceedings,1974.
[6]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urk:Norton&Company,lnc,1981.
[7]Prudhomme.Dangers of Decent realization[J].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International),1995,(10).
[8]Demurger,S.,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
[9]龔峰,盧洪友.公共支出結構,偏好匹配與財政分權[J].管理世界,2009,(1).
[10]尹恒,朱虹.縣級財政生產性支出偏向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1,(1)
[11]Oates,W.E.,Toward A Second Generation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J].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005,(12).
[12]郁建興,高翔.地方發展型政府的行為邏輯及制度基礎[J].中國社會科學,2012,(5).
[13]趙永亮,楊子暉.民主參與對公共品支出偏差的影響考察[J].管理世界,2012,(6).
[14]吉恩·西瑞克斯,加雷思·D.邁爾斯.中級公共經濟學[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5]速水佑次郎.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16]詹姆斯·M.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與供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7]邁克爾·麥金尼斯.多中心體制與地方公共經濟[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18]鄧佑文.公眾參與行政決策:必然,實然與應然[J].理論探討,2011,(2).
[19]呂建華,郭玲玲.論我國政府績效評估之公眾參與的可行性與必要性[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
[20]趙永亮,趙德余.分權體制下的民主參與,政府響應程度和公共品供需偏差[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2).
[21]張成福,孟慶存.重建政府與公民的信任關系——西方國家的檢驗[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3).
[22]上官酒瑞.從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當代中國政治信任變遷的基本圖式[J].學習與探索,2011,(5).
[23]張康之.在歷史的坐標中看信任——論信任的三種歷史類型[J].社會科學研究,2005,(1).
[24]Easton,David.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M].New York:Wiley,1965.
[25]胡榮,胡康,溫瑩瑩.社會資本,政府績效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J].社會學研究,2011,(1).
[26]程倩.論政府信任關系的類型[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
[27]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M].歷以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28]朱國瑋等.公眾信任關系形成機理研究[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5,(2).
[29]吳建南,張萌,黃加偉.公眾參與,績效評價與公眾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員的實證分析[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30]Grimes,M.,Consent ,Political Trust and Compliance:Rejoinder to Kaina’s Remarks on‘Organizing consent’[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008,(4):522 -535.
[31]Chanley,Virginia A.,Thomas J.Rudolph and Wendy M.Rahn,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 Time Series Analysis[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2000,(3):239 -256.
[32]章延杰.政府信用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3]Schyns,Peggy and Koop,Christel,Political Distrust and Social Capital in Europe and the USA[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0,(1):145 -167.
[34]Hudson,John.Institutional Trus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the EU[J].Kyklos,2006,(1):43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