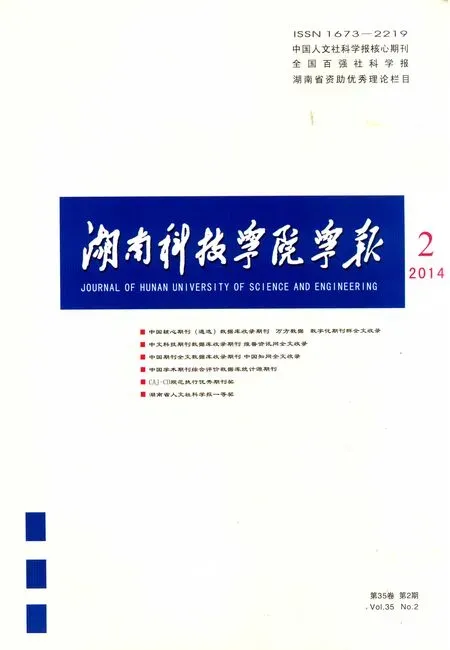明代閩南布衣詩人黃克晦的詩歌內容探析
洪云媛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有明一代,在福建詩壇占據主導地位的是以福州府為主的閩中詩派。因福州是八閩都會,人才輩出,知名者眾,故該詩派影響很大,幾乎成了閩詩的代稱,而閩南地區的詩人則常常被忽視,黃克晦就是其中一位。黃克晦(1524-1590),字孔昭,號吾野,福建惠安人。因高祖為崇武千戶所的兵卒,按照當時的戶籍制度,黃克晦被列為“軍戶”,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雖嗜學苦讀,精通文墨,卻終身無法擺脫布衣身份。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月,倭寇襲占崇武衛城,黃克晦攜家眷搬到泉州城中避難。城中名士、學者和府郡官員,聽其名讀其詩,爭與之相交結識。隆慶四年(1570)第一次離家出游,覽武夷,泛彭蠡,由兩粵入吳楚,適金陵,歷經齊、魯、燕、趙,登泰、衡、嵩、華諸岳。每到一處,則詠景抒情,與當地名士交游。萬歷七年(1579)自燕京歸閩地,同舊日詩社朋友吟詠為樂。萬歷十六年(1588)應好友之約再次出游,兩年后因病返鄉,不久即逝。其亡后,祀于福州烏石山高賢祠。所著有《黃吾野先生詩集》五卷。在其所存的1400余首詩中,體裁多樣,近體優于古體,而以七律最為突出,且數量也最多,有400多首。黃克晦一生歷經嘉靖、隆慶、萬歷三朝,客游在外十余年,足跡幾乎踏遍全國,各地的山川景物、通都大邑、人物風尚,都成為創作的題材,故其詩歌內容十分豐富。
一 感時刺事詩——傷心萬古此年華
明代朝廷一直飽受邊患危機的困擾。除了北方韃靼的威脅,南方沿海地區的日本浪人和中國海盜相互勾結,打家劫舍,殺人越貨,江淮至廣東一代的富庶地區往往損失慘重。明初朱元璋頒布禁海令,派遣大臣前往沿海各地筑城防御,建立起包括衛所、巡檢司以及水寨在內的海防體系,有效遏制了倭寇的肆虐。明中后期以后福建的軍事勢力不斷孵化衰退,倭寇遂日益猖獗,不僅閩東深受其苦,閩南也難幸免。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月,“倭寇襲陷(惠安崇武)所城,駐四十余日,屠掠甚慘”[1]P6。黃克晦之兄為賊刃所傷,家財被搶,全家徙居晉江避難。這一切身的體驗使他將筆觸直接對準倭寇給百姓帶來的災難,如《亂后再過洛陽橋》:“松花小徑過柴車,亂石荒苔去去徐。數里一沾驚蟄雨,二旬三食洛江魚。春來為客多堪恨,亂后空村有廢居。安得閭閻無警報,在家長讀古人書。”[2]P765洛陽橋在惠安縣洛陽江上,是崇武到泉州的必經之道。黃克晦倭亂之后經過這里,只見一副荒村殘破的圖景。“松花小徑”和“洛江魚”這些富有地域色彩的閩南風情,與“亂石荒苔”、“空村”、“廢居”的凄涼氣氛形成鮮明對比。恬然自適的讀書生活被打破,抗擊倭寇、平息戰火成為詩人此時最大的愿望。再如《經惠陽傷亂》:“東粵重來倍黯然,荒村古堡暗蒼煙。山中故老無歸業,水上新民未種田。江燕春深巢樹腹,野狐日落吠溪邊。東風那管亂離事,春色藤花似往年。”[2]P741惠陽在廣東省東部近海地區,隆慶年間倭犯粵東,大肆劫掠。黃克晦離家出游至此,所見亦是倭患帶來的荒涼景況,人民流離失所,田園一片荒蕪。蒼煙暮靄,白日如夜。末兩句的東風暗喻明王朝的統治者,深含規諷之意。另一首《龍川道中》同樣寫出當時的倭禍災情:“渡頭過雨落花泥,嶺上黃昏老馬嘶。欲問江山千里恨,相逢故舊數聲啼。人煙寂寂孤城小,驛火星星去路迷。歸客何能心不戒,逃兵殘寇尚東西。”[2]P742龍川縣在明屬惠州府,倭患頻仍。黃昏的渡頭嶺上,但見孤城寂寥。去路艱難,一方面因雨后道路泥濘,一方面則因倭患未除,不僅有倭寇焚掠,還有不知何時而至的官兵騷擾。結句一針見血地點出百姓面臨的雙重災難,言淡而意深。
明代中葉,特別是嘉靖和萬歷年間,封建官僚政治日趨黑暗腐朽,皇帝昏庸荒唐,民不聊生。黃克晦以布衣身份長年在外奔走,作為游離于階級底層的一員,他能夠廣泛地接觸到社會現實,見證下層民眾生活的艱難,因此多在詩歌中傾注對民生疾苦的體察和理解,大膽言及政治得失。如《呂梁洪得沙字》:“滿目驚濤撼客槎,傷心萬古此年華。舊河屢決徐州野,新水全沉故老家。風雨只今愁白日,魚龍何處避黃沙。臨流思禹心無極,蘋蓼蕭蕭只白花。”[2]P785呂梁洪在江蘇銅山縣,屬徐州地區。黃河流經這個地方時常常決潰,泛濫成災。《萬歷徐州志》載:“隆慶五年九月六日,水決州城西門,傾屋舍,溺死人民甚多。”黃克晦此時恰好在吳游歷,目睹黃河決堤,田園住宅俱被淹沒。當年大禹治水,為民解除了洪水之患,而如今統治者卻疏于洪水的防患治理,秋風中的蘋蓼蕭索,更添凄涼。全詩感慨深沉,表達了作者對災區百姓的無限同情和關心。又如五言排律《聞福安飛粟》中的“倉陳何歲食,村積幾家登”,“善斂官應悔,防貧賈合憎。杜陵餓一老,聞此意難勝”[2]P734,詩人對貪官污吏和奸商囤戶勾結起來剝削民脂民膏的黑暗現實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指責。七言古詩《探春行》“春風莫入貧人家,城中自古事豪奢。中山王孫多第宅,水邊石際皆名花。貧家東阡與西陌,但覺栽桑與種麥”[2]P700,通過鮮明的景色對比,表現出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
除了反映倭亂和民生的寫實之作,黃克晦的諷喻詩同樣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這類詩歌大多以七言古詩的體裁出現,運用白描或比興手法,在對一禽、一獸、一事、一物的描繪中抨擊明代社會的各種丑惡現象。如《觀千里馬》先是用大量筆墨細致刻畫了千里馬的雄姿,結尾則以“乾坤自古憎尤物,鹽車鼓車徒拂郁。漢主安知非好名,燕昭未必真憐骨。何如只放渥洼中,日與真龍相出沒”[2]P681展開議論,古代賢君如漢武帝和燕昭王尚且只是以千里馬來裝點門面,如今的人杰俊才更加得不到重用。作者以千里馬自況,只愿保持本性,自由自在地生活于山野之間。雖懷才不遇,但態度卻是積極的。《二鸚鵡吟》因萬歷元年宮內使臣耗時費力,萬里跋涉為皇帝尋得兩鸚鵡,不料未及回京帝已殯天一事有感而發。全詩純用白描,“鼎湖龍去可能攀,雪涕千行空灑面。小臣辛苦世豈知,二鳥瑰奇君不見。不及山雞死道傍,楚王賞客悲鳳凰”[2]P680。既嘆紅白兩只奇異的鸚鵡不得賞識,又諷刺了中使諂媚求寵的小人嘴臉。《鴉鵲行》則比物寄興,描寫世人愛鵲而厭鴉,“愿君聞鴉莫嗔鵲莫喜,出門大道平如砥。從教百福集君深身,不厭鴉聲在君耳。吁嗟,蒼梧翠竹生高崗,誰能為汝訴鳳凰。罰鵲以佞嘉汝忠,為汝結巢巢其傍”[2]678,詩人以鵲比惑主奸佞,用鴉喻直言君子,希望大道如砥,忠言得用。
二 山水詠懷詩——歸期來日總俱忘
黃克晦一生好游,游屐所及,必有吟詠,故其山水寫景,行旅紀游的篇章數量尤其多,游粵有《七星巖得含字》、《舟中望羅浮》,于贛有《入彭蠡湖口作》、《宿開先寺望香爐瀑布之作》,至吳有《燕子磯》、《石城霽雪》,入楚有《潯陽舟中懷古分得何字》,抵洛有《風雨飲天中閣》、《嵩陽宮三將軍柏》等,而他生長的泉州本身就是風景絕佳之所。作為對美有極其敏銳捕捉能力的詩人,黃克晦以極其細膩的筆觸寫出了家鄉獨特的風貌。比如《清源洞分得堂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其詩云:“飛蘿影外敞僧堂,啼鳥聲深客座涼。出樹低云初渺渺,渡江片云忽茫茫。千灣白處皆煙浦,萬點青中各水鄉。莫道閑巖惟暫宿,歸期來日總俱忘”[2]。清源洞又名純陽洞,在泉州北郊清源山上。作者熟諳閩南海邊景物,從最能顯示亞特帶風光特征的景物落筆,以藤蘿詠山奇,用啼鳥襯托其清幽靈秀,狀洲諸則通過千灣煙浦白中見青的色澤傳神,摹寫出南國雨中山水溫潤、翠澤的獨特神韻。承平歲月中家鄉之景固然美麗,倭亂后復見則更讓人珍惜。隆慶己巳年(1569),因倭患離開崇武十年的黃克晦重回故里,登山縱覽,寫下《秋日奉陪都閫歐陽新田先生集諸彥登龍喉巖用丁仁守韻二首》。其一中的前兩聯“海天南望戰塵收,漠漠平沙罷唱籌。漁艇已聞煙外櫓,農人又住水邊洲”寫出戰亂平息之后一派生機勃然的氣象。漁民出海謀生,農人下地耕田,崇武半島上的人們生活恢復了原來的節奏。其二“十年避亂別江灣,不道清游更此山。野奪長風吹古瓦,海門驚浪破重關。石間龍氣過腥雨,天外禽言絕島蠻。鄉國升平歸思切,釣磯應伴白鷗閑”[2]P766。闊別十年之后重游大岞山龍喉巖,人事已非,唯有長風吹瓦、海門驚浪猶似從前。末聯用白鷺忘機的典故,在海疆的倭患已被大軍掃平的今日,詩人渴望回到家鄉,過著垂釣磯頭,與白鷺為侶的悠閑生活。
王國維曾說:“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3]P1黃克晦的寫景詩,或細筆或工筆,或寫意或白描,都是其情感的寄托。如《白鶴峰謁東坡祠》:“直到明時尚不容,一身萬死任西東。青山猶有當年宅,古木空遺百代風。地靜沙禽巢翠瓦,春深野蔓上虛櫳。江蘺薦罷孤舟去,棹唱含凄月影中。”[2]P742蘇軾在政治清明的時代尚不見容,被貶數地,東西漂泊,詩人之不遇何其相似。如今青山空宅,只余禽鳥蔓草徒增寂寥,任人懷想東坡當年風采。用江蘺祭奠之后,獨自乘坐孤舟,在月影中唱著凄涼的棹歌離去。此詩對東坡寄予無限的同情,憐東坡亦自憐。
黃克晦登山臨水,尋訪名勝,憑吊古跡,往往帶著感時傷逝的沉郁情懷,把歷史的回憶與現實的感觸交織在一起,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南臺懷古》“霸國春云外,高臺釣渚間。白龍潭下水,五虎廟前山。松響風聲幔,潮來雨滿關。翠花終不返,鳧鷺自成班”[2]P705,憑吊古閩越無諸國。首句氣魄雄渾,總領全詩。頷聯福州的白龍潭水、五虎山廟和頸聯的潮雨滿關、松風生幔相承相應,脈絡分明。末句則抒興亡之感。閩越國的霸業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江上鷗鷺成群結隊,鵠立灘頭,像當時人臣朝班一般。
三 酬贈送別詩——故人未暇平安否
黃克晦的交游極廣。據周良寅《明高士黃吾野先生墓志銘配勤懿戴氏墓志銘》中載:“公雖飄然物外,不向人間,而聲名所集,諸豪賢無不愿交公者。及入晉江,則大令玉橋朱公,大宗伯儀庭黃公,司寇咫亭詹公,今大司馬鐘梅黃公,相與分題唱和,非從世態俯仰”,“爰由兩粵入吳楚,適金陵,歷齊、魯、燕、趙,所過大都……隨地應酬,不能枚舉。其名碩,若博羅葉炯齋,楚黃二耿,吳、馮具區,金陵焦從吾,瑯琊二王,諸公咸盟心唱酬。北至京師,則公之游日廣”。[4]P16黃克晦所交,既有上述的達官顯貴,也有社會下層的僧人道士,既有知書達理的文人,也有目不識丁的田野村夫。生活中的廣泛交游,生動地體現在他的詩歌中。
多情自古傷離別。黃克晦輾轉各地,為人送行或與人辭行時,多寫詩相贈。這些送別詩中,不僅有傳統上的惜別之情,有對友人的囑托、勉勵、贊揚、安慰,更有對邊塞景象的展現和對愛國熱情的歌頌。這類贈詩對象,多為當時的戍邊抗倭將士。如《送陳季立領輕車步兵出邊防》三首七絕:“百二輕車鐵作輪,五千步卒去如奔。塵中只有龍蛇影,駐處方知虎豹蹲。”“剖石如瓜試寶刀,眾中誰不羨君豪。數聲畫角城鴉起,立馬轅門太白高。”“鎏金長戢繡鍪弧,千里行邊漢月孤。會得君王開笑面,殿前生獻小單于。”[2]P802陳第,字季立,號一齋,福建連江人。歷任京城兵車營教官、潮河川提調、游擊將軍,坐鎮薊門10年,后隨沈有容渡海東蕃(即臺灣)剿倭。黃克晦曾作七言古詩《閩中豪士歌贈陳游擊》,贊美友人慷慨豪邁,投筆從戎,忠心耿耿的報國情懷。此詩則為萬歷四年(1573)八月陳第領京營兵三千人到薊門駐防,黃克晦相送時所作。先寫雄偉的行軍陣勢,精良的武器裝備和勇猛威武的士兵,次寫主將英雄豪爽,氣概不凡,不顧辛苦深夜巡視軍營,最后想象前線報捷,戍邊將士生俘敵軍首領。三首詩一氣呵成,層層遞進,表現出黃克晦對陳第駐守北疆,抗敵必勝的信心。萬歷十六年(1588),黃克晦進京經過洪川(今屬安徽),偶遇陳第家仆,聽聞好友因剛正不阿,不畏權勢而遭讒被迫辭職,寫下《買舟洪川逢陳游擊邊豎因感舊遊卻寄》,詩中“昔余北上軒轅臺,北風吹律玄冥開。陳君舞劍佐予飲,傾囊盡付纏頭錦。酒酣畫地談九邊,九市雞鳴人未寢”回憶了當年與陳第品茶煮酒,徹夜討論時局的情景,而“舊帥來詢起冢高,故人未暇平安否。薊門夜夜星動搖,邊庭降虜志頗驕。南兵三千豈不壯,鼓旗還屬霍嫖姚。嫖姚守邊胡自遠,謗書盈篋尋常玩。廉藺論交豈易深,田竇門客方相怨。公子能窺晉鄙符,將軍合飽頻陽飯。登壇應屬汝主人,丈夫侯王須即真。若但偏裨借顏色,何時圖像登麒麟。汝今不啻雙鯉魚,刮腹藏余萬里書。為道功成即相覓,幔亭峰頂予獨居”[2]P697,則對陳第飽含牽掛和鼓勵,期盼他能繼續抗敵立功。
在黃克晦的送別詩中,除了生離,還有死別。萬歷八年(1580),抗倭名將俞大猷病逝,作為與其交誼甚篤的同鄉好友,黃克晦寫下了三首五律《挽俞都督》寄托哀思:“大星落東海,涕泣滿城哀。百戰功徒在,千秋夢不會。云消天地氣,世絕古今才。寂寞廉頗館,空余吊客來。”“名在周元老,精淪漢巨儒。百年吾道失,十載友情孤。悲撼將軍樹,哀生孺子芻。淋漓雙淚眼,看碧已成珠。”“駟馬悲鳴日,非熊卜臘年。陰符藏鬼谷,玄甲筑祈連。痛哭余孤憤,艱危息兩肩。惟應麟閣上,遺像儼生前。”[2]P711黃克晦曾在嘉靖年間與俞大猷同游浙江大佛寺,在萬歷初年受俞邀請參觀其在京城的兵車營,并有《觀俞都護戰車二首》、《神機營同黃郎中觀俞都護演車戰法》兩詩表現俞家軍演習的壯觀場面。在黃克晦的心中,俞大猷不僅是朋友,更是保家衛國的良將。如今國家艱危之際,友人的才能卻不能為世所用, 溘然長逝,黃克晦流露出無限的哀痛惋惜之情。挽詩從死后說到生前,又從生前說到死后,狀寫了俞大猷立下的千秋功業,透著一股沉郁頓挫的蒼涼情懷。
黃克晦生長于海上交通發達的泉州,在他的詩作里,對這一方面的內容也有所描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送琉球生還國》:“圣教無天外,華風自海中。三臣辭卉服,五載入槐宮。返國君恩重,談經漢語通。片帆看漸小,萬里去何窮。托宿憑鮫客,傳書倚水童。重來應有日,臨別此心同。”[2]P734萬歷年間黃克晦游歷南京時與被派到國子監學習的琉球生結識,時有詩酒往來。在他們結束學業即將歸國時,黃克晦依依難舍,希望有一天能再度重聚。這首詩反映了明朝與琉球友好往來的歷史片段,是我國外交史上的一篇重要詩作。
黃克晦一生失意,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計,有時免不了應付場合的酬贈之作,然而更多的是與至交好友的唱和,如與故鄉詩社友人顏廷榘、詹仰庇、蘇浚等皆有不少贈答的詩歌。在這類詩歌里,詩人往往能流露出自己的真實感情。特別對于同是布衣的浙東詩人沈明臣,黃克晦更是多了一層同病相憐的感慨。他在七言古詩《送沈山人嘉則之太倉兼寄王廷尉曹文學》中語帶雙關地自稱:“海客家臨日月池,不識江湖水深淺。北游燕薊青天遙,南經維揚路凌緬”[2]P695。明代中后期,政局波詭云譎,黃克晦所交好友黃克纘、俞大猷等在宦海幾經浮沉。詩人作為來自閩海的一介平民,清楚意識到人微言輕的困境,現實政治斗爭的嚴酷,也使他以戒懼之心觀察和表現現實。再看《又答沈嘉則次韻》:“風雨瀟瀟暗綠蘋,一樽湖海共比鄰。自憐多病長為客,還笑無家不傍人。江水空教流日月,云霾何處辨星辰。惟應滿酌黃花酒,共倒南山白氎巾”[2]P786,明確表達了自己獨立不阿的態度。詩人無緣仕途,飄泊在江湖之間,免不了受人冷眼。但他“一切交游,絕無俯仰”(翁應祥序)。生活在內憂外患的時代里,惟愿與有同樣遭遇、同樣志趣的友人遠離鬧市,飲酒為樂。
四 題畫詩——醉里水墨涴縑素
中國的題畫詩歷史悠久,內容廣泛,在浩如煙海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詩作者不是畫家本人,而是作為賞畫者根據畫面所賦的詩。黃克晦卻與之不同,他不僅工詩,且兼擅書畫,有“三絕”之譽。《佩文齋書畫譜》:“黃克晦畫筆蒼勁,閉戶經月成者,尤可傳世”。[5]P1545其題畫詩多是在自己的繪畫作品完成之后所做,善于將詩情和畫境融合為一,詩中見畫意,畫中蘊詩情,以畫家的眼光敏銳地觀察色澤的變化,合理地構圖布局,創造出詩情畫意渾然交融的意境。如《題畫》:“青山不盡大江流,兩岸山高萬壑幽。薄暮風生波頭白,釣航無恙荻蘆秋。”[2]P809青山、白浪、荻花、船聲、風聲、江聲一起投向讀者的視覺和聽覺,以動寫靜,勾勒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畫面。
黃克晦不僅善于以詩寫畫,而且善于根據所畫進行聯想,揣摩畫中人的心理,將人物描繪得豐滿靈動。如《為周文學題美人握絲圖》:“春鶯日高啼百花,屏風卻轉朱欄斜。美人墜髻盤棲鴉,手操絲綸繅小車。一絲一縷澤如發,千尺百尺車軋軋。染處誰憐色最深,合時誰道心如結。窗前欲辦嫁時妝,金針九孔機流黃。錦衣繞體亂蛺蝶,繡枕留夢飛鴛鴦,昨夜三星在北戶,公子同歸何處所。女紅十指無女郎,君裳如綻妾當補”[2]P682。此詩從畫中美人握絲之態想象其正在繅絲織布,一絲一縷,織成千尺百尺,盡是女子對離人的思念。絲線成結,心中亦是千回百轉。巧手置辦嫁妝,織就錦衣上的蛺蝶,繡枕上的鴛鴦,皆是成雙成對,而公子不知身于何處。美人女紅無雙,只盼著他歸來,能有機會為之補裳。全詩將女子思君細膩婉轉的心態展現得淋漓盡致,使人如見其畫。
題畫描圖,直抒個人志趣,彰顯舉世高標的人格精神,是黃克晦題畫詩的一大特點。如《題三友扇圖》:“蒼龍千歲鱗,綠玉四時色。可憐姑射仙,共作山中客。”[2]P794“千歲鱗”象松形,點出其蒼勁老辣,如龍之矯健。“綠玉”標竹色,贊其勁節虛心,四季常綠。“姑射仙”則喻梅凌霜斗雪,潔白堅貞之質。三友結伴遠離富貴人家園圃而在山中作客。短短二十個字,構思別出心裁,托物明志,可視為其不屑于趨炎附勢的剖白。再如《題畫詩》:“巖桂秋始華,芝蘭意亦好。復有籬下英,歲晏同此道。”[2]P795芝蘭生于深山,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德,不因窮困而改節。蘭與桂、菊同是不為秋霜所欺之花,詩人借以寄寓自己高潔的情操。
在黃克晦的題畫詩中,還存在著一類不寫圖,直接對與畫相關的事件、人物遭遇進行評論,抒發自己感慨的詩歌。這類作品往往飛出畫外,畫面只是出發詩歌寄情寓意的憑借。如《為張為春戶部題山水手卷》:“張君游山常作賦,落筆縱橫數千字。黃生只作游山圖,醉里水墨涴縑素。須臾圖成賦亦就,手挽天河揭北斗。醉里但呼各有奇,舉世未能誰可否。君從獻馬燕昭臺,乾坤雙眼蒼眼開。龍駒得路自千里,況乃渡水聞風雷。我亦飄飄何所遇,匣劍孤飛拂云霧。小蹇踏花春忽深,野艇行空月作路。長安市上一逢君,愁盡歡生論往事。案頭橫軸凌亂光,為君拂拭開芳樹。君今簪紱鎮在身,登山臨水愁無因。只合臥游對樽酒,長憶江湖汗漫人。”[2]P799詩從畫的由來寫起。詩人與友人張為春同游,一人作賦,一人作圖,同好而樂。接著敘張得到重用,龍駒得路,到處奔騰。詩人卻凄惶不遇,好似蹇驢尋春,野艇行空,既失卻時機,又沒有門路。相逢愁盡歡生,只是遺憾朋友官職在身,無法盡興游玩,但愿其臥游對酒之時能憶起江湖之友。全詩對畫的內容無直接描寫,更多的是抒發身世之感。
綜觀黃克晦的詩歌,創作時間跨度長,涉及范圍廣,文體豐富,風格多樣,在思想和藝術上都取得一定的成就。徐火勃《筆精》云:“孔昭詩皆清峭絕塵,戛玉敲金……語語新俊可喜。”[6]P133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稱“其古風天籟自鳴,近體森然紀律,清溪社集諸公,允當推為祭酒。”[7]P535二者所說大致不差。黃克晦一生雖無轟轟烈烈的壯舉和功業,其詩名也難以和閩中詩派諸名家相比肩,但作為明代中后期閩南地區影響力頗大的詩人,他的作品確有其價值所在,不應為人們所忽略。
[1][明]葉春及.惠安政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2][明]黃克晦.黃吾野先生詩集[M].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5.
[3]王國維.人間詞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清]黃蘇,黃登基.文獻黃氏家譜[M].光緒丁未版本.
[5][清]王原祁,等.佩文齋書畫譜[M].北京:中國書店,1984.
[6][明]徐火勃.筆精[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7][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