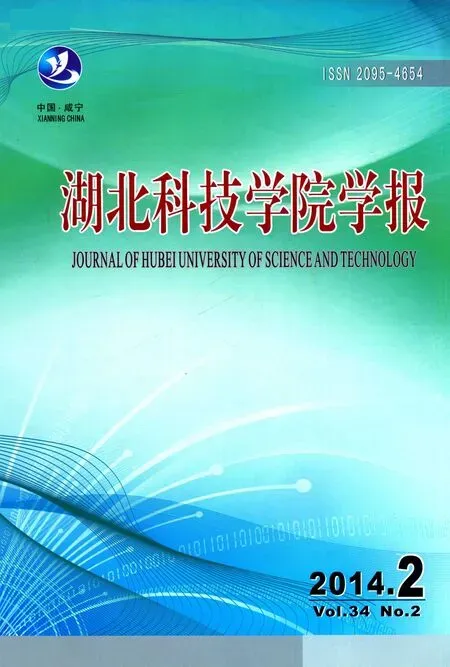中日傳統孝倫理觀對比
江曉燕
(龍巖學院外國語學院,福建龍巖364000)
一、先行研究及本文目的
關于中日“孝”的研究,國內外已有許多的專門研究。國內韓春紅在《<楢山節考>中的日本人孝養觀》中,作者通過分析《楢山節考》這一文學作品,認為雖然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有孝養觀,但是并不是絕對化的,它受很多外在條件與內在條件制約的,是一種有條件的孝養觀。李貴鑫《試論日本孝養觀的歷史演變——以<楢山節考>為視角》一文認為,日本在孝養觀出現以前有過一段“孝”的真空期,在此期間人們心中并無“孝”的觀念。在中國儒教孝道傳入日本之后,經過幾個時代的演進,形成了以“恩”為核心,“忠”大于“孝”,“忠”、“孝”為絕對義務的不平等的日本孝養觀。陳文靜的《中日忠孝倫理對照研究》、宋娜的《“忠”“孝”在中日傳統倫理觀念中的地位》、崔世廣、李含等《中日兩國忠孝觀的比較》、畢艷紅、劉平的《中日文化差異的社會根源探究——以儒家“忠孝觀”視角》等,都是在研究忠與孝之間的關系。此外,還有王勤的《中日“孝”觀念之比較》及桑鳳平、李響的《中日孝道之比較》等。前者比較中日兩國“孝”這一觀念,提出孝觀念應該與時俱進、應該有本質上的新詮釋。后者文章從中日兩國社會制度、思維方式和家庭結構等方面來分析兩國孝道的不同之處。
本論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從中日兩國孝倫理觀的形成時間、對象范圍以及行為表現這三方面來分析不同之處,進而探究造成這些不同的社會文化根源。
二、孝倫理觀的形成
考察“孝”字原本的意思,有兩種。為“孝,善侍父母者”;一為“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它作為一種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學術界普遍認為,“孝”源于西周。但當時個體家庭仍存在于宗族當中,尚未形成獨立的經濟形式,宗族是社會經濟的單位,因此彼時的“孝”是整個宗族的事,而非個體家庭。其表現形式是“祭祀”。以祭祀為手段來維護宗法制度中的血緣性與等級關系。后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與個體家庭能力的增強,“孝”呈現出了從宗族倫理向家族倫理轉變的端倪,“孝”的內涵也隨之發生微妙的變化,個體家庭孝道得到了普及。贍養父母漸漸成為判斷孝與不孝的重要標準。孔子推動了對孝倫理的發展與創新。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所養。不敬,何以別乎?”凸顯了家庭倫理范圍的“孝”。漢代開始家庭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血緣家族共同生產、共同居住的現象。這種家族結構最后演變成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孝倫理觀也逐漸發展為不僅要侍奉父母長輩,還要祭祀祖先,為家族延續香火。
日本原本沒有“孝”的概念,“孝”這個字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現代日語中“孝”字只有音讀而沒有訓讀就能證明這一點。日本的孝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比中國晚了很多。公元5世紀至8世紀,中國的儒家思想傳入日本之時,日本尚不存在孝倫理觀念。雖然在一些政治文獻或史著中出現過一些中國的孝倫理思想,但有著明顯的刻意模仿的痕跡。公元6世紀后半期至7世紀初,日本開始了政治革新,圣德太子推行“推古朝改革”以及公元646年,日本的大化革新,統治階級吸收引入中國儒家思想,并加以改造為己所用,創造了維護封建統治的“忠”倫理觀。但由于當時日本社會家族結構尚未形成家長制的家族制度,孝倫理觀缺乏形成的社會基礎。直到奈良時代,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家族結構的變化,統治者才開始重視孝倫理觀。公元718年國家制定出臺了《養老律令》,要求普通民眾奉行孝道,孝倫理觀不僅成為統治階級的道德準則,而且逐步滲透到日本文化之中。
可見,中日孝倫理觀念的形成有著顯著的差異。在中國,“孝”是內生的;而在日本,“孝”是輸入舶來的。
三、“孝”的對象范圍
東漢許慎則解釋說:“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孝”首先是一種社會道德原則,是處理家庭內部父母雙親與兒女關系即所謂的“親子關系”的準則。但中國和日本的“家”及“親子關系”的概念有很大的差異。
對于中國人來說,“家”是指由血緣和婚姻關系者締結的集團,每個人都有強烈的宗族歸屬意識。“親子”只能是有血親的實父與實子的關系;而對日本人而言,“家”的概念要大得多。它對血緣的強調不像中國人那么的極端,“家人”甚至可以包括長期生活在一起但無血緣關系的人。如長期為某家族服務的管家甚至佃戶和雇工。日本人眼中“親子”的范疇也比中國的廣,親子并非一定指有血親的實父與實子。“親”既可以指處于父母地位的人如父母、養父母、岳父母,也可以是指雇主、師傅、老師、上司等;“子”既可以指處于孩子地位的人,也可以指雇員、徒弟、學生、下屬等。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在祭祀的對象上,中國人一般是祭祀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先祖。日本人卻認為只要是逝于該“家”的,就應成為該家的先祖而受到后代祭祀,哪怕是無任何血緣關系的雇工。
可見,中日在孝的對象范圍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在中國,“孝”的范圍限制于血緣關系以內,且沿著縱向的血脈追朔到遠祖;而在日本,“孝”的范圍突破了血緣關系,沿著橫向的互動延伸到家臣,卻又排斥有血緣關系的遠祖。
四、行為表現
(一)對身體態度的不同
孝經有云:身體發膚,授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自古中國人認為愛護自己的身體是盡孝道的先決條件。
在對待身體這一態度上,日本人與中國人看法卻截然不同。在日語中有個與武士道密切相連的詞“切腹”,它也體現武士道的核心內容之一“重名輕死”。剖腹自殺在他人看來是極其痛苦的,但是日本人卻認為那是為國家為集團光榮赴義,不使家族蒙羞,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算是盡孝了。
從對身體的態度這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為了孝敬父母,盡量避免損傷到自己的身體,把保留自己身體的完整性看作孝道里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而日本人則不那么重視“孝”與身體完整性的關系,認為“殺身成仁”,傷害自己的身體有時反而是向家族盡孝的必要條件,究其原因是因為在日本人的道德體系中,在“孝”之上還存在著對天皇的至高無上的“忠”。
(二)與“忠”的關系
“孝”是一種情感行為,也是社會道德原則,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演變,“孝”被封建帝王利用來為他們的統治服務。這樣,“孝”就由道德范疇擴展到了政治范疇。《孝經》中的《開宗明義章》寫道:“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這就指出了孝是倫理道德“孝親”和政治行為“忠君”的結合體。《禮記·祭義》則說:“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確地指出對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現。但是中國的“忠”是有條件的,是一種臣下對君主的感情回報。孔子講:“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臣下要對君主以忠,但它是有前提的,即“君使臣以禮”。換言之,如果君主不對臣下以“禮”,那么臣下對君主也就無須盡忠。君臣的關系是對等的,而絕非無條件的服從。
忠與孝相輔相成,但自古忠孝兩難全。孔孟都堅持孝重于忠的法則。子思在《六德》一文中提出:“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在孝與忠之間,孝大于忠。孟子繼承并發揮了子思的思想,他說:“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詳莫大焉”,主張在家庭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發生矛盾時,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可見,在中國,忠是依托于孝的忠。
日本在孝與忠的問題上采取的是跟中國截然不同的態度。日本的孝倫理思想并非內生的,而是舶來的。統治階級并未全盤引進儒家孝道思想的體系,而是有選擇地進行吸收、加工,為己所用使之成為鞏固自己統治利益的工具。10世紀時武士團成立,平安時代后期形成了以生命向君主盡忠的倫理道德觀。忠的觀念被不斷提高到最高倫理規范的地位。在他們眼中,忠的地位遠遠高于孝道,在孝與忠之間產生矛盾的時候,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正如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所寫到的那樣:“孝道在日本就成了必須履行的義務……只有在對天皇的義務沖突時可以廢除孝道”。
五、社會根源
綜上所述,中日兩國孝倫理觀在形成、對象范圍及行為表現這三方面都有著顯著的差異。究其原因,與兩國的社會家族結構有深切關系。首先,日本社會的家長制家族制度確立較晚,孝倫理觀的社會基礎形成也較晚,故而日本孝倫理觀形成也比中國的晚。
其次,由于自然因素與地緣關系的影響,造就了家族主義的中國人和集團意識的日本人。在中日家族結構中,中國人重視血緣,在乎血脈的傳承;而日本人重視共同生活的“場”,在乎集團的“和”。日本家族制度的中心思想不在于傳宗接代,而在于延續“家”這一經濟共同體。血緣不是首要素,若是家業的需要,哪怕無血緣關系的人也能繼承家業,也能當孝子。
中國傳統社會,隨生產力的發展,經歷了西周時期的“以國為家”“家國不分”,到宋代逐漸演變為平民化宗族對社會的組織和管理,意味著政權與族權分離。所以出現了行于政治層面的“忠”和調解家庭血緣關系的“孝”。宗族大多以血緣關系為準聚族而居,同族之內,族法大過國法,共同維護本族利益和勢力。人在生產過程中除了賦稅徭役外,很少與國家直接發生關系。故而人們會把為人子的“孝”重于為人臣的“忠”。再且,中國歷史上總共經歷了24個朝代的更迭,使得“忠”的意識觀更被置于亙古不變的孝倫理觀之后。
而日本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組織則呈現一元化特征,忠與孝在功能與意義上是一致的。日本的孝倫理觀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和階級利益,是一種人為的、經過加工后創造出的意識形態。從中國引入“孝”的觀念并加以改造后,日本正式確立了以封建的“忠”的思想為核心的封建主義孝養觀。“忠”作為“孝”的衍生物,在統治階級刻意的宣揚下,人民群眾對于道德倫理規范的認知程度上“忠”要高于“孝”。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是,日本歷史上,只有一個皇室,萬世一系,繼承皇位。日本人之所以把對天皇盡忠看作是最高的道德。
六、結語
中國的孝倫理觀是為了維護社會階級與家族集團的穩定,是一種非人為的、自發產生的社會意識形態;日本的孝倫理觀源自中國,但由于社會政治結構、家族結構發展的不同,以及由于自然因素和地緣關系的影響造成的人思想意識等的不同,與中國的孝又不盡相同。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和階級利益,是一種人為的、經過加工后創造出的意識形態。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應該作為一種美德繼續傳承和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