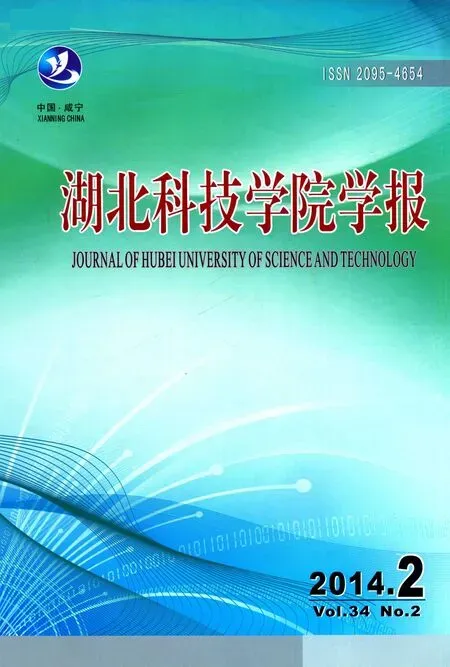基督教文化對冰心早期“問題小說”創作的影響
饒眺
(咸寧職業技術學院,湖北 咸寧 437100)
中國現代作家中,其創作明顯受到宗教影響的可謂舉不勝舉:魯迅、許地山、老舍……相較而言,把西方基督教義理大面積滲透到文學作品之中,極力表現社會現實的作家卻鮮見。冰心無疑是當時耀眼的一位。
基督教是信奉上帝的宗教。歷史上有過不同的教會形式;但作為文化意義上的基督教,卻有著許多相似的信仰和觀念。就基督文化的意義而言,博愛和同情是冰心體驗最深刻,表現最豐富的內容;而且,這種博愛和同情都是超階級的。基督教要求信徒去愛人,去同情人,甚至愛自己的敵人,只是把“愛”作為檢驗對上帝虔誠度的標準。顯然,這種“愛”只是一種原則而不是感情。受其影響,冰心卻把這種“愛”只作為倫理、道德精神。她早期“問題小說”里充滿了這種基督式的博愛和空虛的同情。這些小說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抒寫對封建社會和封建家庭的不滿情緒,二是反映下級官兵生活和反對軍閥混戰,三是從人道主義立場表現對勞動人民的同情。
一
作為剛從封建思想束縛中掙脫出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冰心對封建勢力和舊禮教有所否定和揭露,對被封建勢力吞食的弱小者有所同情,冰心1919年9月連載于《晨報》的處女作《誰之罪》(即《兩個家庭》)中,她否定了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來的女子。小說中,陳華民娶的是官家小姐出身的太太,不會治理家政,不僅不教育孩子,不管家務,還整天打扮得珠光寶氣出去打牌或應酬宴會,家里雖雇了三個老媽子,卻各個護著各人的少爺,常常吵嘴打架,不得安寧。這影響丈夫的事業,摧殘丈夫的身心。相比較而言,三哥與他一同畢業,一同留學,一同回國,論職位沒有他高,論薪水也沒有他多,卻有一個賢惠體貼、精明能干的太太,她不僅把家政管理得妥妥貼貼,孩子教育得聰明懂事,而且還能幫助丈夫翻譯書籍,就連雇來的老媽子也被教會念字片和《百家姓》。毫無幸福可言的家庭生活是導致陳華民的深深惋惜和同情之情。
《去國》是寫一個想貢獻自己力量和才智給祖國的青年留學生,卻不為當時的政府所接納,反映了有愛國心的留學生和軍閥政府之間的矛盾,揭露了軍閥政府的腐敗無能。作者在揭露和譴責的同時,卻同情了從舊民主主義戰場上退下來的父親朱衡。為了突現作者的這種同情之心,小說安排的結局便是兒子重蹈父親敗退的覆轍,再次去國而另覓資產階級的“樂土”。與此相類似,《斯人獨憔悴》中,漢奸父親和略有愛國心的下一代之間沖突的結局,也是愛國心的屈服,兩個曾有愛國行動的青年做封建買辦家庭的順民,變為既成事實。作者沒有鄙視主人公思想的軟弱,卻對他們的“憔悴”寄予了同情。在《最后的安息》中,作家一方面控訴了封建社會童養媳的罪惡,另一方面卻宣揚用同情心來消滅貧富之間的間隔,造成“愛”的世界。
由此可見,冰心初期的此類“問題小說”雖也確實提出過一些問題,勾起了當時的進步青年對封建勢力的某些不滿。可是,冰心雖然不滿封建勢力的壓力,卻不敢正面觸動它。她絕大部分“問題小說”解決問題的途徑是無力的,幾場尖銳的沖突經她一處理,變得黯然失色。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在“博愛”和“同情”的召喚之下,以一種改良、逃跑或妥協的方式解決了。
冰心在“五四”高潮中所寫的問題小說的另一類題材是有關下層官兵生活和反對軍閥混戰的作品。《一個軍官的筆記》中那位青年軍官原想為國效命而從軍,結果卻發現自己不是為著公理正義戰斗,而是為“少數主戰者”賣命,這分明是“軍閥的走狗”,不僅“出師無名”,而且干的是“卑賤的事”。這個作品的矛頭直指封建軍閥,態度也比較鮮明。另外,在《一個兵丁》和《到青龍橋去》等作品中,冰心也寄無限同情于下級官兵。
我們不難發現,冰心的這類作品里“只有厭惡戰爭,只有婆婆媽媽的和平主義,只有些安居樂業的‘理想’……”當時,在冰心看來,只要反對戰爭,世界就光明,人們就和平。但是,在冰心筆下,如《一篇小說的結局》、《魚兒》等作品中,她并沒有具體寫出戰爭的社會背景,背景不清則性質不明。這種將戰爭背景抽象化的反戰小說會使人們不加區別的反對一切戰爭,甚至連正義的戰爭也加以反對。當然,我們不能據此就給作者扣上一頂“階級立場不堅定”的“帽子”。而且,在這里,冰心還是以基督的“博愛”觀來反對戰爭的。作者在作品中曾這樣寫道:“可憐的主戰者呵!我不恨你們,只可憐你們!忠平呵!我不記念你,我只愛你!”她大概想的就是想通過“可憐”來感化軍閥,停止戰爭。這里表現一種以超階級的博愛觀點來反對戰爭,“婆婆媽媽的和平主義”是冰心這類題材作品中消極的一面。
二
冰心寫的反對封建勢力的軍閥混戰題材的“問題小說”大概只堅持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隨即沿著作品中所呈現的博愛和同情的斜坡逐漸走向更博大的“愛”“愛的哲學”,開始從道義立場關注普通民生。母愛、童真、自然愛是冰心“愛的哲學”的三大組成部分,《國旗》、《超人》、《煩悶》等是這一類作品中的代表之作。
《國旗》的主題思想便是借天真的兒童之口說出的:“他也愛我們的國,我們也愛他們的國,不是更好么?各人愛各人的國,鬧得朋友都好不成!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大家合攏來做一個國。”這并非是兒童的戲言,而是作者借童真之口,幻想用無國界的愛來乞求祖國的“安寧”。在《超人》里,冰心設置一個冷漠的心,再設置一個母親的愛。祿兒的呻吟是兩者之間的橋梁。最后完成了一個寓言:冷漠的心如何被母親的愛感化,從而表現出主題:“世界上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在論述“自然之愛”時,冰心常常用的是“造物者”這一稱呼來表達。在她的思想中,造物者是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格神,是萬物的“母親”,“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界上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這正如基督教義《圣經》所說:“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冰心的“愛”是神性與人性、自然與親情的融合,她將母愛、童真、自然愛三者統一起來看,體現出了冰心的人類之愛的博愛理想。她企圖從母愛的深沉、童心的純真和自然的壯美中尋到精神危機中的“避風港”。她勸說那個時代的青年,當感到人生虛無時,當在黑暗的現實中受到心靈創傷時,可以用本能的、天性的、無條件的母愛來治療,并主張由這種母愛而發展的博愛來解除社會上的罪惡,來拯救苦難的眾生。
三位一體的“愛的哲學”建立,目的在于療救社會,那么它的基礎是什么呢?這即是冰心此類小說受基督教文化影響之所在:兒童是通過與母親溶為一體,而人類在童年是通過與大自然取得和諧,宗教表達的是人類與上帝建立和諧關系的精神上的追求。事實上,在冰心“愛的哲學”中,“母親”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母親,而被轉化為宗教般的上帝。她用的是基督教神學中證明上帝存在的五大原則之一“以果求因”法。即從宇宙間一切的天地萬物而推導出最初的設計者造物主(即“母親”)。這一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并非是“盲觸”的結果,而是造物主的化育(即“母親”的孕育)而成;因宇宙萬物而推導出創始成終的造物主,靠著這造物主“慧力的引導”,人在母愛、童真和自然中所受的感悟也正是對上帝“愛”意的領受。
三
茅盾曾在《冰心論》說:“一個人的思想被她的生活經驗所決定,外來的思想沒有適宜的土壤不會發芽。”冰心和基督教文化的確有著很深的情緣。冰心的早期創作風格正是在她個人經歷、文化環境的獨特性和時代因素的共性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1900年,冰心出生在福州的一個海軍軍官的家庭。其幼年時代也是在一個相對優越的環境里度過的。由于她出生的時代正好處在“戊戌變法”慘遭失敗之后,加之其家庭相對開明,所以她的個性能夠較為自由地發展,在她眼中,世間萬物都是那么的單純明朗,充滿仁愛。
除此之外,冰心從小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據她回憶,她的家庭與基督教會有一定關系,二伯父在一所教會學校(福州英華書院)教書,書院里的男女教師都是傳教士,曾來家中做客。冰心說“父母對她們的印象很好”。家遷到北京后,冰心得以進入美國衛理公會辦的貝滿女中讀書。
冰心所在的貝滿女中,并不像人們想象中的教會學校那樣封閉和專制,正是在這里,冰心系統地學習了《圣經》,而且《圣經》課和英文的成績是最好的。每天上午除上課外,最后半小時還有一個聚會,由本校中美教師或衛理公會的牧師來講道。冰心回憶道:“我們的《圣經》課已從《舊約》讀到了《新約》,我從《福音》書里了解了耶穌基督這個‘人’。我看到一個窮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從他的人,而且因為宣傳‘愛人如己’,而被殘酷地釘在十字架上,這個形象是可敬的。”
貝滿女中畢業后,冰心先后又考入協和女大(后并入燕京大學)和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學習。在此期間,她繼續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冰心在她的老師包貴思的陪同下,在一位老牧師家里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從此,基督教文化在冰心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基督教精神已滲入冰心的情思之中。正如她自己所坦言:“同時因著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正是這種愛的哲學,構成了冰心早期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
縱觀冰心早期的小說創作,我們能感受到“博愛”和“同情”中所浸透著的濃濃的基督教文化氣息。在這種文化氣息的浸染之下,作者早期的“問題小說”以自己特有的視角,針砭時弊,揭露現實,抒寫人生,拯救民眾。雖筆端處處略帶夸張,思想也不乏稚弱無力,卻也在時代的興味征途上獨具一格,這種沉積在早期傷口中濃郁的宗教情素,為冰心日后數十年的文學創作打下了濃厚的思想和豐富的情感基礎,使其終生都在以自己的人格與藝術熱情播種“愛”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