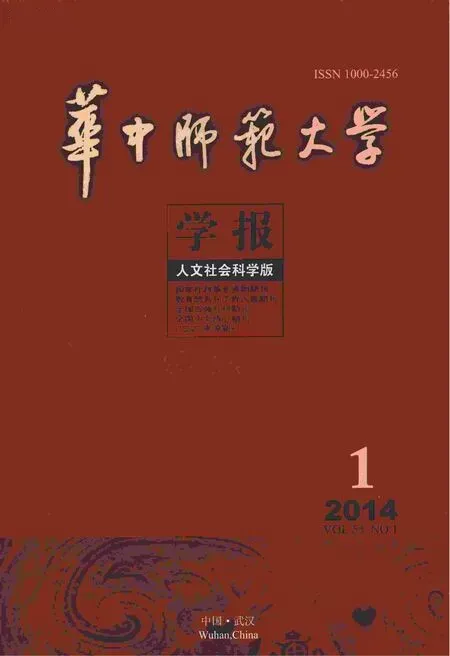論晚明的圖書傳播對社會輿論的影響
劉中興
(華中師范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湖北 武漢430079)
晚明時期,隨著商業(yè)的發(fā)展和市民階層的形成,輿論傳播的空間市場和消費(fèi)需求逐漸產(chǎn)生。晚明時人很善于利用各種方式和工具營造輿論、表達(dá)意見,影響政治和社會生活,豐富的信息和活躍的輿論成為晚明的典型特征。
空前繁盛的圖書出版業(yè)在輿論傳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圖書 “本質(zhì)上是一種傳播媒介”,“實質(zhì)上是人類文化的、精神的符號交流系統(tǒng),是人類憑借組織編碼的有序語義信息的文本,傳播人類信息的重要傳播媒介”,“承擔(dān)著傳播知識及文化的重要使命,既要在空間領(lǐng)域?qū)崿F(xiàn)共時性傳播,又要在時間范疇實現(xiàn)歷時性遺傳”①。在晚明血緣、地緣、階層的限制被不斷打破,社會流動性不斷擴(kuò)大的形勢下,圖書出版業(yè)繁榮,人們對于閱讀有強(qiáng)烈的需求,于是圖書成為了信息傳播的重要途徑和方式,圍繞圖書的編寫、流傳和閱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傳播網(wǎng)。
在輿論傳播過程中,圖書對于 “信息的有選擇性傳遞,將人們劃歸到非常不同的信息系統(tǒng),而創(chuàng)造出各個 ‘群體’”②。相較于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子集,較為另類的時事小說、官員編書、妖書等幾種重要形式的圖書更能體現(xiàn)當(dāng)時輿論與社會的互動關(guān)系。由于作者的出發(fā)點(diǎn)、圖書內(nèi)容、圖書功能的不同,這幾類圖書在信息傳播和社會輿論傳布與構(gòu)建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但都是晚明社會輿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見證并推動了晚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fā)展。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晚明圖書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學(xué)史、出版史以及文人與黨社的關(guān)系等方面,本文試從社會輿論的角度對時事小說、官員編書、妖書進(jìn)行考察,從圖書這一更具象的角度考察晚明社會變遷。
一、圖書與晚明信息傳播網(wǎng)的形成
信息是社會的反映,晚明信息的傳播有著典型的時代特征。明初對人口的控制相當(dāng)嚴(yán)密,社會缺乏基本的流動性。明代中期以后,隨著商業(yè)的發(fā)展,社會流動的頻繁成為當(dāng)時社會的一大特征。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商業(yè)市鎮(zhèn)的激增以及地區(qū)性貿(mào)易市場的形成,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jìn)社會流動:既有地域之間的人口流動,又有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晚明信息的活躍與多樣性,可以從這種廣泛商業(yè)化的社會流動中找到社會根源。
嘉靖后,社會力量發(fā)生了新的分化,傳統(tǒng)“四民”的區(qū)分也越來越模糊。時人姚旅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說:“古有四民……余以為今有二十四民”,除士、農(nóng)、工、商及兵、僧之外,還有道家、醫(yī)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師、駔儈、駕長、舁人、篦頭、修腳、倡家、小唱、優(yōu)人、雜劇、響馬、巨窩等十八民,“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穡,除二三小技,其余世人,豐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懸鐘鼓,比樂公侯,詩書讓其氣候,詞賦揖其下風(fēng),猗其盛哉!”③從“四民”向 “二十四民”的轉(zhuǎn)化,反映了晚明社會大流動的一種必然,也加快了信息流動的速度和信息的多樣性。
隨著社會流動的頻繁,士、農(nóng)、官、商的滲透、融合成為十分普遍的現(xiàn)象。商人階層的興起及其財富大規(guī)模的積聚,為其社會交往渠道的拓寬以及向士人階層的滲透提供了極大的物質(zhì)便利。商人階層不僅模仿士人的生活及品位,還投資于書樓、畫室、古玩等等,活躍在士人的社會文化活動之中。同時,士商交往中更增加了物質(zhì)利益的因素,士人為他人寫墓志銘、壽序、文序、碑銘、傳記以及為商人子弟授課,為書商寫書評等等謀利行為成為平常之事。“富者余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余之貲財,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富者亦分名焉。”④何良俊則描寫道:“蓋吾松士大夫一中進(jìn)士之后,則于平日同堂之友,謝去恐不速。里中雖有談文論道之士,非唯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處有莊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干;或某人為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礙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干,則欣欣喜見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謹(jǐn)。蓋父兄之所交與而子弟之所習(xí)聞?wù)撸源溯呉病!雹?/p>
由此,人們交往的途徑和范圍得到較大擴(kuò)展。商業(yè)利益的驅(qū)使,信息交換、社會交往需求的激增,使晚明信息傳播的內(nèi)容和層次更為多元,而豐富多彩的圖書便是多元信息的有效載體。明代的圖書出版事業(yè)和印刷技術(shù),都可稱為我國的極盛時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印刷出版業(yè)高度商業(yè)化,成為當(dāng)時商業(yè)活動的重要內(nèi)容。查慎行《人海記》有言:“明刊二十一史于北雍,糜六萬金有余。”⑥吳敬梓 《儒林外史》中描寫,明代文人馬靜受雇為嘉興文海樓書坊編選三科程墨,除食宿外,另得一百多兩銀子為報酬⑦。
明代刻書業(yè)的發(fā)達(dá)與下列因素有關(guān):首先,印刷術(shù)的全面進(jìn)步為明代出版業(yè)的繁榮提供了技術(shù)條件。北宋畢昇發(fā)明了活字印刷術(shù),但由于當(dāng)時技術(shù)條件以及其他方面條件的限制,雕版印刷術(shù)仍然占主導(dǎo)地位。直到明代,尤其是在嘉靖之后,活字印刷術(shù)才得到推廣,從而推動了中國古代印刷出版業(yè)新的發(fā)展。明代活字印刷術(shù)中使用最為普遍的是木活字,效率高且費(fèi)用低。其次,紙、墨等原料的降低。竹紙開始大量使用,雖然竹紙的顏色暗黃,易碎不宜久藏,質(zhì)量比不上棉紙,但因其產(chǎn)量大而降低了成本此外,將用過的竹紙回槽后還可以循環(huán)利用,印刷成本得到進(jìn)一步降低。再次,商業(yè)交通及郵驛的發(fā)達(dá)與書籍的社會化流布。明代依托運(yùn)河和長江形成了四通八達(dá)的水陸交通網(wǎng)絡(luò),為信息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隆慶四年,徽商王汴編 《天下水陸路程》,列全國水陸路程143條,其中南京至全國各地的長途路程11條、江南至鄰近區(qū)域路程12條,更有15條水路連接蘇松二府和各市鎮(zhèn)縣城,依賴于發(fā)達(dá)的交通網(wǎng)絡(luò),專業(yè)的渠道如書市、書肆、書攤、書船等,業(yè)余的渠道如考市、負(fù)販、貨、雜貨鋪等,明代圖書交易相當(dāng)繁盛。第四,書坊出版的高度商業(yè)化。明代刻書業(yè)由官家、私家和書坊三家經(jīng)營,其刻本分別被稱為 “官刻本”、“私刻本”和 “坊刻本”,坊刻本即為一般書商刻印的書。雖然受到官府的干預(yù),但圖書出版已經(jīng)商品化,而民間以牟利為目的的商業(yè)化印刷業(yè)尤其繁榮⑧。明代書坊刻書的數(shù)量和規(guī)模都相當(dāng)大。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描述道:“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fēng)華實之一驗也。”⑨刻書中心分布地域廣,較著名的有福建建陽、江蘇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以及浙江的杭州、湖州等地。南京可以考得坊名的有57家之多,其中 “以唐姓十二家為最多,次為周姓七家”⑩。據(jù)統(tǒng)計,到1600年前后,南京至少有93家商業(yè)出版機(jī)構(gòu),蘇州有37家,杭州有24家;在以后的40年中,直到明末,這個數(shù)字至少在蘇州增長了將近3倍。
當(dāng)時出版業(yè)的競爭相當(dāng)激烈,書商會通過各種手段制造有利于營銷并能有效保護(hù)自身利益的商業(yè)輿論。書籍出版之后若是暢銷,會有其他的出版商翻刊盜印圖利。“福建書坊……專以貨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開價高,即便翻刻。”馮夢龍也說: “吳中鏤書多利,而甚苦翻刻。”崇禎時南京書商在其出版的 《道元一氣》書前附有告白:“倘有無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聞之當(dāng)?shù)溃璞斯福宋乙蚓墶!睍恢鳛榱嗽黾訒l(fā)行量,獲取可觀的經(jīng)濟(jì)利益,還競相在書籍上刊登各類廣告,達(dá)到宣傳與促銷之目的。圖書商業(yè)廣告有牌記廣告、序文廣告、凡例廣告、書名廣告、征稿廣告等多種,其形式之繁,內(nèi)容之豐,技巧之新,令人嘆為觀止。
商業(yè)因素之外,明朝政府還采取了一些重要政策,以促進(jìn)圖書出版發(fā)行流通業(yè)的發(fā)展。一是在賦稅方面,《明會要》載:“洪武元年八月,詔除書籍稅。”同時被免稅的還有筆、墨等圖書生產(chǎn)的物料。二是鼓勵文化教育,到明代末期,全國的生員人數(shù)達(dá)50萬人之多。學(xué)校的普及,意味著文盲率的下降和讀書人的增多。三是改變工匠的服役制度,規(guī)定可以以錢代役,使得工匠的時間更加自由,激發(fā)了印刷行業(yè)工匠的積極性。
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晚明時期的圖書出版業(yè)一派欣欣向榮景象。據(jù) 《中國出版通史》(明代卷)統(tǒng)計, 《明代版刻綜錄》共著錄圖書7740種,其中洪武至弘治時期的書共766種,正德、嘉靖、隆慶年間共2237種,萬歷至崇禎年間共4720種,其比例是1∶3∶6。地方志一類書,明初只有數(shù)百種,嘉靖以后共出版1688種。小說、戲曲類圖書,明代初期、中期加起來只有百來種,晚明時期至少有一千多種。私人撰寫的史書,明初和中期加起來不到一百種,明后期撰寫私史成風(fēng),有關(guān)出版物不止千種。
與龐大的圖書市場互為促進(jìn)的,是明中后期人們閱讀需求的增加及新的受眾群體的形成。明代前期書坊所刻圖書主要是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子集,讀者也主要是士大夫階層。而明代中后期市民階層逐漸形成,他們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閑暇空間,閱讀無疑成為消遣的最好途徑之一。但絕大多數(shù)市民階層對于四書五經(jīng)、詩詞歌賦等 “雅文化”并不感興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以小說、戲曲為代表的 “俗文化”。同時,受商業(yè)發(fā)展的影響,明中期以后很大一部分士大夫階層的生活方式、人生態(tài)度、價值觀念以及審美情趣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逐漸與市民階層趨同,于是產(chǎn)生了以市民階層為主體的新興讀者群體。此外,一些晚明士人 “屈就市場”,參與商業(yè)性的寫作和出版,他們撰寫和編纂的書,無論是由政府、書坊或別的民間機(jī)構(gòu)出版,都贏得了廣大的讀者群,把平民甚至工匠,“拉升”為可以泛泛地稱為 “士人作品”的讀者。由此,圍繞圖書的編寫、流傳和閱讀,社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傳播網(wǎng)。
二、時事小說:社會輿論的靈敏性
對于小說這種明代比較流行的文學(xué)形式,臺灣學(xué)者王鴻泰對其在信息傳播中的作用進(jìn)行了很好的總結(jié):“明中期以后,小說已成為一種商品,在市場上擁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的讀者,可說是一種大眾讀物……小說在明末清初期間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它提供了一個公眾化的管道,或者說,它本身就是一個 ‘公眾場域’,就像個開放性的虛擬舞臺一般,小說在明清時期已然成為個別信息與公眾會面的場域。”
在晚明眾多小說之中,自萬歷三十一年的《征播奏捷傳》到明末清初,一大批講述閹黨始末、遼東戰(zhàn)事、李自成起義、清兵下江南的小說集中涌現(xiàn),在小說史上首次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當(dāng)代人寫當(dāng)代軍國大事的長篇通俗小說,并且對事件進(jìn)程展開細(xì)致描寫,文學(xué)史上稱之為 “時事小說”。這類小說從宋元話本中講史一類衍生而出,但其與歷史演義小說已有較大區(qū)別,所講的是當(dāng)代時事,因而滲透了更多的 “當(dāng)代”意識。此時人們對于小說的價值和功用有了新的認(rèn)識,不僅顯示晚明的作者與讀者急于了解和傳播當(dāng)下的輿論熱點(diǎn),也表明小說被認(rèn)為是理解 “歷史即時事”的一種新方式。時事小說類似于今天的 “報告文學(xué)”和 “紀(jì)實小說”,不僅在題材上和藝術(shù)技巧上獨(dú)樹一幟,而且成為時代的歷史見證。晚明劇烈的社會變動、政治斗爭以及即將發(fā)生的鼎革之變,使晚明成為時事小說的繁榮期。
與 《三國演義》等通俗小說不同,時事小說充分體現(xiàn)了社會輿論的靈敏性,一方面直接反映剛剛發(fā)生的、還在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對于重大時事比較敏感;另一方面成書時間比較短,對時事的反映比較迅捷。魏忠賢閹黨集團(tuán)覆滅后不到一年時間便有三部揭露其丑惡行徑的小說問世,其中 《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從寫作到刊行只用了九個月的時間,《警世陰陽夢》則在魏忠賢死后七個月便已發(fā)行。此外,《遼海丹忠錄》的主人公毛云龍去世不久,該書就已刊行于世。《剿闖通俗演義》寫李自成攻陷北都及清兵入關(guān)之事,書成時明廷與清兵仍在追剿起義軍。
晚明時事小說的輿論靈敏性,與當(dāng)時的經(jīng)濟(jì)、社會與政治大背景密切相關(guān)。廣泛的讀者群體是時事小說在晚明勃興的直接推動力。隨著市民階層的出現(xiàn),新的受眾群體開始形成,市民階層的興趣愛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小說創(chuàng)作的流向和趨勢。魏忠賢死后,朝野上下壓抑許久的憤懣之情迸發(fā)出來,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在相當(dāng)短的時期內(nèi),先后有多部描寫魏忠賢閹黨的小說面世,其他時事小說也多有言及。
從時事小說的創(chuàng)作主體來看,作者都具有傳播輿論的主觀意圖和現(xiàn)實需要,對重大事件比較敏感。雖然晚明的時事小說作者的社會地位一般不高,但由于飽受儒家正統(tǒng)思想熏陶,加上受明末啟蒙思想的影響,因而具有強(qiáng)烈的政治參與意識,這也是他們創(chuàng)作時事小說的直接主觀動因。《剿闖小說》作者自陳:“小生上觀古烈,下?lián)釙r事,終宵披衣,毒恨入髓,既因秀才,又無大力,徒傷當(dāng)食,但心刀割。”《定鼎奇聞》總結(jié)說:“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從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
作者把時事小說作為發(fā)泄感情的載體,在反映魏忠賢的小說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陸云龍 《魏忠賢小說斥奸書》自敘:“越在草莽,不勝欣快,終以在草莽不獲出一言暴其奸,良有隱恨。然使大奸既拔,又何必斥之自我,唯次其奸狀,傳之海隅,以易稱功頌德者之口,更次其奸之府辜,以著我圣天子之英明,神于除奸,諸臣工之忠鯁,勇于擊奸。”《皇明中興圣烈傳》的作者也直言:“嗚呼!從來逆賊狠毒有如此者乎?令人千古有恨,萬世為恫矣!此事雖被魏忠賢逆賊所害,若不代他把逆天大罪惡彰揚(yáng)出來,與世共知,使率土唾罵,普天怒責(zé),卻不便宜他,此亦草野公憤,不容不發(fā)泄一番者也。”
為了更好地發(fā)揮輿論傳播效果,時事小說還具有較強(qiáng)的通俗性。由此,時事小說對輿論的傳播更具有廣泛性、公開性,作者可以很快將時事演繹成小說,使更多的人了解。《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序中言及,希望通過本書 “嗣此耕夫牧豎,得戟手而問奸雄,野老村氓,至反唇而譏彪虎”。《皇明中興圣烈傳》:“特從邸報中與一二舊聞,演成小傳,以通世俗,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閱而識其事。”
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晚明高度發(fā)達(dá)的商業(yè)出版促成了時事小說的快速廣泛流布。時事小說規(guī)模龐大、讀者眾多的特點(diǎn),決定了它必須經(jīng)過書坊這一中介環(huán)節(jié),才能廣泛傳播。為了使時事小說在極短時間內(nèi)成書并更為暢銷,書坊主介入了時事小說創(chuàng)作,有的小說家還兼 “書坊主”于一身,如馮夢龍、凌濛初、陸云龍等,大肆推介時事小說。陸云龍吹捧 《斥奸書》“信一代之耳目,非以炫一時之聽聞”,非 “尋常筆墨”,“文人墨士知必奉為一代信書”,“異于稗官野說”。《梼杌閑評·總論》則吹噓 《梼杌閑評》“是非不在 《春秋》下”。
書商及作者為了迅速占領(lǐng)市場,也導(dǎo)致了時事小說大多草率成書,其中突出表現(xiàn)為大篇幅地錄用奏章及詔書原文,而且錯字、漏字、文句不連貫現(xiàn)象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這些小說還存在著大量抄襲現(xiàn)象,同題材小說之間尤為突出。更有甚者,書中版畫插圖也剽竊他書。據(jù)譚正壁先生考證,《圣烈傳》三面附圖系剽竊 《警世通言》。這種“快餐式”制作,說明商業(yè)發(fā)展推動著市民文化進(jìn)一步繁盛,同時又成為文化世俗化的動力,商品經(jīng)濟(jì)效益已成為左右時事小說產(chǎn)生、傳播的重要力 量。
正是因為時事小說對輿論信息比較敏感,具有很強(qiáng)的輿論傳播效果,因而對時事小說所依據(jù)的重大事件的當(dāng)事人往往會產(chǎn)生很大影響,有時甚至引發(fā)政治斗爭或是被用來作為政治斗爭工具。《遼東傳》的傳播就是熊廷弼被殺的一個重要原因,《明史》記載:“忠賢愈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郭興治、石三畏、卓邁等遂希指趣之。會馮銓亦憾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 《遼東傳》潛于 (天啟)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在天啟二年的廣寧之戰(zhàn)中,由于經(jīng) (熊廷弼)、撫(王化貞)不合,明軍慘敗,遼東失守,熊廷弼護(hù)潰民入關(guān),熊、王皆下獄。而馮銓以書進(jìn)讒,熊廷弼被殺。《酌中志》、《三朝野記》、《三垣筆記》等 皆 有 記 載。
可以說,所有時事小說都有傳播輿論的意圖,而且距事件發(fā)生時間越短,作者的這種意圖越明顯,這也是時事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本出發(fā)點(diǎn)。時事小說也因此具有很強(qiáng)的傳播功能,成為輿論傳播的重要方式。
三、官員編書:對輿論主導(dǎo)權(quán)的爭奪
晚明時人尤其是官員也善于用書籍來表現(xiàn)自己的身世和感情,以此來獲得輿論的支持或同情。《明史》記載:“給事中潮陽陳洸素?zé)o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元翰謫戍。元翰摭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 《辨冤錄》。洸由是不齒于清議,尚書喬宇出之為湖廣僉事。”陳洸身居言路,又在朝中有靠山,宋元翰投告無門,遂寫書感懷身世終于獲得了輿論的支持。后來陳洸官復(fù)原職,但不久其他言官彈劾陳洸,在奏疏里附上了 《辨冤錄》,于是輿論大起,最終 “除赦前及暖昧者勿論,當(dāng)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 離異, 子柱絞”。
在當(dāng)時,官員編印書籍影響輿論已經(jīng)成為一種風(fēng)氣。在官員們中間,印刷的書籍常常作為禮物成為社會交往的潤滑劑,幫助他們建立有利的社會關(guān)系。這些書通常包括一個官員自己的著作,或家庭成員的作品,或僅僅是他所喜歡的一部作品,大部分或完全是在某個政府機(jī)構(gòu)資助下用政府資金出版的。明代的地方官尤其是巡按御史,常常用政府薪金款項和地方政府資金來印刷書籍,作為給朝廷官員的禮品。葉德輝在 《書林清話》中指出:“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書,以一書一帕相饋贈,世即謂之書帕本。”陸容也說:“今士習(xí)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后學(xué)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饋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fèi)亦繁。”據(jù)晚明藏書家胡應(yīng)麟記載,官員們中間流行贈送書籍,通常在官員們獲得任命和提升時相互交換。這種做法尤為高級官員所欣賞,他們藏書的主要構(gòu)成是贈書者的科舉程文印本,可以很容易達(dá)到10000卷以上。
探究官員編書在晚明輿論傳播中的獨(dú)特意義,《萬歷邸鈔》和 《萬歷疏鈔》是不能忽視的。這兩部書對于晚明史,尤其是研究東林運(yùn)動,都是極為重要的文獻(xiàn)。《萬歷邸鈔》全三冊,是共有2411頁的大部頭著作,從萬歷元年正月到四十六年六月 (一部分年度闕如),抄錄和重要事件有關(guān)的邸報并加以若干整理,基本覆蓋了萬歷時代。據(jù)粗略統(tǒng)計,萬歷邸鈔總共有45.27萬余字,其中篇幅最多的為萬歷三十六年,達(dá)3.8萬余字;最少的是萬歷三年,僅600余字。該書是編年體,是和 《明實錄》相補(bǔ)的極為重要的資料。據(jù)日本學(xué)者小野和子考證,該書出自于東林人士錢一本之手。
《萬歷疏鈔》是萬歷時人吳亮所編纂。該書五十卷三十四冊,將萬歷時代的奏疏按問題分類,全文收錄,包括圣治、國是、臣道、言路等50個主題。在該書的序言中,顧憲成和吳亮談到了要開通言路,這也是他們力促此書乃至 《萬歷邸鈔》編行的最大目的。顧憲成從言路的視角,回顧了萬歷朝三十多年的歷史:“溯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遂遷怒于執(zhí)簡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留中以泯其跡,令言者以他事獲罪,不以言獲罪,至于邇年,且欲并邸報禁之。”顧憲成認(rèn)為,當(dāng)時最大的危機(jī)就是禁止邸抄。即使不允許政治批判,只要邸抄流布,他們的言論還是可以傳播,還可以引發(fā)社會輿論。如果連這也被禁止,那么言論的傳播就無法進(jìn)行。
當(dāng)時,工科給事中王元翰從國防的角度主張禁止傳抄奏疏,但統(tǒng)治者則表現(xiàn)出由此擴(kuò)大到一般奏疏,進(jìn)而封鎖言路的意圖。對此東林人士以針對內(nèi)閣抗議彈壓言路的目的,編集了翁憲祥《乞亟通章疏以存清議疏》(萬歷三十五年十月)、呂邦耀 《章疏亟宜批發(fā)以開言路疏》(萬歷三十五年十一月)、金士衡 《乞亟寬時禁以通言路疏》(萬歷三十五年十一月)等奏疏,為了造成輿論,促成了 《萬歷疏鈔》的刊刻。在這些奏疏中,也有統(tǒng)治階層不愿意公開的內(nèi)容。他們通過編纂這些書,明確自己的政治立場,宣傳鼓吹輿論,同時也是為了在歷史上留下這些事實。
《萬歷邸鈔》和 《萬歷疏鈔》中所收錄上疏,圍繞著具體的政治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政見。這些上疏,時而被隱匿,時而又被留中不發(fā),時而還被禁止在邸報上傳抄。東林人士把這些言論重新編輯起來,通過向在朝和在野人士的廣泛呼吁,形成政治上的輿論,進(jìn)而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的。
與之相對,閹黨也深諳借編印圖書制造輿論之道。魏忠賢大興冤獄、濫開殺戒之后,閹黨也開始在輿論上大造聲勢,誣陷東林官員,意圖為自己的罪行正名。閹黨群小炮制各種花名冊呈獻(xiàn)魏忠賢,部分編印散布,作為整肅異己的參照,借以羅織罪名,網(wǎng)絡(luò)異己之人,意圖一網(wǎng)打盡。首輔顧秉謙親手編訂 《縉紳便覽》,上列時任官員名單,并分為 “邪黨”和 “正人”兩派,用墨筆在名單上加圈加點(diǎn)。葉向高、趙南星等東林官員皆被列為 “邪黨”,而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余名閹黨追隨者被視為朝中 “正人”。這份名單作為打擊擯斥或提拔任用的依據(jù)。隨后,崔呈秀又進(jìn)獻(xiàn)《東林同志錄》,列葉向高等三百九十人。王紹徽還仿照 《水滸傳》一百零八將的形式,將一大批東林官員編 《東林點(diǎn)將錄》,以獲取魏忠賢的歡心。這樣從淮撫之議起與三黨對立的官員以及后來與紅丸、梃擊、移宮三案相關(guān)的人也都被羅織在 “東林黨”人之內(nèi)。《東林點(diǎn)將錄》中第一人是“托塔天王”李三才,為東林開山元帥,葉向高與趙南星為 “總兵都頭領(lǐng)”,高攀龍與繆昌期被稱為“掌管機(jī)密軍師”等等。此外,閹黨還編造了 《東林朋黨錄》,列趙南星等九十四人;編造 《東林籍貫錄》,列孫承宗等一百六十二人,還有 《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 《初終錄》、 《石碣錄》、《偽鑒錄》等等,名目繁多,不下數(shù)十種。
天啟五年十二月,閹黨成員、江西道御史盧承欽編造了一份三百零九人的 《東林黨人榜》,言“近日邪黨復(fù)熾,皆調(diào)停為害……猶有姑容不盡之虞”,并建議魏忠賢將黨人姓名、罪狀布告天下,榜示海內(nèi),讓東林人士 “躲閃無地,倒翻無期”。魏忠賢又矯旨以 《東林黨人榜》的形式將所謂的“東林黨”人名單刊布,并刻于邸報,將東林士人視作 “邪黨”,“生者削籍為民,當(dāng)差仍追奪誥命,其一切黨人不拘曾否處分,俱著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將姓名罪狀并節(jié)次明旨刊刻成書,榜示海內(nèi),垂鑒將來,以永保清平之治”,東林人士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同時,魏忠賢又對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所發(fā)生的京察、梃擊、紅丸、移宮等重要事件,進(jìn)行了全面翻案。顧秉謙擔(dān)任總編纂,仿照明代大典,組織人手編寫了 《三朝要典》,于天啟六年八月刊刻頒行天下,對東林官員的作為予以徹底否定,為閹黨一系列罪惡行為歌功頌德,以此為閹黨的行徑制造輿論。
“妖”,在先秦與秦漢典籍中也常通 “訞”,《荀子·非十二子》:“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楊倞注:“訞與妖同。”說明 “妖”在最初的解釋中即與言論直接相關(guān)。漢代劉熙則進(jìn)一步指出: “妖,殀也,害物也。”認(rèn)為 “妖”具有負(fù)面色彩,因此 “妖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多被賦予貶義色彩的。秦漢之后的文獻(xiàn)典籍針對“妖書”作了細(xì)致的規(guī)定,《唐律》規(guī)定 “妖書妖言”即是 “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說吉兇,涉于不順者”,疏議對此條律文又有明確解釋:“‘造妖書及妖言者’,謂構(gòu)成怪力之書,詐為鬼神之語;‘休’,謂妄說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咎’,謂妄言國家有咎惡;觀天畫地,詭說災(zāi)祥,妄陳吉兇,并涉于不順者,絞。”而元人徐元瑞認(rèn)為 “怪異不常之書”為 “妖書”,更強(qiáng)調(diào)奸邪的成分。《大明律》規(guī)定:“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又解釋道:“讖緯是誕妄休咎之言,組織未來之事,妖書如鬼神之書。”明代名臣王恕依此重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律 “妖書妖言能惑眾亂民壞國家之事 ”。
具體而言,明代許多被稱為 “妖書”的主要指與叛亂謀反有關(guān)并涉及宗教、天運(yùn)、世道、鬼神等內(nèi)容的書籍,冒犯或觸忤了統(tǒng)治者忌諱的言論和書籍,用于政治斗爭的黨爭文書,帶有政治語言性質(zhì)的讖謠類書籍,擾亂社會秩序的書籍等等。至于妖書的范圍,余繼登 《典故紀(jì)聞》列出了94種之多:“成化年間,因擒獲妖人,追其妖書本圖,備錄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曉諭愚民。其書有:番天揭地、搜神記經(jīng)、金龍八寶混天機(jī)神經(jīng)、安天寶世、繡瑩關(guān)、九龍戰(zhàn)江神圖,天空知賢變愚神圖經(jīng)、鎮(zhèn)天降妖鐵板達(dá)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晶珠經(jīng)……”
在明代,雖然對出版的管制相對較松,但對這些 “妖書”則是嚴(yán)懲不貸:“造讖諱、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皇帝曾多次頒令,嚴(yán)禁私藏和流傳妖書。如成化十年五月,明憲宗 “申藏妖書之禁”;弘治十七年二月,明孝宗 “申藏諱妖書之禁”。從統(tǒng)治者深惡痛絕的態(tài)度,可見妖書在傳播社會輿論方面的巨大影響。
明代初期,由于皇帝對思想控制比較嚴(yán)密,對輿論掌控較緊密,妖書相對較少。到明代中后期,一方面專制統(tǒng)治開始松動,朝政日漸寬大,輿論環(huán)境相對寬松,敢言能言成為社會及政治風(fēng)氣;另一方面各種思想交鋒激烈,傳統(tǒng)禮制束縛較少為妖書開始大肆傳播創(chuàng)造了社會環(huán)境。更重要的,是晚明發(fā)達(dá)的商業(yè)環(huán)境下,底層民眾容易被蠱,或為謀生而傳播和編造妖書;黨爭愈演愈烈,官僚為了政治斗爭而利用妖書,統(tǒng)治者為維護(hù)話語權(quán)而創(chuàng)造了 “文字獄”式的妖書等等。妖書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有其深厚的社會根源和歷史合理性,同時,各個階層對妖書的解構(gòu)及利用,又對當(dāng)時的社會生活以及統(tǒng)治秩序造成了 重 要 影 響。
妖書在晚明的政治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多是制造重大政治事件的有力工具。“有太原人李福達(dá)以妖書惑眾,聚黨至數(shù)千人,改年為亂,震動三河。”而萬歷年間的妖書案則成為晚明時期影響最大、涉及面最廣的事件之一。萬歷二十六年,萬歷皇帝將從民間收集的一本名為 《閨范圖說》的圖書賜給了最寵愛的鄭貴妃,該書主要內(nèi)容是婦德。鄭貴妃自己作序并交由其伯父鄭承恩編印出版散發(fā)。此時,民間出現(xiàn)一本匿名圖書《閨范圖書說跋》,又名 《憂危竑議》,“盛傳京師,謂坤書一首載漢明德皇后由宮人進(jìn)位中位,意以指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為立己子之據(jù)。其文托 ‘朱東吉”為問答,‘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諷,蓋言妖也。”當(dāng)時文官集團(tuán)正在與萬歷皇帝就立儲一事展開著激烈的斗爭,他們認(rèn)為鄭貴妃想通過《閨范圖說》一書制造立愛子、不立長子的輿論,但作者并未查明。
五年后,萬歷三十一年十一月的一晚,“上寢重幄中,初寤,天未曉,忽于枕上得書一卷,呼嬪御取燭夜讀,則皆陳說上過也。上駭,密令心
四、妖書:自下而上的輿論工具
腹大珰出察之,雞人方傳唱,閭闔諸宮未啟,不知其何來。尋問閣部臣入對,諸內(nèi)外大小臣俱于是夜從枕上得書,與所陳事同,無一逸者,眾不敢匿,趨朝中各上之。上下大驚愕,相謂妖書。”這本妖書名為 《續(xù)憂危竑議》, “言貴妃與大學(xué)士朱賡、戎政尚書王世揚(yáng),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yǎng)志,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承恩,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等相結(jié),謀易太子,其言益妄誕不經(jīng)。”朱賡 “已邸門獲妖書,而書辭誣賡動搖國本,大懼,立以疏聞,乞避位。”
實際上,當(dāng)時朝政比較寬松,對 “國本”異議的朝臣大可通過正常的疏議程序表示不滿,而不必?fù)?dān)心被重懲。而散布者以 “妖書”的形式,不僅言辭詭譎,而且刊印散發(fā),一夕間 “黏宮中與城坊皆遍”,顯然其真正目的不在于論 “國本”,而在于通過 “國本”之爭引起朝廷關(guān)注,進(jìn)而趁機(jī)打擊政敵。如御史趙之翰等便借此彈劾前大學(xué)士張位等 “太子黨”官員,并使其遭謫戍,牽連者多遭牢獄之災(zāi)。
如果說這兩份 “妖書”一開始還反映了民眾對于 “國本”的輿論關(guān)注,那么到后來 “妖書”的內(nèi)容被關(guān)注較少,而是成為朝廷內(nèi)部各派勢力政治斗爭的有力工具,由此還牽連了一大批無辜受冤者。對于 “妖書案”,錢謙益感慨地說:“(沈一貫)與宋州 (沈鯉)同輔政,而門戶角立,矻矻不相下,妖書之獄,宋州及郭江夏僅得而免。人謂少師有意齮龁之,海內(nèi)清流,爭相指摘,黨論紛呶,從此牢不可破。雒蜀之爭,遂與國家相始終,良可為三嘆也!”
五、結(jié)論
尹韻公評價說,從傳播學(xué)的角度看,書籍的出版發(fā)行與社會輿論有很強(qiáng)的聯(lián)系,因為書籍不僅具有積累文化、弘揚(yáng)文明的作用,而且還能傳播思想、流布言論,進(jìn)而形成社會輿論的現(xiàn)實作用。雖然明代的圖書出版有著特有的發(fā)展規(guī)律與過程,但它也確實給予了明代的社會輿論以強(qiáng)大的和深刻的影響。如果說言論是社會輿論中的“無形”部分,那么書籍則是社會輿論中的有形部分。有形的比無形的更有力量,更成氣候。商業(yè)發(fā)展的需要,市民階層形成的必然,中國近兩千年政治和思想發(fā)展的高峰,使書籍在晚明成為輿論的代表性符號。東林黨議、魏忠賢亂政、萬歷三案、遼東戰(zhàn)事、李自成起義、清軍南下等晚明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書籍的影子,感受到書籍所傳播的社會輿論的力量。
然而,書籍只是輿論傳播的一種工具或者形式,成為其編者、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一種媒介。通過書籍與社會輿論傳播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書籍的輿論力量在晚明商業(yè)化的背景下被空前放大:書籍不再只是傳播知識、傳遞文化的載體,更是制造、引導(dǎo)、控制輿論的有效手段,甚至影響時局。在中國古代社會,對于思想、文化的控制是統(tǒng)治者所竭力掌握的。而晚明時期,統(tǒng)治者卻有心無力,反而被書籍制造的輿論嚴(yán)重動搖了對思想文化乃至行政權(quán)力的控制。這種控制力的“逆襲”,反映出晚明社會并沒有形成一個信息暢達(dá)、有效的輿情社會,書籍的自由流通、社會輿論的肆意流布,反而映射出 “自由奔放”光彩外衣之下的 “混亂無序”。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書籍所反映的多元思想標(biāo)志著多元社會的形成,但缺少大氣、包容和堅忍、霸氣的正統(tǒng)思想引領(lǐng),王朝就會 “因財富積累而導(dǎo)致貧富不均、因國家承平而導(dǎo)致因循守舊、因社會開放而導(dǎo)致渙散動蕩、因自由過度而導(dǎo)致規(guī)矩喪失。與此相伴而生的,則是國家主導(dǎo)作用的日漸缺失和對外防御能力的急劇下降”。從某種意義上講,晚明的書籍“見證”了社會輿論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的高峰,也參與了晚明政治與社會的動蕩紛爭,記錄并傳播了晚明的風(fēng)雨飄搖,成為晚明社會變遷最好的注腳。
注釋
①周慶山:《文獻(xiàn)傳播學(xué)》,北京:書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97年,第3-4頁。
②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77頁。
③姚旅:《露書》卷9《風(fēng)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6頁。
④鐘惺:《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見徐柏榮、鄭法清主編《鐘惺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247頁。
綠色生態(tài)示范區(qū)應(yīng)在控制性詳細(xì)規(guī)劃階段編制綠色建筑規(guī)劃專章,落實潛力地圖及總體規(guī)劃提出的總量目標(biāo),提出各個地塊的綠色建筑星級要求。建議研究制定地塊生態(tài)開發(fā)控制圖則,加強(qiáng)在土地出讓環(huán)節(jié)對綠色建筑相關(guān)規(guī)劃指標(biāo)的控制。
⑤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34《正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12-313頁。
⑥查慎行:《人海記》卷下,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頁。
⑦吳敬梓:《儒林外史》第13回《蘧駪夫求賢問業(yè) 馬純上仗義疏財》,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第81頁。
⑧葉燮元:《明代江蘇刻書事業(yè)概述》,《學(xué)術(shù)月刊》1957年第9期;李致忠:《明代刻書述略》,《文史》第23輯;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文物》1980年第11期;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yè)的發(fā)展》,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第41-42頁。
⑨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8“時藝坊刻”條,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34頁。
⑩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文物》198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