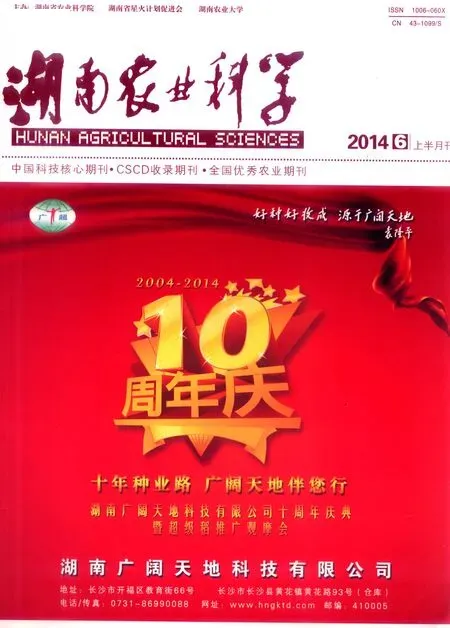發達國家農業生態補償對我國稻作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啟示
莫 童,向平安
(湖南農業大學生物科技學院,長沙 410128)
稻田是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濕地生態系統,由稻田生物系統、環境系統和人為調節控制系統三部分組成。除糧食供應功能外,以水稻為主體的稻田生態系統還具有涵養水源、改善水質、凈化空氣、調節區域小氣候、維持生物多樣性和創造景觀文化價值等多種正外部效應[1]。由于稻田多功能性作用提供的公共物品不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易,而沒有被賦予恰當的價值。
在我國,水稻是最主要的糧食作物之一。然而近年來,由于種植水稻經濟效益相對較低,稻田拋荒現象在農村日益普遍。同時在追求糧食產量和經濟利益的刺激下,農藥、化肥的濫用也造成了面源污染以及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要維持既有的稻作生態系統,使其繼續保持濕地生態特性,發揮正外部效應,減少負外部效應,建立稻作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尤為重要。
對于稻作農業生態補償,國內外專家學者已經進行了較多研究,在美國、歐盟等農業現代化較為成功的國家,其農業生態補償早已進入實踐階段。我國近幾年也在加緊制定相關政策,并在部分地區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如何向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學習,鼓勵和引導農民采用環境友好的生產技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農產品質量,對稻田農業面源污染管理和改善農業生產、生活環境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1 生態補償的概念
生態補償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綜合運用行政和市場手段,調整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相關各方之間利益的環境經濟政策[2]。
許多學者如呂忠梅[3]、毛顯強[4]、李愛年[5]等在生態補償概念的確立上做出了大量研究探討,但國內還沒有形成一個公認的生態補償的定義。呂忠梅認為,從狹義上理解,生態補償是由人類對生態系統和自然資源造成的破壞及對環境污染進行補償、恢復、綜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動的總稱;從廣義上來講,還應包括對因環境保護喪失發展機會者給予政策優惠、物質補償和技術服務,以及為提高環境保護水平而進行的科研、教育費用的支出等。
2 稻作生態系統生態補償方式
國際上比較常見的生態補償方式分為農業補貼和綠色補貼兩種。
農業補貼是世界各國在農業生態補償中最重要和常見的政策,目的是保護本國糧食安全和保障農民收入。在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多邊協議框架下,農業補貼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廣義補貼,即政府對農業部門的所有投資或支持,其中主要是對科技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結構調整等方面的投資。這些投資由于不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發生直接顯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稱為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6]。
另一種是狹義補貼,如對糧食等農產品提供的價格補貼、出口補貼或其他形式補貼,這類補貼通常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造成直接明顯的扭曲性影響,一般被稱為“黃箱政策”補貼,又稱為保護性補貼。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補貼、農產品營銷貸款補貼、休耕補貼等都屬于此類。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精神主要體現為規范“綠箱”、削減“黃箱”。
綠色補貼也是一種運用較為廣泛的生態補償方式,又稱環境補貼,是指為了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各國政府采取干預政策將環境成本內在化,對本國企業在治理環境、改善產品加工工藝的投入進行補貼,以提高本國產品競爭力的一種產業政策[7]。綠色補貼被視為對機會成本的補貼,污染者要得到該補貼,則需放棄一定量的污染物排放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在農業上,可指種植者放棄施用大量化肥、農藥所帶來的增產效益,從而減少土壤和水體污染。
3 國外生態補償的實踐
生態系統服務是一種公共物品,政府通常是生態系統服務的買家或贊助方。國外生態補償的實踐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政府購買模式、市場模式和生態產品認證計劃(間接交易模式)[8]。
3.1 政府購買模式
政府購買模式的生態補償實質是直接公共補償,它是指政府直接向提供生態系統服務的農村土地所有者及其它環境服務提供者進行補償。目前政府購買模式仍然是主導的和最為普遍的生態補償模式。如歐盟為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資源、土壤、遺傳多樣化,并保持自然風景和農村資源的農民提供一筆農業環境保護補貼。歐盟每年對一年生作物支持的上限為 600 歐元/hm2,對多年生作物為900 歐元/hm2,對于其他土地使用為450 歐元/hm2[9]。在德國,實施有機農業生產,發展有機食品的農戶,每公頃可得到政府450馬克的補助。一些地方還可以選擇參與一些項目得到額外的補貼。因此,有些歐盟國家的環境友好型土地達到約2/3,農民可以從政府得到補貼的同時也可在一些機構的扶持項目中再次得到補貼。
美國作為世界上的經濟、農業超級大國,在實施生態補償方面具有較為長期的歷史。早在20世紀30年代,由于受到干旱、沙塵暴以及經濟衰退等方面的影響,美國政府開始采用鼓勵農戶開展土壤保護和其他農業環境的改善。美國生態補償項目的基本做法是政府從國庫中給生產者支付一定的現金,以換取目標區域土地利用方式轉變,有利于生態環境改善。通常政府會劃定一個實施耕地保護的區域,在限定區域范圍內不加入該項目的農戶將不能享受聯邦政府提供的“農民補貼計劃”。在這種政策扶持下,既能保證耕作的土地面積,也保護了稻田生態系的各項服務功能。但是美國對生態補償的研究,大多不是特別針對稻田生態系統,因為水稻的種植在美國并不普遍,而美國農業大多以大型綜合式農莊形式存在,補貼也是針對綜合型農莊。
3.2 市場模式
市場模式的生態補償是私人之間直接進行的補償,這些補償通常被稱為“自愿補償”或者“自愿市場”,因為購買者是在沒有任何管理的情況下進行交易。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澳大利亞“灌溉者為流域上游造林付費”補償項目。澳大利亞面臨大面積土地鹽漬化的生態問題,而土地鹽漬化進程隨著森林的砍伐更加惡化。政府林業部門對此采取了一項生態補償的重要舉措:由灌溉者付費給上游造林者。這種公私合作的模式運作是:灌溉者對于每一公頃新造林地,在十年之內每年向當地林業部門支付一定款額購買上游造林的服務。這項收入由當地林業部門支配,并在公共的和私有的土地上重新種植樹木。
3.3 生態產品認證計劃
生態產品認證計劃,即消費者可以通過選擇,為經過獨立的第三方根據標準認證的生態友好型產品提供補償的計劃。它實際上是消費者為生態環境服務間接付費。如歐盟則對產品的設計、生產和銷售進行綠色認證,以保證產品壽命周期各個環節能夠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物排放。同時通過各種途徑積極地向消費者推薦獲得認證的產品和生產廠家,幫助這些企業塑造良好的社會形象,取得消費者及社會的信賴,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因此即便價格稍高于常規產品,消費者仍傾向于購買綠色產品[10]。
4 國內稻作生態系統生態補償進展
4.1 政策與理論
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入世后農產品進入全球化競爭面臨著質量安全的要求,中國對農業生態補償問題日益重視。學術界也開展了相關的研究工作,為生態補償機制建立和政策設計提供理論依據。從政策上來講,國務院先后與2005年頒布《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盡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要求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要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由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水利部、環保部、林業局等11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條例起草小組,今年已經形成生態補償條例草稿。近年來,各地區、各部門在大力實施生態保護建設工程的同時,積極探索生態補償機制建設,在森林、草原、濕地、流域和水資源、礦產資源開發、海洋以及重點生態功能區等領域取得積極進展和初步成效。
4.2 實踐進展
近幾年,中央政府和許多地方積極試驗示范,探索開展生態補償的途徑和措施。具體到農業領域特別是稻作生態系統,我國對農民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多使用有機肥等一系列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的生產措施還沒有出臺相關的補償政策。從地方試點情況來看,目前江蘇省和浙江省已經走在前列。
浙江省是第一個以較系統的方式全面推進生態補償實踐的省份。2005年8月,浙江省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確立“受益補償、損害賠償”、“統籌協調、共同發展”、“循序漸進、先易后難”、“多方并舉、合理推進”的生態補償機制原則。從2012年開始,浙江省決定對糧食生產功能區內種植水稻實行生態補貼試點。根據2010年到2012年的糧食生產功能區面積,按每畝10元的標準給予補助。盡管補貼標準相對不高,但重要的是引起了人們對農業生產所作生態貢獻的關注。
2008年,蘇州農學專家金偉棟在其調研報告《蘇州市水稻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研究》中,對水稻的生態價值進行了評估:一畝水稻能產出近3 840元效益,其中,生態價值占比81.4%。折合成人民幣,合計3 126元,這項全國首例水稻生態價值調查為政府生態補償政策提供了數據參考。2010年,江蘇省蘇州市出臺了《關于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意見(試行)》,明確對基本農田、水源地、重要濕地及生態公益林給予生態補償。其中,對水稻主產區,千畝以上、萬畝以下的水稻田,按每畝200元予以生態補償,連片萬畝以上的水稻田,按每畝400元予以生態補償;2011年,昆山市也開始試行稻田生態補貼。
5 小結與討論
盡管我國在稻田生態補償方面開展了不少工作,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對生態補償的概念和內涵認識不一致;理論研究落后于實踐探索;生態補償的范疇和總體框架尚未建立;補償標準的確定缺乏科學依據;補償資金來源單一、數量不足;生態補償機制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度不夠;缺乏統一的歸口管理,造成管理上的混亂。其中補償機制的完善和補償標準的確定最為關鍵和緊要。
5.1 完善補償機制
首先應從完善補償機制方面入手,實施試點示范,分步建立稻田生態補償的有效機制。我國農業生態環境保護仍然缺乏強制性的法律和法規,相關機制建設也剛剛起步,尚不完善。目前用于稻田生態補償的專項資金來源渠道過于單一,主要是來自于財政轉移支付、企事業單位的投入,或者是優惠貸款、社會捐贈,而社會捐贈、優惠貸款實際上相對較少。這種專項資金以項目建設的形式,是對特定地區的專項支出,補償的覆蓋范圍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補償的數額也有一定的限制和不足,不能完全滿足建設和保護生態環境的需求。
稻作生態補償的補償模式應以政府補償為主,市場補償為輔,建立水稻生態補償基金。補償的對象為從事水稻生產的農民。可采取以政府為主體的補償模式,補償金由財政統一支出,專款專用。設立無公害稻米生產補償資金,鼓勵稻米加工龍頭企業、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稻農等共同建設無公害有機稻米生產基地,實現水稻的無害化、清潔化生產。同時輔以市場手段,規范生態產品(如綠色、無公害產品)的認證,并加大宣傳力度,提高產品溢價,讓消費者通過購買行為間接為生態保護買單。
5.2 厘定生態補償標準
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是補償機制構建的核心和難點。稻田生態環境具有外部效益,需要將其內在化,激勵保護主體的積極性,彌補供應不足的問題;同時稻田面源污染嚴重,稻田生態正面臨著負外部性行為大量存在和正外部行為缺乏激勵的現實困境。
補償標準的確定一方面要參考農民的意愿。以茗岙鄉和昆陽鄉為例,在基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對梯田水稻生態補償機制研究中顯示,該地區梯田水稻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總價值分別為1 971.09×104元和2 669.63 ×104元,其中,直接經濟價值分別占總價值的20.99%和20.58%,間接經濟價值分別占總價值的79.01%和79.42%,即環境服務價值遠大于產品服務價值[14]。而進行梯田種稻農民則認為每種植一畝水稻田應得到50元以上的生態補償。
對武漢市農民綠色補貼意愿及額度調查則表明:69.32%~85.25%的農戶希望政府按每公頃3 928.88-8 367.00元的標準,來補償他們減少50%的化肥和農藥使用量帶來的經濟損失。該數據由農戶按生產經驗判斷的減產幅度及增加的管理難度和工時工資進行測算[15]。
對于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最終應結合農民的接受意愿,根據生態保護者的投入和機會成本的損失、生態受益者的獲利、生態破壞的恢復成本、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等因素來綜合考量。
[1]李鳳博,徐春春,周錫躍,等.稻田生態補償理論與模式研究[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9,30 (1):102-105.
[2]燕守廣.關于生態補償概念的思考[J].環境與可持續發展,2009,(1):33-36.
[3]呂忠梅.超越與保守—可持續發展視野下的環境法創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55.
[4]楊志峰, 何孟常, 毛顯強等.城市生態可持續發展規劃[M].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04:46.
[5]李愛年,陳蘭圖.我國城市水污染防治立法中存在的問題及完善的建議[M].北京:現代法學;2002:4.
[6]杜 蕓,楊 青.WTO框架下我國農業補貼現狀分析[J].生態經濟,2010, (3) :98-101.
[7]徐曉雯.農業綠色補貼及其經濟學分析[J].《財政研究》,2007,(7) :30-32.
[8]任世丹,杜 群.國外生態補償制度的實踐[J].環境經濟,2009, (11):34-39.
[9]楊曉萌.歐盟的農業生態補償政策及其啟示[J].農業環境與發展, 2008, (6) :17-20.
[10]李鳳博,徐春春, 周錫躍,等.基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梯田水稻生態補償機制研究[J].中國稻米,2011,17(4):11-15.
[11]蔡銀鶯,張安錄.武漢城鄉人群對農田生態補償標準的意愿分析[J].中國環境科學,2011,31(1):17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