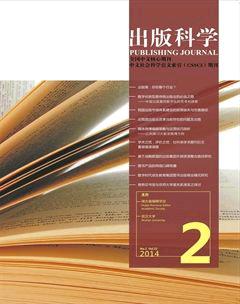商務印書館與京師大學堂關系演變之探討
王波
[摘 要] 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大學是20世紀中華文化的雙子星座。雙方的關系可上溯至戊戌變法,從1898年到1913年,基本上是在京師大學堂時期。雙方的關系經歷了兩個階段:遠觀漠視期(1898—1902)和個別接觸期(1903—1913),該時期為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大學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 商務印書館 京師大學堂 北京大學 關系 晚清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4) 02-0105-05
商務印書館創辦于1897年2月11日,比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的誕生還早一年,創辦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原是外國在華創辦的報館和書館的排字工人,他們文化水平低,和北京大學這個最高學府扯不上關系。但是無論是商務印書館還是北京大學,其機構名稱的宣布或者說是房屋建筑的奠基實際上意義有限,只能說是堆山待龍、筑巢引鳳,只有等到龍來鳳棲,才賦予其真正靈魂。
此龍斯鳳便是張元濟與蔡元培。他們一同參與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張元濟遭遇解職,蔡元培自愿離職,兩人自謀出路。經過一番周折,張元濟于1902年加盟商務印書館,蔡元培于1916年后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這兩個機構才有了館魂校格,從此走上了開創國內一流的光明大道。追根溯源,戊戌變法才是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大學本質上的起點,因此論及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大學的歷史淵源,不能不從戊戌變法說起。
1 本是同根生:戊戌變法的意外收獲
戊戌變法期間,年長于蔡元培,在科舉之路上也一路領先的張元濟,比蔡元培更為活躍,他積極學習英語,主動接觸西學,時常受命為光緒皇帝收集西書,還與友人合辦通藝學堂,聘請嚴復前來講學。
特別是他創辦通藝學堂之舉頗受朝廷關注。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下詔明定國是,正式啟動戊戌變法。兩天后,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以“國是既定,用人宜先”為由,上奏“密保維新救時之才,請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圖自強”。所保薦者5人: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和梁啟超。對張元濟的舉薦意見是:“刑部主事張元濟現充總理衙門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學校,辦事切實,勞苦不辭,在京師創設通藝學堂,集京官大員子弟講求實學,日見精詳。若使之肩任艱大,籌劃新政,必能勝任愉快,有所裨益。”[1]光緒皇帝常令總理衙門代找新書,如黃遵憲《日本國志》等,張元濟是具體執行人,有時以私藏相呈,光緒皇帝曾從藏書章中見過張元濟的名字,對其留有印象。康有為是公車上書的發起者和維新變法的輿論領袖,光緒帝對其早有接見之意,只是迫于后黨力阻,遲未實現。徐致靖的奏折堅定了光緒帝的決心,于是便召張元濟和康有為同日覲見。這在當時屬于破格之舉,因為按照清朝禮制,皇帝只召見四品以上的大臣,而張元濟當時只是六品官,康有為還是尚未授職的新科進士。光緒皇帝先與康有為會談了兩個半小時,當日便賜予其總理衙門章京之職,又與張元濟會談半個小時,了解通藝學堂的辦學情況及張對興辦鐵路、工礦、外交、學堂等方面的建議。張元濟的建議之一是“應責成大學堂認真造就各項人才”,特別是要大力培養工程和外交人才。此日的君臣會談為決策設立京師大學堂起到了一定作用。
京師大學堂領導班子醞釀期間,首任管學大臣孫家鼐曾力主由張元濟出任大學堂總辦,但張元濟看不慣孫家鼐疏遠帝黨,親近后黨,執掌官書局后,篡改其前身強學會宗旨的政治投機行為,力拒邀約。這個事實說明,張元濟和北京大學的緣分比蔡元培更早。
戊戌變法失敗后,張元濟因為有限參與百日維新,成為其外圍人物,而被“革職永不敘用”。他一手創辦的通藝學堂難以為繼,而京師大學堂作為碩果僅存的戊戌變法的遺留如期開設。通藝學堂的校產全部被登記造冊,并入京師大學堂。也就是說,張元濟雖然人沒能到大學堂,但仍然以捐獻校產的方式,為京師大學堂做出了貢獻。從言論促成、校產移交這兩個方面來看,張元濟都應該位居京師大學堂創辦人之列。可能是由于通藝學堂規模小、資產薄,幾可忽略不記,后來的北京大學校史研究者主要關注由強學會、官書局、同文館、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這條發展主線,而選擇性地遺忘了張元濟及其創辦的通藝學堂對奠基期的北京大學的貢獻。
蔡元培雖沒有受到明確處罰,但他對清政府失望之極,和張元濟一樣,也選擇了離都南下。從此兩個人的命運同根發芽,分展兩枝,以致決定了中國兩大文化事業——出版和教育的發展方向。
張元濟被逐出政壇后,經李鴻章推薦,直奔上海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主持譯書院,因印務關系,在與商務印書館老板夏瑞芳打交道的過程中,欣賞夏瑞芳之精明果敢,看好出版業的前景,終于在1902年加盟商務印書館,手創編譯所,以此為津梁,打通了排字工人的小企業與知識精英的通道,將商務印書館由印刷作坊一舉扭轉為現代化出版機構。他選擇的是一條對官場不再戀棧,徹底走向民間、走向市場、走向出版事業的人生道路,終成一代巨擘。
蔡元培脫離清廷后,曾在家鄉紹興短暫辦學,后來受到張元濟的召喚,也到商務印書館工作,出任首任編譯所所長,隨后又在商務印書館的資助下出國留學。在這個過程中,蔡元培勤奮著書立說,在學術上匯通中西、屢有開創,積累了安身立命的資本;在高等教育方面,他留心體驗歐美學制,極力開闊視野,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卓越的教育理念。這些積累為他日后成為北京大學歷史上最杰出的校長創造了優良條件。北京大學正是得益于蔡元培不遺余力地引進人才和大刀闊斧的革新,以及由革新催生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徹底改變了基因和靈魂,終于成為舉國尊崇的最高學府。
應該說,戊戌變法不僅直接醞釀、催生了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的創立,還為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大學靈魂人物的成長埋下了伏筆。它將兩位潛力巨大的青年才俊逐出政壇、推向民間,卻不期然地廣闊了他們的天地,開闊了他們的視野,擴大了他們的選擇,釋放了他們的天才。官場從此少了兩個潦倒的政客,學界從此多了一對濟世的英雄。如果不是戊戌變法的失敗,就不會有張元濟和蔡元培的事業轉型,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大學這兩艘文化航船,很可能因為缺乏天才舵手,而消失于惡浪滔天的中國近現代史的進程中。后來的歷史表明,正是因為張元濟和蔡元培遭遇了戊戌變法的刺激,對人生方向再定位再追尋,對興趣事業的再思考再探索,才在若干年后,一個主持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國立大學,一個主持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民辦出版企業,各以兼容并包的氣魄,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知識分子,締造了“商務文化”和“北大文化”,使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大學雙峰競秀、聲氣相通,成為中國近現代新文化的搖籃和基礎,成為民國時期貢獻最大的兩艘文化旗艦,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最有成就、最為璀璨的雙子星座。如果說北京大學是戊戌變法的“遺腹子”,那么把商務印書館比喻為戊戌變法“宮外孕”的孩子,也不是沒有道理。endprint
以上述事實反觀戊戌變法,不難發現,從短時段的眼光看,它在政治上是流產了,但是從長時段的眼光看,它卻沒有完全失敗,它為未來埋下了暗火和伏筆,它逼迫年輕有為的京官流散各地,為各項事業的開拓輸送了人才,這些人的成長和奮斗,遲到地實現了變法的諸多目標,包括發展高等教育和振興出版事業。從這個意義上講,戊戌變法這個埋葬于血雨腥風的帝國爛根居然開出了兩枝奇麗的鮮花,略可告慰那六位壯烈就義的戊戌君子,以及那個懷有維新之夢而死因蹊蹺的光緒皇帝。
2 商務印書館與京師大學堂關系演變的兩個階段
晚清和民國時期,張元濟始終是商務印書館的實際掌舵者,特別在外務方略方面,張元濟的個人魅力和風采遮蔽了商務印書館的其他所有當家人。
商務印書館與北京大學的關系,從根本上看是建立在以張元濟為圓心的,與嚴復、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等歷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深厚私交的關系基礎上,張元濟終生沒有疏遠且在不斷增進這些關系,這就沒有給商務印書館的其他負責人以與北京大學直接建立特別關系的機會。故而,張元濟與北京大學的關系,基本上代表了商務印書館與北京大學的關系,以張元濟對待北京大學的態度為軸心,商務印書館與北京大學的關系大致經歷了六個階段。下面主要探討中華民國成立之前,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關系演變的兩個階段。
2.1 遠觀漠視期(1898—1902年)
張元濟目光如炬,對創辦初期的京師大學堂并不看好。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反感政治投機的管學大臣孫家鼐,對孫家鼐先是支持光緒,積極參與強學會,后來靠攏后黨,成為官書局管理大臣,改組強學會為官書局,在其所擬《官書局章程》中,刪除了最具強學會特色的辦報一項,并規定不準議論時政,不準臧否人物,不準挾嫌妄議,不準瀆亂宸聽,使之漸諱時政[2]。張元濟認為孫家鼐的這些做法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從根本上閹割了強學會。他曾就強學會改官書局一事上書孫家鼐,對官書局大肆修正強學會的做法發表不同意見,結果是“屢謁而不得一見”[3]。張元濟對孫家鼐這種“徘徊于帝、后之間”,“秉帝命以行革新之政,而陰謀破壞革新之實,兩面狡展,陰袒舊制”[4]的做法頗為不滿。孫家鼐主持官書局后,所出《官書局會報》遭到張元濟的批評,他曾在致友人汪康年的信中批評官書局“所刊局報多系蕪詞,閣抄格言,最為可笑”[5]。張元濟后來創辦通藝學堂,隱約有承續強學會,彌補官書局所不及的意味。
戊戌變法期間,張元濟任總理衙門章京。1898年6月16日,光緒克服重重阻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召見變法輿論的主將康有為的當天,也召見了張元濟,詢問了他所辦通藝學堂的情況和他對興辦鐵路、工礦、外交、學堂等方面的看法。這次召見后所產生的兩個重大決策是:一、6月23日光緒皇帝正式下詔宣布廢除八股。二、6月26日光緒皇帝下諭,嚴詞敦促加緊京師大學堂的開辦:“前因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倡,特降諭旨,令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議奏,即著迅速復奏,毋再遲延……并不依限復奏,定即從嚴懲處不貸。”[6]接到這個上諭后,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立即請康有為起草大學堂章程,康有為因忙于其他變法事務,又將其委托給梁啟超,梁啟超參酌各國學制,起草了章程,由康有為作了審定。總理衙門回復光緒的奏折,乃是經張元濟請康有為代為起草。可以說,張元濟處在總理衙門章京的位置,恰好見證了京師大學堂籌建時奏折、上諭、章程等文牘流轉的過程,并以自己的思想、文書為京師大學堂的籌辦做出過實際貢獻。
1898年8月24日,禮部鑄妥了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的官印,戶部為大學堂劃撥了經費,京師大學堂正式開辦。孫家鼐本欲聘康有為作總教習,但看了梁啟超所擬大學堂章程,其中有大權歸總教習的內容,以為是康梁合謀,要架空他這個管學大臣,于是大動肝火,忿而攻擊和中傷康有為,康有為也十分生氣,命梁啟超轉告孫家鼐:“誓不沾大學一職,以白其志。”[7]后來,孫家鼐又轉而舉薦許景澄,但許不在京城,遂自兼總教習,西文總教習則聘了丁韙良,中文總教習聘了劉可毅。
總教習是教學系統之總管,相當于教務長。辦學離不開行政機關和后勤服務系統,則設“總辦”為最高管理者,相當于總務長,下轄提調若干名,分工管理各類事務。“總辦”一職,孫家鼐擬請張元濟擔任,曾私下征求其意見,因張元濟有創辦通藝學堂的經驗,對創辦京師大學堂的往來策議十分清楚,更能深入理解創辦大學堂的宗旨、使命,便于落實。雖然京師大學堂的創辦和張元濟的建議有關,但如前所述,張元濟對孫家鼐的為人和其訂立的官書局的政策不滿,自感政治立場迥異,道不同不相為謀,便以大學堂“所用提調皆非同志”為借口,力辭之。孫家鼐不允,仍擬奏派[8]。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帝,歷時僅103天的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遭捕殺,康有為、梁啟超遭通緝,維新官員數十人被罷免,張元濟因受過光緒帝的召見,亦于10月8日被“革職永不敘用”,孫家鼐聘他出任京師大學堂總辦一事也就戛然擱淺。
張元濟受到處分后,被迫離京南下。光緒推行的各項維新措施基本上均告流產,唯有京師大學堂之設繼續推行,成了變法維新的“遺腹子”,明眼人對其前途均不樂觀。道理十分簡單:維新黨遭懲,從皇帝到總理衙門章京這樣的低階小官概莫能外,世已無維新銳氣,此時興辦新式學堂,要么戴著鐐銬跳舞,暮氣沉沉,謹小慎微,不克有偉大作為;要么如高空走絲,冒險試探,稍有差池,必定粉身碎骨。或許是出于這些判斷,加上初遭處分,對清廷之事出于本能的反感,1898年至1902年,張元濟對待京師大學堂的態度可謂漠視,對其前景了無期待。他于1902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后,并未立即與京師大學堂發生緊密聯系,也未曾表達過合作的愿望。
事實也吻合了張元濟的判斷。1898年11月到1900年6月,京師大學堂原定招收500人,實招不到200人,無一畢業。1900年京師大學堂被義和團作為“洋學堂”而遭洗劫和占據,部分師生被殺,學堂被設為“神壇”。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后,京師大學堂又被作為義和團的據點而慘遭二次摧殘。1902年京師大學堂得以恢復,先開仕學館和師范館,由各地選送新生182名,于12月17日舉辦開學典禮。由于1903年確定的癸卯學制規定京師大學堂畢業生可授予進士頭銜并獎勵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職,來學堂求學的學生多是官宦之家的紈绔子弟,養尊處優、習氣惡劣,帶聽差、吃花酒、打麻將、捧名角、逛窯子,對讀書毫無興趣。教師或守舊頑固,或官氣十足,或縱容學生,或不學無術。可以說,民國之前的京師大學堂起步受挫、烏煙瘴氣,算起來辦學十年,實則沒有培養多少人才,國外視之為“蒙養學堂”,清廷也自認辦理不善,不但沒有樹立起什么美譽度,反而濁名在外,人人搖頭[9]。此時的大學堂乃變相之官場,充斥著科舉制遺留的劣根性,學術創造力低下,是不可能給商務印書館提供有價值的出版資源的。endprint
這個時期的京師大學堂負責人有的也不得善終。如許景澄,字竹筠,浙江嘉興人,清同治進士,1898年7月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1899年7月—1900年7月任暫行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1900年,義和團活躍于京城,在6月28日的御前會議上,許景澄對后黨提請的“請(義和團)攻使館”動議,獨自一人挺身反對,認為“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不同意對外宣戰,因而得罪慈禧,被以“勾結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等罪名定罪,于7月28日處死在北京,時年55歲。而在此前的7月1日,為保證京師大學堂師生安全,許景澄曾上奏建議暫行停辦京師大學堂,并獲得批準。許景澄被處死后,京師大學堂被迫停辦了兩年。由許景澄個人命運之悲慘,也可見張元濟當年力辭京師大學堂總辦之職之深謀遠慮。
2.2 個別接觸期(1903—1913年)
京師大學堂籌建時,士林和朝廷有一種聲音,呼吁任命張元濟為大學堂總辦,呼吁任命嚴復為大學堂總教習,此二人熱心西學,學識淵博,“京師講求新學之士,莫不以此舉為得人”[10]。張元濟因政治立場和政治判斷原因,對總辦一職不感興趣,竭力拒絕。嚴復則對總教習一職興致很高,但因為他非科舉出身,資格不夠,而最終沒能入圍。嚴復主辦的天津《國聞報》為此抱屈道:“可見中國創辦一事,欲得人而理,有如此之難,其實中國未嘗無人,仍不過以資格二字拘泥困守而已。”[11]
1902年,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的災厄剛剛過去,國內局勢稍加緩和,慈禧太后便在1月10日下諭,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負責全面恢復京師大學堂,并在1月11日再次頒旨,將京師同文館并入京師大學堂,以壯大之。張百熙任命桐城派大師吳羽綸為總教習,吳羽綸是嚴復的好友,向其拋出橄欖枝,邀請其出任副總教習。吳羽綸的提議合乎士望,卻不合當時的提拔選材之規,但嚴復還是很上心,在給張元濟的信中專門提到這件事,曰:“自復振大學命下,冶秋尚書之意,甚欲得吳摯甫而以復輔之。”[12]
嚴復決定主動接近京師大學堂。1902年年初,嚴復拜訪張百熙,建議將大學堂分為正齋、附齋、外齋和外交學堂四個院部,辭退原來的總教習美國人丁韙良,以避免外國勢力干涉大學堂事務。張百熙對嚴復的建議均表示贊成,“四院制”后來雖沒有落實,但果真不再續聘丁韙良。不過嚴復終究沒有當上京師大學堂的副總教習,而是被聘為“譯書局”總辦。嚴復對新崗位的工作十分重視,1902年3月9日,曾寫信給張元濟,請教編譯中小學課本的經驗,說自己應張百熙之邀,主持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編譯小學堂用課本,“聞兄在滬濱已辦此事。弟不知近所已成者幾種,種系何科?”并乞覓編譯人才相助[13]。
張元濟1896年考察天津學堂時結識嚴復,從此成為好友。1902年,張元濟剛到商務印書館,籌辦編譯所,主攻方向是出版譯書,而嚴復到了京師大學堂,負責譯書局,需要開拓的業務是翻譯西書,雙方恰好構成供求關系。另外,張元濟主持南洋公學譯書局在先,嚴復主持京師大學堂譯書局在后,嚴復也需要向張元濟請教經驗。如此一來,客觀上就加強了商務印書館和京師大學堂的聯系。
但是商務印書館的根本意愿和出發點是與嚴復個人合作,而不是與京師大學堂合作。從1903年到1912年,張元濟通過優稿優酬和深化私交的方式,陸續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八種名著,其中獨占版權的有《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穆勒名學》。《天演論》的初版雖非出自商務印書館,而是由別的機構以木刻或石印的方式面世,但真正產生廣泛影響還是自商務印書館推出鉛印本開始。
因為嚴復走進大學堂的目標是出任總教習,但京師大學堂遲遲不能滿足他這個愿望,加上嚴復這個時候的西學翻譯漸入佳境,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上海也有更優良的辦學機會在等待他,所以嚴復在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供職的時間很短,1904年便辭職南行,到上海去了。1905年他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1906年任復旦公學校長,為該校第二任校長。
和嚴復同時到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的還有林紓。林紓是嚴復的福建同鄉,系當時一流的古文家,他和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學術志趣相投,為吳所關注。受吳汝綸和嚴復的提攜,1903年林紓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筆述,與嚴復共事。1906年10月,又轉任大學堂預科、師范科的經文科教習。林紓在京師大學堂供職時間較長,一直到1913年4月辭去教席。
張元濟通過福建籍的商務印書館同事高夢旦、好友嚴復等,了解到林紓才華橫溢、譯筆優美,從1903年起開始大量出版林紓翻譯的外國小說。特別是林紓在京師大學堂任職的這10年間(1903—1913),林譯小說是商務印書館的“搖錢樹”,受到商務印書館的熱烈歡迎,也是商務印書館和林紓關系的“蜜月期”。這10年間,商務印書館共出版林譯小說64種,其中出版種數多的年份是1905年9種、1907年11種、1908年16種、1909年10種、1913年4種。1913年以后,由于林紓倚老賣老,逐利思想大于逐名思想,在翻譯上不思進取和突破,譯稿質量嚴重下滑,給人以老手頹唐的印象。加上讀者對林譯小說也產生了審美疲勞,商務印書館對林譯小說的態度悄悄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絕對歡迎,變成了不情愿的接受甚至嫌棄,年均出版種數逐漸減少,但1916年、1917年出版的種數還是不少,單是1916年商務印書館就又出版了16種。
1910年,嚴復所譯八種西學名著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七種,嚴復此時名滿華夏、聲震士林,成為公認的學界翹楚。鑒于他杰出的文化貢獻,1月17日,清廷賜予他文科進士出身,這就從根本上驅散了一直籠罩著他的“資格”陰影。
中華民國成立后,1912年2月25日,嚴復被任命為民國第一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這也是袁世凱于此年2月15日經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選舉為臨時大總統之后所簽署的第一項重要任命。此時嚴復的學術成就和聲望已遠超1898年京師大學堂初建之時和1902年京師大學堂恢復時期,兼有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和復旦公學校長的經歷,入主京師大學堂可謂實至名歸。應該說,嚴復資歷、地位的遞進,根本上源于他不懈的學術追求和對教育救國理想的一貫堅守,但是商務印書館所提供的及時而便利的出版條件,無疑也使他聲望陡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