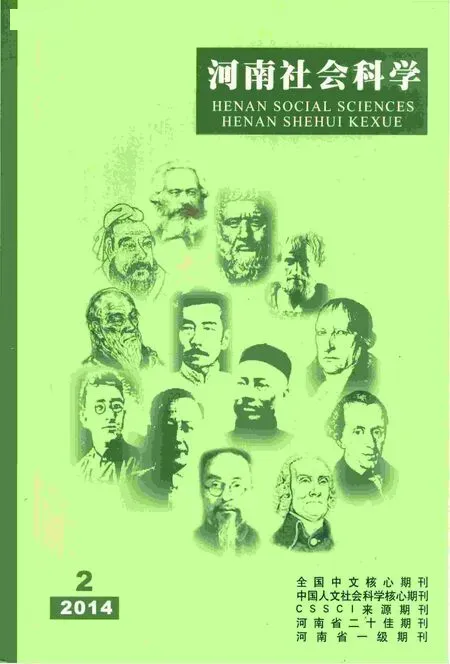現代文明、生態危機與后現代主義立場的沖突——兼論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批判性與建構性的統一
劉向國,魏山石
(東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部,吉林 長春 130024)
現代性問題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盡管在現代性批判的喧囂聲中,承認“現代性”似乎就與“齊一化”“對立化”“本質化”畫上了等號,現代性似乎已成為過去,但事實上,現代性從未遠走,不但身居于生活現實之中,也始終扎根于思想的洪流之中。難怪一些思想家始終認為捍衛現代性與批判現代性始終是思想界的主流。“一邊是哈貝馬斯指責那些批判啟蒙的普遍主義理想的人是保守主義,一邊是利奧塔哀婉動人地宣稱奧斯威辛之后現代性的規劃就已經被根除了”[1]。在哈貝馬斯那里,其所訴求的并非是從結構上去完善和發展現代性,而是需要加強關注如何以一種建設性的哲學維度來對現代性進行反思。在面對新結構主義理性批判時,哈貝馬斯以突破政治、經濟、文化的同一性來建構其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話語體系,在批駁利奧塔的同時也試圖充分展現其哲學思想的內涵和意義。后現代的批判與現代主義的建構似乎成為對立的兩極。但事實上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理論建構始終離不開前提性批判,任何想要分離二者的企圖最終都會被思想的洪流所湮沒,在這一問題上,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就是實現兩者成功結合的典范。為此,以批判性和建構性為視角,可對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之批判和建設及其兩者的一致性重新加以審視。
一
如果柯布可以看作是建設性后現代的中堅力量的話,那么他對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理解可謂尤為關鍵:后現代之“后”代表一種新的時代形勢,基于社會各領域的深刻變化,一些傳統的觀念、固化的模式和確定的知識的確證性、真理性和可信服性遭到嚴重的質疑,以至于使我們再也無法生活于現代文明的基本設想與模式之中,故“后現代主義最有影響力的形式常被稱為解構,解構理論對來自于現代、且仍構成為西方文化主流的假定,進行了明確的批判。這一批判工作是有價值的,甚至是必要的”[2]。解構或曰現代性批判始終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之“建設”的基礎性工作。這一點可以從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起點——懷特海那里得以充分的表達。
盡管懷特海從未用“后現代主義”標榜自身的學說,但毋庸質疑的是,他在對過程性的表達與辯白當中始終流動著后現代主義的語調,值得強調的是,懷特海始終視自身的哲學為思辨哲學,始終強調時代的運動以及思想的體系化是哲學發展變化的關鍵因素,因而“思辨哲學就是努力建構一個連貫的、邏輯的、必然的觀念體系,基于這個體系,我們經驗的一切要素都能夠得到解釋”[3]。內在一致和合乎邏輯是這一哲學的本質特征,所謂“內在一致”,就是要求哲學圖式所借以表達的哲學概念之間應該在彼此互為前提、互相印證中得以辯證發展;所謂“合乎邏輯”,即要求各種普遍概念在一種包含邏輯中的一致性和非矛盾性基礎上獲得具體的呈現,懷特海特意對這一思辨形象加以描述:“宛如飛機的飛行:它開始于具體的觀察基地;繼而飛行于想象的普遍性之稀薄空氣中;最后,重新降落在由理性解釋所嚴格地提供的那種被更新了的觀察基地之上。”[3]如此一來,似乎懷特海在合理性的承諾與思辨性一致的意義上繼承了康德、黑格爾式的建構,進一步完成了理性或思辨的重建。我們通常認為,黑格爾是第一個具有現代性意識的思想家,黑格爾是“使現代脫離外在于它的歷史規范影響這個過程并升格為哲學問題的第一人”,他也闡明了現代世界的危機和優越所在,即“這是一個進步與異化精神共存的世界”[4]。也就是說,在黑格爾那里,歷史規范與哲學問題存在逐層深入和不斷遞進的過程,歷史規范上升為哲學問題才能使哲學不斷呈現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但懷特海認為,現代性正是因為走了一條相反的路向,才使得思辨哲學弱化為歷史規范,哲學的弱化就是人的思辨力和思想力的弱化,“現代性的起源乃是從理性思維到歷史思維的一種轉變。在后一語詞中,他包括了經驗的研究方法。總之,現代思想尋求的不是事物和事件的終極原因,而是在更為有限的領域中尋求理解,并滿足于次終極的(less ultimate)答案”[5]。原本思辨的追求事件、事物的本質、終極性原因的哲學思維轉變為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和發展脈絡的歷史性思維,思維的弱化是理性能力的倒退。
在懷特海看來,當笛卡爾將古代哲學所設立的關于本體的追求以二元的方式予以取代,并力圖建構兩者之間的關系時,對終極性問題的追尋就發生了某種轉向:“當笛卡爾認為思想是精神實體的一種屬性,正如廣延是物質實體的一種根本屬性。但是,笛卡爾不能說明精神實體和物質實體之間的關系,而且現時代已經通過對這個問題的一系列令人不滿的回應得到了概括。對這個問題感到灰心,正是現代后期發展合縱放棄對世界的實在論說明這一方案的理由之一。”[5]對本體問題的追尋變為了對客觀性和可能性的把握,現代性憑借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歷史性認識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就,科學認知能力的提升總是建立在對事物歷史性而非思辨的把握之上。世界和歷史變成了某種可以理解的解釋模式,世界必然與其一致,思想更應與其一致。如果兩者發生了某種扭曲,就需要通過對世界認知的進一步發展予以填補,更需要思想本身發生更迭。如此一來,哲學變成了努力去證明由科學預設了的基本觀念的工具,而喪失了批判性本身。至此,現代性失落了思想,也失落了某些更為關鍵的有價值的東西。
現代性從其伊始就是反理性主義的,如果說以笛卡爾為開端的近代哲學由終極性問題向次終極性問題的轉換標志著柏拉圖式的理性主義的終極追求轉變為人認識世界的實踐努力,那么康德和休謨完成了反理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在懷特海看來,休謨以“不可知論”直接否認了事物本身的認知,也間接否定了對本體的認識可能性,本體在知識的領域已成為不可能;而康德更是干脆將世界的可知性完全劃歸于主體自身之內,“康德及其追隨者們假定,存在著一個人的世界,但不存在達到這個人的世界借以被確定的任何其他世界的通路。如果存在著另一個世界的話,它在整體上也是不可知的。對他們來說,根據定義,這確乎如此。因為被認識的東西正是因此而被引入人的世界中的”[5]。而現代西方哲學的非理性主義特別是反理性主義浪潮則進一步將這種反理性主義的情愫推至極端,從對終極性問題的解答變成了對語言等具體問題的把握,現代性以及現代性哲學因理性的失落失去了自身最有價值的終極性問題。
懷特海指出,后現代性不但與現代性相反表征一種對盲目樂觀主義的天然拒斥,更表征對某種“事物如何真實地存在的精確而恰當的圖景”之確信的放棄,更表達了某種對理性主義的重構和重建——為人類生活尋求無意義之“意義”的努力。那么后現代性就必然意味著“新的根本隱喻或范式的出現,即對全部證據進行徹底的思考和嚴格的檢驗”,這一嚴肅的思考就是理性的思考,理性主義的回歸是全部問題的關鍵。盡管理性主義的回歸在懷特海這里不是恢復被現代性所拒斥了的“前現代”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它必然要求對現代看似取得無以倫比的成就的觀念給予徹底的考察。如此一來,懷特海的“后現代主義”觀的核心就呈現了出來:考察現代性觀念本身,尋求理性主義的重建。
在懷特海的思想中,理性主義的思想傳統、對現代性觀念的自覺反思為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奠定了基調,即批判的現代性、重構的合理性。而對于合理性本身的問題,懷特海似乎沒有作出明確的回答,強調過程性、重構理性便能克服現代性問題和拯救現代性危機嗎?似乎問題并不如此簡單。
二
問題仍在繼續,探索必然延續。如何通過重構理性自身重新建構起一度為現代性所拋棄了的“價值”和“意義”等關鍵性的形而上追求,如何才能重新確立被現代性所遺失了和弱化了的思想,如何才能真正實現從單一的批判到更為合理性的建構,問題的關鍵在于找到某一突破口,以此重新為解決問題尋找契機。柯布與格里芬找到了宗教,他們認為,“現代性正是通過一種世俗化的過程而興起,這部分的乃是基督教中語言的傳統的一種繼續”,“現代主義之更為豐富的發展包括了世俗思想的日益擴張。社會和道德也和自然一樣,開始被理解為和上帝相分離的,并因而擺脫了宗教。宗教曾經起過適當作用的領域日益縮小,而且對更多的人來說,他完全消失了”[5]。既然這一領域與現代性征程的起點密切相關,建構與現代性相反的某種后現代理想也應從重建人們的“信仰”入手。
這一研究的起點,在懷特海、柯布和格里芬那里取得了共識。懷特海在《過程與實在》的最后一篇“終極解釋”中就用了兩章筆墨具體刻畫了上帝之后現代本性以及上帝與世界的關系,上帝并非是形而上學的某種例外,而的確是形而上學的終極樣板,“他是對感受的誘惑,對期望的永恒追求。他與每一種創造性活動的個別性關聯,由于這種關聯性起源于其自身在世界上有條件的立足點,因而把他構成了那種最原初的‘期望對象’,這種對象確立了每一種主觀目的的原初狀態”[3]。故上帝成了形而上之根源,是一切有關人類的價值和意義的代言,“它的痛苦、它的悲哀、它的失敗、它的勝利、它的歡樂的直接性攝入著每一種現實。這些東西由感受的正直性交織進普通感受的和諧之中,它永遠是直接的,永遠是多,永遠是一,永遠伴隨著新穎的進步,永遠向前進而絕不會凋謝”[3]。現代性正因為驅逐了上帝,在事實領域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最終使得上帝在人的精神領域徹底消失(這是康德哲學在現代性意義上的突出貢獻),上帝的消亡意味著人類形而上精神追求的消退,在懷特海看來,更意味著過程性的消失和結果性的重視,而后者構成了現代性的重要特征。故“建設”也應從此問題開始。柯布和格里芬的“建設”也至此開始,他們通過《過程神學》認為上帝的缺失或異化正是現代性及其問題的根源,“上帝這個與此在宗教和哲學中已經部分地脫離了歷史。在宗教中,諸神是信仰的對象,其本體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這個意義上,宗教、民族—國家或性的力量都可能被奉若神明”[6]。一方面,在現代性的反理性主義視閾下,一切形而上的精神性追求都被某種具體的、世俗的力量所取代,這一世俗的力量具有類似中世紀上帝的那種主宰和控制力量。另一方面,當世俗的力量成為某種包羅萬象或統一的力量之時,上帝的信仰也就崩塌了,上帝的存在也值得懷疑——有了現實的統一力量,也就不需要某種虛幻的統一力量。
格里芬認為,現代性取代了中世紀信仰的上帝,而取代之以多樣化的上帝形式:作為宇宙道德主義的上帝。這一現代性的上帝形式將上帝完全置于康德所說的道德領域,上帝承擔了立法者和執行者的雙重功能,“這就把上帝來說是次要的東西,并把人類存在之內在意義的范圍限制在道德態度的存在上”[6]。上帝僅僅承擔了一種外在衡量道德的尺度,而遠離了人的內心及人的存在。作為絕對的、不變的、冷漠的上帝,“絕對”表達上帝的存在與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無關,“不變”意味上帝的缺乏變化性,“冷漠”則說明上帝不受世間任何事物的影響。這種表達說明世界無法影響上帝,上帝的任何決斷都與世界以及世間存在的人的因素無關。上帝就是某種法庭或法則,一如現代性所要求的必然、準確、公正。作為控制力量,上帝成為決定結果的必然因素,它始終掌控全局,并已經先在地決定事情的結果,由此上帝與結果相互關聯,而與過程無關。作為現狀之維護者,上帝無論作為道德的立法者,亦或絕對的不變者,還是結果的控制者,都要求上帝維護某種秩序,維護其良性運行,避免其遭到破壞和損失,這是上帝的職責和使命。上帝也是為現實辯護的最有利的武器。作為男性的上帝,也許從中世紀中上帝圣父、圣子和圣靈的三種位格就已經說明上帝的男性特征,特別經歷現代性對上帝所賦予的主動、控制和獨立的特征并完全缺乏接受性和回應性,上帝儼然成為男性力量的代表。如此一來,現代性的“上帝”在更大程度上已經喪失了精神性和宗教特征,而取代之以現代性的反理性、普遍性、絕對性、中心性、控制性等特點,“上帝”僅僅成了某種稱謂,這一稱謂完全可以被法治、國家、民族、父權等“現代性”所推崇的新名詞所取代,現代性生活中的人也日益被這一系列新變化所“同化”。
在這種情形下,現代性事實上摧毀了上帝及人的精神信仰,取而代之是一切世俗化、刻板化、規則化的新“上帝”。不但如此,現代性通過世俗化的過程限制人們可能提出的各種問題,沒有問題,就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就沒有過程;喪失了過程,一切只是某種必然的結果而已。人將自身與自身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意義分離開來,現代人只看到必然性給予的科學智慧,而完全忽視了與宗教傳統有關的生活智慧。在這一狀況下,問題必然重重,回歸人的心靈世界,找回人的現實生活,重樹理性思索能力,才能克服現代性問題。除卻單一的衡量標準,所有的現實感受對于現實人更具意義,“在我們受難時,上帝和我們在一起受難。在我們歡樂時,他又和我們一起歡樂。當我們給動物以痛苦時,我們便給上帝以永恒的痛苦……對上帝之主要的理解不應是立法者和裁判者,而應是理性的受難者的伙伴”[5]。仁慈、憐憫、理性才是上帝的本性,也應是上帝所創造人的本性。柯布和格里芬發現,宗教意義上的變化也可以從多方面理解,“把事件的世界看作最終是由現在和過去的主體而非純粹的客體構成的,也是一種宗教意義的變化。把我們和其他動物以及作為一個整體的生物圈聯系起來,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對我們的生活來說,人們不可能把我們理解我們自身以及我們的世界的方式和這種認識的意義分割開來”[5]。故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批判現代性的觸角延展到了現實生活領域。
三
當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力圖將現代性批判與人類精神形而上追求之重塑結合起來之時,這種努力必然不僅僅局限于精神層面或思想層面,不能僅僅依靠重塑精神性的信仰,更需要通過對現實生活的現實批判。柯布認為,在現代性思維的影響下,世界的整體被分割為每個細小的部分,世界的模塊化導致人與世界的關系并不是一體化的,而是外在化的,“作為整體的世界被看作是時空上彼此相關的事物的細小部分的組合,因此人類也被看作是外部彼此相關的個體所組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外在關系成為契約關系,政治和經濟理論都是基于此發展起來的”[2]。現代性的政治、經濟都是基于現代性的文化思維而構成的,它們又真實地構成了現代性的世界,最終導致現代世界的生態危機。
現代性的政治是契約政治,是緣起于對中世紀教會權力反抗的社會境況分析,契約制度在合適的時機起到了較好的說明作用。然而在柯布看來,這一建立在神話基礎上的對社會無序性的、骯臟的生存環境所作出的說明,其與歷史之間的真實符合是存在問題的,“這種觀點的合理性在于當人類發展了個性時,對于他們接受政府控制以確保安全是很重要的,這就是霍布斯哲學關于統治者的合法性基礎。按照這種理論,一個不能保護人民和國家財產的統治者就失去了他存在的合法性,只要安全可以得到保障,那么因缺乏自由和不公正而引起的反抗就不重要了”[2]。因此,在西方社會的政治生活當中,首要的即在保證安全的基礎上維護統治,而公正和自由反而成為次生物。這一對政治生活首要目標——公正自由的踐踏,使現代性的政治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對于這一點,王治河先生也有過類似的說明,他認為在西方現代政治生活中,道義的缺席、對競爭的過分推崇、個人主義色彩過濃和均質化特征使現代政治生活充滿了問題和危機。片面追求形式上的平等,換來的恰恰是實質上的不平等,它“是以忽視人們的具體的歷史和社會差異為前提的,它預先假定了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文化之根,共同的未來愿景。因此最終由一個政黨發出一個聲音就足夠了”[7]。在這一情形下,人的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事務都被“權力”這一鎖鏈緊緊束縛住,在這樣一個體制下談“自由”,正如懷特海指出的,無疑是一個“殘忍的玩笑”。
現代性的經濟是個人的經濟活動。柯布認為,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經濟學就使用“經濟人”的概念作為市場交易和契約中的個體,當然這一個體會因種種經濟行為而與其他個體發生某些關聯。正如政治上契約論的假定一樣,個體利益的對立與互不相容是現代經濟學的根基和基本預設。當個人遵循市場規則實施市場行為之時,這一行為能夠增加和創造財富,這成為現代性一切領域的“資本邏輯”。在現代性經濟理論中,團體或團體的政黨利益難以發現或找到其生存的根基。同時,現代性自我的成長,使得經濟日益擺脫政治的控制,成為各領域的主宰力量。在這一形勢下,原本可以以政府或政治的形式為個人和團體之間搭建橋梁的努力也歸于失敗,在原本情形下,“對團體和公正的關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建立,并對其結果加以調節。今天,再也沒有全球性的政府來規范市場,或來保護團體免于被其侵擾”[2]。這一個體與團體之間二元對立的矛盾與現代性經濟的全球化訴求相背離,生產與銷售的全球化要求資本的循環與周轉需在盡可能大的市場中進行,并應受到共同體的監督,而眾多團體之間的界限和利益又反過來起到阻礙世界市場的作用。這是現代性經濟發展所無法解決的悖論。
現代性的文化是斗爭的文化。從現代社會的三個偉大發現之一——達爾文的進化論開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但成為生物界進化的規律,也成為現代性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生存法則。難怪懷特海指出:“在過去三個世代中,完全把注意力導向了生存競爭這一面,于是就產生了特別嚴重的災難,19世紀的口號就是生存競爭、階級斗爭、國與國之間的商業競爭、武裝斗爭等等,生存競爭已經注入到仇恨的福音中去了。”[8]于是從商業的競爭到政治的博弈,從個體的差異到文明的沖突,現代社會的人與人之間始終是斗爭性的。而現代社會的斗爭思維在作用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同時,影響最為深遠的在于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當我們問到從地球的警告中,應該采取什么政策時,經濟學家傾向于規勸我們政策變更的代價不能過于昂貴。他們認為,如果我們積累了相當的資本,當地球發出警告信號時,那我們將會得以應付這一警告。”[2]自然危機與生態危機是斗爭文化的苦澀結果。現代性在破壞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同時,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沖突帶給人類的將是更加冷酷的世界。
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導致的最為嚴重的后果無疑是生態危機和人類文明的危機,這一危機不再是思維領域和理論領域的危機,而是最為嚴重的現實世界的危機。然而現代性在確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立場的同時,帶給自然和生態的始終是無盡的危機,現代性的生活是一種“機械的”生活,經濟理性立場下的生活只能是看似向前實質上不斷重復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是以犧牲自然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和生態危機為代價的。應對如此的危機僅僅依靠現代性批判的力量是不夠的,更需要有建設性的力量在破壞一個舊世界的同時,建設一個新世界。“建設性”的即建構的,后現代主義的標榜則是批判性的,無批判的建構是無力量的,無建構的批判是無目的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之于后現代的思想貢獻正在于此。話說到了這里,或許我們也找到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與哈貝馬斯這一“現代主義”的堅定支持者的共通點——現代性之所以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可能就在于現代性本身需要不斷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與自我建構。在這一點上,“后”現代或許也是“現代”的。
[1]墨菲.政治的回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2]約翰·柯布.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J].求是學刊,2003,(1):27—30.
[3]懷特海.過程與實在:宇宙論研究[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
[4]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5]大衛·格里芬.超越解構[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6]約翰·柯布,大衛·格里芬.過程神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7]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啟蒙[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8]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