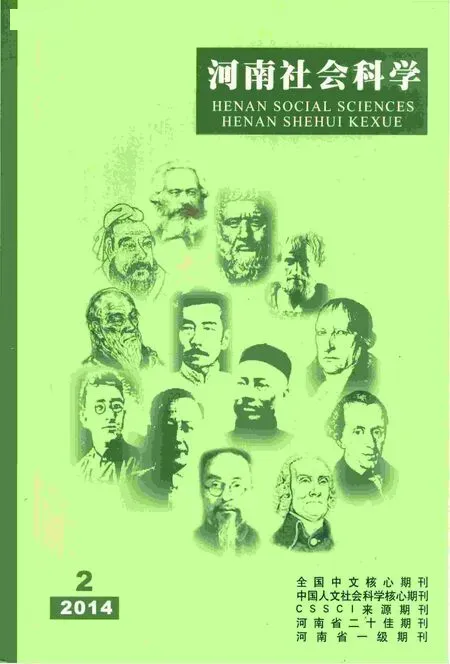論浙江精神及對中原人文精神構建的啟示
李宜馨
(浙江大學,浙江 杭州 310058)
改革開放35年來,“浙江現象”在中國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有著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文化支撐。浙江精神概念的提出以及內涵的闡發,標志著浙江精神的自我激勵從自發的追求走上了理性的自覺,對于河南構建中原人文精神、建設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文明河南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一、浙江精神的提出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浙江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動體現,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來的奮斗發展中孕育出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必將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
浙江精神與浙江人民的歷史生命同行,與浙江人民的現實生活與未來創造相隨,深深融匯在浙江人民的血脈里,體現在浙江人民的行為中,構成了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浙江在改革開放30多年艱難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闖出了一條具有時代特征、中國特色、浙江特點的發展道路,成為了一個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經濟社會發展活力都居于全國前列的省份,成為在全國聞名的“經濟大省”“市場大省”和“民營經濟大省”。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浙江非常重視對浙江精神的提煉和概括。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實現脫貧致富的目標,浙江人形成了以“歷經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為內容的“四千精神”。后來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為推進浙江經濟轉型升級,又提出了以創業創新為核心的“新四千精神”,這就是“千方百計提升品牌、千方百計保持市場、千方百計自主創新、千方百計改善管理”。2000年,浙江精神被概括為“十六字精神”,即“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這十六字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浙江人民精神面貌的生動寫照。然而勇于創新的浙江人民意識到這只是在一定歷史階段體現在浙江人身上的典型特征,必須與時俱進。于是2006年,習近平同志親自將浙江精神界定為“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十二個字。如果說“十六字”精神體現的是浙江人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時期的創業意識,那么“十二字”精神體現的則是浙江人民適應市場經濟轉型而形成的價值導向,標志著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從自發發展到自覺發展的轉變。
我們可以看到,從“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到“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再到以“創業創新”為核心的浙江精神以及“務實、守信、崇學、向善”的當代浙江人共同價值觀,浙江一直十分重視浙江精神的培育和提煉,因為這是進一步解讀浙江現象、總結浙江經驗、開創浙江未來的必然要求,也是進一步拓展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實踐的價值訴求,對培育物質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浙江人意義重大。
二、浙江精神與浙江文化、中原文化的關系
浙江精神與浙江文化緊密相聯。浙江山水秀美,人文薈萃。千百年來,浙江特有的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歷史上的多次人口遷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質。說到浙江精神,就不得不提起習近平同志在總結浙江精神時的那一段動情的描述:“在漫長的歷史實踐中,從大禹的因勢利導、敬業治水,到勾踐的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從錢氏的保境安民、納土歸宋,到胡則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從岳飛、于謙的精忠報國、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張蒼水的剛正不阿、以身殉國;從沈括的博學多識、精研深究,到竺可楨的科學救國、求是一生;無論是陳亮、葉適的經世致用,還是黃宗羲的工商皆本;無論是王充、王陽明的批判、自覺,還是龔自珍、蔡元培的開明、開放;無論是百年老店胡慶余堂的戒欺、誠信,還是寧波、湖州商人的勤勉、善舉等都給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浙江精神得以凝練成了以人為本、注重民生的觀念,求真務實、主體自覺的理性,兼容并蓄、創業創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懷,講義守信、義利并舉的品行,剛健正直、堅貞不屈的氣節和臥薪嘗膽、發憤圖強的志向。”[1]“源遠流長的浙江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浙江文化精神,是浙江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求真務實的精神、誠信和諧的精神、開放圖強的精神在浙江人身上都有著深刻的展現。浙江人追求真理、遵循規律、崇尚科學;他們尊重實際、注重實干、講求實效;他們重規則、守契約、講信用,言必信、行必果;他們具有全球意識、世界胸襟,能夠適應開放的世界全球化競爭的需要,具備積極參與全球化合作和競爭的勇氣和膽略;他們勇于拼搏、奔競不息;他們自豪而不自滿,昂揚而不張揚,務實而不浮躁;他們心憂天下,服務大局,認清目標不動搖,抓住機遇不放松,堅持發展不停步。在浙江人民創造自己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背后,始終躍動著、支撐著、推動著和引領著他(她)們的力量,正是浙江人民的精神。有著這種精神的人,有著這種精神的省份,有著這種精神的民族,其發展動力必然是無與倫比的,其成就也必然是無以替代的。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凡表現,應該說與這種精神的“核動力”有著深切的關系。
浙江精神與中原文化也有著極深的淵源。浙江精神和浙江文化與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具有一脈相承、血脈相連的歷史淵源。大宋南遷,都城由汴州而杭州,其文化血脈相通相連。“暖風熏得游人醉,錯把杭州當汴州”,生動地展現了浙江文化與中原文化具有的傳承關系。可以說,從魏晉南北朝開始,隨著北方移民的南遷,先進的文化和技術推動了浙江地區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政治調整、經濟更新、文化重建等各種要素相互整合,將浙江地區的社會整體發展提升到了全國的最高水平,并在這個基礎上造就了各個領域的精英。到了明、清兩朝,以及民國時期,浙江已經成了全國無可爭議的經濟命脈和文化重鎮。近現代以來,在中原文化發生文化斷層、輝煌不再時,浙江精神、浙江文化因獲得了文化新質而展現出了動人的風采。浙江精神所蘊含的以人為本、創新創業的理念,浙江精神所貫穿的求真務實、與時俱進的原則,浙江精神所具有的誠實守信、開放圖強的品格,對于中原文化建設和中原人文精神的提煉具有重要啟示作用。當然,浙江文化中也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過于重視現實利益、內斂不夠等局限性,與中原文化的“大智若愚”“道法自然”“中庸”“留余”等有著很大的區別,需要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并努力加以超越。儒家經典《大學》里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這一價值系統以“公而忘私”和“以義制利”為終極追求,而浙江文化卻有著逐利的鮮明價值取向,這與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有著極大的一致性,使浙江文化與市場經濟有著深刻的契合性,從長遠來看,從經濟社會發展整體來看,這一行為的短視性需要正視。應當承認,浙江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重功利、講實效的傳統,但是功利主義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進一步提倡科學發展、公平正義和和諧有序。
總之,浙江精神是在浙江文化的土壤上生長起來的,而浙江文化與中原文化有著傳承關系,二者一脈相承。可以說,浙江精神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的因子。但是浙江文化與中原文化卻有著質的區別,在一定意義上,浙江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升級版”。由于不同的地理環境和面對不同的時代和國際背景,浙江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基礎上孕育生成了許多新的特質。這是河南在構建中原人文精神的過程中需要認真考量的。
三、浙江精神對中原人文精神的啟示
我從小生活在中原,對中原文化的厚重有著深刻的體會,于是靈動的浙江文化對我來說充滿了新鮮感與神秘感。我一直認為,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河南人更是具有“平凡之中的偉大,平靜之中的滿腔熱血,平常之中的極強烈責任感”。在浙江,我發現浙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中原文化的很多東西。如若不是兩晉之際的永嘉之亂、唐中期的安史之亂,宋代的“靖康之亂”,導致了政治中心南移,從北宋到南宋,從汴州到杭州,經過大宋南遷,使得“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2],是不會有如今浙江地區的繁華的。雖然遠在數萬年前,浙江大地就已經出現了“建德人”的足跡,河姆渡、良渚文化等更是進一步呈現出了文明的曙光,但是,夏、商、周三代以降,由于生產力水平、人口數量,以及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浙江地區的開發總體上相對落后于北方黃河流域。然而究竟還有什么原因導致了中原文化在大宋南遷之后落后于浙江文化呢?事實上,河南現代文化建設,當代河南人文精神的構建在今天也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我一直在思考,究竟用什么樣的中原人文精神才能引領河南走向未來?到浙江求學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認為,生成于歷史“源頭”的中原人文精神可以到具有現代性特質的浙江精神中去汲取“活水”,從而使中原人文精神推陳出新并煥發出生機活力。為了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為了中國夢的實現,只有讓這“源頭”與“活水”充分結合起來,才能夠不斷滋潤我們的生命,進一步開拓我們的未來。
在我看來,浙江文化與中原文化、浙江精神與中原人文精神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巨大的區別或者質的不同:
(一)地理位置的差異。中原文化是一種內陸文明,和南宋以后風云際會的浙江文化相比較,中原文化就多了一分厚重,少了一分靈動,少了一些創新,少了一個巨大的中西文化沖突的國際化背景。浙江地處沿海,在外國打開中國國門的時候,最先接觸到外來先進事物,使得浙江文化的生成是在中西文化沖突、全球競爭與合作的背景下展開的。晚清以來,在歐風美雨的洗滌之下,浙江兒女中涌現出了頗多學貫中西、獨步一時的大師級人物。
(二)浙江文化、浙江精神的生成與工商文明息息相關。中原文化是在農耕文明的基礎上形成的。重農抑商是我國幾千年來的一項重要國策,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歷代帝王莫不把農業視作治國安邦的根本,與此相反,商業發展則不受重視,有時還受到抑制。河南是糧食大省,有著深厚的農耕文明的背景,而浙江文化、浙江精神集中生動地體現了浙江人民在由傳統農業文明邁向現代工業文明的歷史進程中精神世界所發生的深刻裂變,它的孕育生成既有著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必然性,又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人類精神文明發展演變的走向。浙江人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大膽突破了幾千年被統治者奉為基本國策的重農抑商政策,形成了“講究功利,注重工商”的傳統,形成了浙江人“做大事要敢于冒大險”“贏得起更要輸得起”的冒險精神和商業經營“不拘古法,不唯習慣”的創新精神。先秦時期的陶朱公范蠡是正確處理義、利關系的早期典型代表。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主張“義利雙行”“以利合義”,黃宗羲則堅持“工商皆本”。
(三)浙江文化更加開放,敢為天下先。中原地區,由于處在天子腳下,人們的思想更趨進于保守,很難跳出思想的牢籠,追求新的解放。歷史上的浙江文化就是在不斷吸收吳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大膽吸收異質文化的開放精神成為浙江文化很重要的特色。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浙江知識分子和其他區域的知識分子相比,往往不囿于以往的經驗,不照搬別人的做法,在接受外來文化中也更勇敢、更少顧慮。在明清以來兩次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杭州人李之藻、楊廷筠和海寧人李善蘭都成為吸收和傳播西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龔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喚,直到今天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四)改革開放使浙江人更注重創新和實踐。中原文化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更注重“守成”的力量。就創新實踐而言,浙江精神在體現優秀的歷史傳承的同時,注入了改革開放新的時代內容和時代精神,因而充分顯示了其蓬勃的生機和活力。浙江改革開放的創新實踐,促使浙江精神有了新的飛躍。我們知道,社會歷史是人的自覺活動過程及其結果,人在歷史中具有一定的能動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在浙江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這一真理得到了生動體現。浙江人民具有脫貧致富的創業熱情、勇于探索的創新激情,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壯舉。可以說,浙江精神既淵源于悠久的歷史傳統,又根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五)浙江文化、浙江精神具有“務實”的特點,而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因受北宋理學思想的影響,具有“務虛”的特點。可以說,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體現了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人的精神世界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性,其中內含的現代性價值對于所有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區都具有文化啟示意義。王充的“實事疾妄”、葉適的“崇義養利”、黃宗羲的“經世應務”、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等,都是其“務實”特點的體現。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明確表示“務實而不務虛”“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知府林啟主張“講求實學”。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精神作為引領浙江走向繁榮和富強的重要價值理念,在推進浙江經濟騰飛和社會和諧發展方面顯示出了巨大優勢。浙江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源就在于浙江人有一種獨特的精神理念。
總之,千百年來,浙江特有的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歷史上多次的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具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的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文化特質,兼容并蓄、勵志圖強的生活氣度和崇文厚德、創業創新的精神品格。研究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我們可以看到,當代浙江經濟社會發展與浙江文化、浙江精神是“接茬”的,而河南經濟社會發展與古老的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卻有“斷氣”的一面,從而在一定層面上影響河南發展的“氣象”。中原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剛柔相濟、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特質。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要與時俱進,就應該認真研究借鑒浙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文化基因,抽象傳承,并使之內化為中原文化的特質和中原人文精神的元素。在中原人文精神構建的過程中,如何植入如下文化基因,是河南文化建設需要格外重視的:一是遵循規律、崇尚科學的求真精神。中原人文精神,要崇尚科學,遵循規律,追求真理。二是真抓實干、講求實效的務實精神。浙江人具有穩固的思維模式,以現實為思維的基點,以講求功利為其思維目標,以靈活多變為其思維特征。中原人文精神建設,也要尊重實際、注重實干、講求實效。三是誠實立身、信譽興業的誠信精神。誠信,就是要重規則、守契約、講信用。中原人文精神要適應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著重強化誠信意識,視誠信為現代文明之基,不斷加強現代誠信體系建設,使現代誠信意識深入人心。四是和美與共、和睦有序的和諧精神。中原人文精神要強調在現代競爭的基礎上如何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努力打造自強而不失溫和的文化因子,進一步加強平安河南建設。五是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開放精神。開放,就是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要有全球意識、世界胸襟。要通過航空港經濟區的建設,不斷提高河南的對外開放依存度,進一步樹立開放意識和兼容胸懷,使我們的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和精神素質不斷適應開放的世界和全球化競爭的需要,與時俱進,與世界俱進。六是勵志奮進、奔競不息的圖強精神。圖強,就是勇于拼搏、奔競不息,就是奮發進取、走在前列。中原人文精神要按照“打造河南經濟升級版”的要求,始終保持上進的勢頭,努力做到“先人一步”“高人一招”。只有這樣,中原文化才能贏得新的發展境界,中原經濟區建設才能獲得強大精神動力。當前,認真學習并借鑒浙江精神和浙江文化,對于中原人文精神和中原文化的建設具有巨大意義,對于建設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于河南的文明河南建設也有重要借鑒作用。
[1]習近平.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J].哲學研究,2006,(4):4—9.
[2]陳正祥.中國人文地理[M].北京:三聯書店,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