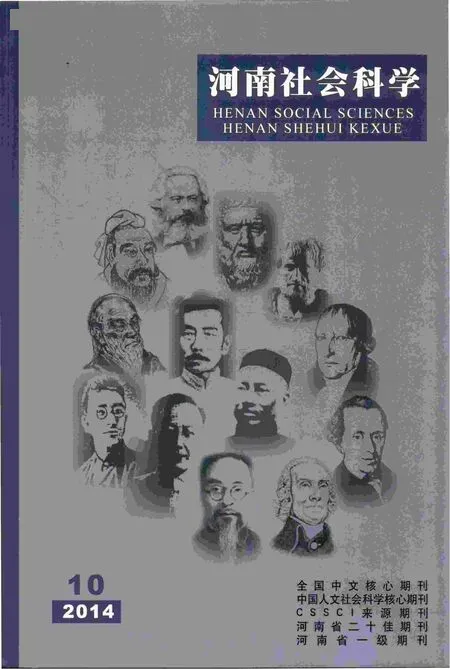論“古史辨”派《詩經(jīng)》研究的得與失
李春青
(北京師范大學(xué),北京 100875)
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是整個(gè)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之所以重要,一則距離我們今日最近,與當(dāng)下文化狀態(tài)聯(lián)系最為密切;二則因?yàn)楝F(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乃是中、西對(duì)話交融的產(chǎn)物,是一種新的熔鑄,而當(dāng)今我們依然處于這樣的文化語境之中,故而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對(duì)于我們可資借鑒之處良多。因此,重新梳理、反思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對(duì)于中國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工作。此前已有一些有識(shí)者做了一些有意義的研究,但亦毋庸諱言,其深度、廣度都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對(duì)于今日中國學(xué)人而言,欲建立具有獨(dú)特性、原創(chuàng)性之學(xué)術(shù),最佳途徑就是總結(jié)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得”與“失”,進(jìn)而在其基礎(chǔ)上“接著說”。
“古史辨”是現(xiàn)代諸多學(xué)術(shù)流派中最具影響力、也最有學(xué)術(shù)方法論意義的一派,其影響不僅在于史學(xué)范圍,而且也及于文學(xué)領(lǐng)域。例如,其《詩經(jīng)》研究的影響至今尚存,尤其是“古史辨”的研究方法對(duì)于我們今日的文學(xué)研究依然具有重要啟發(fā)意義。當(dāng)然,這種方法也有其局限。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就以“古史辨”派的《詩經(jīng)》研究為例,探討一下古代文學(xué)思想的研究方法問題。
一、從歷史角度看文學(xué)
正如有論者早已指出的,在現(xiàn)代,對(duì)《詩經(jīng)》的研究大體分為三派,一是傳統(tǒng)經(jīng)學(xué)的,二是文學(xué)的,三是歷史的。“古史辨”派是一個(gè)歷史研究的學(xué)術(shù)流派,當(dāng)然主要是由歷史學(xué)家組成。對(duì)于《詩經(jīng)》,他們也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的。從歷史的角度或者用史學(xué)的方法研究文學(xué)是一個(gè)十分重要的研究路徑。就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來說,這一研究視角可以說是由“古史辨”派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經(jīng)學(xué)的《詩經(jīng)》學(xué)研究可不置論,此前的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劉師培等人在研究文學(xué)問題時(shí)盡管也時(shí)而會(huì)引進(jìn)歷史的維度,但一以貫之者或者是文字訓(xùn)詁,或者是社會(huì)政治,或者是純文學(xué),都不是歷史。真正從歷史的角度看文學(xué)的乃自“古史辨”始。在以“疑古”為標(biāo)志的“古史辨”派看來,《詩經(jīng)》是少數(shù)可信的先秦典籍之一。這一見解最早由胡適提出,后來為“古史辨”派普遍信從①。然而在他們看來,這樣一部可信程度很高的典籍,在兩千多年的傳承中卻被蒙上了厚厚的塵埃,就像一座被蔓藤層層包裹的古碑,上面的文字都無法看到了。因此尋求“真相”就成了他們研究《詩經(jīng)》的首要任務(wù)。顧頡剛說:
《詩經(jīng)》是一部文學(xué)書……就應(yīng)該用文學(xué)的眼光去考察它……但為二千年來的《詩》學(xué)專家鬧得太不成樣子了,它的真相全給一群人弄糊涂了。
……我做這篇文字,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斬除的工作,把戰(zhàn)國以來對(duì)于《詩經(jīng)》的亂說都肅清了。[1]
這就清楚地說明,他研究《詩經(jīng)》的目的首先是為著“祛蔽”,從而還《詩經(jīng)》以本來面目。至于用文學(xué)的方法研究《詩經(jīng)》,那只能是第二步的事情了。對(duì)于一部古代文學(xué)作品,由于年代久遠(yuǎn),研究者所要做的首先就是盡量弄清楚它究竟是怎樣一部書,是為何而作的,無論是文學(xué)的研究還是歷史的研究,這都是前提,是研究的第一步。
然而如何方能揭示“真相”呢?顧頡剛認(rèn)為,“我們要看出《詩經(jīng)》的真相,最應(yīng)研究的就是周代人對(duì)‘詩’的態(tài)度”[2]。根據(jù)對(duì)《左傳》《國語》等先秦史料的分析,顧先生逐層揭示了周代人“作詩的緣故”與“用詩的方法”。就作詩而言,認(rèn)為《詩經(jīng)》作品“大別有兩種:一種是平民唱出來的,一種是貴族做出來的”。就用詩來說,則“大概可以分為四種用法:一是典禮,二是諷諫,三是賦詩,四是言語”[2]。顧先生從歷史的角度考察《詩經(jīng)》作品的產(chǎn)生,以“詩何為而作”為切入點(diǎn),這應(yīng)該是恰當(dāng)?shù)淖穯柭窂剑驗(yàn)橹挥信宄姼璧纳鐣?huì)功用才能進(jìn)而揭示其作者。根據(jù)現(xiàn)存《詩經(jīng)》作品的情況以及先秦典籍關(guān)于詩歌功能的記載,筆者認(rèn)為,顧先生認(rèn)為《詩經(jīng)》中的作品“一種是平民唱出來的,一種是貴族做出來的”的觀點(diǎn)是具有合理性的。所謂“唱出來”是說這類詩歌是自然而然產(chǎn)生的,即所謂“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后來才被王室派出的采風(fēng)官吏采集上來的;所謂“做出來”是說這類詩歌是貴族們?yōu)橹撤N禮儀或諷諫的需要,專門寫出來主動(dòng)獻(xiàn)上去的。根據(jù)現(xiàn)在學(xué)界的研究成果,說《詩經(jīng)》作品一部分是從民間采集而來,一部分是貴族們專門制作的大體是沒有問題的。只不過民間那些作詩的人是“平民”還是貴族階層,依然是聚訟紛紜的問題。
關(guān)于《詩經(jīng)》的四種用法的見解,根據(jù)現(xiàn)有材料來看,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只不過這四種用法不一定都是共時(shí)性存在的。從歷史的角度看,詩歌功能的演變軌跡似乎應(yīng)該是這樣的:對(duì)于周代貴族來說,典禮或許是詩歌最早的用法,特別是在祭天祭祖的儀式中,詩歌就成為溝通人與神的特殊言說方式。《詩經(jīng)》中那些“頌詩”大抵正是此類,這類詩歌也是《詩經(jīng)》中最早出現(xiàn)的。開始時(shí)詩歌很可能僅僅用于祭祀儀式之中,久而久之也就推衍于朝會(huì)、宴飲及婚喪嫁娶等禮儀之中了。這類作品大約都是“定做的出來的”[2],屬于貴族創(chuàng)作。諷諫應(yīng)該是從典禮中引申出來的一種詩歌功能。因?yàn)樵诘涠Y中的詩歌具有某種神圣色彩,用之于臣子向君主或下級(jí)貴族向上級(jí)貴族的諷諫也就具有了一種莊重的性質(zhì),較之一般的口頭表達(dá)也更具有說服力。由于詩歌在貴族生活中越來越具有重要性,于是在貴族教育中“詩教”就成為重要內(nèi)容,隨之也就出現(xiàn)了比較固定的詩歌集本,都是從各種禮樂儀式中提取出來的,通過修習(xí),受過教育的貴族子弟人人可以隨口吟唱這些詩歌作品。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出現(xiàn)了賦詩與言語現(xiàn)象——在聘問、宴飲、交接等貴族交往場(chǎng)合借助于詩歌來表達(dá)某種不便或不愿直白說出的意思。這類作品則有可能是貴族們主動(dòng)做出來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從民間采集來的。根據(jù)我們現(xiàn)在可以看到的材料以及現(xiàn)代學(xué)者們的研究成果,這一由祭祀到廟堂,再由廟堂到貴族日常交往的《詩經(jīng)》功能演變的歷史軌跡應(yīng)該是可以成立的。當(dāng)然這一歷史軌跡也許還很粗疏,例如何定生先生關(guān)于十三國風(fēng)與“房中之樂”、“無算樂”的關(guān)系的看法也許是重要補(bǔ)充[3]。但總體言之,顧頡剛關(guān)于先秦詩歌四種基本功能的勾勒是具有重要學(xué)術(shù)意義的,可以說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文學(xué)的重要收獲。
錢穆亦嘗運(yùn)用歷史的眼光考察《詩經(jīng)》,可以說是與“古史辨”派同一路徑。在著名的《讀詩經(jīng)》一文中,錢先生亦從追問詩之功用展開自己的研究。他認(rèn)為:“蓋《詩》既為王官所掌,為當(dāng)時(shí)治天下之具,則《詩》必有用,義居可見。《頌》者,用之宗廟,《雅》則用之朝廷。《二南》則鄉(xiāng)人用之為‘鄉(xiāng)樂’,后夫人用之,謂之‘房中之樂’,王之燕居用之,謂之‘燕樂。’”[4]與顧頡剛的見解相吻合。基于這一歷史觀察,錢穆認(rèn)為《詩經(jīng)》原來的排列順序應(yīng)該與今本相反:
惟今《詩》之編制,先《風(fēng)》,次《小雅》,次《大雅》,又次乃及《頌》,則應(yīng)屬后起。若以《詩》之制作言,其次第正當(dāng)與今之編制相反;當(dāng)先《頌》,次《大雅》,又次《小雅》,最后乃及《風(fēng)》,始有當(dāng)于《詩三百》逐次創(chuàng)作之順序。[4]
這是很高明的見解,唯有從歷史的角度方可得之。蓋詩歌作為一種歷史現(xiàn)象,自有其產(chǎn)生與演變的客觀軌跡,從歷史角度考察,緊緊扣住詩歌功能問題,自然會(huì)對(duì)其產(chǎn)生演變軌跡有所揭示。顧頡剛和錢穆都是這樣做的,也都有獨(dú)到發(fā)現(xiàn)。抓住了典禮、諷諫、賦詩、言語這四個(gè)環(huán)節(jié),《詩經(jīng)》作品在西周至春秋時(shí)期的實(shí)際功用就被揭示出來了,進(jìn)而詩歌在彼時(shí)政治生活、社會(hu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就清楚了。那種跳出歷史語境,僅僅就文本而談詩歌意義的做法也許有其價(jià)值在,但不可視為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只能算是個(gè)人化的欣賞。
“古史辨”派的《詩經(jīng)》研究是一種“歷史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真相。但是這種研究與史學(xué)界備受推崇的“以詩證史”是根本不同的。所謂“以詩證史”就是把詩歌作為研究歷史的材料,從詩中發(fā)現(xiàn)可以說明歷史問題的內(nèi)容。而“古史辨”派從歷史的角度研究《詩經(jīng)》則是把這部現(xiàn)代以來被視為文學(xué)作品集的典籍作為歷史現(xiàn)象來審視,看它在怎樣的歷史語境中產(chǎn)生,應(yīng)和著怎樣的歷史需求,發(fā)揮著怎樣的社會(huì)歷史功能等。前者是純粹的歷史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幾乎不相干;后者則是對(duì)文學(xué)的歷史研究,是屬于文學(xué)研究的一種視角和路徑。這一研究視角和路徑與美國的新歷史主義有諸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從歷史的角度研究文學(xué),都是把研究對(duì)象置于復(fù)雜的社會(huì)歷史語境中進(jìn)行綜合性考察,都突破了那種狹隘的審美詩學(xué)或文本詩學(xué)的研究框架。對(duì)于《詩經(jīng)》研究來說,“古史辨”這種歷史的研究視角和路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唯一正確的。因?yàn)椤对娊?jīng)》作品,從其創(chuàng)作、搜集、整理、運(yùn)用、傳播等整個(gè)過程來看,都與周代貴族的意識(shí)形態(tài)建設(shè)密切相關(guān)。詩歌始終是周代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禮樂文化正是浸透了周代貴族等級(jí)制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文化符號(hào)系統(tǒng)。對(duì)于這樣一部曾經(jīng)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shí)形態(tài)之重要組成部分的詩歌總集,如果僅僅從審美的或者文本的角度進(jìn)行研究,那肯定是有問題的。只有把它放回到特定歷史語境中予以審視,我們才有可能對(duì)它進(jìn)行恰當(dāng)?shù)年U釋。
二、對(duì)漢代《詩經(jīng)》闡釋的否定與質(zhì)疑
“古史辨”派是以“疑古”名噪學(xué)界的,他們對(duì)于記載著上古史的那些典籍,特別是對(duì)典籍的傳注大都持懷疑態(tài)度。其中最受他們?cè)嵅∨c嘲笑的就是那部漢儒的《毛詩序》。如鄭振鐸說:
我們要研究《詩經(jīng)》,便非先把這一切壓蓋在《詩經(jīng)》上面的重重疊疊的注疏的瓦礫扒掃開來而另起爐灶不可。
在這重重疊疊的壓蓋在《詩經(jīng)》上面的注疏的瓦礫里,《毛詩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難掃除,而又必須最先掃除的瓦礫。[5]
顧頡剛則以戲謔的口吻嘲笑《毛詩序》的比附史實(shí):
海上(海上生明月),楊妃思祿山也。祿山辭歸范陽,楊妃念之而作是詩也。
吾愛(吾愛孟夫子),時(shí)人美孟軻也。梁襄王不似人君,孟子不肯仕于其朝,棄軒冕如敝屣也。[6]
從這些引文中不難看出,在顧先生眼中,《毛詩序》的作者和那些注釋過《詩經(jīng)》的漢儒是何等愚蠢可笑!于是如何看待漢儒的《詩經(jīng)》闡釋就成為現(xiàn)代學(xué)者提出的一個(gè)重大的學(xué)術(shù)問題。總體言之,在“古史辨”派的強(qiáng)勢(shì)影響之下,現(xiàn)代學(xué)者幾乎沒有敢于為漢儒辯護(hù)的,因?yàn)閺默F(xiàn)代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出發(fā),漢儒對(duì)《詩經(jīng)》的解讀確實(shí)令人難以接受。“古史辨”派對(duì)漢代《詩經(jīng)》學(xué)的否定與質(zhì)疑主要基于三種思想資源,現(xiàn)簡述如下:
第一種思想資源是現(xiàn)代文學(xué)觀念,即認(rèn)為文學(xué)是表情達(dá)意的,《詩經(jīng)》作品,特別是《國風(fēng)》,主要是民歌,根本不可能負(fù)載那么多的政治含義。例如錢玄同說:
《詩經(jīng)》只是一部最古的“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樂府》等書性質(zhì)全同,與什么《圣經(jīng)》是風(fēng)馬牛不相及的。
研究《詩經(jīng)》只應(yīng)該從文章上去體會(huì)出某詩是講什么。至于那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話頭,即使讓一百步說,作詩者確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訴咱們,咱們也只好闕而不講——況且這些言外之意和藝術(shù)底本身無關(guān),盡可不去理會(huì)它。[7]
顯然錢先生是把《詩經(jīng)》當(dāng)作一部純文學(xué)的作品集來看待了。毫無疑問,作為一般閱讀欣賞,《詩經(jīng)》,特別是《國風(fēng)》和大部分《小雅》的詩歌完全是可以當(dāng)作純文學(xué)作品來看待的,從字里行間,從其意象與意境中,我們確實(shí)可以體會(huì)到審美的愉悅。但是作為研究就不同了,對(duì)于《詩經(jīng)》作品為何而作、如何傳承、在彼時(shí)歷史語境中有何功能以及如何發(fā)揮其功能等問題就不能不予追問。如果脫離了具體歷史語境,拋棄知人論世的說詩原則,僅就詩歌文本來談?wù)撈湟饬x,就只能是主觀臆說,算不得真正意義的學(xué)術(shù)研究了。清儒皮錫瑞嘗言:
后世說經(jīng)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cè)古圣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jīng)皆有然,而《詩》為尤甚。……后儒不知詩人作詩之意、圣人編詩之旨,每以后世委巷之見,推測(cè)古事,妄議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實(shí)非者,誤信所不當(dāng)信;不近人情而實(shí)是者,誤疑所不當(dāng)疑。[8]
這雖然是對(duì)經(jīng)學(xué)傳統(tǒng)的批評(píng),但何嘗不是對(duì)現(xiàn)代《詩經(jīng)》研究的警示呢?從今天的眼光看上去應(yīng)該如此,或許在古代剛好相反,反之亦然。要對(duì)《詩經(jīng)》這樣的“歷史流傳物”有恰當(dāng)?shù)年U釋,就必須盡可能地重建其產(chǎn)生、傳承及使用時(shí)的歷史語境。顧頡剛關(guān)于《詩經(jīng)》在春秋戰(zhàn)國間的社會(huì)功能的論述正是一種歷史化、語境化的研究,符合歷史的實(shí)際,可惜的是,當(dāng)他把目光轉(zhuǎn)向漢儒的說詩時(shí),就不大顧及他們何以如此說詩的文化歷史原因了,他是從詩的字面意思出發(fā)對(duì)《毛詩序》的解讀予以否定的。如此把《詩經(jīng)》作品看成是純粹的文學(xué)作品,完全不顧及其產(chǎn)生與使用時(shí)的歷史語境的研究方法,就難免有“我注六經(jīng)”與“妄議古人”的偏頗了。現(xiàn)代學(xué)者受到西方18世紀(jì)以來形成的文學(xué)觀念的影響,對(duì)中國古代詩文傾向于作純粹審美意義上的理解,這對(duì)于魏晉之后的詩文來說似乎問題不大,但對(duì)于漢代以前來說就不那么恰當(dāng)了。
“古史辨”派所依據(jù)的第二種思想資源是宋代以來逐漸形成的“疑古辨?zhèn)巍本瘛>驮娊?jīng)學(xué)而言,宋儒歐陽修的《詩本義》、鄭樵的《詩辨妄》、朱熹的《詩集傳》都對(duì)《毛詩序》提出質(zhì)疑。到了清儒疑古大家崔述的《讀風(fēng)偶識(shí)》對(duì)《詩序》的批評(píng)更是空前的精辟而尖銳。上述諸家都是“古史辨”派否定《詩序》的有力支撐。顧頡剛嘗輯錄久已散佚的鄭樵《詩辨妄》,編訂崔述的《崔東壁遺書》,在重建疑古辨?zhèn)蝹鹘y(tǒng)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此外,清初大學(xué)問家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清季今文家康有為的《新學(xué)偽經(jīng)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乾嘉學(xué)派在對(duì)古籍的校勘、辨?zhèn)巍⒖加喼酗@示出的求真與懷疑精神也都對(duì)“古史辨”派形成了重要影響。從這個(gè)意義上看,可以說“古史辨”派是對(duì)中國古代疑古辨?zhèn)蝹鹘y(tǒng)“接著說”的。
對(duì)“古史辨”派以重大影響的第三種思想資源是來自西方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科學(xué)主義傾向。我們知道,“古史辨”這一學(xué)術(shù)流派的形成得益于胡適的影響,而胡適正是西方科學(xué)主義精神的中國傳人。早在1919年胡適就提出“整理國故”的著名主張,提出要用科學(xué)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他的著名的“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的所謂“十字訣”也是作為科學(xué)的方法提出的。1925年在一次演講中他說:“我覺得用新的科學(xué)的方法研究古代的東西,確能得著很有趣味的效果。一字的古音,一字的古義,都應(yīng)該拿正當(dāng)?shù)姆椒ㄈパ芯康摹!盵9]具體到對(duì)《詩經(jīng)》的解讀,胡適的所謂“科學(xué)的方法”就是拋棄一切前人的傳注,專門涵泳于詩歌文本之中,體察其含義。在此過程中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對(duì)“文法”與“虛字”的關(guān)注。他對(duì)《詩經(jīng)》中“言”字的用法的考辨就是這一方法的具體實(shí)踐。胡適的科學(xué)方法固然受到乾嘉學(xué)派的影響,但究其實(shí)質(zhì)還是來自西方的科學(xué)主義傳統(tǒng),他說:
我治中國思想和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zhuǎn)的。“方法”實(shí)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diǎn)實(shí)在得益于杜威的影響……杜威對(duì)有系統(tǒng)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duì)一般科學(xué)研究的基本步驟的了解。他也幫助了我對(duì)我國近千年來——尤其是近三百年來——古典學(xué)術(shù)和史學(xué)家治學(xué)的方法,諸如“考據(jù)學(xué)”、“考證學(xué)”等等的了解……在那個(gè)時(shí)候,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人)曾想到現(xiàn)代的科學(xué)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jù)學(xué)、考證學(xué),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我是第一個(gè)說這話的人;我之所以能說出這話來,實(shí)得之于杜威有關(guān)思想的理論。[10]
顧頡剛是胡適的弟子,對(duì)老師所倡導(dǎo)的“科學(xué)方法”極為信服,他那堪稱“古史辨”派標(biāo)志性主張的“層累地造成古史說”正是在胡適所倡導(dǎo)的這種科學(xué)方法的影響下形成的。應(yīng)該說,科學(xué)的實(shí)證精神是“古史辨”派的基本旨趣。
另外,“五四”前后形成的“反傳統(tǒng)”思潮也為“古史辨”派的“疑古”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空間。
基于上述這三種思想資源而形成的“古史辨”派的《詩經(jīng)》闡釋學(xué)當(dāng)然無法忍受以《毛詩序》為代表的漢儒《詩經(jīng)》闡釋學(xué)方法與結(jié)論,于是就出現(xiàn)了如前面引文那樣對(duì)漢儒激烈的批判與嘲諷。然而以追問真相為職志的“古史辨”派也許沒有追問過下列問題:《詩經(jīng)》真的僅僅是一部《文選》那樣的文學(xué)總集嗎?果真如此,那么春秋時(shí)的貴族們何以都是在政治、外交場(chǎng)合引詩、賦詩,從來沒有在欣賞的意義上用詩呢?《詩經(jīng)》或稱《詩三百》真的是被漢儒推崇為經(jīng)典的嗎?在西周至春秋的數(shù)百年中“詩”在貴族文化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詩歌作為禮樂文化系統(tǒng)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是不是具有某種權(quán)威性,甚至神圣性的特殊價(jià)值與功能?包括《毛詩序》在內(nèi)的漢儒說詩是憑空產(chǎn)生的嗎?漢儒是不是繼承了某種歷史久遠(yuǎn)的說詩傳統(tǒng)?這都是應(yīng)該追問的問題。如果弄清了這些問題的“真相”,“古史辨”派或許對(duì)漢儒的說詩就不那么輕蔑了。
三、“古史辨”派《詩經(jīng)》研究方法之反思
“古史辨”派是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少有的具有重大影響的學(xué)術(shù)流派之一,其學(xué)術(shù)影響至今依然存在。那么,我們應(yīng)該如何看待他們的學(xué)術(shù)成就呢?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其啟示意義何在呢?以下幾點(diǎn)淺見,請(qǐng)有識(shí)者指正。
其一,如何看待“古史辨”派的“疑古”。“疑古”是“古史辨”派開宗立派的旗幟,也是其《詩經(jīng)》研究的基本精神。在筆者看來,他們的懷疑精神應(yīng)該充分肯定。毫無疑問,近幾十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確實(shí)證明了許多古代典籍的可靠性,古史的記載也大都有其依據(jù),因此,學(xué)界提出“走出疑古時(shí)代”之說是有其合理性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古史辨”派的懷疑精神就毫無價(jià)值了。懷疑是一切學(xué)術(shù)研究的起點(diǎn),沒有懷疑就沒有問題,而有意義的問題正是學(xué)術(shù)研究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對(duì)于汗牛充棟的古代典籍,研究者務(wù)必抱著質(zhì)疑、審視的眼光,鑒別其真?zhèn)危狡浔尽⑺萜湓矗崂砥涿}絡(luò),考察其流變。對(duì)于前人的成說更不能輕率接受,而是要分析其產(chǎn)生之原因,弄清楚決定其不得不如此說的邏輯鏈條,如此才能推進(jìn)學(xué)術(shù)的進(jìn)步。具體到《詩經(jīng)》研究,“古史辨”派對(duì)于《詩序》的質(zhì)疑大都是站得住的,特別是《詩序》對(duì)某詩“刺某王”“美某公”的解說,確實(shí)大多乃附會(huì)史事,缺乏切實(shí)的材料支撐,顧頡剛、錢玄同、鄭振鐸等人的批評(píng)是有力的。
但是“古史辨”派的“疑古”也確實(shí)存在嚴(yán)重問題。首先,盡管他們大多是歷史學(xué)家,但在對(duì)《詩序》的質(zhì)疑時(shí)往往不能用歷史的、語境化的眼光來看問題,對(duì)漢儒缺乏“了解之同情”,只是站在今天的立場(chǎng)上褒貶古人。漢儒說詩實(shí)際上乃是彼時(shí)士人階層意識(shí)形態(tài)建構(gòu)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大一統(tǒng)”政治格局中知識(shí)階層制衡君權(quán)的一種手段。他們說詩的目的其實(shí)并不是追問“真相”,更不是發(fā)掘詩歌的審美意義,而是在建構(gòu)和弘揚(yáng)一種價(jià)值觀,是一種特殊的“立法”——為社會(huì)提供價(jià)值秩序——行為。其實(shí)不獨(dú)《詩經(jīng)》以及整個(gè)漢代經(jīng)學(xué)研究是如此,看漢初的黃老之學(xué)、陸賈著《新語》、賈誼著《新書》、賈山著《至言》、淮南王編《淮南鴻烈》乃至司馬遷作《史記》都莫不如此。可以說,意識(shí)形態(tài)建設(shè)是漢儒問學(xué)致思的首要目的,是他們與由帝王、宗室、功臣、外戚、宦官等組成的統(tǒng)治集團(tuán)爭(zhēng)奪權(quán)力的主要方式。后來儒學(xué)的勝利即可視為統(tǒng)治集團(tuán)與知識(shí)階層相互“協(xié)商”與“共謀”的結(jié)果,也是他們合作治理天下的標(biāo)志。“古史辨”派從追問“真相”的科學(xué)實(shí)證角度固然可以發(fā)現(xiàn)漢儒的諸多錯(cuò)誤,卻對(duì)其“苦心孤詣”則毫無體察了。這顯然不僅僅是“疑古太過”的問題,而且也是“以今釋古”的問題,關(guān)鍵之點(diǎn)在于對(duì)歷史語境的重要性關(guān)注不夠。我們今天反思“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就應(yīng)該既要尊重并繼承其懷疑的、批判的精神,又要運(yùn)用“語境化”的研究方法,把研究對(duì)象之所以如此這般的原因梳理清楚,揭示其在歷史上曾經(jīng)具有的意義與價(jià)值。如此面對(duì)古人方庶幾近于公允。輕率的嘲笑與否定不是我們面對(duì)古代學(xué)人的恰當(dāng)態(tài)度。
其二,如何看待“古史辨”派的方法與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路向的異同問題。當(dāng)年閱讀七大冊(cè)《古史辨》,特別是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cè)上的長篇自序,頗有一種感覺,似乎顧先生倡導(dǎo)的方法與半個(gè)多世紀(jì)之后福柯的“知識(shí)考古學(xué)”以及格林布拉特、海登·懷特所代表的“新歷史主義”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葛兆光則認(rèn)為“古史辨”應(yīng)該屬于“現(xiàn)代性史學(xué)”,并指出其與后現(xiàn)代史學(xué)的差異:
第一,“古史辨”派畢竟相信歷史有一個(gè)本身的存在,他們的看法是,歷史學(xué)的目的是要?jiǎng)冮_層層包裝的偽史而呈現(xiàn)真實(shí)的歷史。可是后現(xiàn)代史學(xué)是“無心”的,是“空心”的,認(rèn)為所用的歷史都不過是層層的包裝……
第二,正是因?yàn)橐陨系牟顒e,“古史辨”派的中心目標(biāo)是“辨?zhèn)巍保瑒兊舻臇|西是隨口編造的廢棄物,它們與本真的歷史構(gòu)成了反悖,所以要尋找本真的東西,其他的可以甩掉不要。后現(xiàn)代好像對(duì)“垃圾”特別感興趣,特別關(guān)注那些層層作偽的東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這一層層的包裝過程……
第三,“古史辨”派的歷史學(xué)方法基本上是針對(duì)“過去”的存在,“過去”是很重要的。他們?cè)诋?dāng)時(shí)確實(shí)瓦解了傳統(tǒng)史學(xué),而且與當(dāng)時(shí)反傳統(tǒng)的激進(jìn)主義吻合與呼應(yīng)……我覺得它仍然是在“六經(jīng)皆史”的延長線上……可是,后現(xiàn)代則直接從“六經(jīng)皆史”走到了“史皆文也”,這是很不同的。[11]
這里的比較大體上是言之成理的。略可辨析與補(bǔ)充的有下列幾點(diǎn):一是關(guān)于“古史辨”派“相信歷史有一個(gè)本身的存在”的問題。我們知道,“古史辨”派的基本觀點(diǎn)是對(duì)中國上古史提出顛覆性質(zhì)疑,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古史說”。按照他們的觀點(diǎn),中國傳統(tǒng)史學(xué)建立起來的從“三皇”到堯、舜、禹的上古史都是后代史家一代一代想象編造出來的,因此才會(huì)出現(xiàn)越是后面的人反而對(duì)古史知道得越久遠(yuǎn)越詳細(xì)的怪現(xiàn)象,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如此看來,在“古史辨”派心目中其實(shí)根本就不存在一個(gè)可以復(fù)原的上古史,這一點(diǎn)和后現(xiàn)代史學(xué)是很相近的。如果把“歷史”理解為“發(fā)生過的事情”,則無論是“古史辨”派還是后現(xiàn)代史學(xué)都是絕對(duì)不會(huì)否認(rèn)的。他們的共同點(diǎn)在于:我們見到的歷史都是人寫出來的,不是“發(fā)生過的事情”的本來面貌。他們的區(qū)別是:后現(xiàn)代史學(xué)不相信任何歷史文本可以接近“發(fā)生過的事情”的本來面貌,因?yàn)闅v史敘事在本質(zhì)上也就是一種文學(xué)敘事。“古史辨”派則認(rèn)為我們之所以不能恢復(fù)上古史的真相乃在于文獻(xiàn)不足,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可靠的文獻(xiàn)。這就意味著,“古史辨”派也已經(jīng)意識(shí)到我們可以看到的歷史其實(shí)都是人寫出來的,都是文本而已。至少對(duì)于中國的傳統(tǒng)史學(xué)來說,他們是這樣認(rèn)為的。就這一點(diǎn)而言,“古史辨”派確實(shí)很接近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xué)了。二是“古史辨”派只管“剝?nèi)グb”,而后現(xiàn)代史學(xué)專門對(duì)這一層一層的“包裝”感興趣的問題。事實(shí)確實(shí)如此。這是“古史辨”派與西方后現(xiàn)代史學(xué)的根本性差異。“古史辨”派立意在質(zhì)疑,在推翻舊說,至于“真相”究竟如何,他們也知道是無法探究的,所以他們追問的“真相”其實(shí)就是指出古史是造出來的、不可信。魯迅批評(píng)顧頡剛有破壞而無建設(shè),將古史“辨”沒有了。應(yīng)該說是很準(zhǔn)確的評(píng)判。在福柯的知識(shí)考古學(xué)影響下的后現(xiàn)代史學(xué)(海登·懷特)則不然,他們知道包括歷史在內(nèi)的任何知識(shí)系統(tǒng)都是人為地建構(gòu)起來的,所以在他們看來恰恰是這“一層層”的“包裝”才有追問價(jià)值,對(duì)他們來說,研究這些“包裝”是如何產(chǎn)生的,其背后蘊(yùn)含著怎樣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等,正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主要任務(wù)。在這一點(diǎn)上,“古史辨”派是遠(yuǎn)遠(yuǎn)不及的。在后者看來,漢儒說詩是胡說八道,急于棄之而后快,哪里管他們?yōu)槭裁慈绱苏f,其背后隱含的文化邏輯與意識(shí)形態(tài)是什么呢?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古史辨”派確實(shí)沒有達(dá)到后現(xiàn)代史學(xué)的深度。三是關(guān)于“六經(jīng)皆史”與“史皆文也”的問題。誠然,在“古史辨”派眼中,六經(jīng)都是作為史料來看待的,其中最為可信的大約要算是《詩經(jīng)》了。但章學(xué)誠等人的“六經(jīng)皆史”之謂似并非從這個(gè)意義上說的。章氏的意思主要并不是說六經(jīng)都可以作為史料來運(yùn)用,而是說它們?cè)静贿^是對(duì)于古代政事的記載,并不像后世儒家理解的那樣是什么圣人垂訓(xùn)的經(jīng)典,沒有那么神圣。而在“古史辨”派看來,六經(jīng)不僅談不到神圣,而且其作為史的記錄也大都是不可信的,是質(zhì)疑的對(duì)象。因此說“古史辨”派是對(duì)“六經(jīng)皆史”說的繼承并不準(zhǔn)確。另外,即使“古史辨”派信從章學(xué)誠等人的“六經(jīng)皆史”之說,這也不是其與主張“史皆文也”的后現(xiàn)代史學(xué)相區(qū)別的關(guān)鍵所在。也就是說,承認(rèn)“六經(jīng)皆史”與主張“史皆文也”并不矛盾,二者是可以并存的。事實(shí)上在“古史辨”派那里,我們可以看到到處都流露著“史皆文也”的觀點(diǎn)。讓我們看看顧頡剛所擬的論文題目:
春秋、戰(zhàn)國間的人才(如圣賢、游俠、說客、儒生等)和因了這班人才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戰(zhàn)國、秦、漢間的中心問題(如王霸、帝王、五行、德化等)和因了這種中心問題而生出來的古史。
春秋、戰(zhàn)國、秦、漢間的制度(如尊號(hào)、官名、正朔、服色、宗法、階級(jí)等)和因了這種制度而生出來的古史。[12]
從顧先生擬出的這些題目中可以看出,他是要從言說主體、文化問題、政治制度三個(gè)層面對(duì)“古史”被建構(gòu)起來的具體過程與原因進(jìn)行深入解剖,這是很了不起的史學(xué)意識(shí)。較之福柯的“知識(shí)考古學(xué)”、海登·懷特的“新歷史主義”在思考的深度上毫不遜色。故而對(duì)于顧頡剛的史學(xué)觀,我們至少可以說他堅(jiān)持的是“古史皆文也”。
根據(jù)上述分析我們可以說,“古史辨”派固然不能算是“后現(xiàn)代史學(xué)”,但他們的許多見解已然超出了以揭示歷史真相為職志的傳統(tǒng)史學(xué),與福柯的知識(shí)考古學(xué)、海登·懷特的“新歷史主義”有著諸多相近的歷史洞見。
其三,在現(xiàn)代中國歷史語境中如何建構(gòu)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問題。“古史辨”派在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即使今天學(xué)界已經(jīng)宣布“走出疑古時(shí)代”,而且考古發(fā)現(xiàn)也不斷證明著“古史辨”派“疑古”的偏頗,但是我們依然要說,這個(gè)學(xué)派對(duì)于現(xiàn)代以來的中國學(xué)術(shù),特別是今日中國學(xué)術(shù)的啟示意義是巨大的,而且這種意義遠(yuǎn)沒有被充分認(rèn)識(shí)到。對(duì)此,我們可以從三個(gè)方面來看:
首先,當(dāng)下的中國人如何做學(xué)問?今天的中國人有資格做學(xué)問嗎?不管承認(rèn)不承認(rèn),今日中國學(xué)人是存在著這種惶惑的。相當(dāng)一批學(xué)者一談起中國的學(xué)術(shù)文化,都是不屑一顧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西方才有學(xué)術(shù),中國從古到今根本就談不上真正的、現(xiàn)代意義的學(xué)術(shù)研究。有相當(dāng)一批做中國學(xué)問的人在西學(xué)面前感到自卑,無地自容,感覺一張嘴就說的是別人的話,一句自己的話說不出,于是只好“反對(duì)闡釋”,躲到考證學(xué)、考據(jù)學(xué)中去保持自身的純潔與獨(dú)立。這樣一來,真正有價(jià)值的中國學(xué)術(shù)在今天就很難建立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古史辨”派就顯得極為可敬了。其最可敬者,他們的研究方法不是簡單照搬別人而來,更不是憑空想象出來,而是針對(duì)中國歷史存在的問題而總結(jié)、提升、建構(gòu)起來的。因此以“層累地造成古史說”為標(biāo)志的“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是中國式的,是適合著中國的研究對(duì)象而生成的,因而是有強(qiáng)大生命力的。其再可敬者,他們并不諱言對(duì)古人和外國人的吸納與借鑒。但也絕對(duì)不唯前人或西方學(xué)術(shù)的馬首是瞻,真正做到了廣采博取與獨(dú)出機(jī)杼相結(jié)合,造就了自己獨(dú)特的、又具有前沿性的學(xué)術(shù)研究思路。
其次,在“信古”與“疑古”之間。做中國的學(xué)問,面對(duì)的是汗牛充棟、卷帙浩繁的古籍,今日的學(xué)人應(yīng)該采取怎樣的立場(chǎng)?“古史辨”派的“疑古”精神是極為可貴的,因?yàn)橐磺袑W(xué)問都是從懷疑開始的,沒有懷疑就不會(huì)有問題,沒有問題也就不會(huì)產(chǎn)生有價(jià)值的學(xué)術(shù)研究。因此對(duì)于“古史辨”派的懷疑精神是應(yīng)該充分肯定的。“古史辨”派的問題在于:他們似乎先設(shè)定了古史的虛假,然后想方設(shè)法找材料證明其虛假。這就有問題了,如此便不能客觀地審視研究對(duì)象,特別是不能體察古人何以如此說的原因。即如《詩經(jīng)》研究而言,顧頡剛、錢玄同等人對(duì)漢儒的說詩采取了簡單否定的態(tài)度,對(duì)于他們說詩傳統(tǒng)的形成過程及其原因不予深究,這就遮蔽了許多值得追問的學(xué)術(shù)問題。他們未能意識(shí)到,在人文領(lǐng)域中的學(xué)術(shù)問題常常是不能簡單地用“對(duì)”和“錯(cuò)”來判定的,這種判定是缺乏學(xué)術(shù)意義與思想蘊(yùn)含的。真正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不僅要追問“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追問“為什么”。漢儒說詩傳統(tǒng)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gè)極具學(xué)術(shù)史、思想史意義的話題,用幾句簡單的話否定甚至嘲笑來了結(jié)這一話題是太可惜了。因此,無論“信古”還是“疑古”都不能作為學(xué)術(shù)研究的前提,只有根據(jù)研究對(duì)象的自身特點(diǎn),通過重建歷史語境的方式,揭示其背后隱含的文化邏輯,揭示之所以如此這般的文化歷史原因,這樣的研究才是令人信服的。
再次,今日學(xué)人對(duì)包括“古史辨”派在內(nèi)的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應(yīng)該予以高度重視與深刻反思。我們一提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會(huì)想到從先秦到明清,近年開始重視近代。其實(shí)對(duì)于我們今天的學(xué)術(shù)研究來說,現(xiàn)代傳統(tǒng)具有更重要的借鑒意義。這是因?yàn)閺那迥┟癯醯叫轮袊闪⒌慕雮€(gè)世紀(jì),是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時(shí)期,是確立今日中國學(xué)術(shù)文化之根基的時(shí)期。即如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學(xué)術(shù)語言也是現(xiàn)代學(xué)人融合了古代漢語、日常白話、從西方或通過日本引進(jìn)的新學(xué)語幾個(gè)部分而成的。因此,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既不是中國古代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一大批現(xiàn)代學(xué)人建構(gòu)起來的新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與我們今日學(xué)術(shù)話語可謂一脈相承。對(duì)于這一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得與失進(jìn)行深入研究與反思,對(duì)于我們當(dāng)下的學(xué)術(shù)研究無疑是極為重要的。
注釋:
①胡適說:“古代的書,只有一部《詩經(jīng)》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因?yàn)椤对娊?jīng)》中關(guān)于日食的記載可以得到現(xiàn)代科學(xué)的證明,故“《詩經(jīng)》有此一種鐵證,便使《詩經(jīng)》中所說的國政、民情、風(fēng)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價(jià)值了”(《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卷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3頁)。顧頡剛說:“《詩經(jīng)》這一部書,可以算做中國書籍中最有價(jià)值的……我們要找春秋時(shí)人以至西周時(shí)人的作品,只有它是比較最完全,而且最可靠。”(《詩經(jīng)在春秋戰(zhàn)國間的地位》,見《古史辨》第3冊(c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頁)
[1]顧頡剛.詩經(jīng)在春秋戰(zhàn)國間的地位[A].古史辨(第3冊(c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09—310.
[2]顧頡剛.詩經(jīng)在春秋戰(zhàn)國間的地位[A].古史辨(第3冊(c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20—322.
[3]何定生.詩經(jīng)今論[M].臺(tái)北: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館”,1968.
[4]錢穆.讀詩經(jīng)[A].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8冊(cè))[C].臺(tái)北:臺(tái)灣經(jīng)聯(lián)出版社,1998.165.
[5]鄭振鐸.讀毛詩序[A].古史辨(第3冊(c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85.
[6]顧頡剛.論時(shí)序附會(huì)史事的方法書[A].古史辨(第3冊(c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05.
[7]錢玄同.論詩經(jīng)真相書[A].古史辨(第1冊(c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6—47.
[8]皮錫瑞.經(jīng)學(xué)通論·詩經(jīng)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4.
[9]胡適.談?wù)勗娊?jīng)[A].古史辨(第1冊(c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77.
[10]胡適,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11]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
[12]顧頡剛.古史辨自序[A].古史辨(第1冊(c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