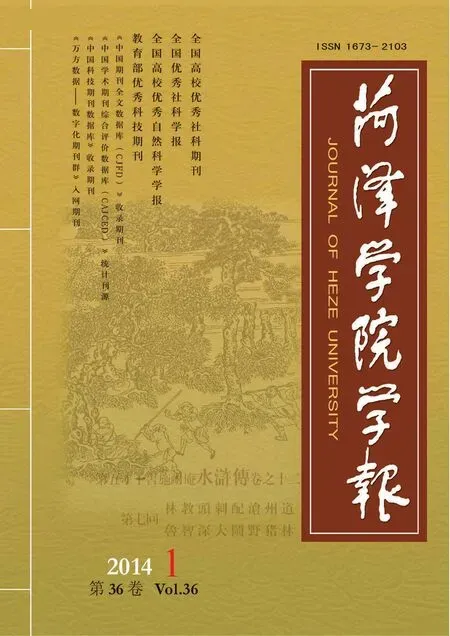論十七年合作化小說中心話語的哲理性蘊涵*
曹金合
(菏澤學院中文系,山東菏澤274015)
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說是由帶有價值規約的不同話語組成的文本,不同的話語由于各自的價值觀念不同、話語主體所站的立場各異、話語的等級地位有別等各種因素,就會在傳達不同的倫理觀念和情感意蘊的時候,發生相互沖突的現象。而在實際的交流過程中,在同一語境下,由于說話人、聽話人之間價值觀念和知識背景的不同,也會形成一個動態的充滿張力的領域。因為從話語的功能和表現形態來看,“話語并非僅僅是語言學的單位,而是人類行為、互動、交流和認知的單位。話語不是一種詞語和意義的靜態的、理想化的、總體的一致性,而是一種利益、爭斗、張力和沖突的動態領域。”[1](P203)對合作化小說而言,政治話語、革命話語、階級話語所代表的倫理價值觀念,由于有主流意識形態的支持而處于中心話語的強勢地位,特別在主流文化想憑借中心話語的權威優勢,為合作化運動的方針政策搖旗吶喊的時候更是如此;代表人文關懷的人性話語和歷史深層律動的歷史話語有時并不同于中心話語所表達的價值觀念,特別是極左意識形態導致的公有制的成分越來越純粹的情況,并不符合客觀歷史發展的規律,也與農村和農民的生產、生活的發展態勢不相吻合。這樣以知識分子和民間之類的話語主體表達的關懷生命個體的自由倫理的價值觀念就與集體倫理的價值觀念發生摩擦。因此,放到十七年的文化語境中進行考量,可以說“‘十七年文學’的歷史,其實是主流文化與文學文本之間,不同話語之間交流和摩擦互動的歷史。”[2](P129)只不過合作化小說由于是對現實的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生活進行反映的特殊性,使得它與當時的政治文化的關系更為密切。而且當時的中宣部和文化部也要求作家要切實地承擔起輿論宣傳的任務,為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提供形象的合法化和合理化論證。這樣,中心話語內容的哲理權威性和隱含作者的哲理說教性就成為作家進行形象化論證的不二法門,由此也構成了合作化小說的中心話語比較豐富的哲理性蘊涵。
一、中心話語內容的哲理權威性
“任何一個新興民族國家的建立,都需要借助敘述來爭奪話語權和歷史的闡釋權。”[3](P6)合作化小說之所以成為政治文本,就是與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帶來的思想文化和倫理觀念的更迭有密切的關系。新政權是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蒼涼面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要在農村中開展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運動,就必須將異質的文化價值觀念和思想信仰通過通俗的富有哲理的權威論證,來俯就比較務實的民眾的思想意識和接受心理。這樣,才能在“大眾化”的藝術要求與“化大眾”的接受效果之間搭建理想的溝通平臺,讓民眾覺得合作化運動確實是從他們自身利益出發的切實可行的政治政策。這就給合作化小說的敘事者提出了一個話語權和歷史的闡釋權的問題,也就是說,要刻畫時代的變遷和生活的變化的現實題材的小說,既要采取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如實地描繪農村合作化以后的比較復雜的現狀;又要采取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段,暢想克服困難之后的未來的美好前景,以增強民眾堅定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因此合作化小說的中心話語對民眾的信服性和感召力,不僅體現在是“誰說的”即話語主體的身份重要性,而且是“說什么”即內容的哲理權威性。只有采取這樣的方式,通過中心話語的文化領導權的建立,才能讓民眾自覺贊同主流意識形態所宣傳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公有制的倫理觀念。因為“根據葛蘭西的理論,文化領導權的確立并不是一種外在的強制性過程,而是通過各種方式日益轉化為大眾積極主動的認可和默許。這種“自動贊同”主要是通過各種文化機制(如文化生產與接受、教育、出版等)和意識形態手段,在特定社會造成某種共同的價值觀或共識。”[4](P15)因此,合作化小說的中心話語作為意識形態的載體,為了取得民眾的認可和默許的積極效果,就在話語的哲理性和邏輯性上,借鑒了社會發展簡史以及馬列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觀點,來為自己話語領導權的獲得提供強有力的論證。綜觀合作化小說的中心話語對哲學理論的借鑒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關社會發展規律的展望和籌劃遵循的是馬列主義的社會發展簡史,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上的,論證了走合作化之路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避免社會再次出現兩極分化的康莊大道;二是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分析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的基礎之上的,并結合中國特殊的國情進行了創生性的轉化,因此具有豐富的哲學內涵和哲理權威性。
合作化小說中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新名詞和政治經濟學以及哲學術語不斷在反映社會現實的字里行間穿插,增強了中心話語的權威性和說服力。有時候為了增強無可辯駁的縝密的邏輯論證的力量,就大段大段地引述毛澤東文集或者是復述當時統計的合作化運動所產生的成效,這顯然是違背文學創作和藝術審美規律的。文學的感性和理性、審美和宣傳并沒有達到有機的融合,并不是作家沒有能力融會轉化理性的政策條文成為感性的血肉豐滿的形象,來達到教化民眾的目的,而是政治權力借助中心話語動員組織民眾的強烈沖動使然。“但像借助政治權力推行集體化,卻是掌握國家權力者有意識的施為,顯示出依靠政權力量和意識形態動員組織鄉土社會的強烈沖動。”[5](P330)因此,越來越左的意識形態要求政治術語和新鮮名詞原汁原味地展示出來,這樣,敘事者為了動員民眾引述領袖的語錄或者革命導師的哲學觀念當然是最具有說服力了。在《創業史》中,縣委楊書記和區委書記王佐民探討農民在新社會的階級定位、功能作用和復雜特點時,就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復述和翻版。“農民嘛,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是勞動的階級嘛。民主革命階段是同盟軍,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還是同盟軍嘛。工農聯盟是永久的,不是臨時的。但是,革命革到要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啦,農民小私有者和小生產者的一面,不是變成矛盾的一個方面了嗎?不是應該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嗎?”對于在新的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如何引導農民克服小私有者和小生產者的一面,那就是根據毛澤東的“嚴重的問題還是在教育農民”的綱領要求下,采取辯證分析的方式,看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下中農身上體現出來的渴望繼續革命的優點。合作化運動作為新的事物是在新舊矛盾的激烈斗爭中站穩腳跟的,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合作化運動的發展變化。為了讓這些中心話語的內容更具有哲理性,小說干脆設置讓縣委副書記伸手接過毛選,很熟練地翻到第三百一十一頁念毛選的情節:楊書記非常快活地念道:“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爭。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于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于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對“互助合作和小農經濟的關系”開出了辯證對待的藥方。這樣的矛盾論、發展論和辯證法都以先在的權威性為合作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支持,即使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困難,也不會再繼續質疑合作化運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這樣就達到了宣傳和教育的目的。由于柳青經常看報刊社論、看有關的合作化運動的生活報道、論文和通訊,加強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哲學觀念的修養,因此也形成了他的比較迷信哲學觀點的創作經驗。他認為“真正震撼人心的現代文學作品,只有運用嚴格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才能寫得出來。這是因為需要將對立的政治思想,正確地融貫在對立的人物性格沖突中,引起讀者感情上的激動”[6](P67)。由此也不難理解作為他的經典作品的《創業史》會有那么多的政治和哲學術語,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在日常的談話中時常冒出與語境不太吻合的新的概念名詞。而且在第一部的小說結尾,更是將社會發展簡史和黨在過渡時期的路線方針原封不動地搬入小說,斬釘截鐵的話語方式顯示出作者急于教育民眾的焦灼心態:“必須使他們懂得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是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或者說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將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使我國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使他們懂得只有實行黨在過渡時期中對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即按照農民自愿的原則,經過發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業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方針,才能一步一步地發展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業的產量,才能使所有的農民真正脫離貧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來,并使國家得到大量的商品糧食及其他農產品……”除了《創業史》,其他的合作化小說雖沒有大段引述領袖語錄或者是哲學原著,但靈活運用哲學術語和注重辯證邏輯的條理性也成為常見的敘事風格。如《山鄉巨變》中區委書記朱明在合作化會議上的總結發言,就是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哲學觀念活學活用的典型表征,對合作化中出現的現象和問題的分析所具有的條理性和嚴密性顯然非常令人信服:“在整個運動中,我們要堅持三同一片的傳統的作風,深入地了解并設法徹底打通各家的思想。思想發動越徹底,將來的問題就越少。發動時,首先要對癥下藥,對象害的什么病,你就用什么方子,不要千篇一律,不要背教條;其次,要注意去做說服工作的人選,要選派合適的人去做這個工作;第三,要盡量解決發動對象的迫切的問題。”到了文革前出版的《艷陽天》中,更是讓許多文化水平比較低的民眾,說出與其身份和文化修養不太吻合的哲學名詞,以突顯加入合作社的合理性和必然趨勢。其中的孤兒馬翠清對農業社忠心耿耿的表態堪稱代表:“我是個最無產最無產的階級,我是光著身子進農業社的,我當然沒有金銀財寶,我沒有房子,沒有地,連個家,連個媽都沒有,黨就是我的媽,農業社就是我的家,拿炮彈轟,也不能夠把我跟黨、跟農業社轟開!這是真的,信不信由你們!”由此可見中心話語的權威性與政治哲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可以說,沒有這些哲學概念和政治名詞提供的強有力的價值支撐,合作化運動也不會在神州大地上如此迅速地普及到鄉村的每一個角落,從而將民間社會千百年來形成的一盤散沙的自由狀態,動員組織起來成為集體生產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在合作化小說中中心話語強調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路線的斗爭模式,與主流意識形態強調的“打破一個舊制度,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價值體系相吻合,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劃分和斗爭學說與中國特殊的國情相結合之后進行的創造性轉化,其中包蘊的哲學理念是不言而喻的。具體到十七年的政治語境,以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進行階級的劃分首先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念,但這種以物質范疇為基礎的劃分又超越了物質性的界定,從而與個體的道德觀念掛鉤,成為了按照“敵、我、友”的范疇站隊的象征性符碼。特別是在用戰爭年代形成的超常規的政治運動的方式來建構和穩固新政權的合作化時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觀念為了保持革命的警惕性來換取新政權進一步鞏固的資本,需要斗爭對象的長期存在,“即使消滅了曾經的階級敵人,但為了打擊新的斗爭對象,所以不斷以各種方式塑造敵對階級,通過將打擊對象定性為對立階級(以前是定為地主階級,后來是納入資產階級的范疇),以維持斗爭政治的蓬勃發展和無限推進,實現國家對鄉土社會的持續介入與動員,在運動中建立高度一體化的國家結構和社會秩序,以至于這種‘革命政治’不斷發展,到后來成為建立一個全面純化的新世界的工具。”[7](P191)不過,在合作化小說發展的不同階段,對某一部分內容的強調使它成為小說的突出部分,是隨著政治政策的發展變化而進行調整的。在合作化小說的早期階段,這個時期的矛盾斗爭主要表現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道路、走個體發家致富之路還是集體共同富裕之路的沖突斗爭。因此,小說的中心話語就是圍繞著上述的矛盾沖突而展開的。如《三里灣》中支部書記金生批評村長范登高的話語,就是兩條道路之間勢不兩立的斗爭沖突的表征:“就是群眾,也是接受了黨的領導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等到別人把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好了以后再繳出財產來。大家都發展資本主義,還等誰先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呢?”理直氣壯地反駁和明確的價值引導功能,都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基礎之上的。在社會發展學說上,社會主義社會是比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更高、制度的優越性更加明顯的社會,因此當然對想鉆合作化政策的“入社自由、退社自愿”的空子的范登高無疑是當頭棒喝,駁斥得他啞口無言乃是情理之中的結局。到了《山鄉巨變》,階級斗爭的倫理觀念已深入鄉村日常生活的空間,正如區委書記朱明所分析的:“不過這運動越到以后,矛盾越深刻,復雜,我們還不能預料,各鄉會發生什么事情。也許會平靜無事,也許會發生意料不到的事故。反革命殘余的趁火打劫,也可能會有。總之,我們既要快,又要穩,要隨時隨刻,提高警惕,防止敵對分子的破壞。”區委的指示在清溪鄉的具體落實過程中,就按照階級的標準劃線站隊,對全鄉的地主、富農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跟壞分子都得進行訓話,并告訴他們“只要守法,不造謠破壞,惹是生非,好好地接受勞動改造,將來不久,農業社可以分批吸收他們做社員,或候補社員。”其實,這種階級意識和倫理觀念的劃分是有許多不合理的成分的,而且民眾的階級意識也不是從宗法倫理觀念濃厚的民間社會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的,所以自外而內、自上到下灌輸的階級意識也不是“社會階級成員對他們共同處境與共同利益的共同意識”[8](P262),因此就更需要在小說中充分論證階級意識和階級斗爭在合作化運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引導民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因此,在《艷陽天》中通過馬翠清之口得出結論:“無產階級,才是最革命的,才是最擁護共產黨的,才是最愛咱們東山塢農業社的,才敢跟壞人斗爭,才能跟落后分子一刀兩斷,才是大公無私的。”其一環扣一環的邏輯論證顯示出作者急于引導群眾的敘事倫理觀念,一系列的政治術語和哲學名詞為結論的邏輯論證提供的權威性和信服性,正是作者最想要的敘事效果。在以后的階級斗爭成為日常生活的常態時,合作化小說對階級理論的圖解和演繹也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由此對審美倫理的傷害和與文革文學的政治美學的聯系,也許只有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才能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
二、隱含作者的哲理評論性
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隱含作者插入的哲理性評論對讀者的影響力和價值引導功能是有目共睹的,“在很多情況下,敘事者對人物和事件作出評述性評論是試圖使隱含讀者接受其所作的判斷與評價,按照他或她所給的定義去對事件和人物加以理解,以使隱含作者與敘述接受者在價值判斷上保持一致。”[9](P77)尤其對合作化小說這樣的特別注重讀者的閱讀反應的文本更是如此,小說的作者為了使政治主題的明晰性和精確性進一步凸顯,以便更好地為大眾所理解并心甘情愿地接受,達到作者所表達的倫理價值觀念和讀者的接受心理契合和情感共鳴的目的,在敘事情節、人物行為、結構布局等方面往往采用隱含作者的哲理性評論的敘事方式,進一步加強中心話語的普世性、真理性和權威性。眾多的作者在小說中不僅讓正面人物作為中心話語的載體達到言傳身教的敘事目的,而且忍不住在文本中就某些人物的所作所為和問題的癥結所在進行評論,讓那些識字不多、理解水平不高的民眾進一步明晰故事情節中所包含的哲理觀念,由此也不難看出作者的敘事倫理:“促使讀者按照所給定的倫理原則去對事件和人物加以理解,以使隱含作者與讀者在倫理判斷上保持一致,這當然是故事倫理干預的一般目的。”[10](P144)
合作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探索性和試驗性的農業生產運動,在宣傳動員和具體生產過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問題也層出不窮。對于特別務實的民眾來說,如何通過評論性話語將深奧的道理淺顯化,使民眾理解并接受合作化運動,也如同任何其他的新生事物的發展規律那樣,總是在挫折和總結失敗的經驗中逐漸向前發展的。也就是說,用“失敗是成功之母”之類的鮮活事例增強民眾對合作化事業的信心。這就要求作者配合在主流意識形態所設計的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階段的情況下,通過隱含作者的哲理性評論來加強對民眾的價值觀念的引導。如《創業史》中第十五章的開篇就是一段對民眾的倫理觀念和精神境界影響深遠的格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這段說教性評論包含的哲理色彩是非常明顯的,當然作者不是抽象地談論人生道路的問題,而是通過解放前的年輕人由于沒有正確的價值觀念的指導而造成生命力的浪費,碌碌無為地度過終生的現象與解放后的青年團員徐改霞相比較,在新社會的陽光雨露滋潤下,盡管她是個鄉村閨女,但在合作化運動中所煥發出的熱情和信心,表明她早已懂得用正確的態度對待人生了。這樣理論與實踐的比照使這段評論所包蘊的倫理觀念深入人心,成為許多參加合作化運動的民眾,特別是青年積極分子的座右銘。當然,農民世世代代與土地和莊稼打交道,對于熟悉鄉村生活的敘事者來說,采取農村生活中最常見的事物的發展規律來比附合作化運動的發展情況,對民眾來說就會更加相信合作化的光輝燦爛的前景。因此,隱含作者對民眾的說教功能要達到最佳效果就必須考慮農村的現實情況和民眾的接受水平,合作化小說選擇莊稼之類的植物蘊涵的哲理來教育民眾正是基于這一點。柳青在這部小說中對鄉村不同的人在大體相同的生活環境中,由于思想意識的不同、倫理觀念的不同、道德境界的不同而導致的千人各面的情況,以及在合作化運動遇到考驗的時候不同的人的不同表現,用莊稼地里作物生長情況的議論就淋漓盡致地揭示了出來:“和谷苗一塊長起來的,有莠草;和稻秧一起長起來的,有稗子。莠草和稗子,同莊稼一齊生長,一齊吸收肥料和土壤里頭的養分,一齊承受雨露的恩澤,但它們不產糧食,只結草籽。不幸這種情況,超出了自然界。高增福有他哥高增榮,梁生寶有他的鄰居王瞎子。”這樣的形象性說教比起其他方式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因此成為合作化小說的作者在說教性議論中最常用的一種敘事策略。《水向東流》(李滿天)拿秧苗的成長過程和合作化的發展規律相比較就非常形象:“苗兒剛出土的時候,總是很小很嫩的,過不了多久,它就會長得枝繁葉茂,開花結果。”因此,即使在運動中遇到什么石頭或是棘針,只要在黨的堅定領導下,將來的農民肯定會在合作化道路上發展壯大的。所以,最后用“浩浩群眾朝前進,滾滾河水向東流”來對所表現的主題作總結就顯得水到渠成。馬德昭的《在芙蓉大隊》在表現芙蓉農業社和支部書記的成長歷程時,也是采用了類似的手法來加強議論的說服力的:“經過六年來的艱苦奮斗,如今,芙蓉的山變了,田變了,人也成長起來了。金德也象一株小樹苗一樣,在黨的陽光雨露滋潤下,在與窮山惡水的斗爭中成長起來,現在已經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擔任了共青團芙蓉大隊的支部書記。”這種現象的普遍性顯示出隱含作者的說教性議論絕不是泛泛而談眾人皆知的大道理,而是從讀者的認知觀念和接受水平出發,實實在在地宣傳合作化的優越性而采取的教化民眾的敘事策略。
將合作化的道理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和在提高的基礎上普及是小說的隱含作者必須要完成的政治任務,教化的倫理觀念猶如一條掙不斷的紅絲線,牢牢地將敘事的倫理價值觀念綁在政治倫理、革命倫理和階級倫理的戰車上。因此,在對某些事物和現象發議論的情節中,隱含作者往往采取反問的方式和祈使句的形式來加強說服的氣勢和力度。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在倡導互助取得了一定階段的勝利之后,隱含作者通過他的心理所發的議論就很有代表性:“這難道是種地嗎?這難道是跑山嗎?啊呀!這形式上是種地、跑山,這實質上是革命嘛!這是積蓄著力量,準備推翻私有財產制度哩嘛!整黨學習中所說的許多話,現在一步一步地在實行。只有偉大的共產黨才搞這個事,莊稼人自己絕不會這樣搞法!”可以說,這樣的議論是建立在理論與實踐、批判與繼承的辯證關系的基礎之上的,也是柳青在皇甫村多年農村生活經驗的積累與主流文化有機融合的藝術結晶,非常形象地詮釋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關普及和提高的辨證關系的精髓:“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正因為這樣,我們所說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范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給將來的范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11]李準的小說《進村》在隱含作者的議論方式的設置上和《創業史》非常類似,在合作化的積極分子楊大伯的心目中,縣里老郭同志一進村就開貧農根子會,動員加入互助組的行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小說也是通過楊大伯的心理反應來生發議論的:“全中國有多少個農村呀,要是每個農村都在這不冷不熱的春夜里,講著革命的道理,提高著階極覺悟,扎著革命根子,那不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最牢靠的基礎嗎!”由特定的語境進一步生發議論的目的就是讓更多的民眾認清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為合作互助的順利進行提供明確的價值指導,這正是隱含作者將高深的道理淺顯化和形象化的價值所在。
不可否認,“17年時期的社會主義生活本身就是全方位政治化的,而作為一種‘現實主義’的文學,由于它‘真實’反映‘現實’的本性和自我認知,決定了它在這一層面反映內容的必然政治化。”[12](P339)因此,合作化小說的中心話語借助現實主義的修辭藝術,可以將十七年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化過程的哲理性蘊涵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從而對民眾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引導起到了其他話語方式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但細讀文本不難發現,當中心話語借助權威的意識形態成為藝術的巨無霸,而沒有其他的力量與之抗衡的時候,辯證的邏輯就充分地顯示出走向極端之后的審美觀念的偏枯和缺失。就僅僅是對人物塑造方面來說,其中的審美欠缺也是有目共睹的:“意識形態的政治話語直接轉化為文學的倫理和審美要求,‘冷戰’中階級意識的現實要求遮蔽了藝術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層揭示,新人物塑造的新,便在于抓住人物的某個方面推向全體推向極致,但求典型不求豐富。”[13](P206)因為人物是中心話語的最有效的價值載體,通過人物的話語所表現的哲理觀念的鮮活性和生動性,在教化民眾方面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而人物完全成為政治的傳聲筒之后,其對民眾耳提面命的教化作用是大可質疑的。這就是中心話語在轉化為審美形象后面臨的邏輯悖論,其中的敘事手法和修辭藝術的補償機制以及各種哲理觀念的動態博弈卻是常常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層面。因此,通過這樣的探討,不難發現中心話語的哲理蘊涵對作家的敘事觀念的影響程度。
[1]王曉路.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程光煒.文學想像與文學國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1949 ~1976)[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3]陳順馨.1962:夾縫中的生存[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
[4]陳偉軍.傳媒視域中的文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5]劉志榮.潛在寫作1949—1976[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6]蒙萬夫.柳青寫作生涯[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 .
[7]樊佩佩.從鄉土社會到階級社會:土地改革與階級劃分的權力實踐[J].社會科學論壇,2012,(10).
[8]戴維·波普諾.社會學[M].李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9]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0]伍茂國.現代小說敘事倫理[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
[1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N].解放日報,1943-10-19.
[12]朱曉進.非文學的世紀: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關系史論[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3]朱水涌.冷戰的焦慮:“十七年”文學的文化心態與特征[G]//吳秀明.“十七年”文學歷史評價與人文闡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