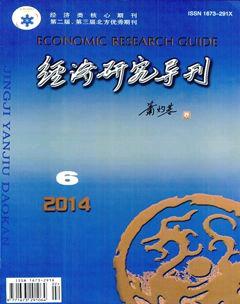從《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看戚繼光的軍事教育思想
侯陽
摘 要:戚繼光的軍事思想主要集中在《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中,作為其軍事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軍事教育思想,也同樣為后人所矚目。他的軍事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了為誰而戰、愛護士卒、“實戰”訓練、嚴肅軍紀和尊師重教等五個方面。這些思想對我軍的發展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戚繼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軍事教育思想
中圖分類號:E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6-0275-02
戚繼光(1528—1588),字元敬,號南塘,祖籍安徽定遠。他繼承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優良傳統,總結了自己練兵作戰的經驗,寫下了眾多的軍事著作,如《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儲練通論》、《哨守條約》,以及《孟諸公武略類編》和《洪尚書重補戚少保南北平定略》等。尤其是《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被稱為“中國軍事教育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軍事教育專著”。而本文則主要從以上兩書①入手,來研究戚繼光的軍事教育思想。
戚繼光的軍事教育思想體系龐雜、條目眾多,現僅就幾點關鍵內容做一簡單梳理。
一、為誰而戰
為誰而戰,這是一個關乎責任與使命的問題。只有確立了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奮斗目標,才能在日常中辛勤訓練,在戰場上奮勇拼殺。戚繼光就反復強調,養兵的目的即在衛國保民。他對士兵說:“凡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哪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今日食銀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隨后又說:“凡你們本為立功名報效而集。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百姓豈不是要你們去殺賊!設使你們果肯殺賊,守軍法,不擾害地方,百姓如何不奉承,官府如何不愛重!……今練之后,但凡軍行,必是依令抬營,一人不得攙越生事。”通過士兵與百姓、官府的利害關系,來教育士兵要懂得為衛國保民而戰的道理。
二、愛護士卒
這點主要是從軍官的角度來闡發的。戚繼光針對當時軍中存在的拿士兵當奴仆使喚的普遍現象,曾說“位有貴賤,身無貴賤”。他認為,“將誠勇以力相敵,不過數人極矣。數十萬之眾,非一人可當,必賴士卒”。
緊接著,他又把普通士兵的地位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說:“凡軍稱曰軍士、戰士、力士、勇士、義士、士卒。夫必稱曰士者,所以貴之也。朝廷之命名貴士如此,所以望之出力疆場,衛國保民,其責非輕。今卻使之為轎夫廝役,以廝役待士,而欲其出死力,捐命御寇,有是理哉?”把士兵和排在中國古代四大階層首位的“士”聯系起來,可見對他們的尊重。
戚繼光還要求軍官平日要率先垂范,嚴于律己、身先士卒,與士兵同甘共苦。“平居之時,實心愛之,真如父子一家,諄諄以忠義感召之;入操之時,虛心公念,犯必不救,至親不私,必信必果;出征之日,身先士卒;臨財之際,均分義讓。”之所以這樣做,其原因是:“夫士卒雖愚,最易感動。死生雖大,有因一言一縷之恩,而甘死不辭者。”
他說:“所謂身先士卒者,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苦處要當身先;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處時亦要同滋味”。具體來講,“(軍官當)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共跋涉;或夜宿隊伍之中;或出其私積之物。雖士卒一尺之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習之為諸士倡。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怠”。只有這樣,才能使三軍歸心,自覺地聽從指揮,才能在日常中提高效率、在戰場上英勇殺敵。
三、“實戰”訓練
戚繼光主張訓練要講究實用,不搞花架子。他痛斥當時軍隊的訓練,稱:“今所習所學,通是一個虛套。其臨陣的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原無一字相合。及其臨陣,又出一番新法令,卻與平時耳目聞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臨時還是生的。且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看周旋左右,滿片花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視為戲局套數……此是花法勝,而對手功夫漸迷,武藝之病也;虛文張,而真營卻廢,制陣之病也……”
為此,他要求訓練要從實戰出發,戰術訓練、兵器訓練以及訓練難度等都要符合實戰需要。“若是平日教場所操練,金鼓號令,行伍營陣,器技手藝,一一都是臨陣一般,件件都是對大敵實用之物,便學一日有一日受用,學一件有一件助膽,所謂藝高人膽大也。學則便熟,不學便生。學的便會殺賊,保得自己性命,立得功;不學便被賊殺。你們知道這個緣故,豈肯不學!今凡教場內行一令、舉一號、立一旗、排一陣、操一技、學一藝,都是臨陣時用的實事。臨陣行不得的,今便不操,不使你學。到彼時實行出,實用出,爾官軍方信之。”
在強調刻苦訓練的重要性時,他認為“(武藝)是爾等當兵防身殺賊立功的勾當。爾武藝高,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爾;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在個人武藝熟練的基礎上,還要加強營陣訓練。營陣訓練不僅在操場上進行,還要到野外實地操練。只有這樣,“臨時方無差錯。若操于場,不操于野,終未見實境,臨時仍是不合彀”。
此外,他還表述了訓練不止于教場的思想。“夫陳師鞠旅,列眾于場,謂之操練,爾等知之矣。殊不知教場操練,不過明金鼓號金,習射、打、擊、刺手藝之能。此等事不是在人家房門院墻內做得,故設教場操練之。平時在各歇家之時,若肯心心在當兵,起念一心,以殺賊為計,蓄養銳氣,修治軍裝,講明法令,通之以情,結之以心,何嘗不是操練也。”
四、嚴肅軍紀
如果士兵只有殺敵本領,而無嚴格的紀律,這樣的軍隊是沒有戰斗力的。因此,戚繼光一向注重軍隊紀律,強調部隊的紀律訓練與武藝訓練應同時進行,“藝與法令,當并行不悖者”。同時,執行軍紀要從嚴,在獎懲方面,也要不避親仇。“凡賞罰,軍中要柄,若該賞處,就是平時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賞,有患難也是扶持看顧;若犯軍令,就是我的親子侄,也要依法施行,決不干預恩仇。”
他說:“凡古人馭軍,曾有兵因天雨取民間一笠以遮鎧者,亦斬首示眾。況砍伐人樹株,作踐人田產,燒毀人房屋,奸淫作盜,割取亡兵的死頭,殺被擄的男子,污被擄的婦人,甚至妄殺平民假充賊級,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決以軍法從事抵命。”
針對當時明軍存在的陋習,擬定了詳細的懲罰措施,而且頗為嚴厲,這也正反應了戚繼光對軍隊日常紀律的重視程度。
戚繼光認為,戰場上應嚴格遵守紀律,切實執行各項條令條例,是戰爭取勝重要保障。他說:“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戰百勝者。”他在《紀效新書·號令篇》中要求將士:“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里火里,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止,也要依令退回。”凡違令者,皆以軍法處置。
五、尊師重教
戚繼光非常重視軍人的培養教育工作。然而“教習之道,須先重師禮。古云,師道立而善人多。教師之類,于位甚卑。然在兵卒之間,即師傅之尊也。”把軍隊中的尊師放在重教之前,毫無疑問在當時是頗有見地的。他隨即又言:“師道不立,則言不信,教之不遵,學之不習,習而不悅,師道廢而教無成矣。須于兵卒間隆以師禮,付以便宜。凡士兵之不聽教者,得徑行責治,稟官示以軍法。將士頭目,皆習其業。”只有尊重教師,學習才能有收獲。當然,這里的教師不僅僅限于上級指派的軍官,也包括普通的、有一技之長的士兵。
當然,戚繼光的重教思想在設立武學館這一點上體現的更為集中。戚繼光興辦的武學館,每期招收學員300多人,學習和訓練時間為三年。對于武學館的學員選擇問題,戚繼光主張“無分于武弁也,無分于草萊也,無分于生儒也,遴其有志于武者,群督而理之”。就是說學員主要從部隊初級軍官、優秀戰士、世襲武職之家的子弟和武生員中挑選,不論出身如何,只要有志于軍事工作,都可以挑選來武學館受訓。
對于學員畢業后的分配使用原則,戚繼光主張學員畢業后到部隊去接受訓練和實踐檢驗,然后再根據學員德才擇優錄用。他說:“諸藝俱通,然后付各實用營中習教陣法操法。俟其習有成效,然后總調一處考校之;果為精通,又再付各有事地方將領,隨營出征,習臨敵真戰真法。俟效而量才擢用。”他把經過考核的學員分為三等:第一等“兼以文義,雅有德量,則大將也”。對于具有較高文化修養與軍事理論修養,品德高尚且有度量的,可為大將。第二等“優于技藝,勵于鼓舞,短于文學,則偏裨也”。有些學員武藝很好,作戰勇敢,但因缺乏文才,難成文武兼備者,只能擔任副職。第三等“才有余而志不足以當之,勇有余而志不足而承之,皆小將也”。有些學員或有才華或作戰勇猛,但卻胸無大志、沒有高尚的情操,就只能當下級軍官。
言而總之,“從明朝后期到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直至其后的一段時間,戚繼光軍事思想已成為中國軍事領域的主導思想。”“……戚繼光是站在當時社會軍事思潮的前列,領導著這個思潮,推動著這個思潮前進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它確立了戚繼光在中國軍事思想史上的地位。戚繼光對中國兵學的貢獻即使不能同孫武并駕齊驅,也是繼孫武之后的第一人。”作為戚繼光軍事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軍事教育思想,自然也是對后人產生深遠影響。中國自明以后直至近代的軍事訓練、軍事教育,也多半是奉其為圭臬。
認真學習與深入研究戚繼光的軍事教育思想,對于我們大膽探索和改革軍事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形成一整套適合我軍特點的現代軍事教育制度,以履行好新世紀新階段我軍的歷史使命,有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1] 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 紀昀,等.四庫全書[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3] 范中義.戚繼光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責任編輯 魏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