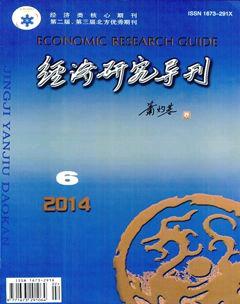中國土地整理研究進展與展望
吳孟珊
摘 要:通過系統地回顧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土地整理研究的主要文獻并進行未來展望,旨在對新一輪土地整治規劃的修編進而對未來十年中國土地整理事業又好又快發展提供理論支持。研究發現: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土地整理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基本模式、規劃設計和綜合評價等方面;今后應加強土地整理的基礎理論、復墾開發項目、評價指標和模式、方法體系等方面的研究力度。
關鍵詞:土地整理;進展;展望;中國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6-0053-03
引言
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及其所處的不同地區,人類對土地利用的方式以及對土地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隨著土地環境與土地供需狀況的變化,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和促進經濟、社會向前發展,土地整理也應運而生。作為一種能有效增加耕地面積、提高土地質量和促進土地集約利用的方式,土地整理對于緩解人地矛盾、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保證糧食安全以及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系統地總結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土地整理研究的主要文獻并進行展望,旨在對新一輪土地整治規劃的修編進而能對未來十年中國土地整理事業又好又快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一、研究進展
總體來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主要學者對土地整理問題的研究集中在土地整理基本模式、規劃設計和綜合評價等方面。
(一)模式研究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土地整理得以開展,眾多學者從內容、功能、運作方式、地域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土地整理模式體系,旨在通過特定區域土地整理目標和模式的構建,為土地整理實踐提供借鑒與參考。吳蘭田等、劉晶妹等認為中國農村土地整理總體上分為專項土地整理模式和綜合土地整理模式兩種。專項土地整理模式包括對農村居民點的改造、農地整理和開荒復墾及鄉鎮企業用地的集中等。綜合土地整理模式即田、路、林、水、村等的綜合整頓及治理[1~2]。楊慶媛以中國西南地區為特定的研究區域,對土地整理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調查和區域特征分析,把西南地區土地整理的類型模式劃分為一般分類模式、以提高土地生產力為中心功能的土地整理模式、以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中心功能的土地整理模式、以經濟增效為中心功能的土地整理模式等四種類型。同時,分析了制約土地整理產業發展的因素,包括社會環境制約因素、土地整理的管理制約、土地整理理論建設與科研不足、土地整理的資金制約等[3~4]。涂建軍等提出了農林綜合開發、新村建設整理兩種模式。通過對西南丘陵地區土地整理理論及實證分析,提出以下建議:模式的理性選擇要與當地的實際相適應;土地整理成功與否的決定因素和必要前提是農民可獲得的收益;地方政府的合理引導和資金保障是土地整理活動順利開展的關鍵;對模式的探討要不斷深入[5]。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土地整理是消化貧困山區剩余勞動力的有效措施[6]。劉筱非根據不同的整理項目,將城市土地整理劃分為四種應用模式:(1) 舊城改造的市地整理模式;(2)低收入居住區、貧民窟、非法聚集居住區改造的市地整理模式;(3)城市蔓延區的市地整理模式;(4)城市污染地改造的市地整理模式。基于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間格局,根據整理單元的劃分方案,將江北區城市土地整理分為三種不同的應用模式:舊城更新模式、“退二進三”模式與“城中村”改造模式[7]。馮廣京指出推進土地整理工作應當首先研究農地整理的模式,這種模式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作業模式;二是組織模式;三是投資模式。研究方法是:在調查統計的基礎上,采用Q型群分析的方法,對調查樣點進行分類,然后繪出聚類圖,將樣點分為若干類。根據這樣分成的若干類,對每一類內調查樣點的社會、經濟、自然因素統計分析,研究并確定社會、經濟、自然因素與農地整理的關系及影響,評價目前農地整理的模式、水平及影響因素,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8]。由于這種分類方法兼顧了多種綜合因素,較為客觀,因此對中國其他社會、經濟、自然條件與調查樣點一致或相近的地區具有較大的參考和指導意義。
(二)規劃設計研究
土地整理規劃與設計既有區別又有密切聯系,土地整理規劃著眼于項目區甚至更大區域,對原有土地利用的優化組合以及重新配置或引人新的土地利用類型,調整或構建新的土地利用格局及功能區域,而土地整理設計著眼的范圍比較小,往往是對田塊、路、林、渠等的設計或某一功能區域特定功能的實現過程,一般都與具體的工程相聯系,以具體的技術應用為特征,土地整理規劃與設計是從結構到具體單元,從整體到部分的逐步具體化過程。當前中國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地區進行土地整理設計時,存在一種誤區,過分追求田間道路、溝渠等的高品位設計,道路、溝渠多用混凝土鋪設,這種做法無疑便于通行、機械化操作和溝渠的美觀,但卻減少了綠地面積和生物棲息的場所,不僅降低了景觀的多樣性,也使得項目區土地利用系統簡化,不利于整個系統功能的穩定與提高[9]。土地整理的規劃設計在土地整理專項規劃與土地整理工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也是土地整理工程實施的重要保障,所以科學合理、切實可行的土地整理規劃設計是保障土地整理成敗的關鍵一環。這就要求規劃設計需要多方面的信息支待,包括地方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水土資源約束以及對土地利用和覆被變化資源環境效應的認識,更應注重利用生態學的有關成果,探討將土地整理規劃設計融入景觀生態設計的理念,盡可能改善生態系統結構簡單、生態系統脆弱的狀況,注意景觀多樣性的設計,使系統的穩定性進一步提高[10]。
(三)綜合評價研究
由于土地整理過程改變了地表生態系統,必然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例如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景觀格局的變化、原有水系的改變、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化學元素遷移和轉換的變化等,從而對局域、區域乃至全球的環境變化和地表生態系統有所影響[11]。因此,土地整理的生態環境影響將越來越大,對土地整理的生態評價顯得尤為重要。盡管當前的土地整理也涉及到生態評價,但更多地是從土地整理后的生態效益進行評價,指標多是森林覆蓋率、水土流失治理面積、土地沙化治理面積、土地污染治理面積和人均綠地面積等。從區域生態學和景觀生態學的角度出發,利用土地利用和覆被變化過程的研究成果,將土地利用和覆被變化研究與土地整理的生態環境影響結合起來,探討土地整理生態評價的評價過程、評價指標和方法,對土地整理的生態合理性進行評判,做到趨利避害、未雨綢繆,這方面的研究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以防止土地整理而產生新的環境問題。土地整理對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土地質量,具有明顯的社會經濟效益[12],由于增加耕地數量和產出仍是目前土地整理的主要動力,社會經濟效益評價集中在耕地增加面積、土地利用率、投入產出率、農產品人均占有率和農產品商品率等方面,缺乏深層次和綜合的評價。粟輝提出城市土地可整理性評價的思路:在城市土地利用現狀分析的基礎上確定評價對象;根據待整理土地的實際情況,從經濟密度、環境優劣度、景觀協調度、功能合理度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對評價對象進行診斷,設定評價指標值;最后,對評價結果進行分析,初步確定待整理土地的整理方向、措施和整理的時序安排[13]。張正峰等人對土地整理的潛力預測和分析、土地整理模式的劃分和分類、土地整理效益評價方法的論證和分析等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4~15]。羅明等人對土地整理對生態環境的評價方法和生態環境影響因素以及區域對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論證[16~17]。高向軍等、龍花樓等從國家、區域及景觀的尺度層面和土地轉型的視角重點研究了LUCC與中國土地整理活動的結合方式與途徑[18~19]。薛繼斌提出了土地整理立項決策評估的指標體系與方法[20]。評價方法方面,李正等運用物元評判模型、韓立達等運用DEA模型、劉世梁等運用景觀連接度模型,評價了土地整理綜合效益[21~23]。因此,對土地整理的社會經濟效益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并提供規范化、操作性強的方法及標準,將為進一步完善土地開發整理活動的規范化、科學化管理提供基礎。endprint
二、研究展望
(一)加強土地整理的基礎理論研究
大多數土地整理研究還是以應用性為主,基礎研究較少,土地整理研究所依據的基礎理論大多是從別的學科借鑒而來,尚未形成自身的核心理論。以問題為導向的土地整理研究,經常將研究焦點集中在土地整理政策的解釋上,忽視了對土地整理科學問題的提煉,難以得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基本理論或原理的研究成果,削弱了解決土地整理問題的指導作用。由于缺乏原始創新性成果,造成集成創新的能力不夠,限制了土地整理研究的發展。雖然土地整理研究是中國土地研究中的傳統優勢領域,但只有通過大量的實證性應用研究,進行歸納與總結,尋找科學問題,分析規律結論,凝練出科學原理,才能形成土地整理的理論和方法體系,進一步建立符合土地整理研究的學術范式,僅如此才能從深層次上指導土地整理的實踐與應用。
(二)重點關注土地整理項目規模化及其資本運作研究
今后應進一步研究東中部糧食主產區基本農田整理、農村空心化下的土地整理利用等重大項目的規模化成效等。同時,強化研究土地整理重大項目的資金渠道來源和分配使用問題,著重對土地整理產業化的新型資本運作模式進行研究。
(三)注重耕地整理質量研究
隨著中國新增耕地比例逐年減少,而用于單位新增耕地面積的資金投入逐年增加,說明通過多年來的不斷實踐,今后應不斷地深化和拓展復墾開發的內涵和外延,大力關注增加耕地、關注產能、關注改善土地整理、關注改善生態環境、關注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環境等更加豐富的目標。
(四)加強區域土地整理評價指標和模式研究
當前,人口增長、資源短缺、生態與環境問題突出等問題,直接或間接地與土地整理的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強化土地整理研究與PRED及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相結合。之前的諸多研究主要以土地整理的實證研究為主,今后應加強土地整理的標準化研究如典型區域評價指標體系及模式等。
(五)重視土地整理的方法體系研究
計算機技術、遙感技術、數學方法在土地整理研究中的應用不斷對土地整理研究方法與手段產生重大的影響。隨著數學與計算機技能的普及,定量化研究已經成為土地整理研究的主流趨勢。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出現了濫用數學統計方法動向,分析模型方法的優缺點和適用范圍研究極為不足。今后的關鍵問題在于先要重點分析清楚因素對土地整理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并對相關數據進行甄別,選擇適當的數學模型進行科學計量,并對結論進行合理解釋與驗證。因此,合理的定性分析應是定量研究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土地整理的復雜性決定了采用從定性與定量綜合集成方法來研究。
參考文獻:
[1] 吳蘭田,彭補拙.中國土地整理模式的多元化探析[J].土壤,1998,(6):305-310.
[2] 劉晶妹,張玉萍.中國農村土地整理運作模式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1999,(11):33-35.
[3] 楊慶媛.土地整理目標的區域配置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03,(1):40-45.
[4] 楊慶媛.西南丘陵山地區土地整理與區域生態安全研究[J].地理研究,2003,(6):698-708.
[5] 涂建軍,楊慶媛,周寶同.農村土地整理產業化模式體系研究[J].農村經濟,2005,(1):33-37.
[6] 丁霞.貧困山區土地整理模式研究——以山亭區為例[J].中國土地,1997,(7):23-25.
[7] 劉筱非.城市土地整理模式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0:78-85.
[8] 馮廣京.中國農地整理模式初步研究[J].中國土地,1997,(6):14-20.
[9] 劉友兆,王永斌.土地整理與農村生態環境[J].農村生態環境,2001,(3):59-60.
[10] 王軍,傅伯杰,陳利頂.景觀生態規劃的原理和方法[J].資源科學,1999,(2):71-76.
[11] 陳百明.土地資源學概論[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290-305.
[12] 謝經榮.整理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J].中國土地,1997,(3):16-17.
[13] 粟輝,邱道持,曹蕾,劉力.城市土地可整理性評價——以重慶市江北區為例[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4):45-51.
[14] 張正峰.中國土地整理模式的分類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7,(4):82-86.
[15] 張正峰,陳百明.土地整理潛力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2002,(6):664-669.
[16] 羅明,張惠遠.土地整理及其生態環境影響綜述[J].資源科學,2002,(2):60-63.
[17] 羅明,王軍.中國土地整理的區域差異及對策[J].地理科學進展,2001,(2):97-103.
[18] 高向軍,羅明,張惠遠.土地利用和覆被變化(LUCC)研究與土地整理[J].農業工程學報,2000,(4):151-156.
[19] 龍花樓,李秀彬.中國耕地轉型與土地整理:研究進展與框架[J].地理科學進展,2006,(5):67-76.
[20] 薛繼斌,吳次芳,徐保根.土地整理立項決策評估的指標體系與方法探討[J].自然資源學報,2004,(5):392-400.
[21] 李正,王軍,白中科.基于物元評判模型的土地整理綜合效益評價方法研究[J].水土保持通報,2010,(6):190-194.
[22] 韓立達,吳懈,左宇.基于數據包絡分析法的土地整理項目效率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12):130-133.
[23] 劉世梁,楊玨婕,安晨.基于景觀連接度的土地整理生態效應評價[J].生態學雜志,2012,(3):689-695.
[責任編輯 劉嬌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