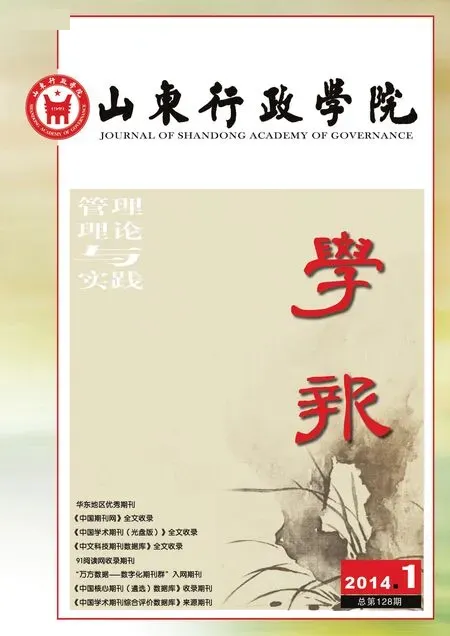新刑訴法視野下律師調查取證的風險防控
陳玉忠
(山東行政學院,濟南250014)
調查取證權是律師刑事辯護資源的主要獲取機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效行使防御權的保證和訴訟理性的體現[1]。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新《刑訴法》”)對刑事辯護制度進行了重大修改和完善,賦予律師在偵查階段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后以辯護人的訴訟法律地位,在立法上強化了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這些制度的出臺,進一步完善和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對于推進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具體到律師業務,新《刑訴法》對辯護律師調查取證也提出了新的挑戰,不是降低而是有可能加大了潛在的職業風險,對此必須認真對待、加以重視。
一、新《刑訴法》律師調查取證制度的改進
新《刑訴法》在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方面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偵查階段律師享有調查取證權,但有很大限制
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業務限于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訴訟、申告以及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并沒有得到立法上的全面確定。律師以辯護人的訴訟地位出現是“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原第33條),相應地,辯護律師自該階段開始享有閱卷權、調查取證權。2012年新《刑訴法》第一次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聘請的律師是以辯護人的訴訟地位出現(第33條),也就是說將律師的辯護人身份從審查起訴階段提前到偵查階段,按照辯護人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第35條),辯護律師取得了在偵查階段進行調查取證的權利。
當然,與刑事訴訟其他階段相比,律師在偵查階段時的調查取證權是有限制的,或者說其內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該法第36條對偵查期間辯護律師的業務范圍作了更加具體的規定,一方面,與原第96條相比,辯護律師不僅可以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而且增加了向偵查機關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的權利(第159條更加明確規定了辯護律師在案件偵查階段有提出辯護意見和要求的辯護權利);另一方面,按照第36條規定,辯護律師在案件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至少在內容方面,好像又沒有涉及到,立法上模糊規定意味著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在實踐中還存在不少體制上的障礙。該法第40條規定了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佐證了辯護律師接受委托后在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是有限制的、部分的,涉及到其他方面的調查取證權立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同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51條同樣規定了人民檢察院偵查過程中辯護人擁有收集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的權利。
新《刑訴法》賦予律師在偵查階段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后以辯護人的訴訟法律地位,對于我國法制建設具有很重要的實踐意義。及時、有效地搜集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將其告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可以彌補偵查遺漏,使不應入罪的案件在盡早訴訟階段終止,在某種程度上說,偵查階段辯護律師調查取證對于減少冤假錯案發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然,也必須認識到,與其他訴訟階段相比,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還是部分的、有限制的。那種盲目地認為律師調查取證權在不同訴訟階段是無區別的觀點是片面的,會隨時讓律師的職業風險不期而至,甚至從天而降,為律師本人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
(二)新《刑訴法》實施后,律師調查取證的職業風險是否有所改觀還須進一步觀察
新《刑訴法》并沒有排除律師調查取證的職業風險,但力圖從小處著手,降低辯護律師的職業風險,為刑事辯護創造良好的環境。
首先,新《刑訴法》第42條與1996年刑訴法38條相比,主體由“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改為“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從形式上看,力圖弱化“律師偽證罪”的特定主體的窘況——“任何人”而不是特指規范律師的行為。當然,司法實踐中該條與刑法第306條就像懸在律師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如果真能借此改善辯護律師的職業環境也是我國法治建設的幸事。
其次,在界定“律師偽證罪”的客觀要件“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中刪掉了“改變證言”,直接規定“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也就是說,從字面上解釋,“改變證人證言”行為并不是構成律師偽證罪的客觀要件;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引誘證人作偽證”、“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涵蓋、包括“改變證言”行為,這項修改更多在字面上進行規范而已,實踐中律師的職業風險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
再次,在新《刑訴法》第42條第二款,增加了“律師偽證罪”承辦機關的規定,“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以及“及時通知律所或者所屬協會”。2012年六部委《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第9條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細化規定,“以外的偵查機關”是指“上一級偵查機關或者由其指定其他偵查機關立案偵查,同時不得指定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的下級偵查機關立案偵查”。立法意圖運用“任何人不得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公正的原則,通過在制度上回避原偵查機關達到對“律師偽證罪”立法規定不進行大修改的基礎上運用程序公正改善律師執業大環境的目的。當然,實踐中通過上級監督下級的途徑實現“律師偽證罪”責任追究機制的公平正義,有待于今后實踐觀察。
二、刑事律師調查取證職業風險的防范措施
如何避免因調查取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風險,這是一個理性的職業律師必須思考和研究的現實問題。近幾年,律師在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辯護過程中,因涉嫌偽證罪被拘留、逮捕甚至判刑的新聞屢上報端,例如李莊案、北海四律師被拘案等。在如此大環境下,律師從事刑事辯護業務尤其要充分意識到調查取證存在著極大風險,一定要慎之又慎,安全執業總是第一位的。
(一)律師調查取證要時刻繃緊風險防范意識之弦
第一,不要直接向被害人或者其家屬或者被害人提供的證人收集證據,以免被反誣,如確屬必要,則盡可能多的向法院、檢察院申請收集證據和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方式收集證據。對于律師能夠識別的偽證,不要交給法庭,防止陷于當事人的圈套。有些被告人或者其家屬為了“撈人”不惜一切手段,例如事先“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然后請律師調查取證,或者讓律師把證人證言交給法庭,結果可能是律師栽進去。
第二,律師取證要有程序意識,嚴格遵守程序法規定的取證程序。刑事訴訟法規定,律師可以向證人或者其他單位和個人取證,但是前提是必須經得相關人的同意才可以進行。律師制作詢問筆錄,就必須記載證人是否同意,就必須亮明律師身份,不然就會構成自己執業的危險[2]。所有調查材料均應有律師對被調查人要求如實提供證言、作偽證應負法律責任和被調查人同意接受調查的記載,在調查筆錄制作完畢之后,應交證人仔細核對,并在修改處加蓋證人的印章或證人按指紋確認,最后由證人簽名或蓋章,同時簽署或由他人代書說明“筆錄已看過或已向其宣讀過,與其所述無誤”的意見。
第三,律師取證時不宜一個人,至少由兩名以上的人員進行,可以由一名執業律師和一名律師助理進行,以免證人將偽證責任推給律師而無旁證。一方面,律師兩人調查可以相互配合、相互監督,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避免違法調查取證;另一方面,可以相互進行照應,一旦發生風險時,可以相互證明調查取證工作的合法性。
第四,律師調查取證時能夠錄音錄像就錄音錄像,請公證處一起固定證據也是個不錯的辦法。在中立的公證人員在場見證下,提供法定的公證書證明,很大程度上可以肯定律師調查取證的合法性。但是,不能將公證見證和錄音錄像作為非法取證的手段,認為有公證和錄音錄像就律師就可避免風險了,縱使做的再天衣無縫,也終有被查究的可能[3]。
(二)遵守職業紀律,律師調查取證不得泄露國家秘密
新《刑訴法》賦予律師自偵查階段開始就以辯護人訴訟地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務。在偵查階段,律師可以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在與犯罪嫌疑人會見中,可以“不被監聽”地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及其案件相關情況;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這些內容在未公開之前,根據有關國家法規的規定,絕大部分屬于國家秘密(例如,公安部《公安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定》等)。有資深律師得出一條結果:刑事案件中,偵查情況和案卷材料均屬于國家秘密,不得泄露[3]。由此可見,每個刑事案件,律師調查取證的案件有關內容均可能成為泄露國家秘密罪的規范內容。如律師從檢察院復印案卷后,在接待當事人過程中,當事人趁律師不注意時,用手機輕易拍走幾份證據材料,那么律師有可能陷于為過失泄露國家秘密罪的嫌疑。因此,律師在調查取證工作中了解到的犯罪嫌疑人的詳細情況、會見筆錄、在逃同案犯、關鍵證人、關鍵證據的重要內容不能告知家屬,讓家屬查閱、復制和摘抄,一旦發生家屬利用得到的案件信息串供、毀滅證據、證人改變證言、案犯逃匿等嚴重結果,以泄露國家秘密罪追究律師的法律責任的風險隨之而至。在遵守職業紀律與家屬溝通方面,一定要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既要向家屬解釋律師的職業道德,國家秘密的法律規定,律師違法的后果,又要研究提高與家屬的溝通的技巧和水平,創造和諧、安全、愉快的執業環境。
(三)對于風險大的主觀證據一定要慎之又慎
新《刑訴法》第48條規定的法定證據中,物證、書證、鑒定意見、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客觀性較強,可變性較小,律師取證的風險較小,律師可以依法謹慎取證。例如證明被告人不在現場的機場登機記錄、貪污案件需要取證的會計賬簿、銀行匯款憑證、工商局登計檔案,律師應當積極、盡力地依法調查取證。
對主觀性證據而言,如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客觀性差、可變性強,律師一定要認識到只要接觸一定就有風險。對于偵查機關已經調查過的證人,律師要認真審查其是否改變證詞,其改變證詞的目的是否系有意包庇犯罪嫌疑人而作偽證。如果確實存在作偽證的可能,則應當立即拒絕調查。如果證人對犯罪嫌疑人作不在場的證明,而卷宗內有數人已證明該犯罪嫌疑人在場,則要審查證人是否存在作偽證的可能性[3]。
對致力于為被告人辯護的律師而言,調查主觀性證據可能是個“囚徒困境”,不取證沒把握,取證又有風險。對一個有責任心的刑事律師而言,始終存在一個職業道德與職業風險相糾結的兩難境地。有沒有一個更好的辦法,既規避風險,又能取證?律師對人證最好的解決之道即按照刑事訴訟法第41條規定,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四)控方證人盡可能少碰,律師可以申請法院通知證人出庭為宜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5條的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為實現上述職責,律師不可避免地在刑事訴訟中千方百計地收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證據,研究、琢磨、提出對其有利的各種理由。而控訴機關與此相反,公訴人為了追究控訴的成功,也總是尋找列出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和理由。按照目前的體制,公檢法辦案人員的業績考核與案件有著重要的關系,“錯案責任追究”使得公安拘留、逮捕的案件,只要不起訴就是錯案,起訴了不做有罪判決對檢察機關也是錯案。錯案影響辦案人員的福利、待遇甚至政治生命,這就是刑事律師職業風險存在的一個大的制度環境。其實,“律師輕易就調查控方證人,在香港也是非常危險的,雖然不會定罪,但會懲罰律師”[4]。大部分國家強調一旦發生爭議,證人筆錄就沒有法律效力,證人要出庭,律師遇到這種情況不會去調查,而是申請法院傳喚證人出庭作證。因此,刑事訴訟中證言的筆錄中心主義與不合適的司法辦案人員獎勵和懲罰機制糾纏在一起,使得律師一碰控方證人,面臨的風險可想而知。筆錄中心主義產生的大問題,必須用證人出庭來解決。律師申請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通過法庭詢問、質證達到辯護的目的是比較好的解決辦法。如果多次申請證人出庭,法院依然未予采納,對其采取相應的對策,立即以真偽難辨為由請求法庭排除證言筆錄。
[1]賀紅強.論我國刑事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權的困局與突圍[J].海峽法學,2011(4).
[2]段建國.大律師法庭攻守之道[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徐宗新.刑事辯護實務操作技能與執業風險防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18,93,114.
[4]陳瑞華.刑事辯護的前沿問題[EB/OL].華律網,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