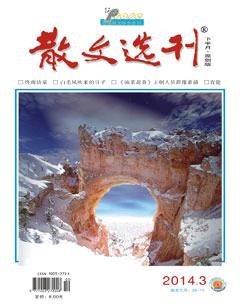城垣之重
天疆

夜靜得出奇,那顆星宿仿佛看懂了我的心思,跳動著,想下界來與我交談些什么。
法海寺就在城中心,那里仍有僧尼,木魚聲聲,間或著傳來,就如我晨來時看到的景象,香客盈門,一撥撥響起,又一撥撥落下,歸入凡塵,落入心里,直至夜更,信念是老城的香火。據記載這座寺院是宋真宗四年時就已經建造的廟堂,多少年來香火不斷,算來,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只可惜戰火損毀不曾斷跡,卻在“文革”期間破壞殆盡。如今,雖然城市遷址了,但是,老城人還是懷念這座寺,那些一心向佛的香客陸陸續續自籌資金,捐資重建了這座佛寺。
在它的近旁,是一座城隍廟,橫聯寫著:“密縣城隍紀信爺誕辰2217年”慶詞。紀年進入我的眼簾,讓我詫異,這城如此之老,會留下多少中原的痕跡呢,紀信是誰?歷史像一串燈謎,閃著謎云一樣從我眼前飄過。有些事情不入時流,自不如歌星閃亮,而老城是有記性的,故事都藏在碑文貼字的暗處,與城市叢林一樣要耐心尋找,等待眷戀它的過客打馬走過。“城隍”這個詞本已經過于老舊了,很多人都不太懂,我其實也并不太知曉其中的個就。今日看到紀信爺,不免更是覺得蹊蹺。有白須長者講來,我才略知一二。《易泰》有“城復于隍”之說;《禮記》曰“天子大臘八”是說臘祭八神,其七水墉相傳就是后來的城隍;而密縣的紀信爺據傳是楚兵圍漢兵與城臬之時的事情。當時,紀信事漢,為將軍,城急民不得出,紀信為救民于水火,事楚王來日于東城請降,楚人以為實皆往東城,紀信隨開西門走,后路遇羽,火焚紀信。漢王即位后,追封紀信為天下城隍。有《火焚紀信》折子戲,常常在城隍戲臺上演,歷久不衰。
走在四向歸聚的舊街上,城垣歸入歷史原來都是用舊瓦蓋屋的。三兩層的院子不大,門對門,院臨院,卻比鄰而居。此時,正是桃樹、核桃下果時節,一些院落的門前屋后可以隨手采摘。綠茵層層,漫過了屋頂,陰著宅院,還有那些耐不住地下寂寞的根須,盤根錯節地順著地表墻根鉆出了石街的路面。那些千年的風千年的雨,此刻沒有到來,都停在云層里,醞釀著,候著氣象,一挨時機成熟,就會順著瓦當流入地面,鉆進泥土,給果實以養分的水頭。看多了,相信風塵是摧毀人心的力量。無緣由地想著,這個方圓大約在5平方公里的城池,其實在中原多如牛毛,我來時,總是沖著老縣衙而來。聽人說,市政府為了留景,很花了些銀兩。大堂肅靜,驚堂木與縣衙寶座一應俱全,堂鼓都有,沒有喊冤的擊鼓人,所以,空留余音,面對“正大光明,明鏡高懸”的匾額,很多的想象皆從做舊的器什中冒出來,小白菜,竇娥冤,還有那些一茬茬的縣衙們……衙門景觀一天沒有開放,來的人太少,走到跟前,門閂緊扣。除了門前的兩尊石龜斷殘著頭顱尚可一睹尊榮,前堂后院都是人為翻蓋的痕跡,無法叫出管理人員。這些政府投資的做舊古跡,與臨近的法海寺、城隍廟相比,人流還要少得多。新的舊不了,舊的在時間的長河里一點點灰飛煙滅。而那些由民間集資修繕的法海寺和城隍廟卻能留得住人們信仰的目光,雖然規模很小,卻總有靜客入堂拜奉,前來燒香。
忽然冒出些無由的聯想,想到的是老城的形象,它就像我在寺院里看到的彌勒菩薩,笑盈盈地向我走來。它笑迎風雨,樂觀豁達,禪透世道,有眾多的弟子跟隨其后,一步步地緩緩走來,走成一座神圣的殿堂,走向無為的安逸。外觀或許就是街面上某一位嬉戲無常,慈眉善目的濟公,它淡泊名利,裝滿生存的智慧和勇氣,吹散無數迎面而來的瘴氣,高傲地揚起頭顱,迎接殺戮。一茬茬再生,封殺一陣陣遠來的塵泥。居水而坐,神情淡定,禪悟,解惑,告慰,理順,耳聰,行俠大義。原來,老城就是一座碑,無法否定了。
舊的,新的,去去來來,毀的毀,埋的埋。在建的,還有很多理由再建,在記憶中挖掘。如今,留下些殘片,那也要修舊翻新,這是事實。去的,記著那一段老早的建城歷史。新的,寫滿了密密麻麻捐款人的姓名,張三李四,無從知曉。千百年后,可能還會是一個謎,留待史學家們再去考證。
洪荒戰亂如果歸結不完我的祖輩,又怎能描寫的了一部清晰的城郭歷史呢?這是《清明上河圖》稀世的真正因由。翻一卷畫容易,翻一部城池,只怕要挖地三寸,留出一門考古學說來書寫我的論文。廢墟上的廢墟,就是我的家園。靜靜的明月,朗朗的乾坤,一樣的太陽,永遠在移動著一寸寸光陰,刨出一道石,移動一寸瓦,力量比對著。一段段時光,走過了唐宋元明清,走過了一個個模糊不清的身影,不曾了結。
如今,還會造就城垣,摩天的,現代的,成為城隍,成為信仰中的法海。精神之存,便是能量,時髦的當下術語,就是所謂的正能量,一遍遍地交代,一個個地感化,去教化后人。多了,歷史都會成書,經卷一樣地留著,紀信爺一樣地供著,誰能說中原無人,誰能說我的理解會有誤差呢?
星星累了,不再下界與我共話,眨著眼,在等待著下一個凡客。
責任編輯: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