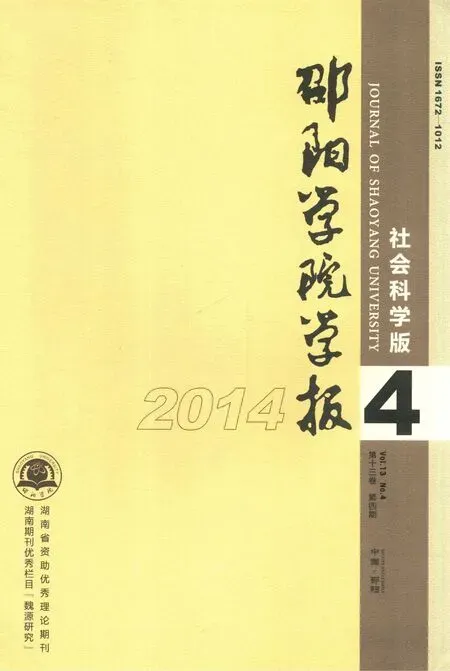我國著作權法中錄音制作者權及其完善研究
鐘麗瓊
(中國政法大學 民商經濟法學院,北京 100088)
《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在體例上的一大變化是突出了傳播者的相關權——也即傳統稱為鄰接權的這一類權利的地位和作用。相關權是作品傳播者的權利。一般地說,作品要為世人所知,發揮其在建設精神文明領域的作用,都要依賴傳播者。例如,文字作品、美術作品要出版者出版后才會有大范圍的流通;戲劇作品、曲藝作品、舞蹈作品等要通過表演者的表現和詮釋;音樂作品、視聽作品也需要表演者、錄音制作者、廣播電臺、電視臺的通力合作才能極大地滿足和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當然,傳播者也依賴作者創作出好的作品才有用武之地。可見,用源與流來形容作者和傳播者的關系是非常恰當的:作者創作出好的作品是“源”,傳播者將作品傳播出去是“流”,二者對于傳承中華文明、發揚文化傳統、發展精神文明是不可或缺的。本次的《著作權法》修改中突出和加強傳播者的相關權即可見一斑。
錄音制作者權一般是承載于音樂作品上的相關權,也可以針對其他聲音進行錄制而產生。模擬錄制技術的產生催生了唱片產業,使欣賞音樂從歌劇院搬到了家里;而電子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發展則使人們能夠隨時隨地欣賞音樂,家庭、學校、商場、辦公樓到處都能聽到音符的流動,廣播、電視、網絡上也充斥著各種風格的音樂,還如在線收聽、免費下載、手機播放音樂等。可以說,我們的社會生活已經離不開音樂,沒有音樂的生活將索然無味。但是,我們在欣賞美妙音樂的同時,不應當忽視其背后所承載的著作權人和相關權人的權利,尤其是在當今社會盜版充斥、普通民眾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強、法律規定不完善的社會現狀下。也正因為如此,《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的征求意見稿第1稿一經公布,其第46條即引起了包括詞曲作家、歌唱家及唱片制作者在內的音樂界的軒然大波。本文即跟隨本次《著作權法》修改的步伐,梳理錄音制作者權的產生背景、發展和現狀,結合國際條約及各國著作權法中的相關規定,對修改過程中的熱點問題進行剖析,重點討論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錄音制作者的二次使用獲酬權以及數字技術背景下錄音制作者權的保護。
一、錄音制作者權與技術發展
技術的發展總是引發社會利益格局的變化,相關利益集團在技術發展的過程中總是希望通過法律確認并保護其利益。[1](P108)正如印刷技術的出現催生出了盜版市場,作曲家們希望通過復制權來保護紙面音樂作品;音樂機械的發明使音樂作品通過機械再現成為可能,作曲家們又將其權利成功擴大到機械復制權;錄音技術和傳播技術的發展逐漸危及到表演者和錄音制作者的生存,①根據國際勞工組織1939年出版的報告,1932年到1936年間,音樂等藝術行業的表演者進入前所未有的失業高峰期,美國、法國、日本與奧地利都有數以萬計的表演者失業,比如:1936年日本,音樂工作者的失業率為41%,而維也納音樂工作者的失業率更是高達90%。國際勞工局:《演奏者在廣播節目、電視及聲音機械復制方面的權利》,1939年6月。轉引自[西班牙]德利婭·利普希克:《著作權與領接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0版,第277頁。因此,錄音制作者保護其錄音制品的訴求產生。音樂創作者、傳播者及相關出版商圍繞錄音技術而產生的控制作品新的利用方式的權利訴求也不斷的隨著技術在發展。
(一)錄音制作者權的出現
愛迪生在1887年發明的留聲機開創了人類錄音歷史的先河。而路易和奧古斯特兄弟的電影放映機、赫茲和馬可尼的收音機使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錄音技術發展到新的高度。就如同印刷機打破作者道德主張與經濟主張之間的平衡一樣,錄音技術的廣泛應用迅速改變了音樂產業中原有經濟利益的平衡。[2](P22-23)20 世紀上半葉,模擬復制技術的飛速發展使未經許可的翻錄唱片和磁帶現象普遍出現,錄音制品還成為廣播電臺、電視臺免費的節目素材。錄音制作者通過對錄音制品的銷售來支付其獲取作者與表演者的許可費以及對錄音設備與錄音技術人員的投資,并獲取利潤的市場秩序被打破,這種經濟利益格局的改變使錄音制作者(一般為唱片公司)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根據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的權利訴求,德國(1910年)、英國(1911年)、奧地利(1920年)、瑞士(1922年)、意大利(1941年)等國家的著作權法相繼開始保護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的權利。[3](P222)也由于這些國家的努力,在 1961 年制定的第一個關于領接權保護的國際條約——《保護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羅馬公約》(簡稱《羅馬公約》)中對錄音制品的保護作出了規定,只是沒有明確提出“錄音制品制作者權”這一概念。在1971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主持下締結的《保護錄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經許可復制其錄音制品公約》(簡稱《錄音制品公約》),以及1995《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協議》)中都是繼承《羅馬公約》的規定。直到1996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簡稱WPPT)中才明確提出“錄音制品制作者權”。
(二)錄音制作者權的發展
錄音制品制作者權隨著技術的進步逐漸由一種防御性的保護發展成為專有權,由復制權、發行權擴張到出租權、向公眾提供權以及二次獲酬權等。《羅馬公約》只要求成員國承認錄音制品制作者有權授權或禁止未經許可的復制行為,同時保證錄音制品制作者和(或)表演者在廣播和向公眾傳播錄音制品的情形下享有獲取報酬權,但各國在加入公約時可以對后一種保護作出保留。②《羅馬公約》10條、第16條這種防御性的保護隨著盜版唱片和光碟的猖狂而逐漸顯得捉襟見肘,錄音制作者迫切需要通過專有權來控制未經許可的復制和發行行為,于是錄音制作者的復制權和發行權得以產生。而基于發行權權利用盡的原則,錄音制品的出租漸成氣候,如果不對其予以控制,則侵占了錄音制作者的市場利潤,錄音制作者于是成功將出租權納入麾下。而在數字技術時代,通過網絡傳播音樂作品更是以其快速性和范圍的全球性而再次打破音樂市場的格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起草WPPT時就指出:“音樂工業和唱片零售店將會被向公眾開放、通過網絡向公眾家用計算機直接發送音樂產品的數據庫所取代”。[1](P108)于是各國參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簡稱WCT)第8條的“向公眾提供權”紛紛在各國國內法中規定了錄音制作者的“向公眾傳播權”③如英國2003年的《版權及相關權法令》規定:向公眾傳播作品,是指以電子形式、通過有線或無線的方式,使公眾可在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獲取作品的行為。、“信息網絡傳播權”④如中國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即是對這一權利的落實。,或對“發行權”⑤如《美國版權法》第106條所指的發行權即可認為包括經由互聯網傳輸作品的行為。進行擴充解釋。
我國雖然是在1992年才加入《錄音制品公約》,但實際在1990年的《著作權法》中即已規定了錄音錄像制作者的許可權和獲酬權。在2001年修改《著作權法》時更是參照了WPPT的規定,賦予了錄音制作制作者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和向公眾提供權。2006年出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進一步明確了錄音制作者向公眾提供權的涵蓋范圍和限制情形。在本次的《著作權法》修改中,關于錄音制品的法定許可、錄音制作者的二次獲酬權以及網絡信息環境下錄音制品的保護問題更是錄音制作權一次與時代和現實接軌的發展。
(三)錄音制作者權保護制度的現狀
錄音制作者權之所以在本次的修法中被分外關注就是在于唱片產業的萎靡和錄音制作者權保護的現狀不甚理想。由數字技術帶來的盜版技術使在線音樂成為網民免費的午餐,免費下載是中國網民在思維和行動上都難以撼動的習慣,而通過技術壁壘和付費音樂模式給錄音制作者帶來的收益也是杯水車薪。當然本次修法對于錄音制作者已有的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并沒有做出實質性的修改,但不可否認錄音制作者的這些權利在實踐中遭遇的困境。
首先是復制權和發行權。復制權和發行權是錄音制作者的基礎權利,任何對錄音制品的利用行為都是以復制和發行為基礎,錄音制作者通過復制和發行錄音制品來獲取收益。但是由于免費在線音樂和盜版的猖獗,錄音制品的發行量逐漸遞減,其所提供的利潤無法維持錄音制作者正常的經營。其次是出租權。出租權是指錄音制作者對錄音制品的租賃行為予以控制。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公眾欣賞音樂的方式,唱片租賃行業與錄音制作者呼吁授予出租權的時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這從社會上所殘留的不多的音像租賃店即可看出,所以錄音制作者從錄音制品的出租所得的經濟收益不甚樂觀。至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狀況則更加堪憂。國內現有的提供MP3下載的音樂網站數以千計,而合法經營的不足半百。信息網絡傳播權本是在互聯網時代規制經由互聯網以互動的方式向公眾提供錄音制品的行為,卻因為互聯網的難以控制性反而深受網絡免費下載的侵害。錄音制作者寄予通過網絡傳播權獲取收益的期望也難以實現。
二、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存廢之爭
現行《著作權法》第39條第3款規定了制作錄音制品的法定許可。修改草案第1稿對這一條進行了修改,其第46條規定:錄音制品首次出版3個月后,其他錄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條規定的條件,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其音樂作品制作錄音制品。該征求意見稿已經公布,即引起了音樂界和法學界的關注和討論。音樂界人士通過各種媒體反對其對修改草案第46條的規定,認為這些新的音樂著作權制度徹底剝奪了音樂人的權利,將使他們成為集體管理機構謀利的工具。在音樂界的反對聲和巨大的輿論下,立法者在修改草案的第2、3稿和送審稿中均刪去了制作錄音制品的法定許可制度。法學界對于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的看法則有褒有貶,關于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的存廢之爭引起了一場唇槍舌戰。
(一)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的產生背景
正如上文所言,在機械錄制技術發展之后,音樂作品著作權人取得了“機械復制權”,即音樂作品著作權人享有授權將其音樂作品固定在任何形式的錄制品上的專有權。在20世紀初,唱片的復制技術掌握在少數有實力的大唱片公司手中,唱片的出租市場也尚未形成。這樣,在大的唱片公司通過與音樂作品的版權人簽訂專有許可協議后,借助其市場壟斷地位控制了唱片市場的價格。為了使唱片市場形成合理的競爭環境,將唱片的價格拉回到合理的水平,以保證社會公眾欣賞音樂的渠道暢通,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版權法修正案》率先對“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做出了規定。也即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的產生是為了防止唱片市場被壟斷。因此,是否應當在《著作權法》中保存或廢除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也應當從這個目的出發。
(二)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的存與廢
贊成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的出發點即是該制度可以促進競爭,降低唱片行業的壟斷。且該制度經過長時間的存在,已為音樂作品的版權人、錄音制作者所熟悉和接受,并形成了適應該制度的商業模式。有學者指出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能使不同的錄音制作者可以選擇不同的表演者詮釋同一部作品進行錄制,公眾可以欣賞版本各異的錄音制品,避免著作權人與某個錄音制作者訂立專有錄制合同、造成版本單一的狀況”;[4](P206)該項法定許可不但能夠達到反壟斷的立法目的,而且已成為唱片業商業模式的基礎,為利用他人音樂作品制作和發行唱片提供了穩定的法律預期。[5]
反對保留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的學者認為該制度所發揮的防止壟斷的作用可以通過其他的方法如反壟斷法來阻止版權人濫用其機械復制權。英國通過自身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其在1956年著作權法第12條第(6)款賦予錄音作者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權,但是在1988年英國著作權法修訂時取消了這一條款。[6](P193-194)其次,現行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的“但書”規定也飽受詬病。因為一旦著作權人在首次發行錄音制品時作出聲明,那么該法定許可制度則成了擺設。從法理上說,現行《著作權法》第40條對音樂著作權人的限制可被歸納為“默示許可”(Implied License),而非“法定許可”(Statutory License),即只要權利人未明確表示不許可,那么在其音樂作品被錄制為錄音制品并發行后,其他錄音制品制作者即可在無須征得著作權人許可的情況下利用該音樂作品再行制作錄音制品。[7](P295)
(三)小結
應當說,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的出發點值得肯定:從市場的角度說可以防止壟斷,鼓勵更多的錄音制品通過不同表演者的詮釋進入市場,這也是文化繁榮的一種表現;從音樂作品著作權人的角度來說,雖然法定許可制度剝奪了權利人的許可權,但是其報酬權并沒有喪失,而且不同制作者的錄音制品進入市場是對音樂作品的宣傳和傳播;從錄音制作者的角度來說,在向音樂作品制作權人支付了報酬后可以對已經合法錄制的錄音制品再行錄制,簡化了制作程序。從修改草案的第1稿看,立法者對于該制度也是存保留態度的,之所以在之后的幾稿中刪除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制度,很大部分是輿論的壓力。因此立法者應當考慮的是在刪除本制度后,對于該制度的功能應當通過怎樣的途徑來實現。
三、錄音制作者的二次使用獲酬權
應當看到,在新科技和新媒體的刺激下,音像產業依靠實體唱片銷售的傳統經營模式面臨來自消費者和侵權者的雙重考驗。消費者不愿購買實體唱片而更愿意從網上免費下載,而網絡環境下的侵權行為具有違法成本低、侵權范圍廣以及難以察覺的特點。在已有法律框架下錄音制作者所享有的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同樣因為網絡媒體的出現和盜版產業的猖狂而難以實現其功能。錄音制作者在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精力創造出的錄音制品,豐富了社會公眾的精神生活并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的同時,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回報,無法刺激錄音制作者創造出更加優秀的音樂制品,音像產業處于一個尷尬的地位。因此,有錄音制作者欲尋求廣播權和表演權的保護,以走出音像產業的困頓之狀。
(一)專有權或是獲酬權
對于是否賦與錄音制作者廣播權和表演權,相關人員的看法不一。唱片公司和中國音像協會是支持賦權方的主要倡導者。其主要理由是:首先,WPPT第15條規定了表演者和錄音制品制作者應享有因廣播和向公眾傳播獲得一次性合理報酬的權利;其次,表演者和錄音制作者對推動錄音制品的面世投入巨大,理應和作者一起分享利益的果實;最后,由于上述音像產業所遭遇的盜版危機和困頓之狀,錄音制作者的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實質意義不大,錄音制作者在現有的法律框架的保護下無法收回其成本以創造出更好的音樂作品。[8]強烈反對授予錄音制作者表演權和廣播權的是同濟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的張偉君教授,他的觀點是:盜版猖獗和非法網絡傳播是造成當前唱片業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這是既有權利沒有得到維護,而絕對不是因為權利不充分導致的。其次,雖然我國加入了WPPT,要履行WPPT的條約義務,但其第15條第3款同時允許締約方聲明將根本不適用這些規定,這正是我國在加入WPPT予以保留的條款。再者,《羅馬公約》和WPPT也沒有規定專有的廣播權,只是規定了錄制者享有“廣播”和“向公眾傳播”的“一次性合理報酬”權。[9]對于這個問題的關注也引起了立法者的關注。在本次《著作權法》的修改案中,立法者采納了比較折中的辦法,賦予錄音制作者對錄音制品二次使用的獲酬權。
實際上,我國1990年的《著作權法》曾經對錄音制作者的廣播權有過規定,其第43條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非營業性播放已經出版的錄音制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表演者、錄音制作者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也就是說,只要是營業性播放就應該取得錄音制作者許可,并支付報酬。但是2001年修改通過的現行《著作權法》取消了錄音制作者的廣播權,而規定為錄音制品的法定許可。這就出現了上面所討論的錄音制品法定許可的存廢之爭。
(二)“二次使用”行為之界定
如果用一次使用指代錄音制品的發行、銷售,那么二次使用(Secondary Uses of Phonograms)即是指錄音制品在發行、銷售后,廣播組織在節目中播放錄音制品以及其他合法購買者將錄音制品用于在營利性場所或娛樂性場所播放的行為。換言之,“二次使用”,是指將錄音制品用于公開表演和播放。公開表演的用戶主要是飯店、酒吧等娛樂場所,播放的最大用戶則是廣播電臺電視臺。[10]“二次使用”一詞其實是源于《羅馬公約》第12條的表述,公約將為商業目的發行的錄音制品用于廣播和向公眾傳播概括為錄音制品的二次使用。這里的廣播,不僅包括傳統的無線廣播電臺,還包括電視、衛星廣播等多種形式。而“向公眾傳播”,即是指利用除上述廣播以外的任何媒體向公眾播送表演的聲音或以錄音制品錄制的聲音,如餐廳、酒店、娛樂場所或其他公共場所通過安裝有線播放系統或者通過擴音器播放錄音制品或轉播電臺、電視臺節目,傳送給一定范圍內的公眾。對“二次使用”行為進行報酬權的規制,授予錄音制作者對錄音制品這些新的利用方式進行控制的權利,是從經濟上改善唱片行業所開辟的新道路。
(三)國際條約中的二次使用獲酬權
《羅馬公約》第12條規定:如果為商業目的發行的錄音制品或這種錄音制品的復制件直接用于廣播或任何方式的向公眾傳播,使用者應該向表演者或錄音制作者或向二者支付單一的合理報酬。在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情況下,國內法可以規定這種報酬的分配條件。WPPT第15條“廣播與向公眾傳播的報酬權”規定了與《羅馬公約》內涵基本一致的錄音制品二次使用權,即:“對于直接或間接使用為商業目的發行的錄音制品進行廣播或向公眾傳播,表演者和錄音制作者應該共享單一的報酬權;締約方可以在其國內立法中規定,對使用者主張該單一的報酬權可以是表演者、錄音制作者或兩者,締約方可以在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沒有約定的情況下,規定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分享該單一報酬的條件;任何締約方可以再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交存通知時,聲明其僅適用該條中的某些使用,或將以其他方式對這些使用進行限制,或聲明其根本不適用這些規定。”相對于《羅馬公約》,其進步之處表現在:權利人明確規定為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共同享有對錄音制品廣播與向公眾傳播的報酬權,至于由誰對該權利進行主張以及具體的分配辦法則由國內法進行規定;涵蓋的范圍更廣,使用方式包括廣播和向公眾傳播,無論是直接使用還是間接使用,都需要向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支付報酬,將有線的轉播之類的間接使用納入了保護范圍;作為該條約協調信息社會著作權問題的特色,將通過網絡向公眾提供的錄音制品視為商業目的發行的錄音制品。
由于上述兩個國際公約允許對錄音制作者的二次使用權作出保留規定,因此,這兩個公約都未能建立起一個有關錄音制品二次使用權的全球最低標準,從而導致世界各國著作權法對錄音制品二次使用權的規定存在較大差異。比如在享有權利的性質上有規定為專有權,①巴西、印度、英國等國家選擇全部或部分采用專有權的方式配置錄音制品二次使用權的模式。有規定為獲酬權;在享有權利的模式上有規定為表演者和錄音制作者共享,有規定為表演者或者錄音制作者之一獨享。②如《日本著作權法》的規定就是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對其錄音制品被用于廣播時,分別享有報酬權,而《印度版權法》就規定錄音制品向公眾傳播權(僅為遠程傳輸)就由錄音制作者單獨享有,并不與表演者分享。
(四)《著作權法》修改中的二次使用獲酬權
在《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過程中,錄音制作者的二次使用獲酬權幾經修改。《送審稿》第40條規定:“以下列方式使用錄音制品的,其錄音制作者享有獲得合理報酬的權利:(一)以無線或者有線方式公開播放錄音制品或者轉播該錄音制品的播放,以及通過技術設備向公眾傳播該錄音制品的播放;(二)通過技術設備向公眾傳播錄音制品。”其使用方式由第1稿的“用于無線或者有線播放,或者通過技術設備向公眾傳播”擴大到第2、3稿以及《送審稿》的“以無線或者有線方式公開播放錄音制品或者轉播該錄音制品的播放,以及通過技術設備向公眾傳播該錄音制品的播放”,將對錄音制品的公開播放、轉播和廣播行為納入到二次使用的范疇;在報酬權的主體上也由第1、2、3稿的“表演者和錄音制作者共同享有”最后定為《送審稿》的“錄音制作者享有”。對于權利主體的確定,立法者的考量不得而知,但這也是符合《羅馬公約》規定的。這或許是表演者一般隸屬于唱片公司——即錄音制作者,因此在簽訂合同時已將自己的權利讓渡給錄音制作者;又或是表演者在和錄音制作者簽訂授權錄制合同中可以對報酬自由協商,為充分尊重表演者和錄音制作者的自由意志,表演者可以通過合同享有分享報酬的權利。但是,《送審稿》中對錄音制品二次使用獲酬權的規定也并不是很完美。比如《羅馬公約》和WPPT都規定了二次使用是一種商業性質或目的的使用行為,這樣規定是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其次,有學者認為也應當對錄音制品的二次使用獲酬權予以一定的限制,如為教學與科研目的對錄音制品的廣播與使用、宗教、民俗儀式以及在以慈善與福利事業為目的的活動中對錄音制品的廣播與表演等,[2](P180-183)也有學者認為“對表演者、錄音制品制作者準許或禁止二次使用錄音制品的權利進行限制是因為必須保護錄音制品的商業化及保護作者向公眾傳播其作品的專有和絕對的權利。”[11](P309)再有,按照國際慣例,錄音制品二次使用獲得的收入由集體管理協會為錄音制作者收取,實現錄音制品二次使用報酬權的關鍵還有待于著作權集體管理機制的完善。因此,這些在《著作權法》或《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中有待明確和完善。
(五)小結
應當說,賦予錄音制作者二次使用獲酬權,而不是表演權和廣播權這樣的專有權利,讓錄音制作者從國內外的廣播和公開表演中獲得穩定的收入,既可以帶動唱片產業走出現在的經濟發展困境,有利于錄音制品的制作和傳播;同時,錄音制作者與廣播組織等錄音制品的使用者分享因使用錄音制品而獲得的巨大收益,亦可以平衡與錄音制品相關的各利害關系人間的利益平衡。因此,有學者認為賦予錄音制作者為其錄音制品“二次使用”報酬權,應當是我國未來著作權法完善鄰接權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12]
四、數字時代下錄音制作者權的保護
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錄音制品的傳播方式和消費模式。在P2P技術的影響下,普通網民既是數據的接受者,也是數據的提供者,錄音制品徹底脫離制作者的控制,成為網民免費的午餐。學者通過對國際唱片協會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盡管實體音樂銷售(CD、磁帶、黑膠唱片)在2006年下降了約21%,但數字音樂銷售的增長抵消了這部分差額;實體音樂銷售量的遞減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但從全球來看遞減的速度在年5%—8%,而中國衰減的速度高達20%,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線音樂在中國是免費的。[13](P23)因此,數字技術時代保護錄音制作者權,不僅要解決盜版和非法傳播等老問題,更要順應技術的發展,調整和變革其發展模式。
(一)在線銷售錄音制品的發行權是否用盡
所謂在線銷售錄音制品,主要是指錄音公司(或其授權者)在與消費者達成銷售協議后,直接經由互聯網向消費者傳輸錄音制品的復制件。在線銷售與傳統實體銷售不同的是,前者在銷售完成后,傳輸者的服務器中還保留著錄音制品的復制件,而后者是該所銷售的錄音制品發生了物權的轉移。網絡環境下錄音制作者發行權是否用盡關系著消費者在線購買錄音制品后能否再行處置。對于這個問題,我國在《著作權法》、《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都沒有規定,可參照美國和歐盟這兩大地區的規定來看國際上對于該問題的態度。
美國對錄音制品提供的是版權保護,①美國版權法所列作品中就包括“經固定的一系列音樂、口述或其他聲音產生的作品,不論承載這類作品的物體(例如唱片、磁帶或其他錄制載體)的性質如何,但不包括伴隨電影作品或其他試聽制品中的各種聲音”這類與大陸法系所稱的錄音制品并無不同的作品。在線傳輸錄音制品被認為是一種發行作品的行為。而美國《版權法》第109條是關于錄音制品發行權用盡的規定。對于在線提供錄音制品是否受發行權用盡原則的約束,美國白皮書中明確提到:“在當今的技術條件下,傳輸者在接收者獲取復制件的同時仍然可以保留作品的復制件,接收者所得到的并非是傳輸者手中的那份復制件;立法的歷史和判例的發展都表明首次銷售原則只適用于被發行作品的那個特定復制件(that particular copy)的占有而進行處置的情形。”[1](P149)也就是說,傳輸者對于其占有的錄音制品的復制件仍然享有控制權,并不受首次銷售原則的約束。歐盟歷來反對將權利用盡原則適用于在線傳輸作品和鄰接權客體的情形。對于網絡環境中發行權用盡原則,歐盟在1996年的《關于信息社會中著作權與相關權利的綠皮書續篇》中指出,網絡傳播與發行不同,傳播者所提供的不是作品的有形復制件,而是可以被無限復制的無形服務,因此不適用權利用盡原則。[1](P150)
首次銷售原則解決的是作品的有形載體轉移之后所有權與著作權的沖突,換句話說,權利用盡原則的適用針對的是某一特定的錄音制品復制件而言,并非是指無形的錄音制品本身。在傳統的發行情況下,錄音制品的傳播以物理載體的轉移為前提,傳播的速度和范圍必然受到限制,這樣即使規定首次銷售原則,對錄音制品著作權人的影響也是可預見和可控。而在網絡傳播錄音制品的情形下,傳播者手中的錄音制品復制件并沒有轉移,而只是被復制,如若適用權利用盡原則,則是對在線侵權行為的容忍,不利于在線錄音制品的保護。因此,針對錄音制品的特定復制件轉移而設定的權利用盡原則不適用于依賴復制對信息進行傳輸的網絡環境。
(二)將非交互性在線傳播納入獲酬權的范圍
信息網絡傳播權是在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而賦予錄音制作者的新權利。但是《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將錄音制品制作者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涵蓋范圍與作者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等同起來,即只能控制“以有線或者無線的方式向公眾提供錄音制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錄音制品”這種交互性的網絡傳播行為。除了這種交互性的網絡傳播,還存在著非交互性的網絡傳播,以網播為例,“網播”是指以有線或無線的方式,通過計算機網絡,使公眾基本同時得到所播放的聲音,或圖像,或圖像和聲音,或圖像和聲音表現物。①WIPO doc.,Working Paper On Alternative And Non-Mandatory Solutions On The Protection In Relation To Webcasting,SCCR/12/5,Apr 2005,Article 2.網播的顯著特點是“接收者可以再某一特定時間登錄節目信息流,并接收傳送來的任何內容,但不能以其他方式影響該節目信息流。”②Ibid:explanatory comments 1.06.可見,這種播放方式與交互性的“在選定的時間”、“在選定的地點”獲得節目信息流是不同的。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即出現了將網播等同于信息網絡傳播的行為。例如,在“寧波成功多媒體通信有限公司(簡稱成功公司)訴北京時越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簡稱時越公司)著作權糾紛案”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終字第5314號判決書。中,時越公司所有的悠視網以非互動的方式在線播放了電視劇作品《奮斗》。網絡用戶只能在某一時間點觀看正在播放的《奮斗》的某一集,并不能在其選定的時間觀看未播放的其他集的內容。本案的一審法院海淀區人民法院和二審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均認為該未經許可的定集在線播放行為侵犯了成功公司的信息網絡傳播權。這雖然是網播視聽作品的案例,卻反映出司法實踐對“網播”這種網絡傳播形式性質的誤解。
網播錄音制品同樣是對錄音制品的一種利用行為,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內并不屬于信息網絡傳播權所規范的范疇。分析WPPT第2條對第15條(即表演者和錄音制品制作者的獲取報酬權條款)的解釋,“向公眾傳播”包括使公眾能聽到以錄音制品錄制的聲音或聲音的表現物。也即WPPT語境下的獲酬權的判斷標準是以公眾能夠聽到錄音制品所承載的聲音這一結果而言的,至于是以什么方式導致的這一結果沒有要求。因此,可以將“網播”這種非交互性的網絡傳播行為納入到二次使用獲酬權的保護范圍。隨著網播站點的不斷增加,承認錄音制品制作者在網播錄音制品的情形下享有的獲取報酬的權利,以充分保證其在數字空間下的利益,這無論是對于司法實踐中指導案件的判決還是錄音制作者權利的保護都將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三)小結
數字時代對于音樂作品的傳播既是契機,也是挑戰。借助于網絡的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的特點,“網絡紅曲”很容易產生;而如果沒有完善的著作權和鄰接權保護制度,伴隨著音樂作品傳播的則是音樂作品的侵權。錄音制品是音樂作品傳播的載體和媒介,錄音制品在數字領域的保護是保護音樂作品版權和鄰接權的重點,錄音制作者在數字領域基于其所制作的錄音制品的權利同樣不得侵犯。不管是在線傳播、銷售錄音制品還是向公眾提供、網播錄音制品,錄音制作者在網絡環境下的復制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和二次使用獲酬權不應當成為擺設,積極發揮這些權利對于錄音制品的非法使用行為的控制,保障錄音制品制作者對于其所付出的勞動成果的回報,這樣或許才能迎來唱片行業的第二春。
[1]孫雷.鄰接權研究[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2]劉鐵光.錄音制品二次使用的法律問題研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
[3]Stephen M.Stewart,ed.,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2nd ed.)[M].London:Butterworths,1989.
[4]李琛.知識產權法關鍵詞[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5]王遷.論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及在我國著作權法中的重構[J].東方法學,2011,(6):50-58.
[6]吳漢東,曹新明,王毅,胡開忠.西方諸國著作權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7]李明德,管育鷹,唐廣良.著作權法專家建議稿說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8]賴明芳.中國音像協會再次呼吁,賦予錄音錄像制作者廣播權和表演權[N].中國新聞出版報,2007-07-03.
[9]張偉君.錄音制品制作者的廣播權和表演權應該緩行[J].電子知識產權,2007,(10):66-67.
[10]張今.試論錄音制品二次使用報酬權[J].中國知識產權,2011,(6):131-135.
[11]德利婭·得普希克.著作權與鄰接權[M].北京:聯合國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
[12]張今.振興音樂產業的立法應對[N].中國新聞出版報,2010-02-04(6).
[13]棋其格.論錄音制作者權的立法完善——以錄音制品的二次使用為視角[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