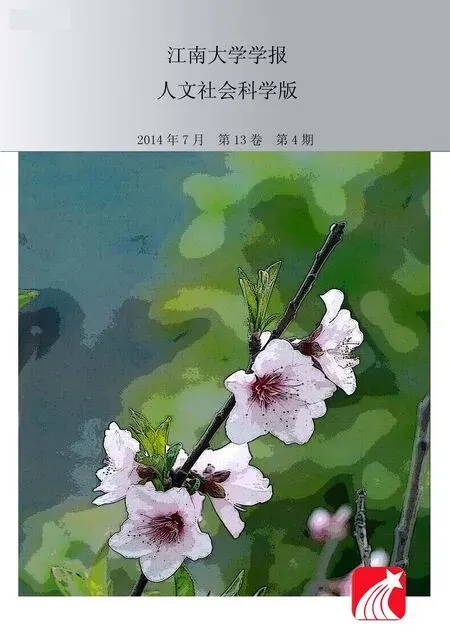當代小說視域中的農民身份問題研究
張春歌,張玉玲
(江蘇理工學院 中文系,江蘇 常州 213001)
隨著我國城市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進程逐漸加深,農村的社會結構、價值體系以及思維方式等正出現顯著的變化,作家對鄉村的想象性敘述也在發生著相應的改變。從作家對鄉土的認知與審美表現形式的變化過程中,我們充分感受到了鄉村與現代性的復雜關系,尤其是小說中折射出的農民身份內涵的變化,無不展現了國家意志與農民對現代化的訴求之間的深層關系。尤其是“新時期”以來,農民身份的變遷是一個逐漸“去政治化”、“去國家化”的過程,伴隨著同步的商品化、市場化的進度,農民的現代個體意識也不斷得到強化——被原來的“組織”、“集體”逐漸拋離,而被市場化逐步吸納,還原為經濟層面上的個體存在。而這種個體意識的興起及身份的變遷在當代小說中得以充分地體現,小說作為一種現實的隱喻化和象征性的文本實踐,從中可以解讀出的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的關聯性內涵,則顯得意味深長。
一、集體身份的認同與個體意識的忽視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之間,文學對農民的敘述,多是在國家與農民的政治關聯中展現的,農民的無產階級意識的獲取與體現,在作品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這也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現代革命哲學的集體主義理念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與文學界主流意識形態的結果。以“十七年文學”為例,在作品中“‘農民’不但被敘述為一個革命階級的主體,也被敘述為一種民族國家的主體,同樣也被敘述為一種歷史的主體”[1]。這三種主體的建構充分體現了農民對于階級、國家、社會的依附和順從。“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中主要描寫了合作化運動和階級斗爭,這正是當時農村集體化的國家訴求的直接反映,與當時國家對農村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治策略是一致的,充分體現了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對實現共同富裕、完成農業現代化建設,從而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熱情期待。所以對于農民而言,他們必須從思想上對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精神理念給予充分的認同,才能確立其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但是長期處于小農經濟狀態下的農民,無論在生活形式、觀念形態還是風俗習慣等方面依然留有“封建殘余”,于是集體主義的時代訴求與現實的農民個體意識間的矛盾,就成為作品關注的焦點。為了集中、典型化地展現當時的農村現實,多數作家將農民形象進行了簡單化的歸類處理,分為左、中、右三派,尤其突出具有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思想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塑造。這使得“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在創作上具有某些共性:敘述模式雷同,人物形象相似,主題思想一致。這種共性的存在恰恰折射出了當時農村的現實,讓我們感受到了國家主義權威對鄉村社會的強力滲透與整合,正是由于國家主義話語占支配地位,鄉土社會內部所依據的宗法關系、人倫關系等逐漸讓位于簡約、粗放的階級關系,全民的階級團結、對集體主義的片面強調在小說中得到全面實現,而農民自身的個體意識卻被忽視,甚至被壓制。
在“十七年”文學中,一群“落后分子”形象的存在直接表現了集體與個體關系的對立。這些“落后分子”形象不僅充分展現了當時農民真實的心理,更體現了農民自身對集體身份的選擇存在著一定的顧慮與分歧。如西戎的《賴大嫂》中,圍繞著養豬的問題,賴大嫂的心理卻經歷了“為公還是為私”的折磨,當隊長告訴她新的養豬方法“隊里不供應飼料,自喂自養,收入歸己”時,賴大嫂卻是不信任,“鬼才信你的話,到時候豬喂肥了,賣了錢要交公,還不是白白操勞一場!”這種對付出與收入的計較其實是農民的真實心態,不僅充分反映了集體的意義與農民的現實愿望之間的距離,更折射出長久以來由傳統的家族、村落觀念所形成的“農民意識”的穩固性,而這種落后的農民意識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卻是農民個性主體意識的體現。《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其思想和行動都是傳統的農民發家思想的具體體現,想通過個體實現物質的占有,達到富裕的目標,所以對集體化、共同富裕不滿,對合作化運動也就采取了不理解、不支持的態度,但是個人發家政治上不允許,所以最終只得與黨、與互助組保持一致。在小說中,農民的思想矛盾更多地糾結在了革命與私有化的關系上,當革命的思想與農民的物質欲望達成一致時,農民的思想與黨的思想就保持了高度一致,反之亦然。如《三里灣》中的范登高和《創業史》中的郭振山,土改時兩人都是積極分子,與黨的政治思想保持一致,后來因反對走集體化道路、反對共同富裕而成為革命的改造對象。其實,走集體化的道路,是要把農民從“小農經濟”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從集體經濟中體會到一種平等和公正,但是在當時的政治語境里,對集體利益的強調,對個人利益的忽視,使得集體與個體的關系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這種意識形態化的集體觀不僅規訓著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而且使個人的言說方式、價值取向等都趨向一致,所以在作品中那些具有個體思想的農民經過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造,他們逐漸認同了集體化的道路,肯定了自身的集體身份。當然這種認同卻導致農民自身的愿望訴求被埋沒在社會主義集體化的浪潮中。
在建國初期的文學作品中,農民的身份無論是互助組成員還是社員,其實質都是集體的一分子,是集體主義精神理念的具體體現,這也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要建立現代化農業的戰略構想的文學表達。這種對農民集體身份的革命化的敘述,一方面充分展現了國家對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激進想象;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農民個性主體意識的忽視,過多地強調國家建設主體、歷史主體、文化主體,唯獨缺失了農民愿望表達的個體主體。從作品的主題思想來看,作家普遍選擇了遵從政治指令來反映所謂時代的本質規律,試圖揭示當時的農村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和深遠意義,這種“政治與藝術的完美結合”方式可以視為中國現代性的文學渴求,但是這種從政治出發的文學作品卻忽略了農民最質樸的生活愿望,充斥在作品中的意識形態色彩也使得農民對集體身份的認同存在一定的被動性。隨著國家政策的調整,關注農民自身的主體訴求在后來的路遙、張煒、賈平凹等作家的作品中實現了。
二、自我主體價值的確立與國家主體身份的弱化
20世紀80年代后,以經濟改革為中心的社會改革運動使得我國的社會結構得以重新調整,農民逐漸從宏觀的國家關系層面的人民、群眾、階級等概念中擺脫出來,農民的個體主體性開始受到重視與肯定。建國初期文學中沒能實現的農民的個體訴求,隨著政治環境的大松動在文學作品中得以展現。
古華《芙蓉鎮》中的“胡玉音”,粉碎四人幫后,重新開起豆腐店,成為致富的典型,其個體價值得到了充分的實現與肯定;何士光的《鄉場上》里的“馮幺爸”前后的改變,意味著經濟上的獨立讓農民的個體價值、自我的人格與尊嚴都得到了社會的肯定,農民的思想正發生著很大的改變;賈平凹的《雞窩洼里的人家》中兩個家庭的重新組合,回回與禾禾形象的對比,不僅展現了改革開放的環境下農村新舊生活方式的變化,而且進一步肯定了農民自身的主體價值;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與孫少平兩兄弟,更是體現了新一代農民的精神世界。孫少安,立足于黃土,希望“在雙水村做一個出眾的莊稼人”,孫少平,擺脫黃土的牽絆,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與價值理想,他身上更體現出了一個自尊、獨立、進取的現代農民形象。他并沒有為自己的農民身份而自卑,而是努力超越農民自身的局限性,他的奮斗是對自我主體價值的肯定與自主把握人生的強烈愿望的實踐。可以說,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為這些新時代的農民走向外面的世界提供了至少看起來無限多樣的可能與希望,所以這些作品著重突出黨的好政策帶給農民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及精神境界的變化,雖然這和“十七年”文學對黨的政策的歌頌有某種一致性,依然突出了農民“國家主人翁”地位的自豪感,但是這些作品對農民個體價值的張揚與肯定擺脫了國家政治權力話語的束縛,使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自己的主人。隨著國家建設中心由鄉村轉向城市,城市主體地位的確立使得農村、農民的地位也隨之發生改變,這種變化是在農村與城市的差距中逐漸體現出來的。雖然在80年代城鄉之間的差距并不是很明顯,但是,小說在關于“走向城市”的主題敘述中已觸摸到了城鄉之間的差異。
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小說,通過陳奐生的命運變化概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中國農村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歷史和農民的變化歷史,從“漏斗戶主”到稍有溫飽去城市里賣油繩,到被人利用當了次不光彩的采購員,最后受到良心責備老老實實回家“包產”。這一過程充分展現了變革中的農村、農民的精神狀態與現代文明之間的差距,這一差距是在與城市生活的對比中體現出來的,尤其在《陳奐生上城》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城市,正在成為青年農民實現人生價值的夢想之地。《哦,香雪》中,香雪對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已傳達出了多數農村人的內心世界;在《人生》中,高加林對于城市的向往已變得有些焦灼,對于自身的農民身份已有些厭惡,曾想法設法想擺脫父輩們的辛苦單調的生活;而《老井》中的巧英更是毅然決然地奔向了城市。城市,不僅是承載與實現年青農民夢想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種身份的優越與高貴。而本質意義上的農民身份,則意味著屈辱與卑賤。由此可以看出,社會主義革命文學所建立起來的農民的國家主體身份正被逐漸弱化,農民的階級屬性、集體身份的優越感也正逐漸消失,農民這一稱謂所具有的某些隱喻含義正被作品充分表現。隨著這些人物形象對于城市生活在情感上的認同與接受,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之間的地位懸殊也已成為現實。
那么,此時農村、農民、城市三者之間的緊密關系在商品經濟的涌動下該如何呈現?作家在小說創作上的某些一致性充分折射出他們內心深處的某種期待與焦慮。雖然,農村的體制改革已使農民與土地的依附關系有所松動,農民在國家建設中主體地位的弱化已呈必然,但是作家依然寫出了土地對于農民的靈魂指引,尤其在80年代初城鄉差別不太明顯的情況下。所以,重返農村成了一些小說結尾的共同安排。《陳奐生包產》的結尾,陳奐生重新回到了農村,認識到了農村發展的新的出路就是包產,立足于土地實現富裕;《人生》中高加林帶著懺悔重新回到了農村,撲向了土地;《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在省城經過一番努力打拼后又自愿返回到了家鄉。另外,賈平凹等作家的作品雖然立足于鄉村這片土地寫出了改革開放所引起的農民在婚姻、愛情、人生觀等方面的變化,但是土地對于農民的牽絆與靈魂的感召依然充分展現了出來。所以在80年代初,盡管有外在城市的繁華與吸引,但是作家憑借自己的創作經驗與政治、道德、情感上的指引依然將農村視為城市發展的母體依賴。這種對于鄉村、農民主體地位的情感認同與創作理念雖然一度模糊了城鄉之間的距離,但隨著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城鄉沖突明顯,農民在國家建設中的主體地位被真正取代,農民這一身份在現實中的尷尬才充分體現出來。雖然農民的集體身份逐漸弱化,自我的主體價值得以確立,農民在真正地走向城市后卻面臨著身份的尷尬與精神的焦慮。
三、“亦工亦農”游移身份的雙重焦慮
在城鄉社會流動加速和經濟社會結構劇變的新型背景下,城鄉關系陷入失衡狀態,農民及其衍生出的“農民工”群體面臨著嚴重的身份焦慮。“農民工”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關鍵詞。它的出現完全標示著現代化建設對農村的巨大沖擊、城鄉差距的拉大及農民進城后面臨的身份危機、精神危機與文化危機。此時的“農民”,不再具有建國初期的光榮與自豪,更多地帶有了卑賤與低下的隱喻意味。與80年代作品相比較,關于農民工題材的小說雖然延續了走向城市的主題,不同的是,農民對城市及其文明向往的主動姿態已演變成生存壓力之下的無奈出走,理想化與詩情化的色彩已逐漸消失。當進城成為謀生的主要手段時,農民對城市現代物質生活的追求與現實生存壓力下的無奈掙扎就成為小說的表現重點。綜觀90年代以后作家對農民的關注,一般從以下幾點進行描寫:農民進城后的現實困境,主要從物質欲望的追尋與墮落中來傳達農民在現實中的生活狀況及生存焦慮;農民進城后身份的邊緣化所導致的精神困境;農民自身鄉村文化人格缺陷與弊端的揭示;進城與返鄉的靈魂漂泊等。作家關注這些內容的前提是基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沖突,對城鄉二元對立的認識使作家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對現代化建設、城市化進程的某種憂慮,這就使作品表現出對現代化建設的某種排斥感。城市與鄉村在現代性為主導話語的背景下就這樣以不可協調的方式進入了文學的想象中。諸如劉慶邦、胡學文、陳應松、王祥夫、孫慧芬等作家主要從現實、精神、道德、人性、文化等層面對農民工生活進行了文學解讀,全面展現了農民工的生活狀態,傳達出作家深沉的人文關懷。苦難與欲望的博弈是這些作家關注的突出角度,群體生存困境的展現是這些作家的表現焦點。不僅如此,尤鳳偉、賈平凹等作家主要從鮮活的個體形象塑造中讓我們看到了農民工瑣碎悲涼的庸常人生。如小說《泥鰍》中“國瑞”在城市中的命運正如“泥鰍”一樣,無論在城市中如何奮斗都難以擺脫被他人吞食的宿命,這正根源于生存于泥垢之中的卑微身份;小說《高興》中作家讓拾荒者“劉高興”艱難而高興地活著,將苦難與詩意并存于此人身上,試圖在現代性語境下為這些城市異鄉者樹立高尚的人生信念。但是對城市的自主選擇、對城市物質層面的單一認同使他們無法真正地融入城市,他們的“高興”也只是作家美好愿望的一種表達。另外諸如《民工》等小說,作家悲憫的情感之下難以掩飾對鄉村命運的焦慮。這些小說都不同程度地展現了當代鄉村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遭受的種種困境,尤其是農民的身份尷尬更深入地體現了出來。“農民工”這一稱謂,從詞語表面來看只是“農民”與“工人”兩個名詞的疊加,但是卻充分顯現了農民在意識形態、社會地位、文化身份上的不確定,戶籍上的農民身份與現實中的“亦工亦農”的身份漂移也就注定了他們在城市與鄉村中的尷尬困境。如果說農民進城后面臨的是求生的艱難與城市人的排斥,那么返鄉就成為他們的歸路。
如果說,80年代作品中出現的返鄉是作家為尋求鄉土詩意與道德安慰的精神補償,那么此時的“返鄉”卻是農民工逃離尷尬、重拾尊嚴與尋求慰藉的無奈方式。從陳應松、孫慧芬、劉慶邦等作家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關注的角度雖然有差異,但是反映農民返鄉后的現實處境卻極為相似:鄉村現實的凋敝,鄉村人性的冷漠與功利對返鄉者的排斥,鄉村淳樸的道德體系、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等在現代物質文明沖擊下的瓦解等。與描寫“鄉下人進城”不同的是,作家更側重于對“返鄉者”獨特個體經歷與感受的呈現,寫出了返鄉之后難以言說的心痛和迷茫。諸如《回家》、《我們的路》、《歸來》等作品,依據城鄉互望的視點寫出了農民工的“回家”之痛,都市與鄉村的雙重絕望。“城市掛著一把刀子,鄉村同樣掛著一把刀子,一個硬,一個軟……”[2],如此,作家將農民工題材小說推向深入,最終指向現代化進程中農民工被城鄉邊緣化的精神困境,同時也對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發展的錯位現象進行了深入思考。
無論是進城還是返鄉,農民工這一身份正經歷著雙重尷尬:他們在城市中生活,卻不能擁有真正的城市身份或城市人的尊嚴,農民的本質使他們得不到城市的真正接納;返回自己的家鄉,城市生活的經歷與某些觀念的變化使他們失去了農民本身的純粹而遭遇家鄉的排斥,這種尷尬的雙重身份就使他們處于無根的漂泊狀態而充滿悲劇況味。我們發現,文學中所展現的農民工的生存狀態與現實的國家發展是如此的不相協調。當中國更全面更深入地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時期,中國當代文學卻回到了對苦難、對鄉村、對底層民眾的敘述中,關于城市的美學想象、文學表達并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而在文學作品中關于城市的形象多半是酒店、歌舞廳、發廊等象征城市物質文明繁榮的標志,真正代表城市現代文明的現代意識、以人為本等觀念并沒有真正體現出來,在鄉村面前,城市又再次成為欲望與墮落的象征,也不再是年青人的理想與主體價值實現的向往之地,鄉村也不再是靈魂棲居地,農民工這一稱謂所帶來的是農民、農村、農村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邊緣化的現實。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農民進城是時代的巨大現實。“農民—工人”的這種雙重身份所帶來的尷尬,“其應對策略既依賴于國家、社會等外在力量的支持,更離不開自身的訴求與爭取。”[3]而農民的這種身份焦慮正傳遞到下一代人身上,無論是新生代農民還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的價值觀念于父輩已有著明顯的不同,但是“我是誰”的困惑依然纏繞著他們,并呈現出進一步模糊化的現象。所以楊爭光的小說《少年張沖六章》是一個特殊的文本。它不是單純地寫一個問題少年,它集中展現了一個個體生命與父輩、老師、社會的緊張關系中難以突圍的悲愴,而這更暗示了農民、農村未來的模糊命運。根據一些教育學者的調查研究,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孩子上高職、上大學的比例正逐年下降,上重點大學的比例更是嚴重下降。許多農村孩子的教育正止步于高考,甚至止步于初中,現實中的他們更多地是延續著父輩們孤島化的生活,不同的是他們很難像父輩那樣依戀鄉土,對農村、對父輩的否定使他們更傾向于在城市生活,盡管城市帶給他們更多的是酸楚、迷茫。
從當代小說中農民身份內涵的變化來看,農民身份曾經具有的政治意味已被弱化,原有的階級優越感及國家建設的主體位置已徹底喪失,“為生存掙扎”的強大現實感正日益凸顯,“在資本現代性的規訓下逐漸縮減成單向度的弱勢群體”[4]。作家對農村、農民不同角度的敘述正讓他們的真實現狀呈現出來。從中國現實來看,當前農民的生活狀態已逐漸呈現出三種常態:留守農民,農民工以及所謂的新市民。三十年來,國家的轉型與現代化建設在繼續,農民命運的轉型在他們自身的堅持下也在繼續——不管是在農村復制父輩的命運,還是到城市中求生存……
[參 考 文 獻]
[1] 李祖德.“農民”敘事與革命、國家和歷史主體性建構[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1):198.
[2] 羅偉章.我們的路[J].長城,2005(6):6-8.
[3] 李海金.身份政治:國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構[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0(6):89.
[4] 蔡志誠.底層敘事的現代性悖論[J].東南學術,200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