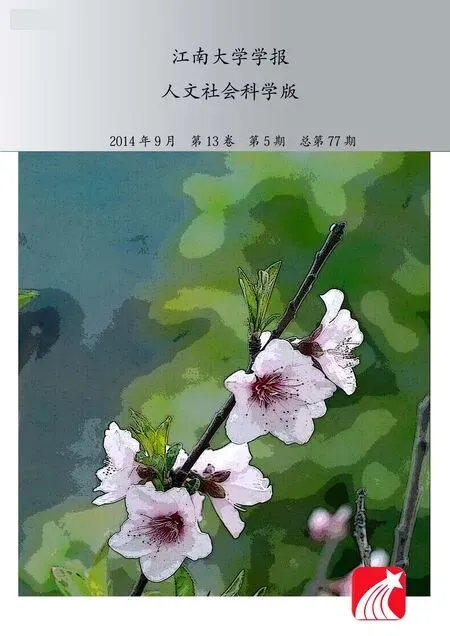海德格爾對技術時代的世界觀的批判
宋清華
(河南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洛陽 471023)
在我們的哲學教科書中,通常把世界觀界定為:“人們對整個世界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或“世界觀亦稱宇宙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在我國,這一界定已經成為哲學界關于世界觀的權威定義,它最先是由艾思奇提出的,“哲學就是關于世界觀的學問,哲學觀點就是人們對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對于整個世界的最根本的觀點。因此,它和任何一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不同,它所研究和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僅僅關于世界的某一個方面或某一個局部的問題,而是有關整個世界,有關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普遍的問題。……人們的世界觀是多種多樣的,從古到今,哲學家們對世界作了種種不同的解釋,彼此進行了激烈的斗爭。”[1]2它包括三層含義:其一,哲學乃是有關世界觀的學問;其二,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的根本觀點;其三,世界觀自古就有。這一界定后成為我國哲學界和哲學教科書長期沿用的權威定義。但這種界定本身還是存在一些問題的,說明人們并未理清這一概念的來源、本質和含義。在此,我們將通過德語世界的哲學家包括海德格爾等人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來探討這一問題。
一、德國哲學史上的世界觀概念
在德語中,世界觀概念是由Weltanshauung或Weltbild二詞表示,二者都是復合詞,分別由Welt(世界)與Auschauung(直觀)或Bild(圖像)構成,一般來說,人們常把Weltanshauung譯為“世界觀”,把Weltbild譯為“世界圖像”。不過,在不太嚴格的意義上,人們也把后者稱為“世界觀”。可見,二者有共同點,即它們都把世界作為直觀的對象、作為整體的圖像加以把握。最先提出這一概念的是康德,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討論人心的知覺能力時提出了這一概念:“如果人類的心靈甚至能夠思考特定的無限事物而不陷入矛盾,那么它本身必定具有一種超感性的能力,我們不可能直觀它的本體觀念,但是我們可以認為,本體是單純現象的基礎,質言之,是我們直觀到的世界(世界觀)的基礎。因為只有通過這種能力及其觀念,我們才能以純粹理智的形式評判事物的大小,才能完全根據一個概念來理解感性世界的無限性。不過,根據量的概念,以數學的方式來評判事物的大小,我們是永遠不能完整地思考這一概念的。”[1]111-112康德看來,世界觀一詞的意思就是人們對世界的感性知覺。康德的這種定義,很快使“世界觀”成為一個哲學范疇,意指人所理解的宇宙。康德發動了所謂哲學領域中的“哥白尼革命”,強調讓對象(客體)圍繞主體轉,強化了主體認知或表征現象世界之徑,而且斷定人只能認知現象世界,無法達到物自身,并以此區分了認知的自我和有意志的自我的作用范圍,并由此構建宇宙的知識中心和道德中心,也為世界觀概念的傳播開辟了思想空間。
康德的門徒也接受了這一概念,并在此意義上使用之,費希特接受了康德對它的基本界定,認為世界觀就是對感性世界的知覺。他還提出了一種更高的立法原則,此原則可以在道德自由和自然因果律之間起調和作用,能夠作為人們感知經驗世界的一種方法:“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原則作為一種世界觀的基礎,那么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就會認識到,統一的結果是完全必要的——在我們與感性世界的關系中,這種結果會根據道德律而表現為一種自由,如果把它作為一種理性的因果關系,它就會在自然界表現為一種偶然性。”[3]對費希特而言,上帝乃道德領域和自然領域得以統一的基礎,二者的現實統一基礎是上帝的“世界觀”。在上帝那里,萬物在本質上并無根本的差異。因此,兩種立法在上帝那里統一起來,它們共同依賴的那個原則,是以上帝的世界觀為基礎的。
不過,后來的謝林改變了此詞的含義,將世界觀視為一種“有意識、有創造性、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方法,能夠理解和解釋宇宙萬物。”[4]4在1799年謝林所著的《論思辨形而上學的概念》一書中,他表述了這種世界觀概念,他在書中指出了兩種理智的可能性:“理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盲目的、無意識的,或自由的、有意識的意識;另一種是隱含在世界觀之中的有創造性的無意識,在創造理想的世界時,潛意識就會上升為意識。”[5]67因此,世界觀是無意識的理智的產物。它是世界留在潛意識中的印象,心靈固然處在陶醉狀態,但仍能發揮作用,可以產生這種印象。另一方面,已經創造了一個理想世界的理智,充分了解自身的作用和內容。因此,由康德、費希特到謝林,世界觀的基本含義已發生變化,由對世界的感性知覺轉化為對其的理性把握。
而另一位大哲學家黑格爾則早就對此概念產生了興趣,在1801年的《費希特和謝林哲學體系之差異》一書中指出,借助辯證運動,理性將主客雙方聯系起來,從而形成了一個無限獨立存在的世界觀概念,“客觀的主體性與主觀的整體性是對立的,理性能夠將二者連接起來形成一種無限的世界觀,理性的這種擴張同時也是一種收縮,因此,理性成為一種內容最豐富、關系最單純的統一性。”[6]114黑格爾認為此概念最適合于表述其辯證法思想。在《精神現象學》一書中,黑格爾更明確地提出了他的道德世界觀:“從這個規定開始,一個道德世界觀就形成了,這個道德世界觀是由道德的自在自為存在與自然的自在自為存在的關系構成的。這種關系以兩種假定為基礎,一方面假定自然與道德(道德的目的和活動)彼此是全不相干的和各自獨立的,另一方面又假定有這樣的意識,它知道只有義務具有本質性而自然則全無獨立性和本質性。道德世界觀包含著兩個環節的發展,而這兩個環節則處于上述完全矛盾的假定的關系中”[7]126這種世界觀無疑是對康德、費希特思想的發展,并將基本的道德經驗轉化為道德世界的一種秩序。它開始指謂一種切實可行的人生觀,一種包含著道德關切與道德義務之沖突的自覺態度。它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看待宇宙的方法。在他看來,只有通過歷史長河的辯證運動,絕對精神才能實現具有末世論意義的自我意識。在此全過程中,絕對精神會具體化為人類的思想和文化,故此,世界展現為不同的存在方式。在此進程中,人們會形成不同的人生觀,并對之進行比較和綜合,由是,世界觀概念孕育于絕對精神的歷史進程中。這是一種典型的理性世界觀。
由此開始,世界觀概念深深地植根于德語世界中后又擴及至整個歐洲思想界,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有弗雷德里希·施萊爾馬赫,A·W·施萊格爾,諾瓦利斯,讓·保羅,G·W·F·黑格爾,約瑟夫·居勒斯,歌德等。在19世紀20年代,世界觀概念主要在哲學家和神學家那里使用,到了19世紀中葉,開始擴及到其他學科,如歷史學家瓦格納,神學家費爾巴哈。物理學家馮·洪堡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認為:語言旨在表達一種特定的世界觀,“各種語言之間的差異不在于聲音和符號,而在于不同的世界觀。”[5]68可見,世界觀概念在19世紀已經廣為接受,一位西方學者認為,在有思想的德國人心目中,世界觀與哲學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二者是一對并列的概念,“換言之,這個詞在19世紀已成為有文化的德國人的一個普通單詞。它與‘哲學’具有同樣的地位,用K·凱柏斯的話說‘哲學有了一個特殊的近鄰,即世界觀,我們很難對它進行分類,德語的用法尤其如此’。”[5]68
二、海德格爾的世界觀概念
海德格爾的世界觀概念無疑要受德國哲學家的影響,海德格爾始終關心的問題是“何為哲學”,哲學是否像世界觀一樣,能夠明確地給出生命的意義、目的,為人們的生活提供指導。或者說,哲學可否是一門具有嚴密性和準確性的健全學科,像科學的哲學所希望的那樣,能夠確立一些清晰的、永恒的、普遍的原理呢?海德格爾一直關注哲學觀問題。他認為,世界觀思想的不斷擴展已威脅到此在的真正的形而上學,故此,他要認真地區分存在概念的科學的本體論與漂浮不定的世界觀哲學。海德格爾指出,哲學與世界觀有關聯,但也有顯著的差別:首先,如果從哲學史看,哲學與世界觀有密切的關系,“所有的重要哲學歸根到底都是一種世界觀。”[8]一直以來,哲學的任務就是提出一種最終的實在論,進而提出一種生活的理念。哲學還得審視真善美的價值,盡管它們也是對事物的整體性的把握,已遠離經驗世界。由是,所有哲學歸根到底都是世界觀的哲學。然而,現代科學的一些理論已否定了哲學與世界觀的這種合二為一,這就形成了哲學與世界觀的第二種關系:科學的哲學既是科學世界觀的基礎,又是其終點。因為人類無法理解經驗背后的那些實在和原因。只有嚴密的科學方法才能證明那些命題,才能作為知識。也就是說,為了其合法性,哲學的世界觀必須具有科學的基礎。世界觀與哲學還是統一的,但必須建基于科學的基礎上。其三,哲學和世界觀在本質上不相容,必須分離。海德格爾認為,前批判時期的哲學和批判時期的哲學,不管強調實踐,還是科學,它們都以世界觀為終點,二者是統一的。但現在世界觀對哲學則是有害的。哲學的任務既不是確立一種世界觀,也不是尋求一種具有批判精神或嚴密方法的世界觀。哲學與世界觀“互不相識”,世界觀其實并無哲學的特點,它反而是人們認識哲學的真實身份的最大障礙。海德格爾從現象學的元科學這一概念出發,對二者予以界分,認為:“現象學旨在研究人的生命。雖然它看似生命哲學,其實它是世界觀的對立面。世界觀是某一文化中的生命在某一點上的客觀化和凝固不動。與此相反,現象學從未與世隔絕,它總是無條件地深入生活,因此它總是相對的。在它里面,沒有任何理論方面的爭論。只有本真的認識與非本真的認識。只有實實在在、完全徹底地深入本真的生活,人們才能獲得本真的認識;只有通過本真的人生,這種認識才能最終的實現。”[9]他強調,現象學哲學完全不同于世界觀哲學,必須劃清二者的界限,“我們提倡‘科學的哲學’的主要原因是,現行的哲學概念不僅危及、甚至否認哲學是真正的科學。這種哲學觀并非現代思想的產物;自從哲學作為一門科學存在以來,這種哲學就始終伴隨著科學的發展。”[4]4
針對人們對世界觀的不同理解,海德格爾認真考察了日常生活語言中世界觀的含義,認為,世界觀概念有二層含義:它不僅僅是對自然事物的結構的一種理解,同時也是對人的此在及其歷史的意義和目的的一種詮釋。世界觀往往包含人生觀。世界觀產生于人們對世界與人的整體性反思,這種反思方式各不相同,個人才能進行清楚的有意識的反思,也可能接受當時流行的世界觀。人們成長于這樣一種世界觀思想中并逐漸習慣了它的思維方式。人們的世界觀是環境的結果,環境即人民、種族、階級、文化發展的程度。個人樹立的任何世界觀皆起源于一種自然世界觀,起源于人們對世界與人的此在的規定性的認識,無論何時何地,任何此在都會有這樣一些清晰程度各不相同的觀念。人們必須區分個人樹立的世界觀,或文化世界觀與自然世界觀。世界觀不只是一個理論認識或記憶的問題,它是一種能動的實體,能夠影響人類的事務,為他們指引方向,鼓舞士氣,因此,毋寧說世界觀是一種連貫的信念,它能夠程度不同地直接決定人們現在的生活狀況。世界觀的含義涉及某時某刻某個具體的此在。鑒于此在與世界觀的這種聯系,世界觀就是此在的向導,是此在應對壓力的力量源泉。無論世界觀的決定因素是迷信和成見,抑或是純粹的科學知識和經驗,或如通常所見,是迷信與知識、成見與嚴肅的混合物,其含義都是大同小異;其本質規定性并未改變。由此,他得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世界觀總是扎根于現實生活,總是起源于“人類具體的現實的生存,他們的生存依據是他們對現實可能性的縝密思考以及生存態度的樹立;因此,它的出現完全是為了這個真實的此在。歷史地看,世界觀總是源于實際的此在,伴隨著實際的此在,服務于實際的此在。”[4]6也就是說,世界觀并非純粹思想的產物,乃是人類經驗發展演化的結果。
海德格爾的思想以哲學與存在觀念的關系為中心,立足于他的基礎本體論,他認為哲學不是以實證的方式來探索某種具體存在者的存在,它不設立任何存在。從歷史上看,探索世界觀的思想家們總是把存在者當作對象,但他們遺忘了存在。他認為,人們首先必須在一種廣泛且普遍的意義上理解存在本身,在此基礎上,才能理解存在者。嚴格來說,哲學是研究存在本身的科學,它是世界觀的先決條件,因為世界觀旨在解釋具體的存在者。因此,存在是哲學真正的、唯一的論題。他強調必須明確區分以存在為論題的哲學和以存在者為論題的世界觀哲學,后者與真正的哲學相差太遠。在他看來,哲學旨在以理論的、概念的方式,解釋存在及其結構與可能性,哲學是本體論。比較而言,世界觀旨在認識存在者,旨在樹立對存在者的正確態度;它不是本體論,而是一種實體論。樹立世界觀不是哲學的義務,但這不是因為哲學尚未發展成熟,不能夠以普遍的一致的方式,中肯地回答世界觀問題;毋寧說世界觀的塑造不是哲學的義務,因為哲學原則與存在者無關。不是因為存在某種缺陷,哲學便放棄了樹立世界觀的義務,而是因為它堅持這樣一條獨具特色的優先原則:所有存在者的存在,甚至包括某種世界觀所設定的那種東西的存在,本質上都必須設定的那種東西(即存在),才是其研究對象。故此,世界觀以具體存在者為對象,而哲學則研究存在本身,這才是二者產生本質區別的原因。
三、作為世界圖像的世界觀
雅斯貝爾斯在其《世界觀心理學》中著力考察了世界觀概念,認為世界觀是一些思想框架。他把人類靈魂對生命的終極處境的思考,與主觀的人生態度和客觀的世界圖像的產生聯系起來。世界觀被描述為一些與人類的終極性和整體性相聯系的觀念,它們或許是主觀的,也有客觀的可能性。這種超時空的性質激發了海德格爾的思考。海德格爾的論文《世界圖像的時代》實際上是對雅斯貝爾斯著作的回應。海德格爾不認同世界觀是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它扎根于人類此在的基本心理結構。只有當我們把人類理解為主體、把世界理解為有待解釋的客體時,世界觀才會被視為世界圖像。
海德格爾對主客二元論持保留態度,認為實在不僅是世界圖像得以產生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它遮蔽了存在的本質,又掩蓋了此在的真實面目。為了闡釋其存在論哲學,他視世界圖像的世界觀為誤入歧途的形而上學的衍生物。在他看來,要弄清這一問題,需要思考和審查形而上學基礎,因為形而上學是存在者及其真理的基礎,而世界圖像的世界觀則是由此主客二元分立的形而上學的產物。
為了討論這一問題,海德格爾分析了現代思想的五大重要特征:科學、機械技術、作為美學的藝術、文化和諸神的消失。由此,他想弄清楚哪種形而上學思想及其真理觀引發了它們。他選取當代科學,研究其本質特征,試圖揭示其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基礎,借此研究現代思想的哲學基礎。通過分析,他認為,現代科學的特點是預測性、嚴密性,注重方法和過程,這些特點使科學成為一種研究的綱領。而作為一種研究綱領,科學則包含著命題式表述的必然性,這樣,科學研究就必然將作為對象的存在者客觀化、對象化。他認為:“作為研究,認識對存在者作出說明,說明存在者如何和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為表象所支配。當研究或者能夠預先計算存在者的未來過程,或者能事后計算過去的存在者時,研究就只配著存在者。可以說,在預先計算中,自然受到了擺置,在歷史學的事后計算中,歷史受到了擺置。自然和歷史成了說明性表象的對象。……只有如此這般地成為對象,如此這般地是對象的東西,才被視為存在著的。唯當存在者之存在在這種對象性中被尋求之際,才出現了作為研究者的科學。”[10]896這段話涉及三層含義:其一,科學研究使存在者成為對象;其二,存在者成為被支配者;其三,自然和歷史也成為被支配的對象。這充分表達了海德格爾對科學技術支配客觀對象的憂慮,其深層意識是對人對世界的宰制的憂慮。
海德格爾認為,形而上學把世界萬物客觀化、對象化了,這是現代科學發展為一種研究綱領的基礎,應該對此負責的乃是笛卡爾。他說:“最早是在笛卡爾的形而上學中,存在者被規定為表象的對象性,真理被規定為表象的確定性了。……整個現代形而上學,包括尼采的形而上學,始終保持在由笛卡爾所開創的存在者闡釋和真理闡釋的道路上。”[10]896同時,海德格爾還認為,作為研究的科學乃是現代的一個本質特征,而構成研究的形而上學基礎的東西,則從根本上規定了現代之本質,這種本質就是人類的自由和自主,“人通過向自己解放自己來擺脫中世紀的束縛。”[10]896伴隨著解放,就產生了了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更為根本的是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相互作用,構成了人類存在的一種新形式——人成為主體,并導致人之本質的改變,人作為基礎把一切聚集到自身那里,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體——“人成為那種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這種存在者之上。人成為存在者本身的關系中心。”[10]897這是一場真正的哥白尼革命,因為人成了世界萬物的中心和基礎,成了首要和唯一真實的主體,人從此成為宰制一切的主體,這一發展歷程可追溯到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
由于人成了主體,成為了世界萬物的中心和基礎,人類不但徹底改變了其對自身的看法,對宇宙萬物的理解也發生了改變,這就是世界被圖像化了。海德格爾認為,從根本上成為圖像這樣一回事情標志著現代之本質。“在世界成為圖像之處,存在者整體被確定為那種東西,人對這種東西作了準備,相應地,人因此把這種東西帶到自身面前并在自身面前擁有這種東西,從而在一種決定性意義上要把它擺置到自身面前來。所以從本質上看來,世界圖像并非意指把握為圖像。”其實質是“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狀態中被尋求和發現的。”[10]899其意是說,世界被理解為一幅圖畫,是在人的表象中顯現為圖像,把它們作為對象、作為客體擺置到主體面前。所以作為圖像的世界,其實是作為客體的世界,世界是認識和表述的對象,是使用和支配的對象。與此相對,人類的自我被視為主體,視為世界的認知者和解釋者,因為世界是客體,人類才是世界的支配者、主宰者和使用者,世界的存在是為了被主體征服、占有。然而,對基督徒和希臘人而言,人為主體,世界為客體,世界是人的直觀的圖像,這種關系會令其震驚。他們認為,真實的關系應是造物者與受造者、墮落者與被拯救者的關系,造物者是一切之根本和源泉;而現代思想則認為,人不僅擺脫了存在的直觀,也擺脫了上帝對他的主宰。人是最高的主體,他試圖主宰大自然,而非成為大自然的管理者;人獲得了解放,但人也成為了萬物中之一物,成為圖像世界的對象、客體,從而被他人表述、解釋或觀看。故此,海德格爾認為,世界成為圖像,與人在存在者范圍內成為主體是同一個過程。
海德格爾的主體主宰世界的邏輯是這樣展開的,其一,現代科學研究建基于主客二分的笛卡爾哲學基礎上,把世界變成對象、客體來計算,而人成為主體;其二,世界在科學研究中成為被表象者,唯當存在者成為表象之對象之際,存在者才以某種方式喪失了存在。這種喪失則由人對此解釋、評價的價值來取代,從根本上以價值尺度來衡量存在者,使價值成為一切行為和活動的目標。而這種價值又成為證明人之意義和追求成功的尺度。價值終成為圖像世界人之欲望目標的對象。這實際上是對存在的遺忘,是一種遮蔽狀態;其三,從基礎存在論出發,海德格爾認為,普羅泰戈拉的存在者始終關涉著作為我的人。這種我逗留于無蔽領域的范圍中,這樣,我就可覺知著作為存在者的在此范圍內在場的一切東西。借助與存在者處于澄明狀態的共在關系,就可用界線把在場者與不在場者區分開來。從這些界線中,人獲得并保持著在場者和不在場者的尺度。這種尺度不同于前述的價值尺度,因為它源于一種對存在的本質規定性。而后者源于對可表象之物的計算、把世界圖像化而得的。因為它是主體的表像活動,它把存在者構想為作為對象的存在者,使其進入圖像的世界中而獲得的。由是,這就造就了現代之本質具有決定意義的事項——世界成為圖像和人成為主體,顯現出近乎荒謬性的現代歷史進程。而且對世界作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廣泛和深入,客體之顯現越是客體,則主體也就越主觀地、越急迫地凸現出來,世界觀和世界學說也就越無限地變成一種關于人的學說,變成人類學(以人為中心的學說)。“它標志著那種對人的哲學解釋,這種哲學解釋從人出發并且以人為歸趨來說明和評估存在者整體。”[10]903
因此,現代性的大事就是人類對世界的征服,就是世界被理解為一幅圖像。作為主體的人,視世界為圖像、為客體、為結構分明的表象、形象,并由他來擺置、設計、操縱和宰制。為了獲取人之地位,他使自己成為一切存在者的尺度和準繩。于是,人要凌駕于一切存在者之上,他試圖統治世界,試圖隨心所欲地解釋和規劃世界。人的這種顯赫地位就突出地表現在世界觀中,由此,有重要影響的世界觀必然發生沖突。為了爭奪統治權,不同的世界觀開始較量。這是由于人的這種位置是由世界觀來確保的,并由之協調和組織人展示自身,維護其利益、地位,所以現代人與世界萬物的關系轉化為不同人群的世界觀的爭斗和沖突,也就無可避免了。
事實上,不同世界觀的較量,甚至要求諸于科學的權威,因為科學不僅僅是工具,而且還意味著真理和權威,“為了贏得世界觀斗爭的勝利,為了保持世界觀的本來意義,人類極盡其思考、設計、塑造世界萬物之能事。科學是一種研究活動,在自我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過程中,它的作用是絕對不可或缺的,……伴隨著世界觀的斗爭,現代思想第一次邁進自己的歷史,這是決定性的一步,也可能是影響最深遠的一步。”[5]160海德格爾認為,科學不僅使世界成為主體的客體,而且作為科學成果的技術更強化了人宰制世界的危險。在《技術的追問》中,海德格爾指出,現代技術是一種解蔽。技術的解蔽功能,使人們了解現代技術的新特征。“解蔽貫通并統治著現代技術。但這里,解蔽并不把自身展開于制作意義上的產生。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自身能夠開采和儲藏的能量。”[10]932現代技術是一種逼迫式的解蔽。由于對自然的無限的索取的欲望,科學和技術都是為了滿足人的欲望而設。人走向了一條特別的“解蔽”的道路,科學和技術逼迫著自然將它隱藏的可能的可供人使用的東西都開放出來,從而使得自然日益成為人索取的對象、使用的工具。海德格爾對將世界視為客體或對象、并加以宰制的世界觀甚為憂慮,這種憂慮在其他哲學家那里也同樣存在,如舍勒就指出,人力所能及的知識有三種:宰制知識或成效知識、本質知識或教化知識、形而上知識或救贖知識。第一種知識即宰制知識,“使得我們有可能運用技術來控制自然、社會和歷史。這是一種實證的專業知識,它支撐著我們整個西方文明。”這種知識的最終目的是找出規律,以滿足人“宰制世界和我們自身的意志的需要。”[11]78-79而本質知識是一種同宰制知識剛好相反的知識,它要“克服宰制世界的態度,并盡最大可能地中止一切欲求行為。……提倡一種追求世界始現象的理念的愛的行為。”[11]82-83他強調,通過哲學而形成的整個形而上學的世界觀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對絕對自在的存在作獨特的思考和直觀,以便使它同“第一哲學”所揭示的世界的本質結構和我們克服重重阻力才能把握到的世界的現實此在以及偶然本質存在的現實此在徹底地吻合起來。舍勒認為,作為最高存在者具有兩大基本屬性,其一,它必須具有塑造理念的無限精神和同時派生世界和人本身的本質結構的理性;其二,確立非理性的此在和偶然性的本質存在的沖動。有了這兩種屬性,最高存在的兩大活動屬性之間不停地相互滲透,便形成了時間中的歷史意義,這種歷史我們稱之為世界。同時,它們的相互滲透也是理念和終極價值源初創造沖動不斷精神化的過程,或者說是無限精神獲得權利和活力的過程,它的具體表現是理念和道德價值與旨趣,激情及其他人類規范相融合而產生的影響力。這種知識才能制衡宰制知識,從而進入拯救知識的境界,由此“也是通向上帝的首選途徑”。[11]90所以“通達上帝的唯一途徑不是理論關照,即對象性的關照,而是位格主動投入到上帝的懷抱中去,盡量促成它的自我實現,并共同完成永恒行為。這種永恒行為既包括創造理念的精神活動,也包括我們生命本能中顯而易見的沖動力量。‘人’本身就是該雙重屬性所共有的最精致的終極體現。把上帝弄成對象和東西,對于這種形而上學來說就是偶像崇拜。要想分享到神性,只有深入到‘內在于他’、依據于他,仿佛由他而來的生命、活動、欲望、思維和摯愛中去。奧古斯丁稱之為‘神的子民在圣光的啟悟下認識’。當我們用這一種立場來關照世界、自我和他者時,其中不再有絲毫對象性立場的痕跡。”[11]91這樣,舍勒就最終用上帝來化解人的這種對世界的暴戾之氣。于是,這種世界觀因最終無力解決工具理性主導下的價值追求,只好求助于上帝,這在海德格爾那里也是一樣。海德格爾最后也提出“只有一個上帝能拯渡我們”[10]1306.
四、海德格爾世界觀概念的意義
海德格爾的世界觀是對工具理性支配下的人類價值追求的一種憂慮,是對人類只顧沉醉于感性享樂而遺忘了自身存在的批判,是哲學家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在海德格爾看來,世界觀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概念,乃是一個極具消極傾向、需要人們對之高度警惕的哲學觀,這種觀念的出現,使得世界在人們觀念中被圖像化,也就是主體化、主觀化,它揭示的是,在以當代技術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全球性帝國主義中,人的主觀主義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但“世界”在這個存在者整體成了人們隨意擺布的客體,而且人也被擺置到被組織、被控制的千篇一律的狀態中。當代人類面臨的諸多災難,如人之異化、生存環境惡化、犯罪、戰爭、種族主義無不源于人的主體化,而人的主體化的根本性標志性正是世界圖像化和世界觀概念的形成。同時,當世界被主體圖像化以后,人們的關注對象是周圍世界的存在者,而遺忘了對存在意義的追尋。也就是說,執著于世界觀討論的哲學真正思考的乃是存在者,而非存在。即使其偶爾談論起存在,也僅是它所理解的存在者的總和。正是在此總和中,不僅存在與存在者之間的差異被削平了,而且作為此在的人與其它存在者之間的差異也被磨平了。其實,大哲學家康德也早就注意到這一問題,他說,“前面那個無數世界之集合的景象仿佛根除了我作為一個動物性的造物的重要性,這種造物在它短時間內(人們不知道是怎樣),被配備了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曾由以生存的物質歸還給于行星(宇宙中的一個純然的點)。與此相反,后面這種景象則通過我的人格性無限地提升了我作為一個理智的價值。”[12]169-170康德所說的前一個世界即是存在者的世界,后面的景象則是指人之存在,即價值世界。康德所指的提升人之人格的世界則是海德格爾基礎本體論所要揭示的被“此在”的日常狀態和“此在”的其他存在者遮蔽的存在意義的世界。海德格爾指出,“把存在者從存在者中嶄露出來,這是本體論的任務。”[13]
可見,海德格爾憂心的是圖像化時代的人們,沉迷于人的主觀性、主體性的力量之中,這種主觀性與客觀性相對立,它從自己選定的目標出發,對后者加以判斷和操縱。海德格爾對這種無休止的更多索取深惡痛絕,認為這種索取的根源在于:空虛的主體為證實其統一性及對客體的力量,它們就永無休止地追逐其利益,不停地操控世界。在這種主體性力量展示中,事物被轉化成了商品,自然僅僅被當成了一個工具,而罪惡則通過更多的計算來加以解決,這已經成為市民社會成員的普遍思維。更為嚴重的是,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提倡它,其所造成的破壞性后果是人遺忘了存在,只追求存在者,從而造成了人的無家可歸性狀態。他認為:“關于人的本質,有些人承認、有些人否認的無家可歸性,被轉換為對大地的有組織的全球性征服,并直刺蒼穹。……在我們時代的歷史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這樣的幻想:就人性而言,人已經是自由的了,他可以自由地將普遍物納入到他的力量中來,并隨意擺布。正確道路仿佛已經找到了。接下來只需要正確地推進就行了,進而樹立計算化的正確性(Gerechtigkeit , ‘合法性’)的統治地位,并以此來作為意志到意志的最高代表。”[5]189-190
海德格爾認為,一種對存在者的技術性的理解早已沿著柏拉圖主義的路線發展出來,并得到鞏固,后被認識論所吸收(只有從存在的理念出發,或者說只有從加諸存在之上的支配性的主觀性出發,存在才能得到理解)。這樣一種技術性的理解將會抹除存在的神秘性和最初的涌現,但并未能將存在廢黜。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是否只有從對象化的現成在手狀態出發才能設想存在之在場嗎?與存在的技術性的或對象化的關系是唯一的、真正的基礎關系嗎?這難道不是根源于對一種更為源初的經驗的遺忘或遮蔽嗎?海德格爾在此并不是要反對技術會反對柏拉圖主義,他只是覺得,如果我們一下子就處于一種理性算計的考量來建構存在,這很可能會把存在之慷慨贈與的經驗掩埋,我們從此對于它的綻出將會不聞不問。由是,海德格爾所言的對存在之遺忘的觀點揭示了所有形而上學的簡單而基本的特征。
海德格爾向我們展示,這種技術性理解的巨大危害在于它切斷了一切通往更高秩序的聯系。正是這種秩序、這種尺度才是存在及其遺忘的主題所最終指示出來的東西,在一個萬事萬物最終都要依靠人類的世界里,沒有神的容身之地。或者神只能通過滿足人類需求、心靈的慰藉或進行解釋的需要而得以出現。神因而只是一個人類制造的偶像而已,它的一切崇高的神性都被褫奪了。他指出,思考存在就等同于思考諸神之神性的危困,也就是思考一個還具有神性的神明。在海德格爾看來,這種神性荒蕪狀態的最鮮活的病癥就是我們在這個一切事物都在運轉的世界中竟不能覺察到這種病癥,因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把這種危困稱為危困之缺席,或者遺忘之遺忘。人們常說,我們這個時代是以一個幻滅的時代,海德格爾則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諸神離棄我們的時代,這不僅僅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諸神,也說明諸神在某種意義上將我們遺棄了,將我們拋給我們自己的技術偶像,不再在我們身上幫助遏制我們那妄求操控一切的欲望。在此,他的意圖顯然不是要尋求這種苦難的解決或安撫之道。就人類今天的生存處境而論,“現在只有一個神靈可以拯救我們”!他希望借助在這種危困缺席的荒漠中的吶喊來激發對這種苦難的認知,他要告訴人們,人類的境況已經陷入了一種無可依靠的困境,這種困境無法通過技術的回應得到解決,當試圖掌控存在者的意志已經掏空一切不可計算的經驗時,在這樣一個世界上,只有一種對存在的別樣的思才能守護神之神性的希望。也許這正是這個守護者引導我們重提存在之問!
[參 考 文 獻]
[1] 艾思奇.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ement. translated and introduction by Werner S. Pluhar, Foreword by Mary J. Gregor (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111-112.
[3] Johann Gottlieb Fichte,Attempt at a Critique of All Revelation,translated and introduction by Garret Gre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119.
[4]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translation , introduction , and lexicon by Albert Hofstadter , 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2).4.
[5] 大衛·K·諾格爾.世界觀的歷史[M].胡自信譯,北京大學出版,2006:67.
[6] G·W·F·Hegel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 trans·H·S·Harris and Walter Surf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7).114.
[7]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26.
[8] Georg Kovacs, “Philosophy as Premordial Science in Heidegger’s Courses of 1919,” in Reading Heidegger from the Start: Essays in His Earliest Thought, ed. Theodore Kisiel and John van Buren, SUNY Series in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94.
[9] Kisiel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3.17.
[10] 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M].上海三聯書店,1996.
[11] 舍勒.哲學與世界觀[M].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 李秋零主編.康德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69-170.
[13]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