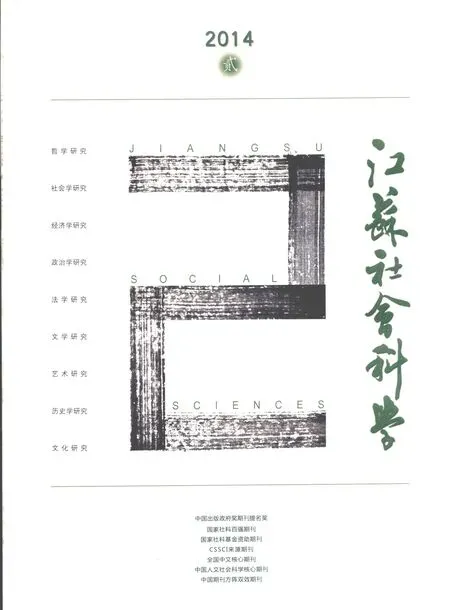誠信體系建設與司法公信力的道德資本
姜 濤
誠信體系建設與司法公信力的道德資本
姜 濤
如果司法不能有效應對民眾集體意識的挑戰,那么將無法避免司法信度喪失、效度缺損和地位下降的趨勢,從而引發司法公信力降低。司法公信力降低凸顯了誠信體系建設的重要性及其必要路徑:不僅應當形成一個合理、周全、妥當,并清晰地標示出司法誠信的規范體系,為重塑司法權威提供充分的制度激勵,而且應該強化司法對立法的忠誠,重視司法的道德基礎和確保司法的公正廉潔,以確保司法公信力的制度化實現。
司法誠信 公眾認同 司法公信力
一、問題的提出:由“信訪不信法”現象切入
“信訪不信法”是一個特有的中國問題。可以說,涉訴信訪已經成為當前司法信任危機的體現,終審不終、終而不結、反復交辦、“信上訪不信法”等現象日趨常態化。與此同時,“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也成為上訪者的基本信條。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有一種聲音頗具代表性:“解決糾紛‘信訪不信法’,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如果任由各種糾紛肆意發展,最終沒有進入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渠道,而是循著信訪這條路上下反復處理,將導致法治社會的倒退。”[1]《信“訪”不信“法”擾亂法治生態》,〔北京〕《人民論壇》2010年第21期。顯然,這一質疑是基于“信訪=有損法律權威=信訪是向人治屈從”的思路而邏輯展開。
問題的關鍵在于:信訪不信法之癥結何在?其實,造成信訪不信法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信訪這條救濟渠道比司法更具有權威性,也更為有效。這從反面表明了當代國內司法信仰的缺失和法律權威的弱化。作為前提,司法救濟渠道之所以具有權威性,就在于它是最有效且最值得信賴的救濟渠道,但是,法律的神圣性與權威性是以法律自身所體現的主體情感與社會正義為紐帶的,具體可表現在司法機關嚴格執法、規范辦案,實現公平與正義。這一紐帶的某一鏈條一旦出現扭曲或斷裂,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即可能被削弱甚至喪失。這又可以視為是司法之社會資本的缺失。
從根源上分析,司法公信力是社會組織、民眾等對司法行為的一種主觀評價或價值判斷,是司法行為所產生的信譽和形象在社會組織和民眾中所形成的一種心理反映[1]關玫:《司法公信力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2008年版,第61頁。。它主要取決于兩個基本條件:一是社會公眾是否相信司法是公正的,是維護公民利益的,這不僅需要精通法律、經驗豐富、不徇私情、剛正不阿、清正廉潔的司法者,而且需要司法者具有很好的法律修養和較高的職業素質、職業能力等。二是他們是否相信司法有足夠的力量按它自己的規律發生作用。如果司法是公正的,并且有足夠的力量按它自己的規律發生作用,也就意味著在司法活動中,對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而言,凡是合法利益都會得到尊重和保護,凡是被侵害的權利都有機會獲得救濟,凡是違法責任都不會由于對法外因素的考量而得到豁免[2]鄭成良:《法治公信力與司法公信力》,〔北京〕《法學研究》2007年第4期。。而國內“信訪不信法”現象的普遍存在則說明,當今司法不僅不能很好地回應公眾的信任和信賴,而且也沒有摸清司法運行的基本規律,同時,也暴露出現行司法公信力之法治保障的制度性缺失。正因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坦言,“當前,部分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步泛化成普遍社會心理,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現象。”[3]吳兢:《最高法副院長:不信任司法漸成普遍社會心理》,〔北京〕《人民日報》2009年8月19日,第6版。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亟待反思:(1)形成現代司法信任危機的原因是什么?我們能不能為此從理論上建構一種全新的理論分析范式?(2)誠信體系建設是否可以增加現代司法的公信力?如果是,我們又應該如何以社會資本為分析范式,有效論證司法公信力的道德屬性?本文認為,提升司法公信力意味著司法需要更多的社會資本,而這種社會資本的獲得則需要司法誠信為保障,以引導民眾逐步變信訪為信法,并逐步樹立、鞏固與強化司法權威。
二、基于認同的權威:誠信體系建設視域下的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意指司法通過誠信體系促進司法權威的形成,提升司法權威,而成為一種“資本性”資源。司法權威是司法獲得社會資本的基石,也是司法公信力的源頭;司法權威的缺失將是一種司法災難,帶來的結果必然是以力量的邏輯代替誠信的力量。從類型上說,司法權威有基于恐嚇的權威、基于認同的權威和基于知識的權威之分,它們都是提高司法權威的可能路徑。然而,基于恐嚇的權威是政治文明低下狀態下的選擇,而基于知識的權威則是以法律教育為內容的軟約束,只有基于認同的權威才能帶來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要形成基于認同的權威,則需要我們從誠信體系建設入手強化公眾對司法的認同。認同是一種制度性的資產,社會結構提供像銀行系統般可確保的制度性功能,其關鍵點在于社會結構與組織的運作。社會道德規范、制度、規章等是社會與法律機制形成信任的基礎,這些機制支撐著信任的運作,決定了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及其影響力。如果司法能爭取民眾對其的認同,并藉此擴充對司法活動的信任,則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目標指日可待。而相反,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一般民眾與司法機關之間沒有信任,那么司法權威、司法公信力等將還只是一個“美麗的夢”[4]Emile Durkheim and Lewis A Coser,The Devison of Labour in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64,p.80.。
在認知心理學上,認同其實是人類的情感與理性共同作用的結果,當感情與理性都高漲時,產生的意識形態的信任是驚人的,比如,宗教領袖及其信徒,集權主義者及其追隨者等。盡管司法不同于心理測驗,但透過心理學的結論,我們也大致能推導出信任在現代司法中的功能:一方面,國家一般從公共利益出發來安排司法策略與技術,民眾則有自利性的要求,這就產生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對立關系。要消除這種對立,爭取司法中的公眾認同至為關鍵。另一方面,認同是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可以使合作更為簡單。一個互相信任的社會比一個相互猜疑的社會更有效率,正像貨幣交換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樣,信任也會為司法運行增添潤滑劑,民眾如果認同司法,也會比抵觸司法更富有效率。對此,我們還必須意識到,無論何種類型的司法,都在于致力于永恒秩序的追尋。當司法是誠信的,且能為民眾謀取利益時,比如,既維護了良好的治安環境,又重視保障人權時,民眾對司法的信任會增加。反之,如果司法活動存在著權力尋租、投機行為和欺騙,或者偏離民眾的利益偏好時,民眾必然會失去對其的信任。而一旦發生信任危機,則會面臨司法困境。具體來說,誠信體系建設的司法價值體現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
其一,就宏觀層面而言,誠信體系建設的司法價值體現在,誠信是推動某一國家、地區司法權威的強大動力。人類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結成社會,為了特殊的利益分割和基本信仰建立國家,形成了不同于私人領域的社會、政治、經濟等關系。一個國家和一種社會秩序的維系,一般來說要靠兩個方面,一是道德,二是法律。前者是軟的一手,后者是硬的一手[1]焦國成:《關于誠信的倫理學思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緣于此,信任程度的高低成為影響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文化因素。正如弗蘭克納所指出的:“在任何有效的選擇中,一個行為是正當的,當且僅當它或是它的指導準則能夠促成或趨向促成的善至少超過惡;反之則是不正當的。在任何有效的選擇中,一個行為是應該去做的,當且僅當它或是它的指導原則能夠促成或趨向促成的善最大限度地超過惡。”[2]〔美〕弗蘭克納:《倫理學》,關鍵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8頁。進一步而言,誠信體系緣何會成為影響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在這一問題上,制度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具有資源價值的理論路徑。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司法的一個重要表現方式就是其能夠確立穩定的社會預期。司法的運作過程,也就是法律直接作用于當事人與間接作用于公眾,是一個化解社會糾紛,懲治和教育犯罪人,安撫被害人和教育一般民眾遵紀守法的動態過程。對此,可以簡稱為司法的回應功能,即在動態的司法過程的背后,擔當的卻是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的重任。以刑事司法為例,一方面,它會盡力減少犯罪的危害,并通過發揮司法激勵作用,使受害者、一般民眾能夠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另一方面,它會合理組織對犯罪的反應,并通過發揮司法激勵作用引導犯罪分子積極接受教育改造,以使他們能重新回歸社會關系之中。在這里,司法回應功能的發揮與司法誠信體系建設及其運作密不可分,提倡并重視司法誠信的目的就是通過公開化的、可接受的司法裁決,以減少摩擦。這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二,就中觀層面而言,誠信體系建設的司法價值體現在,誠信能夠通過司法活動過程帶來社會正義和司法效率。應當看到,基于司法與倫理內在統一的立場,司法具有明顯的道德性。司法通過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和公開透明的審理模式獲得司法認同的回報,這一趨利行動本身內含“滿足民眾之正義要求”的向善目標,實現了司法運作與司法誠信的內在統一。從這一意義上說,誠信建設能夠成為實現司法權威的積極的文化資源。之所以如此,是與民眾對司法公正的期待正相關:司法公正不僅體現為案件處理過程及結果是否公正,而且體現為民眾對司法裁決過程及其結果的感受。在司法信任面臨危機的當下,后者對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意義更大。這就需要現代司法激發民眾對司法公正的感受,進而形成司法認同。在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中,任何有效的、立足于誠信體系的激勵,都必須能夠滿足個體的需要,這就是所謂的“需要動機理論”[3]“需要動機理論”可以簡單的概括為:需要引起動機,動機決定行為。。我國學者又把該理論細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動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內容型激勵理論;另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過程和行為過程相互作用的動態系統為研究對象的過程型激勵理論。應該說,心理學中有過程型激勵理論與內容型激勵理論的劃分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分別揭示了“需要動機理論”的系統性和動態性,但在司法的道德性中,過程型激勵與內容型激勵無法截然分開,即每一層次的激勵都可能對其他層次的激勵產生影響,各個激勵層次之間存在著一個相對的滿足程度和滿足標準,每一個層次的激勵的內容和滿足標準都會影響到其他層次的激勵,同時又受到其他層次的激勵的影響。而司法也是一種交往活動,誠信在減少司法沖突和增加司法認同上至關重要,一個沒有信用的司法是不可能獲得公眾認同的,而不受公眾認同的司法也是難以有正義和效率可言的。
其三,就微觀層面而言,誠信體系的司法價值體現在,誠信能夠通過對司法人員品質、素養和境界的提升而成為一切司法活動不可或缺的精神動力。司法活動從根本上說是人的活動,但司法人員是否能夠真正成為司法活動的“第一要素”,卻與其價值理念和道德素養密切相關。具備積極的人生價值、心中充滿正義感和具有職業道德的司法人員,方能成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資本”。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道德資本與司法權威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與司法權威直接關聯的道德資本,又影響或制約著司法權威的形成。司法人員的司法能力提高、司法公正的實現等等,轉而又有賴于司法人員的正確的價值取向、司法倫理精神與道德實踐。易而言之,誠信體系之于司法的推動作用,正在于它以一種“非正式的制度”成為不可或缺的資本性資源。此種資本的存在及其運行,可通過減少不必要的摩擦、保障正式制度運行而起到降低成本、提高產出的作用。單就制度對司法的激勵作用而言,亦有正激勵與負激勵之分。一般地說,如果制度激勵能將司法主體、司法客體、司法關系人的價值追求和行為目標向著與“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相統一的方向上引導,并使他們確立和采取一種為社會所需要和提倡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那么這種激勵就是正向的或良性的。相反,如果制度激勵只是激發、引導司法客體、司法關系人追求個人的、眼前的利益,而忽視了社會的、長遠的利益,并使他們確立和采取了一種為社會所不容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那么就會導致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司法裁決與民眾認同關系的嚴重失調,就會滋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這就是一種負向的激勵。無疑,我們需要的是司法的正向激勵,同時,應當對司法的負向激勵保持必要的警惕。很顯然,誠信體系建設就是一種正向激勵,它不僅能夠激勵司法者始終堅持清正廉潔,一身正氣,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而且激勵司法者在確保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最大的限度地節約司法資源,減少當事人的損失,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強化信任,意在增加現代司法的社會資本,為此,除了強化司法人員的道德素養,培養司法人員的良知與正義觀念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重視司法的道德性。這是形成司法認同,進而形成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條件。
三、認同的自我激勵:司法公信力的制度決策展開
完善的法律不存,圣智的法官難求。我們應該借助于立法決策展開,主動去尋求司法公信力,這主要涉及強化司法對立法的忠誠、重視司法的道德基礎和確保司法的公正廉潔三個基本維度。
1.強化司法對立法的忠誠
司法誠信首先意味著對立法的忠誠,即司法活動(包括法律解釋)應該依法而為,不允許逾越法律規定而任意為之,在確保法安全的基礎上,實現司法權威。司法誠信意味著對正義的追求,這也是司法誠信的題中之義。但是,在立法表述模糊之時,就可能面臨兩大難題:一是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以及近年來民眾參與意識的提高,在一些存在道德困境的案件,或者說是情理、倫理與法律沖突的案件,由于它們不具有“邏輯上之必然”的特性,而是屬于“可爭辯的”問題領域,這又使司法與道德之間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困惑變得至為復雜。司法實踐也大抵如此。這幾年中國司法一個極為熱鬧的場景是:無論是許霆案的無期徒刑判決,鄧玉嬌案是否應被判處刑罰,抑或李昌奎案之死刑判決,民意都構成了對司法的強力制約,并影響到刑事審判的最終結果,甚至導致一種“生死兩重天”的結果。二是成文法的穩定性、安全性與其自身的不合目的性、模糊性相伴而生。以刑法為例,由于刑法采納了大量的簡短詞匯(盜竊、搶劫、搶奪、詐騙等),這就不可避免地繼承了法律用語的模糊性、多義性以及開放性的特質。而同時,刑法文本中大量的“情節嚴重”、“造成嚴重損失”、“后果特別嚴重”等作為罪量的表述形式,雖然起著限制犯罪圈或加重處罰的效果,但是,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可操作性上存在著灰度較高、解釋難以統一等弊端。這樣一來,立法權與司法權之間的界限劃分就成為了突出問題,司法克制主義與司法能動主義就是為處理兩者之間的界限而形成的兩種理論,并互相爭執,難決高下。
由此決定,司法對立法的“忠誠”必須一分為二:一方面,對于法律的明確性規定,司法必須予以充分尊重,并無權自行變通,否則,就是一種違法司法;另一方面,對于法律的不明確規定,司法必須從法正義出發,正確對待道德問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道德是法律的最高價值宿命。“道德上如何,法律上亦然(Aswithmorality,so with law)”[1]〔英〕艾倫·諾里:《刑罰、責任與正義關聯批判》,楊丹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這是現代司法正義理念的格言。究其根本,司法最終的力量來源于公眾內心的支持與信賴,這是一種“道德強制力”(moral sanctions)。如果司法能夠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向,反映公民社會長久而穩定的價值,那么它就能贏得公眾的支持,并不斷積累其制度上的聲譽。這是因為:司法本身并非目的,使人們共同的價值觀化為現實的理性規則秩序才是其根本所在。其中,由司法所保障的價值就是法律價值,“而這些各種法律價值的總體,又被抽象為所謂的‘正義’。”[2]〔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頁。從人們共同的價值觀到法律秩序的“物化”過程,正是司法價值有效內化,并成為社會成員自覺的價值選擇和行為準則的過程。如果說在野蠻的古代社會,法律秩序靠宗教神諭和武力強制尚可勉強維持的話,那么在現代社會,沒有社會成員對法律規范的合法性認同,則社會將面臨著深刻的危機,法律秩序只有滿足了集體意識中的正義情感與價值訴求,獲得了普遍的公眾認同,才可能具有存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3]梁根林:《合理組織對犯罪的反應》,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頁。。約翰·密爾指出,“使我們認為不正義的行為得到懲罰,總會給我們帶來快感,并與我們的公平感一拍即合。”[4]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in John Stuart Mill and Bentham,Utilitarianism and other essays,ed.Alan Ryan, Harmondsworth,Penguin,1987,p.321.其實,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構成了他們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這種生活體系便是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特別在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道德同質性程度較高的社會中,這種集體意識的力量更為強大[5]〔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42頁以下。。
2.重視司法的道德基礎
德國學者認為,“法并不是一個自我陶醉的封閉系統;它要受到公民的‘民主的倫理生活’的滋養和一種自由的政治文化的呼應。”[6]〔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698頁。事實的確如此。在一個價值單一化的時代,司法裁判并不是什么難事,法官之間“心有靈犀”,較易達成共識。而在一個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各種各樣的價值立場粉墨登場,大放異彩,這在創造了精彩紛呈的“劇場”效果的同時,也使司法裁判變得艱難,討論何為正當性的司法裁判則往往“眾口難調”。這就給當代司法帶來了巨大挑戰:面對同一案件事實,但因不同的言說者的價值立場與分析工具不同而導致觀點上的“紛爭”,這在許霆案、李昌奎案、藥家鑫案等中得以集中體現,以至于在實踐中“法官的專業”屢屢讓位于“民眾的憤怒”或“不當的行政干預”。然而,司法裁判追求結論的唯一性,它顯然不能不滿足“怎么都行”的現實。其實,司法是適用法律進而實現法律價值的一個能動的過程。古斯塔夫·勒龐曾指出,人類群體是個活生物,它有自己的感情、思想,這種感情和思維就是“群體心理”[7]〔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戴光年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2頁。。
在這一能動司法的過程中,唯有司法者堅守人類在長期社會生活實踐中積淀下來的、作為人共通部分的“常識、常情、常理”,才能保證司法裁判的結果不違背普通公民的意志,也才能夠最終實現法律的價值。這就是能動司法的底限,也是能動司法在面臨多選題時得出“唯一正解”的最終衡量標準。對此,拉德布魯赫曾把良心與正義觀念區分開來,他認為,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雙重倫理秩序之下,其一方面的要領序列可以稱為:義務、和平、仁愛、謙恭;其另一方面的價值概念可以稱為權利、斗爭、榮譽、自尊,第一類詞語主要見諸于我們的良心,第二類詞語則主要見諸我們的正義觀念之中[1]〔德〕拉德布魯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國瀅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源自于民眾“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豪邁氣概以及推己及人的心境,如果司法判決違反正義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則失去效力,這就是李昌奎案在不少法學家的反對聲浪中被“再翻燒餅”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重要原因。當然,這也正是拉德布魯赫所倡導的價值相對主義法哲學對不正義司法的有效過濾。唯有如此,現代司法不僅能使當事人“心悅誠服”和一般民眾“無話可說”,而且也才能實現“書本上的法律”到“活的法律”的順利轉變。
3.以判決書說理增強司法裁決的說服力
缺乏公眾認同的侵潤與支撐,司法就會出現所謂“雙重不確定性(double contingency)”無法解消的困境。“假如誰要進行論證,那么他就必須既要保證(人們)對其前提的認同,也要保證(人們)對每一個證明步驟的認同。”[2]〔德〕羅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作為法律證立理論的理性論辯理論》,舒國瀅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頁。這就需要判決書說理制度予以保障。
在以往的法哲學家中,如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盧梭、康德或邊沁等及其各自的支持者們也都能夠用道德性觀念來正確地說明權威問題,并且聲稱他們的權威理論都表明了其合法性條件能夠得到滿足的方式[3]參見鄧正來、約瑟夫·拉茲、朱振:《關于道德與政治哲學視野中的法律哲學的對話(上)》,〔北京〕《哲學研究》2010年第2期。。為了實現這種認同,哈貝馬斯還別出心裁地在民主時代提供了溝通理性,以交談、論辯等方式使法律或司法裁判取得民眾的認同。問題只在于,民眾自愿認同的基礎是什么?不難想象,保持司法與市民感覺、國民規范意識之間的一致性,強化一種回應性、服務性司法權威觀,以保持司法的親和力,并使之獲得公眾對司法的認同感,在我國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所謂司法的公眾認同,即考慮什么樣的判決結論是一般的國民可以接受的,符合一般國民的規范意識,從而肯定司法的經驗、情理、感受的合理性,肯定道德判斷的重要性。公眾的司法認同最終表現為結局合理、對行為過程的妥當評價兩個方面,前者意味著人們愿意看到正義得到伸張,邪惡得到懲治,后者體現為司法過程本身符合國民一般的規范理念或道德觀念[4]周光權:《論刑法的公眾認同》,〔北京〕《中國法學》2003年第1期。。而集體意識、正義情感對司法的廣泛的公眾認同,又使司法獲得了超然于所有的功利性追求之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以藥家鑫案的死刑判決為例,在一般民眾看來,即使死刑不具有威懾效果,只要基于道義責任而公正地適用,滿足了集體意識中的正義情感,獲得了廣泛的公眾認同,就具有存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5]參見梁根林:《公眾認同、政治抉擇與死刑控制》,〔北京〕《法學研究》2004年第4期。。
如何實現民眾對司法的認同,則需要我們以法律論證理論建構判決書說理制度。一如我們所知,法律是事實、規范與價值的結合,它連結著“此岸”的規范和“彼岸”的事實兩個不同的世界,并受價值選擇的影響。單一強調事實的作用是片面的,也是沒有生命力的,最典型的分析莫過于韋伯的扔進去事實丟出來判決的自動售貨機式的比喻。當司法裁判導入道德話語系統的分析模式之后,一方面,它離不開對現行法律規范的解釋,以促進法律規范的正當實施,從而形成一種已然的法律秩序;另一方面,法律也承載著民眾對未來理想法律秩序和美好生活秩序的向往,期望能夠通過司法向人們輸送一種應然的法律秩序。如果遵循權威能夠使人們服從正當理由,那么這個權威就是合法的[6]參見鄧正來、約瑟夫·拉茲、朱振:《關于道德與政治哲學視野中的法律哲學的對話(上)》,〔北京〕《哲學研究》2010年第2期。。故而,道德話語系統對司法的敘事自然也包括規范解讀和價值引導兩個維度,這兩種敘事方式伴隨著司法裁判的始終。
以刑事司法為例,我們必須正確處理法官的定罪、量刑與民意之間的辯證關系。在難辦案件中,人們很容易從裁判結果的關注(比如許霆案的無期徒刑判決,李昌奎案二審的死緩判決等)轉入對裁判依據及其說理的深度關注。當人們對裁判理由提出若干“何以如此”的質問,而法院提出的裁判理由又難以自圓其說或者與民眾共同的價值觀發生沖突之時,這就帶來了司法認同危機。怎么辦?在法律論證理論看來,既然價值判斷是多元論的,人們應該生活在一個多元的世界中,人們在為某一裁判結論進行辯論時,必須要考慮到不同聽眾(讀者)的感受,這種辯論必須符合民眾共同的道德觀而不是形式邏輯的原則。法律論證理論的最大的特色與優點就在于它將受眾放到了一個中心的位置,強調一種情境性。它突破了原來法官說著晦澀的行話、而公眾停留于認識法學黑箱的外包裝上的局面,在法官與公眾之間開拓了一條溝通的渠道。它主張通過對話、辯論來說服聽眾相信自己提出的裁決,在多種裁決結論競爭中爭取最大支持而成為正當性的判決。而要實現這一點,必然要求法官共同體的價值判斷與受眾們的價值判斷保持一致,必須締造一個“公意的巢穴”。龐德說,“許多時候,正義的實現是兩種趨勢的妥協:一種趨勢是將每一個案件都當做某一類案件中的一個,另一種趨勢是認為每一個案件都是獨一無二的。”[1]轉引自〔美〕卡多佐:《法律的成長法律科學的悖論》,董炯、彭兵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不難看出,兩種法律方法都有其獨立的價值,并且分別適用于不同的案件,因此強調“公意的巢穴”并不必然帶來對司法獨立、司法權威和刑法平等的破壞,也不必然帶來民粹主義。從這個角度講,判決書說理決不是“反理性”的,毋寧說它將司法裁決隱含的論辯活動帶入更復雜、更可靠、更貼近人們共同的道德觀的交往結構之中,它是法官在司法領域中通過對話、商談或論辯來形成司法認同和增進司法權威的必經的門扉。
“那里有危險,那里就有拯救的力量”(荷爾德林語)。當現行司法對誠信體系的背離使司法活動面臨昧于非正義、不被認同的危險的同時,也展示了一種拯救的力量,那就是,立足于社會資本理論重新審視和正視司法中的誠信體系。其中,在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方法選擇中,在司法權威的自我重塑中,我們需要不斷地重溫和思索伯爾曼的著名論斷:“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它不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還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覺和獻身,以及他的信仰。”[2]〔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梁治平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8頁。這句名言所蘊含的智慧給我們以重要啟示:作為立足于刑法認同的司法公信力的意義,也就是以“道德資本”為依循而增加司法認同的制度性努力。
〔責任編輯:錢繼秋〕
Integrit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Ethical Capital of Judicial
Jiang Tao
If judicial adm inistration fails to effectively face public intellectual challenge,the tendency is unavoidable of loss of judicial integrity,effect deficiency,and drop in status,leading to the decline of judicial accountability.The declining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ng an integrity system and the necessary approaches:Not only should a sensible,thorough and appropriate standard system clearly indicating judicial integrity be established to provide adequate institutional stimulation for judicial authority,but also the loyalty of judicature to legislation should be reinforced,the moral basis for judicature should be valued,and judicial justice and purity should be guaranteed to achiev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judicial integrity;public identification;judicial accountability
姜 濤,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210023
本文系“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PAPD)資助,同時也受到本人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刑事政策制約刑法解釋的理論建構與制度實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