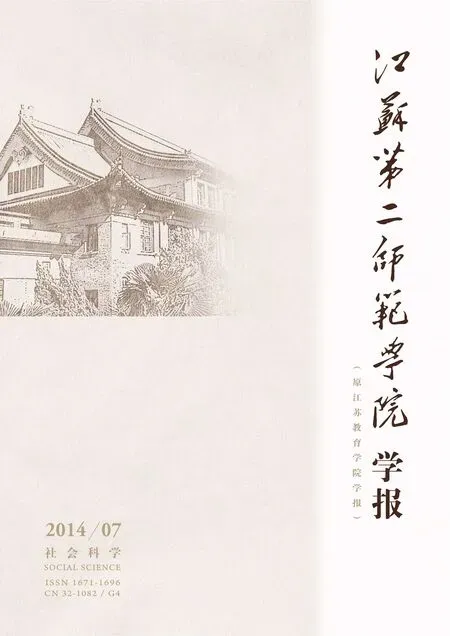辛苦營生的近代江南村婦——以民國時期的蘇州轎婦為例
張 帆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江蘇蘇州 215123)
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似乎是傳統中國民眾日常家庭生活的一個縮影,相夫教子、奉公婆是一個妻子的本分。提起傳統中國婦女群像,恐怕大多數人腦中第一時間出現多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深藏閨閣;三寸金蓮”等等詞匯。在傳統中國的文人筆下,傳統中國女性往往不茍言笑,著裝素樸,以傳統的“德”作為立身處世的根基;她們的活動半徑只限于家庭之內;她們奉老撫小,侍夫和親,主持一家生計;她們孝順貞潔,慈和仁愛,安靜地扮演著她們“應該”的角色。方志中一個個名載“列女”的名字,地方上一座座標榜貞潔的牌坊,也都體現了傳統中國社會關于婦女的一種價值導向,即便到了近代也依舊如此。可是,這些并非傳統中國婦女日常家庭生活的全部,任何試圖用固定的一面去概括中國鄉民的日常生活場景的努力都很可能掩蓋或抹煞掉他們各自有意義的特點。從近代關于蘇州天平山轎婦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她們為了生活而拋頭露面、出賣體力、狡黠經營,甚至比他們的丈夫對家庭收入的貢獻還大,可是她們的家庭地位卻仍然和傳統居家婦女一樣,是丈夫的附庸,蘇州轎婦的境遇頗令當時人嘖嘖稱奇。立足于民間——地方世界,追尋當時蘇州轎婦的形象和日常生活場景,有助于對此得到合理的認識。
一、蘇州轎婦的群體形象:健壯活潑、狡黠營生
提起江南女性,特別是蘇州女性,絕大數人想到的或許都是從古到今文人墨客創作的詩詞小說等數不清的文學作品中那經典的蘇州女子形象。她們講一口吳儂軟語,體態嬌柔纖弱,邁著三寸金蓮;她們可能還會點昆曲評彈,有幾筆寫意書畫,一舉一動都像是有溫度的藝術品。這樣的女子當然未成年時深藏閨樓,出嫁之后又多在內室,外界的紛紛擾擾似乎和她們的一生沒有太多關系。除了親屬,她們也見不到太多的異性;除了繡花,她們也不必做其它的勞動。而天平山的轎婦們所代表的的則是大多數人聞所未聞的蘇州女性形象,她們體格粗壯,四肢有力,膚色黝黑;邁著大腳在山間健步如飛;一口吳儂軟語并不用來唱曲而是大咧咧地招攬生意,和游客討價還價;她們不是深居內室,而是拋頭露面;她們不是全憑父母、夫君做主的小女兒,而是自己動動頭腦耍出花招多賺生意的大女子。
1.健壯與活潑:蘇州轎婦的外在形象
雖是蘇州女子,靠著體力掙營生的天平山轎婦們可全然沒有文人墨客中面容姣好、體態纖細的蘇州女子形象。天平山的轎婦大多是20多到40歲,甚至不少“只有十七八至二十余歲……正在最動人愛的時代”[1]。在這人生青春動人的階段,她們的膚色已經因為長期的日曬等原因呈現出栗色,“都市中人的所謂朱古力色,”[2]她們“乃是十足的農婦,手臉的皮膚都粗糙枯黃,更毫無我們想像中蘇州女人的風度。”[3]蘇州天平山的轎婦們穿著藍布束腰短衣,身體結實,粗黑健壯,“腿和臂,是挺壯碩的。腰肢雖還保持著女性所固具的曲線條,但是襯托著寬闊的肩膀和臀部,充分的表現著健康的征象。”[2]“那健壯,活潑,渾厚而誠樸的模樣,每個人身上都蘊藏著一種活力,這種活力是青年的生命,是城市中人所沒有的。”[4]
她們當然也不像傳統中國的女子邁著三寸金蓮緩緩前行,在天平山的上下山路上,她們邁著大步,輕巧熟練地扛著山轎,走得飛快,讓有心觀察的人驚嘆她們在山路上一路健步如飛。她們的性格也活潑、大方,一點不拘謹忸怩。夏天的時候,抬著客人上下山路,“大汗也已似潮水一般從額上滾到嘴邊,濕透了頸背,滲入了衣褲,全身如洗了個澡,熱氣蓬勃地發散著。”[1]
她們真實健康的體態、活潑自然的性格,讓一部分人贊嘆轎婦們是完全符合著都市中人所說的健康美的條件的,也使一部分人覺得她們是十足的農婦,“毫無我們想像中蘇州女人的風度”[3],認為轎婦難以代表姑蘇的女子。
2.賣力與狡黠:蘇州轎婦的抬轎營生
轎婦們大多是天平山附近的村婦,她們就近在天平山做起了抬轎的營生。抬轎子這門營生,除了出賣體力,其他的成本不高,“轎是一張竹椅子安上二根桿,裝上個扶手,便行啦”[5]。考慮到不是所有游客都選擇坐轎,以及游客在游玩時的飲食等其它需要,轎婦們往往還會“在那山腳設個攤,賣自己把樹枝砍成的手杖,合水果糕餅等外,有正廣和汽水,大英牌香煙”[5]。也有些不從事小生意買賣的轎婦,會把“繡花的繃子架在一邊放著,若是有了生意就停止繡花去抬轎,若是價錢說不好或沒有客人來,她們就坐下來繡花”[9](P.28)。這樣就充分利用了沒有抬轎生意時的時間,也能看出蘇州轎婦們為了生計的精打細算與勞作之辛苦,不能不讓人產生敬佩。
一個天平山附近的女子大概從十五六歲時差不多就開始練習抬山轎。剛開始的時候,她們因為體格尚未發育完全,體力不夠,經驗也不足,往往傾向選擇一些瘦小的女客或者小孩子。等到慢慢經驗和體力都增加了,“對于游客,只要是肯出錢的,便沒有什么取舍,都爭著兜攬。”[7]還有的轎婦,生了孩子還在哺乳期,就抱著嬰兒出來抬轎,“給小孩抱在懷里用一根腰布捆在衣內抱著,一面抬轎一面喂奶,”[6](P.287)游客覺得她不容易,講可以等一等,轎婦自己反而不介意,希望馬上抬轎子前行。因為“快去快回來也許還可以多趕一班生意呢!”[6](P.287)蘇州天平山轎婦們為了營生,吃苦耐勞程度可見一斑。
轎婦們平時都在聚攏在游人登岸附近,還沒有到下車或下船以前一里半里的時候,她們就已在沿河岸邊等著,看見客人來了,就跟著車或船在岸上跑著說價錢。一旦當船靠了岸,轎婦們便迅速聚攏過去,爭先搶著用吳儂軟語說:“轎子要吧?坐轎上山去吧”。讓聽著她們說話的游客覺得她們招攬生意的話甚至“比爵士音樂更為動聽。”[1]她們開出的價格倒也不貴,攬客態度又非常積極,“有不坐者。必尾其后。呶呶不休。”[8]這樣一來除了本來就愿意坐轎的人坐了轎,連一部分原本沒有想著要坐轎的游客在搖擺中也成了她們的顧客。“若是價錢說好了,客人坐上去,她們兩個女人抬著就走,若是人分量重的,就三個女人輪班的換著抬”[6]。
價錢談好,客人落座,轎子向著山上走。客人坐在轎上,還可以聽轎婦用柔美的蘇白,伴你談談,給你擔負起向導社員的職務。可是當客人優哉游哉,以為這就既可以節省體力,又可慢慢欣賞天平山色的時候,轎婦們的狡黠便逐漸展現出來了。她們往往在走到半山腰的時候會停下轎子,“說肚子餓抬不動了,要點心錢,或者說草鞋破了,家中還有三歲的新滿月的小孩,等他(她)們回去哺乳討點心。”[9]“跡近詐欺的勒迫行為,如若不肯付給的話,便將你停在半途而不前,致令坐者不得不敷衍若干。”[10]這種行為往往使游客興致頗受打擾,一些本來對轎婦自食其力行為心懷贊賞的人也對轎婦的評價打了折扣。對于那些本來因為轎錢開價不高,而模棱兩可中放棄步行選擇坐轎的游客,更是因為付了比轎錢多了幾倍的“點心錢”而大呼被轎婦敲了竹杠。
對于天平山轎婦在講好轎錢之后,上下山途中借故再索要小賬的行為,絕大多數記錄者是以親身經歷持批評態度的,認為這是訛詐欺騙行為。旅游區的私人服務者在與游人講好價格以后再乘機另行要錢這種行為無論在哪個時期都是負面的,天平山轎婦這種行為也并非孤例。不過一些人在批評之余也做了更深層次的思索,認為“我們對于這般耐勞忍苦自食其力的女轎夫,自然應予敬佩,雖然游客因其無理索詐而不免引起惡感,然而較之一般不勞而獲的市儈,究竟要高明得多。而且她們根本未受敎育,更應曲予原諒啊!”[10]還有為轎婦做辯護的人認為,批評轎婦索小賬行為的人是沒有體會到轎婦們生存的艱難,對于基本生存都很難保障的轎婦,她們不偷不搶靠著自己的體力來掙一點點辛苦錢養家糊口,哪里還顧得上清高,顧得上旁人評價的好壞呢?況且她們在掙錢的同時也會為顧客著想,抬轎的時候和顧客聊天,為顧客做旅游講解;顧客與她們討論起生計等問題,她們也樂于答話;遇上了山間乞討的人,轎婦們也往往也從不肯在有乞婦的地方停下轎來,以免乞丐影響了顧客的游興。
多數的游客在描述天平山轎婦抬轎的身姿時都用健步如飛、矯健等詞語,讓人以為轎婦們身體健壯,抬轎并不是多難承受的事情。可是也有細心的人提到“久聞蘇州女轎夫健步如飛,此時我細細觀察,卻并不盡然。我注意到前面的那一個,盡是把轎杠在肩膀上移動著。她將轎杠斜放在兩肩上面(或者不如說她扭轉了肩膀承著那堅硬的轎杠),所以老是有點歪來歪去。”[3]想想“轎的構造雖只是在兩根竹桿中間裝上一只藤椅,但加上乘客的重量,也在一二百斤之間。”[10]一般游人空手走山路都覺得吃力,轎婦們抬著轎子,為了一天多拉幾趟還勉力盡量加速,真是非常令人敬佩。也許,多設身處地為她們想想,就能對她們要小帳的行為多一點點體諒、少一點點批判了吧。
二、蘇州轎婦的家庭地位:男人的附庸
近代女子平權主義者在提高女性地位的呼吁中,很重要的一項是女性的勞動權,女子平權主義者號召女性不做家庭主婦而是走出房門參加勞動,自力更生,從而提高婦女的地位,頂起家庭半邊天。也有人認為單單依靠丈夫的收入過活的女性是寄生蟲,想要提高自身地位,不做男人的附庸,必須要獨立,要有能力賺錢養活自己。女性通過獨立勞動獲得收入對于女權的重要性也許是很重要的,但是作為女權提升中的眾多有利因素之一,女性走出房門參加勞動并獲得收入這件事本身卻未必能直接提升其個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蘇州的村婦為了賺錢不可謂不辛苦,她們平時參與農作物耕種,“在那田間,有點點的青布頭巾一起一伏,這是農婦在播種,一撮撮的豆或是一撮撮的麥,從她們手中點入土中,埋伏著未來的萌芽,而為人類的養料所仰給。雨來了,她們的衣服濕了,她們的身體濕了,然而她們并不躲避,依舊在雨中辛勞。”[11]在參與農活的同時,村婦們還在日常利用長輩傳下來的織繡手藝制作工藝品、日用品補貼家用,而當天平山游人多的時候,村婦們又變成了轎婦,抬著轎子到天平山去靠著女性劣勢的體力來賺取收入。
轎婦的丈夫,在種田之余,也有抬轎的,也有開山石的,也有打獵的。可惜的是,男人們并不像他們的妻子那樣知道利用每一段農閑來掙錢,他們也不像妻子們那么省吃儉用。“他們把所獲得的山雞,獐,兔等換得的錢,除了捐外,便在“太白遺風”的小酒店里消磨整年的傍晚,晚上呢?給卅二張骨牌迷住了心。”[5]而做開山石工的男子,“更沒有一個是不吃鴉片或吞紅丸的,他們工資是三天一元錢,可是他們的煙毒消耗、一元錢只夠二天。”[1]
作為山嶺附近的鄉村,出產不多,夫妻若能在農忙之余都做些副業,攜手同心,勤儉持家,也未嘗不能使家境越來越好。本來日常生活中,勞動之外偶爾去去茶館,喝喝老酒消遣一番倒也無可厚非,但是一旦沾染了大煙和賭博,就簡直成了欲念的俘虜,只愿意去享受了。自己的收入如果不夠煙賭享受,便從妻子那里討要,更有男子甚至幾乎不參與勞動,“盡有整天的盤桓在(酒館)內的。高興時,還可暢快地賭一陣子。這么著消耗掉的金錢,卻都不是用自己的血汗去換來的。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向出賣著勞力的妻子們,所壓榨得來的。”[2]
按說,妻子靠著自己的勞動成為了家庭收入的主要貢獻者,她們是配說平等也應該有權享受平等的。可是事實卻不如此,蘇州的轎婦們不僅沒有因為為家庭貢獻了收入而提高地位,反而使丈夫們因著家里面有這么一筆收入而愈發好逸惡勞、胡作非為起來。“天平山附近的男人們,他們毫無羞愧地從勤苦的女人手中不勞而得來的錢,養活自己,而更令人發指的,他們一點不知儉省,一味縱任著自己的劣性情,吃喝呀,嫖賭呀,任所欲為,假使賭輸了,或受了外邊的氣,回家還找尋老婆出出怨,不是打就是罵”[7]。女人們面對丈夫的胡作非為,所能做的竟只有更加賣力的抬轎賺錢,努力維持家庭的正常運轉。在了解這些情況的人心中,除了贊嘆轎婦們矯健身姿,自食其力的做法,也會感慨一聲“伊們的實際生活,卻是如此的苦痛呀!”[1]
沉迷于賭毒的丈夫們不知道是否想過妻子們的艱難,但他們似乎并無多少愧疚,依舊游手好閑、日復一日把妻子掙來的辛苦錢花費在享受上。他們像所有貢獻了家庭大部分收入的男人一樣,是家庭的主人,而真正為了家庭貢獻了大部分收入的妻子不僅地位沒有什么提高,簡直像是丈夫的奴隸了。
對于這種現象,有人歸結為是中國普遍夫為妻綱的傳統觀念所致:“做女人的,總是忍受,除了自嘆命苦之外,是不加以些微反抗。她們雖是粗糙女子,但因為出身良家,對于服從丈夫的傳統觀念,不敢,而絕也沒有存心去破壞它。”[27]晚清時來華的美國傳教士盧公明也曾對近代中國家庭夫妻關系留下記錄,認為當時中國家庭“權力都在男人手中……如果你問一個中國人,婦女是否可以因為丈夫通奸或什么理由要求離婚,他會覺得這個問題荒謬可笑。做女人就是要一輩子服從丈夫,任由他反復無常”[12](P.53)。也有人認為蘇州轎婦的命運是一個極為獨特的地方現象,“能頗有歷史的維持著這么個制度,這真不能不說是蘇州風土志中的一個奇跡。”[2]
若想很好的解釋這個問題,恐怕還需要涉及勞動收入與家庭地位,傳統中國社會的夫妻關系,傳統社會的家庭構成,男女社會觀念等方面進行細致探討,還需要在以后做進一步研究。所幸的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傳統社會中男尊女卑的觀念在現代中國人腦中以越來越淡漠;法律的逐步健全,社會風氣的提升也都使家庭內部的不平等情況越來越少。造成近代蘇州轎婦那樣可憐家庭境遇的社會氛圍,也隨著近代社會的劇烈變動,而漸漸遠離了我們的時代。
三、蘇州轎婦的存在因素:環境與時代使然
通過目前掌握的材料,眾多記錄者關于初次知道轎婦存在時的驚異,我們大概可以推斷蘇州天平山轎婦的存在,至少呈群體性廣泛的存在大概是在近代以后。轎婦這一固定營生模式作為近代以來蘇州區域社會生活深刻變遷過程中的伴生物出現的原因有如下幾端:
第一,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中國,大紡織工廠的出現,劇烈地沖擊了傳統蘇州地區家庭的手工紡織刺繡生計。蘇州婦女歷來重視女紅,富家小姐、太太們的繡品或許大多只是用來陶冶情操、傳續傳統和展示技藝;普通農家的刺繡則一直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綾綢之業,宋元以前惟郡人為之。至明熙宣間,邑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雇郡人織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居民乃盡逐綾綢之利。”[13]到了近代,蘇州的刺繡依然頗有市場,“剌繡的副業,這差不多是伊們世傳的技藝(,)而且人物花卉,都繡得異常精妙。在上海市場上銷行著的顧繡,實際上全是伊們的出產。”[1]可是因為大工廠高效低成本的規模化沖擊等原因,織品、繡品的市場價格被愈壓愈低,因而商人到鄉下收繡品的價格也被越壓越低,“顧繡莊派跑街下鄉,把應做的工作交給伊們,約定時期再來收取。然而工資是異常的低薄,統扯只二三百錢一天。”[1]微薄的紡織刺繡收入已經不能像從前那樣支撐家庭日常支出,所以村婦只得紛紛想別的出路,增加收入補貼家用。可是在農村生活環境中所積累的生活經驗,并不足以使村婦們在近代急劇變遷的都市環境中游刃有余,因而“在絕大多數江南鄉村,就地改變職業,是婦女們的首選目標”[14],天平山腳下居住的婦女們因而也就開始了抬轎的營生,在春秋兩季農忙之余,為家庭賺取一點收入。
第二,天平山山田出產微薄,卻自古就是一處有名的旅游勝地,有可利用旅游資源,“山頂有蓮花洞,又有白云洞,皆山中最勝處,山皆奇石,環形異狀,可喜可愕”[15]。蘇州天平山地區,土地生產力薄弱,山田不值錢,山中又沒有什么出產,“上面竟沒一株樹,遠望著僅是紫色山石而已。”[5]本來農村的主要收入即為自家田地中的出產,天平山地區山田貧瘠,雖然是一樣的辛勤勞作,可是一年到頭的田中出產卻不多。而天平山山中也無出產,擔柴販運更加勞累利薄。相對來說,利用天平山春秋兩季往來不絕的游客上下山想坐轎的念頭掙幾個抬轎錢,已經是附近農人能找的較為穩定又能掙到錢的好途徑。“抬轎子,雖則勞苦,至少終有幾毛錢可得。”[1]
第三,男人們的慵懶與喜好煙賭。抬轎子本來是出賣體力的活計,各處轎夫多為男子,但天平山的轎子卻多是女子來抬。從時人留下的文字記錄來看,一是男子有諸如打獵、為人開山搬掘石頭等其他營生;二是因為男子多嗜好大煙,沉溺于賭博,開銷大,自己的收入不夠用,女人們只好出來做事掙錢;三是男子多慵懶,“在這些蘇州的名山左近的小村落中,特別發達的,是茶館,酒館,以及煙館等等。年青的漢子們,盡有整天的盤桓在內的。”[2]丈夫們被游樂給迷住了心竅,家庭的維持需要收入,女人們只好獨自肩負其本該夫妻一同肩負的重擔。而這些男人們反而還須給女人養他們。
結語
一定的俗例是特定人文環境的產物。近代蘇州轎婦的出現,是有其自身存在的小環境與整個變動中社會大環境所共同作用的。在一些人看來,她們似乎正順應了女子平權運動,可以不依靠男人而走出家門自食其力,是生活的強者。可是在傳統價值取向根深蒂固的鄉間,她們所處的小環境中,轎婦們依然是男子的附庸且難以抗爭。“中國婦女運動發軔于辛亥革命以前,至五四運動而傳遍全國”[16],不過蘇州轎婦選擇抬轎的營生多半是生存逼迫下的使然,而非響應近代特別是五四之后女子獨立的呼聲。“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育著太復雜的內質”[17](自序),近代江南村婦群像也是一個多色彩,多角度的大畫卷,立足于民間——地方世界,盡可能還原蘇州轎婦的日常生活場景和生活規則,有助于進一步認識近代江南村婦生活場景的多樣化和豐富性。
[1]朱維明.蘇州天平山下的抬轎婦女[N].申報,1934-08-11(15).
[2]周賢.蘇州的女轎夫[N].申報,1936-04-11(14).
[3]錢公俠.蘇州的女轎夫[J].雜志,1944(12).
[4]周光熙.杜鵑花[N].申報,1933-05-17(12).
[5]沈右銘.山游拾得[J].十日談,1934(29).
[6]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M].長沙:岳麓書社,1987.
[7]江鳥.蘇州天平山的女轎伕[J].婦女雜志(北京),1941(2).
[8]蔡釣徒.蘇行拾趣[N].申報,1929-05-03(21).
[9]孫福熙.「文藝茶話」的蘇滬往還[J].文藝茶話,1933(2).
[10]君宜.蘇州的女轎夫[N].申報,1946-5-23(8).
[11]孟.蘇州散記——農業都市的剪影[J].民間(北平),1936(3).
[12][美]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中國人的社會生活(1865年初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13][清]丁元正等,修.倪師孟,沈彤纂.乾隆吳江縣志(卷三十八風俗一生業)[M].民國石印本影印.鳳凰出版社選撰.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二十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14]小田.江南鄉村婦女職業結構的近代變動[J].歷史檔案,2001(3).
[15][清]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卷六山一)[M].江蘇書局刻本影印,1882(光緒八年).鳳凰出版社選撰.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七冊)[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16]張維禎.抗戰以來婦女問題言論集序言[A].陳庭珍.抗戰以來婦女問題言論集[C].青年出版社,1935.秦孝儀.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影印版[M].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
[17]林語堂.吾國與吾民(1934年)[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