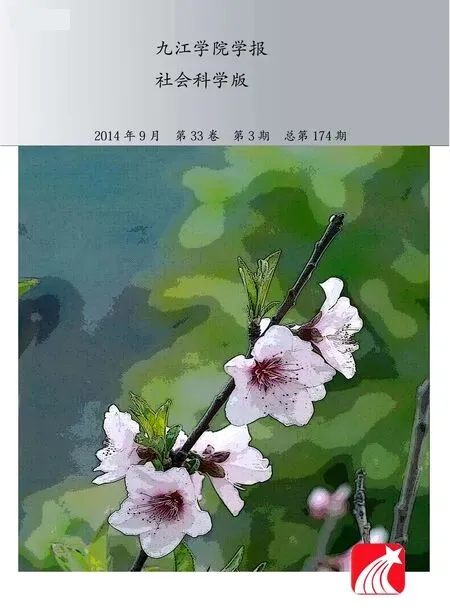政治、法律視野下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持
王 曉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廣東廣州 510275)
政治、法律視野下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持
王 曉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廣東廣州 510275)
一直以來,政治和法律被視為分析社會秩序的兩大研究路徑,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十分豐碩的成果。本文從學術史的角度,試圖對與之相關的過往研究做一番梳理。
政治 法律 社會秩序 建構 維持
社會秩序,簡單地說是“社會得以聚結在一起的方式”[1]。它不僅是人類的本能需求①,更是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前提。美國學者亨廷頓曾強調認為,“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2]也正是緣于此,社會秩序一直是中外學術界共同關心和大力探討的重要問題。若把開拓新領域的研究稱為為跑馬圈“生地”的話,那么有關社會秩序的話題無疑已經是一塊地地道道的“熟地”。時至今日,涉及社會秩序研究的成果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也不為過,政治學、歷史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及各相關交叉學科都從不同的視角對其進行了闡釋,并為改善社會秩序的實踐作出了重大貢獻。但為了凝聚話題,不致面面俱到卻泛泛而談,本文僅對圍繞“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持”這一主旨所展開的國內研究予以梳理和檢閱。
一
一直以來,歷史學界有關傳統社會秩序的探討不絕于耳。但在“國權不下縣”的傳統政治框架下,有學者就把中國傳統社會分為兩種秩序形式:一種是以皇權為中心的“官制”秩序,形成自下而上、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另一種是“鄉土”秩序,以家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村落,每個村落是一個天然的“自治體”,結成蜂窩狀結構[3]。因此,傳統的鄉土社會是散漫和諧的自然社會,皇權政治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4]。韋伯的《儒教與道教》就持這樣的觀點,“事實上,正式的皇權統轄只實施于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出了城墻之外,統轄權威的有效性就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因為除了勢力強大的氏族本身以外,皇權的統轄還遭遇到村落有組織的自治性的對抗。”[5]與此相伴生的是,亦有學者強調專制政權的全面控制,即歷代王朝無不自上而下將高度集中統一的國家權力經各級各地的行政管理機構一直延伸到底層的鄉村社會,把分散的小農置于體現國家君主意志的行政控制之下,維系大一統的社會秩序。這一自上而下立體式的社會控制思想在蕭公權的《中國農村:十九世紀帝國政權對人民的控制》一書中得以集中體現。通過對作為治安工具的保甲制度和作為農村征稅機關的里甲制度,以及作為饑饉管理的“常平倉”、“義倉”、“社倉”等谷倉制度和作為意識形態統治的“鄉約”等制度的考察,蕭氏認為,帝制統治下所謂的“自治”并非專制政府的意圖所在,而是不完全集權的結果。作為一個獨裁政府,它可以通過保甲、里甲、鄉約等類似的民間組織②把政權力量延伸到自然村內,乃至每一家農戶,只要覺得有必要它就會隨時隨地干擾鄉村的生活[6]。此外,在吳晗對士紳階層③的角色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相類似的觀點。在他看來,士紳階層是皇權的執行者,與官僚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是作為國家控制地方的延伸形式而存在的[7]。
這種“官府—民間”二元對立的經典表述,在上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基層社會史研究的繁榮,很快就受到了挑戰。牛津大學教授科大衛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國家控制論的弊端,他說:“‘控制論’令我們不滿的地方,是被統治者往往被描述成被動者。政府制定了政策,人民乖乖地適從,社會由此而得安定。這個理解解析不了動亂,所以就把動亂說成是失控。這個理論也解析不了經濟發展,以為經濟發展必然來自政府政策。”[8]于是,在以后的研究中,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走出書齋,步入田野,用自下而上的人類學研究視角和互動模式審視區域與基層(鄉村)的社會秩序問題。
在區域研究上,華南學者卓有成效。比如劉志偉的《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稅制度研究》[9],就是從區域視野出發,關注里甲賦稅制度在規范地方社會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此外,鄭振滿對明清福建家族組織的研究也可劃歸此類。依他的陳述,明代中葉以后,地方政府職能萎縮,鄉族組織開始全面接管地方公共事務,從而擁有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權,成為名符其實的地方管理者[10]。徐曉望曾總結過宗族組織的社會控制功能,主要表現在:①懲惡揚善,維護地方治安;②以族正、家長、“公親”調解族內婚田爭執等民事糾紛;③以宗族共同體、祠堂所屬的祠產,賑濟贍養本組孤寡孤獨,避免其流離失所,或轉化為社會的對立面;④組織宗族武裝,團結丁壯,自保鄉井,防范盜賊[11]。弗里德曼認為,正是因為宗族組織的地方管理功能減輕了國家社會控制的很大一部分負擔,所以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會支持宗族,甚至還通過賦予士紳特權而造就強大的房支和宗族來穩定地方秩序;但另一方面,族權膨脹也容易破壞封建法制,擾亂社會治安,國家也會對其進行必要的制裁和抵制[12]。
論及地方社會的秩序問題,日本的“地域社會論”無法回避。作為該理論的領軍人物之一,岸本美緒曾總結過“地域社會論”研究路徑的兩大特點:一是它基本上是以“秩序稀少性”的感受作為前提;二是它試圖追問“秩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13]正是基于這樣的視角和研究路徑,岸本美緒對明清交替之際的江南社會秩序展開了細致入微地考察。作者認為,明清政權交替之際社會秩序松弛甚至瓦解,出現的權利真空也導致人們的不安心理凸顯。受不安左右的人們為了找到新的全體秩序,紛紛加入到各式各樣的社會集團中去。臺灣學者巫仁恕對岸本美緒從心理學角度強調人們的不安全感提出質疑,他認為與其強調人們的不安全感,不如說成是當時人們對社會競爭激烈化的感受。尤其是中國人口的壓力與既有經濟資源的萎縮,在明代中期可能達到空前的程度,這也是為何只有在明中期以后,人們會感到高度的社會競爭,進而非得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社會結合[14]。除岸本美緒的江南社會研究外,森正夫對明末清初福建寧化縣“寇”、“賊”的把握、山田賢對于清代四川移民與地方秩序的研究等,都很有價值。
與區域研究同時,以解剖麻雀式的鄉村個案調查也如火如荼④。其中,諸多作品都涉及到了與本文主旨密切相關的社會秩序問題。如蕭鳳霞在《華南的代理人與受害者:鄉村革命的協從》[15]中,就通過個案考察對鄉村秩序進行了整體把握。她認為,傳統時代的中國地方社區離行政控制中心較遠,具有較大的自主性,然而隨著20世紀以來國家行政力量的不斷向下延伸,鄉村的權力體系已經完成了從相對獨立向行政“細胞化”的社會控制單位的轉變,而新的政治精英也成為這些“行政細胞”的“管家”,造成社區國家化的傾向。在黃樹民對福建林村自建國后的變革考察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觀點。在黃看來,中國農村中有一種全國性文化明顯抬頭。傳統上小型、半自治而獨立的農村社區,慢慢被中央政府為主的大眾文化所取代[16]。這種趨勢的出現,毫無疑問是與國家權力通過各種渠道深入鄉村密不可分的。徐勇及其弟子在他們的“下鄉”系列文章和學位論文中就對國家如何通過政權、行政、政黨、財政、金融、法律、服務及現代民主制度等渠道深入鄉村,國家意志如何貫徹以及在此過程中又如何與基層社會力量進行互動等方面進行了探討⑥。
論及鄉村場域下的權利互動與秩序維持,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7]是不能不提及的,作者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新概念,即包括不斷相互交錯影響的等級組織(諸如市場、宗教、宗族和水利控制等)和非正式相互關聯網(諸如庇護人與被庇護者、親戚朋友間的相互關聯等),它們共同構成了施展權力和權威的基礎。“權力的文化網絡”的提出,糾正了以前的鄉村社會研究只關注政治、經濟等方面,而忽視宗教、文化和價值觀念等文化因素對鄉村社會運作影響的缺陷,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鄉村社會控制體系的復雜性和多元性。吳毅通過對一個村莊一百年的村治歷程的詳細考察,認為影響20世紀雙村村莊權威與秩序形態的基本變量是現代性、國家和村莊地方性知識,國家的因素是連接和溝通現代性和村莊地方性知識的中介。國家與現代性對雙村公共權威體制進行重構和再造,極大地擠壓了村莊地方性知識存續和活力空間,但地方性知識也不是完全被動地等待國家與現代性的銷蝕與拆卸,以其頑強的生命力,通過各種方式表現自己的存在。[19]上世紀90年代后,隨著國家權力后撤和基層組織建設,鄉村自治的研究也蔚然成風,為人們更深一步了解地方社會的政治秩序打開了另一扇窗口。⑤
二
在大批學人關注權力運作與社會秩序時,亦有學者從法律的角度展開對社會秩序建構與維持的考察。法律與秩序密切相關,“與法律永相伴隨的基本價值,便是社會秩序。”[19]奧古斯丁曾說,“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要求和平和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和秩序的必要工具。”[20]雖然不少人類學家在不斷向我們提供證據,試圖說明無需法律的秩序不但存在且運作良好。但“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欲暴弱也,然不敢者,畏法誅也”的至理名言卻清晰表明了法律存在的必然性。
經過對成文法的討論,越來越多的學者眼光向下,挖掘民間社會中活生生存在的、非國家范疇的法律資源。其中,梁治平有關民間習慣法的解釋尤其值得一提。按他的陳述,習慣法乃是由鄉民長期生活與勞作過程中逐漸習慣的一套地方性規范,它被用來分配鄉民間的權利與義務,調整和解決他們之間的利益沖突。習慣法并未興諸文字,但并不因此缺乏效力和確定性,它在一套關系網中被實施,其效力來源于鄉民對此種“地方性知識”的熟悉和信賴,并且主要靠一套與“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有關的輿論機制來維持[21]。在他看來,民間法與國家法從屬于不同的知識傳統,原則上,以朝廷律令為主干的“官府之法”凌駕于民間法之上,以體現且保證帝國法律秩序的統一性。但實際上,官府并沒有足夠的財力和人力對州縣以下的廣大地區實施直接統治。朝廷律例也遠不曾為社會日常生活提供足夠的指導原則,所以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倚賴于民間的習慣與規范,以維持整個社會的秩序。這也意味著,不但人們的日常生活大都受習慣支配,一般紛爭也很少提交官斷,而且地方官在審理所謂“民間詞訟”的時候,也經常要照顧到民間慣習和民間的解決辦法[22]。
這種“分工與合作”的關系在黃宗智對“第三領域”的研究論述中清晰可見。黃氏認為,中國地方社會處理糾紛中存在著正式系統、非正式系統和第三領域三種形式。在傳統社會調解糾紛的過程中,官方法律與民間慣例相互影響,由此形成不同于正式系統即衙門審判和非正式系統即民間調停的第三種途徑,即第三領域,或中間領域。在他看來,近百年來中國雖然在法律理論和條文層面上缺失主體意識,但在法律實踐層面上卻一直顯示了相當程度的主體性,第三領域一直在中國治理制度中齊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其中,簡約治理原則和半正式行政方法——依賴不拿國家薪酬的準官員以及國家機關只在發生糾紛時介入的方法,一直延續了下來。集體時代的鄉村治理、文革時期的“民辦公助”村莊教育,甚至今天的村莊治理和上訪制度都可以看到這一原則和治理方式。在強調民間因素對案件審理的影響上,日本學者滋賀秀三比黃宗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認為,“清代地方官在處理民事糾紛時,更多的是依據情理來對當事人之間的關系進行全面的調整,而非運用法律對事實作單方面的判斷。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就被輕視或無視,因為法律本身是基于情理而定的——國法就好比情理大海上的冰山。”[23]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巨大發展和社會轉型,傳統的地方性規范式微,已無力應對新出現的混亂狀態,“送法下鄉”遂成為國家治理鄉村的不懈努力。“不但有時令性的‘普法’運動來刷幾條標語,而且還建立了自己的機構,比如派出所、法庭、司法所、法律服務所,養下一大幫人。”[24]對于這種送法下鄉,蘇力認為這本質上是國家通過司法的路徑來加強國家政權建設,進行對鄉村社會的控制。但同時,蘇力又承認現代性法律制度的干預使得村莊秩序處于極度艱難的地位:一方面正是的法律制度沒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務,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與熟人社會性質相符卻與現代法治相悖的實踐[25]。
但毫無疑問的是,“送法下鄉”的多年堅持還是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使得農民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一些現代的法律常識。雖然這些知識對于農民來說是模糊而抽象的,而且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之中他們也是絕少地使用這些知識,但一旦其處于事件之中,特別是經過他人點撥之后,這些蟄伏的模糊的概念便可能被激活而成為一種博弈的武器。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董磊明提出了“迎法下鄉”的概念,他認為在地方性規范越發疲軟的今天,鄉村社會內部越來越期待國家法律或者說國家權力來整合鄉村的秩序。在他看來,在新近的鄉村社會場域之中,現代法律剛剛進入鄉村時的那種粗暴和強制可能會少了一些,地方性規范不斷地援引國家法律作為助力,這表明法律已經未必是造成鄉村混亂的力量,相反它還有可能是維持秩序的力量[26]。李連江、歐博文對農民政治參與中法律意識的研究為此提供了佐證。通過一番考察,他們認為農民在政治參與時,為了抵制各種“土政策”和農村干部腐敗行為和獨斷專行,經常援引相關政策或法律,并有組織地向上級直至中央政府施加壓力,以促進官員遵守有關的中央政策或法律。[27]
三
由于社會秩序問題涵蓋面較廣,上述檢閱不可能是完整的。其實,除政治和法律視角外,亦有諸多學者從其它不同的側面對社會秩序進行過考察。如,從經濟方面談起的有惠雙民的《社會秩序的經濟分析》、楊春學的《經濟人與社會秩序分析》等;論及宗教信仰與社會秩序關系的有劉紹云的《宗教律法與社會秩序——以道教戒律為例的研究》、楊春花的《論信仰對于社會秩序的價值》等;討論社會控制與社會秩序的包括池子華的《流民問題與社會控制》、金玉學的《民俗與社會控制》等。這些成果,與前述那些研究一樣,也為人們認識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持打開了多扇不同的窗口。
[1](美)李普塞特著,張華青譯.一致與沖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12.
[2](美)亨廷頓,李盛平等譯.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華夏出版社, 1999.300.
[3]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4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336.
[4]秦暉.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A].(美)黃宗智.中國鄉村研究(第一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68.
[5](德)馬克斯·韋伯著,洪天富譯.儒教與道教[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110.
[6]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pp.261.
[7]吳晗.論士大夫[A].皇權與紳權[C].長沙:岳麓書社,2011.60.
[8]科大衛.告別華南研究[A].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C].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 2004.24.
[9]劉志偉.在國家和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稅制度研究[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7.16.
[10]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14.
[11]徐曉望.試論明清時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關系[J].廈門大學學報, 1985(3):110.
[12](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劉曉春譯.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7.
[13](日)岸本美緒.明清地域社會論的反思——《明清交替の江南社會》新書序言[J].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2000(30):172.
[14]巫仁恕.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の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J].新史學, 2000(3):223.
[15]Siu. Helen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26.
[16]黃樹民著,素蘭,納日碧力戈譯.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M].北京:三聯書店, 2002.17.
[17](美)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18]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72.
[19](美)彼得·斯坦著,王獻平譯.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89.38.
[20]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學說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66.
[21]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6.127.
[2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 1994.15.
[23](日)滋賀秀三著,王亞新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36.
[24]趙曉力.基層司法的反司法理論?——評蘇力《送法下鄉》[J].社會學研究, 2005(2):219.
[25]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50.
[26]董磊明.宋村的調解:巨變時代的權威與秩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11.
[27]李連江、歐博文.當代中國農民的依法抗爭[A].吳毅.鄉村中國評論[C].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8.1.
注釋:
①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指出,對安全的渴望是人類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需求之一,而社會有序則是人類獲得安全感的不竭之源。在馬斯洛看來,無論是兒童還是成年人,都有追求安全的自然趨勢,都不愿意生活在一個紛亂無序的社會和組織之中。見(美)馬斯洛.人的動機理論[A].陳炳權、高文浩譯.//林方.人的潛能和價值——人本主義心理學譯文集[C].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162-177
②有關民間組織的其他研究成果可參見王日根.近年來明清基層社會管理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江蘇社會科學,2001(3);朱德新.民國保甲制度研究述評[J].安徽史學,1996(1);沈成飛.近十年來民國保甲制度研究述評[J].福建論壇,2003(6);秦富平.明清鄉約研究述評[J].山西大學學報,2006(3),等。
③其他相關研究可參見尤育號.近代士紳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史學理論研究,2011(4),等。
④其實,早在上世紀初,就有諸多人類學家進行過鄉村考察。有代表性的是葛學博.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村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1925;李景漢.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1929;費孝通.江村經濟,1939;林耀華.金翼,1948;等,也都從不同的側面涉及到了社會秩序的問題。
⑤參見徐勇.政權下鄉:現代國家對鄉土社會的整合[J].貴州社會科學,2007(11)、“政黨下鄉”:現代國家對鄉土社會的整合[J].學術月刊,2007(8)、“行政下鄉”:動員、任務與命令——現代國家向鄉土社會滲透的行政機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7(5)、“政策下鄉”及其對鄉土社會的政策整合[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1)、“法律下鄉”:鄉土社會的雙重法律制度整合[J].東南學術,2008(3)、“服務下鄉”: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服務性滲透——兼論鄉鎮體制改革的走向[J].東南學術,2009(1);黃輝祥.“民主下鄉”:國家對鄉村社會的再整合[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7(5);吳素雄.政黨下鄉的行為邏輯:D村的表達[D].華中師范大學,2009;樊銳敏.“行政下鄉”與依法行政[D].華中師范大學,2008;任寶玉.“財政下鄉”:農村基層政府財政合法性問題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07;戴禮蓉.“金融下鄉”:構建構架與農民建的信用[D].華中師范大學,2008;等。
⑥代表性成果有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賀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賀雪峰.遭遇選舉的鄉村社會[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白鋼、趙壽星.選舉與治理:中國村民自治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仝志輝.選舉事件與村莊整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
(責任編輯陳平生)
2014-05-12
王 曉(1984-),男,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宗教社會學。
D 631
A
1673-4580(2014)03-0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