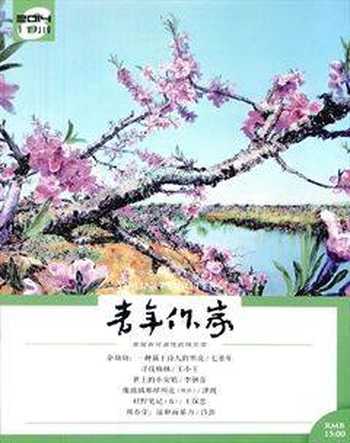余幼幼 一種屬于詩人的明亮
在眾多的年輕詩人當中,余幼幼無疑是特立獨行的。在《星星》《詩刊》《天涯》等一系列純文學刊物上,她的名字已然不陌生,然而直到去年赴北京參加全國青創會的時候才見到她本人。個子小小的,實在有點難以想象那些辨識度極強的詩是怎樣從這個嬌小的姑娘身上綻放出來的。我難以忘記那一次隨意的聊天,她對我說起她去貴州鄉下見到的種種趣聞軼事,她說著,眼睛明亮,語言也很明亮,那是屬于詩人的明亮。
——采訪手記
七堇年:最早是什么時候開始寫詩的?
余幼幼:我從2004年開始寫詩,那會兒上初二,成績還可以,上課也不怎么聽講,經常聽著聽著思想就走遠了、跑偏了。我一般都是桌上放當堂課的教科書,下面放著另外的書,一邊要假裝自己很認真聽課,一邊又在看其他的東西,經常搞得自己神經緊繃,有點小刺激。其實這種精神高度緊張的情況下特能激發靈感,有時候突然被某個點刺激了,就趕緊在教科書上寫下來,扮成在做筆記的樣子,我也被老師逮過很多次,反正死性不改,他們也拿我沒辦法。回家以后整理那些碎片,忽然感覺,咦,怎么特像詩歌。估計我的語感就是那個時候慢慢訓練出來的。那會兒我才十四歲,什么也不懂,不知道怎么寫是好怎么寫是差,我就憑著直覺去寫,直到現在都覺得寫詩我的直覺大于其他。也許是由于年齡小,我的好奇心和對世界的探索欲望很重,喜歡涉足和嘗試未知,喜歡陌生化、反傳統的表達方式,雖然是個標準的魔蝎女,但特別反感俗套和舊式的抒寫形式,于是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寫,愛咋咋愛誰誰,反正也沒人看。但是我從來不硬寫,硬寫不但寫不出好詩,而且還是一種自損。寫詩還是自然而然的好,就像遇見一個喜歡的人,詩歌也是一樣,講求緣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強求不來。
七堇年:就文學類型來說,為什么你最傾向于用詩歌,而不是以小說、散文等形式來進行表達?
余幼幼:其實我最早寫的就是散文,小說一直寫得少,因為思維跳躍得有時候連我自己都駕馭不了,很難去布局寫個故事什么的,寫過好多次小說,中途都放棄了,反正寫小說我有幾個字形容就是:憋屈、痛苦、難受。不過最近我寫了個《即興表演》那種瞎扯淡的,沒什么結構的小故事,把自己給寫嗨了,好多人讀了也覺得挺嗨。通過這事兒我也自我總結了一下,結論是:還是寫詩吧!目前,小說注定是寫不出能稱之為“作品”的東西出來了,不過話也不能說死了,將來人老遲鈍,思維跳不起來了,沒準就能寫了,詩人寫小說可有天生的語言優勢。散文雖然寫得沒有詩歌多,但也一直沒丟,大三到大四的時候寫了個《迷失在九州大道》的四萬多字的隨筆,想的是給馬上結束的大學生活留下一點東西,算是把我精、氣、神都掏空了,沒想到反響還不錯。不過我最鐘愛的表達還是詩,就像電路串聯似的,線路搭對了,燈才能亮,我覺得我寫詩就是屬于文字和交感神經搭對了吧,腦子和心里都特亮堂、特通透,說白了就是爽歪歪。那種感覺就好像詩歌跟我通了靈,觸電一樣,再拿剛剛喜歡一個人來比喻,就是看對眼兒了,怎么著都覺得舒服。
七堇年:寫作對于你現在來說意味著什么?
余幼幼:寫作真的是一個“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東西,但我還是想讓它伴隨我越長越好。如果我有能力讓我的作品留在這個世上,并且可以超越時空,那最好不過。我以前一直覺得能寫就寫,寫不了就拉倒,看得挺開的。但現在越來越覺得,我真的是“拿得起,放不下”,如果哪天讓我不寫了,我還真的會不知所措。如果沒有寫作,我想我還是我,只是不是現在的我,也許是另一個我,我覺得現在的我挺好,沒什么貪念,也不崇拜金錢和物質,這些都是寫作讓我慢慢養成的秉性,喜歡自然澄澈的東西,喜歡自由簡單的生活,不會被世俗的一些浮夸的欲望和膚淺追求所拖累。寫作讓我保持了自己的風格,不容易被外界所侵蝕,我獨成一個世界,我有我自己的主張和觀點,我看透或者看不透都無關乎其他對我的影響,人其實想保持純粹是很難的,我一直在努力做到這一點,寫作幫了我很大的忙。
七堇年:聽說你之前也有過一段上班族的生活,對于這種生活,你有什么感想?
余幼幼:嗯,我剛好上了一年班。感想是,如果當成一種生存手段的話簡直不是用悲催二字就可以形容的。工資付了房租幾乎所剩無幾,還要吃飯坐車買書,養活自己真的不太容易,有段時間特別自棄,感覺自個兒特沒出息,這種狀況維持了半年,然后找單位把住宿解決了,情況要好一點,不過依舊窮得掉渣。我朋友開我玩笑說:“你當個窮人還不夠,還要當個喜歡思考的窮人,你覺得這兩個哪個聽起來更搞笑?”好在我自嘲已經養成習慣,別人怎么講我都當給自嘲添加素材,無所謂了。如果是當成一種經歷的話那還是挺值得回味一下的,甭管好壞,對你的人生都是一種充盈和豐富。只要餓不死,一切都還有余地。不過上班確實很磨損人,一天打三次卡,就如同一天殺三次頭,感覺是對于人身自由的無形監控,有點受不了。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工作單位環境還是比較單純,不用花費精力處理人際關系。由于工作原因還完成了我一份小小心愿,創辦了“52赫茲詩歌網”,專門針對大學生詩人開設的網絡詩歌平臺,希望通過這個平臺,有更多熱愛詩歌的青年人能夠發表自己的作品和文學創作言論。由于諸多客觀因素,網站建成后的運營比想象中艱難,為了詩歌我堅持了一年,有點疲倦和無奈。接下來對于自己的未來我會重新考慮,但我還是持有一種樂觀的態度。我不喜歡上班——也許這就是一個決定。
七堇年:也許難免會被貼上“90后詩人”這樣帶有前綴的標簽,對此你有什么想說的么?
余幼幼:這個標簽其實一直存在,不是偶然,也并非難免。說實在的,我覺得這種劃分除了方便歷史向度的研究外,好像年齡越小越受益。寫得好別人評價你天賦異稟,寫得不好也沒關系,反正還小嘛。其實這是帶有功利性的,我不敢說我沒有從中受益,但我盡量避免標簽大過了我的詩歌本身,首先我是詩人,哪一年出生是自己沒法決定的,是詩人就寫詩,把詩寫好就行了。對待標簽我的態度是你們隨意我自嗨,我的目的不是要去獲得某個標簽上的認可和成立,而是寫出自己想寫的東西。對于那些大張旗鼓宣稱反對被劃分或者被歸類的人其實挺沒意思的,標簽會妨礙你寫作嗎?會讓你變質嗎?既然不能,那管它干嘛。好好寫自己的東西不就完了,耗費精力去反對,其實不就是想獲得另一方面的認同嗎?寫作的人就是拿作品說話,拿不出作品的人才需要搞些別人看得見的東西來撐門面。
七堇年:有最喜歡的詩人嗎?
余幼幼:加個“最”字讓我有點為難,不同的創作階段喜歡讀的東西不太一樣,不過我更喜歡讀詩以外的東西。好像是因為缺啥補啥吧,我比較喜歡看小說和一些內心深處的獨白,自言自語的那種。要說幾個比較喜歡的詩人的話,最早很喜歡保羅?策蘭,喜歡他那種憂傷自抑而又充滿爆發的語言,主要是喜歡他詩中那些象征意味濃重的修飾。前陣子很喜歡貝恩,一個怪誕的醫生兼詩人,他寫了很多關于診所、病人這樣意象的詩歌,讀來十分受震撼。墨西哥的詩人帕斯,一直很吸引我,他關于詩歌理的論也非常精辟。辛波斯卡、阿多尼斯、海子、普拉斯、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都還很值得一讀。不過我現在更喜歡表達簡練、精準、一針見血的東西,不太喜歡打磨得過于光滑的詩歌,粗糙一點讀來更有味道。有時候我還會看一些民謠和搖滾的歌詞,好的歌詞都是詩,這個要說到詩人兼歌手科恩,簡直太有魅力了。
七堇年:寫詩之余喜歡做什么?
余幼幼:不寫詩的時候喜歡發呆,別人看來有點兒浪費時間,但我覺得挺好,讓自己靜下來,用心來呼吸,啥也不想,把腦子放空,有時候我坐著發呆不知不覺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然后就是旅行,旅行也是換個地方發呆,不過那種發呆的感覺是新鮮的。喜歡大自然,喜歡脫離人群的味道的地方,去看看山水,隨意地走,讓人輕松愉悅。
七堇年:你喜歡和同為寫作者的朋友圈子交往嗎?
余幼幼:隨著寫作時間的增加,好像認識的人也多了起來,除了幾個習氣相投的人偶爾聯系一下,其他人幾乎都不怎么來往。經常在一起的朋友幾乎都不寫作,在一起彈吉他唱歌,聊聊有趣的事兒,感覺都比幾個人湊在一起聊文學要放松自由得多,畢竟寫作是很自我和私人的事兒,聊也聊不出個所以然。
七堇年:推薦一些你喜歡的書?
余幼幼:帕斯《詩與思的激情對話》、伍迪艾倫《門薩的娼妓》、曹乃謙《到黑夜想你沒辦法》、大江健三郎《個人的體驗》、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書》、三島由紀夫《潮騷》、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七堇年:最后問一個很老套的問題:你為什么寫詩?
余幼幼:我為什么寫詩跟我為什么吃飯睡覺其實是一樣的。多做一些不為什么的事兒其實并不壞,這樣更從容更心無旁騖。寫詩已經成為我的一種本能,本能的東西也就是你沒辦法克制也沒辦法改變的。我無法回答我為什么寫詩這個問題,只能回答我為什么不寫詩,那大概就是因為我的生命終結了吧。我對詩歌的熱愛也許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如若這是一種偏執,那我寧愿為此瘋狂。
[作者簡介]七堇年,本名趙勤,女,1986年出生于四川瀘州;2006年,她在二十歲的時候寫下第一部長篇小說《大地之燈》;曾獲第九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10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