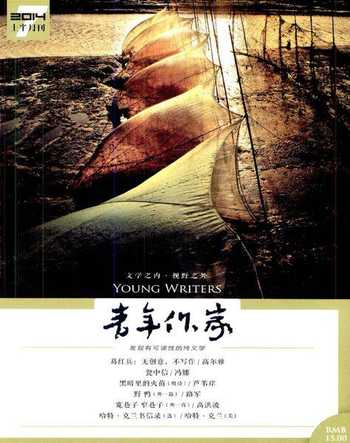老歪
我們常說,一個人的綽號最能看出這個人的特征,這話用在老歪身上,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到現在為止,沒有哪一個人能夠把老歪恰好地歸類于某一類型之中。
可以看出,老歪不是他的本名。可他的本名叫什么,除了少數的幾個人,如單位里人事部門的有關同志知道,沒有人記得。說來也怪,與人見面認識,自我介紹,老歪也會告訴對方他叫什么,可過不了一小會,對方就像別人那樣,喊他老歪,而把他剛告訴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凈了。
老歪出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身高一米八九,山東人,今年三十六七歲,頗瘦。為人俠肝義膽,做事卻隨心所欲,甚至有些虎頭蛇尾。
老歪最常說的話是:“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有敬畏了,才會虔誠,對生命,對宇宙,對自然萬物。否則,即便有生之年得到許多,心里也不會安生。”聽起來,這話很有哲理,甚至大義凜然,但單位老總卻這樣評價他:做事總不上路,能把人活活氣死。我們幾個熟悉老歪的人,認為這樣的評價,最貼近他。
大學畢業,正趕上國家最后一批分配工作,為了能分到一個好單位,他的父親動用了一生的積蓄,就差圍欄里那頭耕牛沒賣了,給他謀得了一份在縣衛生局工作的差事。可他倒好,屁股沒坐穩,還沒把椅子暖熱,就在當年的冬季征兵時報了名。氣得他父親差點吐血,揚言要與他斷絕父子關系。
隨著運兵車來到西安,由于本科學歷,他被授予了副連級中尉軍銜。他寫信給父親,這才讓父親的氣順了一些,認為兒子目光遠大,自己錯怪了他。在部隊老歪很爭氣,獲得過二等功兩次、三等功六次,沒到復員就混到了副團級。按此級別轉到地方,最不濟也是個正科,他的父親正等著享清福時,他卻選擇了放棄。父親一下子血涌大腦,中風了,差一點就搶救不過來了。
他的放棄,自然成全了別人。那位戰友謀得科長之位后,弄了兩瓶“特供酒”,請他喝,他左一杯右一杯,很隨性,卻不醉。他的酒量在全團是出了名的,那人眼看著酒幾乎被他一人全喝了,急紅了眼:“老歪,你多吃菜,酒給大伙留一點!”
他笑笑,以水代酒,仍與大伙喝了個盡興。
酒散后,他跳上火車,只身前往了西藏,自此后,那幫戰友再也沒有見過他。他的父親臥病在床一年多,也沒有收到他的半點消息。
在藏區,他進入一所小學,當了老師。那所學校同他一樣與世無爭,在地圖上你根本就找不到它,就連附近的小村子,也寂靜得讓人以為這兒的人都不食人間煙火。老歪卻很享受,課余,就跑到山里,躺在草地上看藍天。看著看著,他的心就跟著飛了,就像他后來在一首詩里寫的那樣:
身體是透明的玻璃
盛開在純凈的天空
沒有人在我和它中間
也沒有一只動物,或行走
云朵間的風
就這樣飛翔,飲完一壺冰涼的河水
愛與恨,都留在了黑色的大地
從此都與我無關
……
他寫的都是自己的心路歷程,很細膩,卻不追求意義,更沒有想過發表,寫完就丟了。
一場罕見的地震襲擊了四川,許多座美麗的城市,一夜之間變成了廢墟。雖遠在藏區,這兒的人也明顯感受到了余震,屋頂的電燈晃來晃去,藏在暗處的老鼠,也明目張膽地跑了出來。
學校接到通知,放假,是無限期地放假。到底啥時候開學,通知上沒寫。
老歪沒有告訴任何人,就走出了山區。山里到山外,有五六十里的路程,老歪昏天黑地地走,腳心被路上的石子磕得生疼,他也沒有知覺。
在山外的公路上,他搭乘了一輛運輸汽車。坐在汽車上,他沒有像常人那樣,回頭再望一眼山村。他也沒有像要決絕這里似的,把眼睛閉上。他只是望著前方,眼睛像一只死魚眼,平靜,沒有光彩。
前方的路被封了,司機說什么也不愿往前開了。老歪二話沒說,把他的帆布背包一背,就下了車,徒步前行。他走了兩天一夜,終于進入災區,看到卡車一輛一輛地往外運尸體,那些尸體都大大地睜著眼,他的手心里不自覺地冒出了冷汗。
工廠、學校、銀行、商場……所有的建筑都如蜂窩煤那樣易碎。到處是人,各種膚色的搜救隊。老歪加入了其中一隊,隨他們一起,在廢墟中搜尋可能存在的生命。
在路邊一座傾倒的平房里,老歪聽到了微弱的求救聲。“這房子里有人。”他立即向大伙吆喝道。
“不可能!”領隊斷然說道,“那么多支搜救隊都過去了,如果有人,不會不被發現的。再說了,這是平房,對人也造成不了多大傷害,即使有人,也早就自己出來了。”
即便是這樣說,領隊還是側耳細聽了一會,可是什么聲音都沒有。
“前行。”領隊發出命令。
可是,那求救聲卻在老歪的耳邊,真切地存在著。“你們先前行吧,我再看一下。”他對領隊說。
站在廢墟上面,老歪又一次聽到了那種聲音——藏區的生活經歷,讓他的聽覺比常人更為敏銳——他確信下面還有生命存在。隊伍已經前行了很遠,他無法再讓他們回來。他用雙手搬開磚頭,搬了很久,發現了一雙受到驚嚇的眼睛,他仔細地看了看,竟然是一個四五歲的女孩。他下意識地把頭探過去,又聽到了一聲稚嫩的呼救,那個女孩居然還動著。
他用盡全身的力氣,把壓在女孩身上的樓板抬開,幸運的是,樓板壓在了沙發上,并沒有砸在女孩身上。他把女孩抱在懷里,帶到醫療隊檢查是否受了傷害。女孩仿佛把他錯認為自己的父親,死死地抓住他的衣角,說什么也不肯放手。
老歪只好留下來照顧她。
或許,女孩已經意識到,地震把她的家人都帶走了,她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便只有跟著老歪,做了他的女兒。無論是誰問她,她都指著老歪:“他就是我的爸爸。”
老歪哭笑不得,總不能把她送到孤兒院吧?女孩的稱呼讓他百口難辯。
就這樣,老歪在他三十而立這年,還沒有結婚,卻無端地多了一個女兒。
當笑容重在女孩的臉上綻放,老歪給她洗干凈、換上新衣服之后,女孩竟然異常的漂亮可愛,每天在他的身邊,像一個貼心的小棉襖,爸爸長爸爸短地叫著。老歪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茍言笑,就連女兒叫她,也不會露出半點笑容。他的同學問他:“老天平白無故地賜給你一個千金,你咋就沒一點兒高興的樣子?”
他說:“誰知道她是不是來折磨我的呢?得,我單身的日子看來是要結束了,以后有得罪受了。”
同學不解,他又接著解釋:“我總不能一個大老爺們,帶著一個小丫頭過日子吧?現在她還小,還好一點,等再過幾年她長大了,那就很不方便了。說不定,還會惹來閑言碎語呢。”
這是老歪的一點小心機。一旦他成了家,給女孩應該享受的父母之愛,女孩也就真的成為他貼心的小棉襖了。
其實,老歪還是在信奉著他的一個原則:人應有所敬畏。有敬畏,才會得到應有的回饋。他相信女孩就是大自然的回饋,他要繼續保持這種虔誠,即便是意外所得,也不能得意,要隱忍,繼續謙卑。
老歪帶著女孩來到深圳,在同學的幫助下,進入報社做了一名記者。他有這方面的天賦,他對文字的感覺,對事物的銳敏,使他在記者這個職位上,得心應手。在他入職的第二個月里,一場雨使紅花路人行道出現了塌方。這是一件常見的事情:每逢大雨,總會有這樣或那樣塌方的消息。只是,紅花路前不久剛剛重新修整過,還架起了一座人行天橋,天天車水馬龍人流如注。老歪感覺這件事背后大有貓膩,他以一個軍人雷厲風行的作風,查閱了許多建筑方面的資料,最終認為這個塌方事件,可能是由工程質量引起,那就是這條道路還存在著嚴重的安全隱患。
老歪決定追查下去。生命是平等的,他不容忍因工作錯誤,而造成對別的生命產生威脅,更不容許自己對這件事有所察覺卻假裝視而不見,最終釀成更大事故的情況發生。
毫無疑問,采訪工作并不那么順利。有人拉攏他,有人威脅他,就連介紹他進入報社的同學,也找到他,對他說:“有些事情知道了,并不一定非要報道出來。在深圳,靠的是人脈,多結識一個朋友,就多一條路,何必非要跟人家結仇呢?”
同學是為了自己好,老歪從來就沒有懷疑過這一點。只是,他像是鉆進牛角尖,出不來了。他說:“我不會刻意與任何一人結仇的,但如果別人非要這樣認為,我也毫無辦法。”
聽他的話茬,好像有慷慨赴義的悲壯。
老歪掌握了足夠的數據,支撐他的報道。報道出來后,整座城市都掀起了軒然大波。一項造價數千萬元的工程,經過層層轉包、層層克扣,最終只以數百萬元的成本完成施工,這樣的工程質量如何確保人民的生命安全?
一系列的黑幕被揭露,多位領導被查處。老歪因此被升職加薪,榮登金牌記者行列。辦公室內,同事們向他表示祝賀,他只是詭秘地一笑,走進了領導辦公室。
“我申請調換崗位,希望您能考慮,把我調到編輯崗上去。”面對領導,他開門見山。
“你這是怎么啦?”領導嚇了一跳,“你剛剛榮升為報社的金牌記者,怎么就想換崗了呢?要知道,許多人用幾十年,也拼不到這個崗位呢!”
“天曉得我還會捅出啥樣的窟窿來!”他說,“通過這段時間,我發現更適合做編輯,當然,我這也是為了孩子著想,我自己倒無所謂,但總不能讓孩子也跟著我擔驚受怕吧。”
他的請求理由充分,領導不好駁斥,只好應允。他轉職為副刊編輯,薪水也相應地跟著降了不少。
同事們說他傻,有著高工資的活不干,偏偏要干不被人重視沒有任何好處的副刊編輯。他像個沒事人一樣,兀自開始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好像他的價值并不是用工資高低來體現的。
副刊編輯是個閑職,專門編發本地作者寫的散文隨筆之類的小文章,每周二四六三個版面。老歪總是提前一個星期就把稿件編好,這樣,他就有許多時間,用來思考、閱讀、陪女兒。
同所有的副刊編輯一樣,老歪身旁很快就聚集了一幫文學青年。他們常常以文學的名義,邀請老歪喝酒、打牌、桑拿、逛公園。每到這個時間,女兒就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噘著小嘴,滿臉的不高興。老歪明白,他的確該考慮個人的婚姻大事了,就是為了女兒,也要這樣。
老同學出面幫忙,給他安排了幾次相親。每一次,他總是顯得憂心忡忡。他說:“我現在都不敢給爹娘打電話了,每次,他們總是會問:什么時間帶媳婦回家。人生在世,啥時間才能真正為自己而活呢?”——一場大病,使父親豁然開朗了,兒子的路就由兒子去走,走成什么樣子,是他自己的事。可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他還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夠抱得上孫子。
但抱怨歸抱怨,老歪還是打扮得整整齊齊的,去見對方。
有那么兩年多的時間,老歪常去相親,幾乎每兩個星期都會相親一次。這令我們大為不解,這么多的女孩子中間,沒有一個讓他滿意的?
老歪說:“也不是完全這樣,還是有兩個在保持交往的。”
老歪說的這兩個,我都見過,其中一個是我們的同事,每天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另一個是位中學老師,戴著一副高度近視鏡,斯斯文文的。
“與她們在一起,根本就體會不到愛情的激情,她們都過于沉悶了。”老歪說這話的時候,表情幾近麻木,似乎選對象這件事情,他壓根兒就不愿意干。
“那這兩個中間,你更傾向于哪一個?”
“半斤八兩吧,談不上傾向。她們兩人給我的感覺就像雞肋,丟又舍不得,不丟又沒啥味。”
這個老歪,相親都相出味道來了。
一天,我們正在一起打牌,一個年紀看起來二十三四歲的女孩走進來,站在一旁直勾勾地盯著老歪。他嚇了一跳,問她:“你好,你有事嗎?還有,我們認識嗎?”
那個女孩長得真是青春。她好像剛從健身房出來,一身運動短裝,暴露出她潔白的肌膚。見老歪這樣問,她并不急著接話茬,反而,像觀賞藝術品似的,從上至下把老歪打量了一遍。
在女孩幾近挑剔的目光中,我們又打完了一把牌。洗牌間余,女孩才開始說話,她是對著老歪說的,她說:“我喜歡你,如果你愿意,我們可以處對象。”
這算什么事情,把我們都當成透明的了?談情,也應該找個私人一點的地方呀!我們極為不滿地盯著老歪,其實是羨慕嫉妒恨地看著他。
老歪幾乎是用斜睨的眼光看了女孩一眼,繼續發牌。人都說,情場失意,賭場才會得意。可老歪,一邊贏著我們的錢,還一邊享受著這“飛來的艷遇”。他笑著說:“哦,就這事兒呀?”
我們幾乎想沖上去揍他一頓了。什么叫就這事兒呀?
女孩眼里含著淚水,反問道:“怎么了?你嫌我長得不夠漂亮,還是覺得我這樣直接,不夠矜持?”
“都不是,”老歪把牌發完,直接撿起底牌,頭也不抬,就開始理他手中的牌了,“愛情是一件很鄭重的事情,怎么能在打牌的時候談呢?”
“要不然,我們今天先玩到這兒,你先處理正事。”我們建議他。
“打牌也是很鄭重的事情。”老歪說,“我開始出牌了,你們要小心了。”
女孩一聽,知道跟這樣的男人談愛情是沒有希望的,便反過來安慰他說:“老歪,我就不讓你分心了,你們先玩牌吧。”
老歪毫不羞愧地笑了,“嗯,這樣的女子才對我胃口。”
面對著這找上門來的艷遇,老歪表現出一副欠揍的模樣。
雖然他看起來吊兒郎當,做事兒也總不上路,一年后,他卻組建了一個溫馨的三口之家,且這種溫馨讓我們每一個有責任感的男人,都很氣憤——
他的老婆,就是那位青春靚麗的健身女孩,年紀比他小十歲,還是個典型的“富二代”,父親是本地的一位建筑開發商,身份以億來計。她自己更是剛從海外留學歸來,在一家高新技術企業任財務總監,出入都是奔馳寶馬的。他的女兒,那位上天賜給他的孤兒,該讀小學了,在別人都為一個學位擠破腦袋時,某位校長卻主動找到老歪,說學位這是小事情,根本就不用操心……感受到父母之愛的女兒,更像個貼心小棉襖那樣的知冷知熱,嘴上甜甜地叫著“爸比”“媽咪”,讓他們夫妻倆高興得嘴都合不上。
這幸福而甜美的生活,讓老歪感到很滿足,周圍的人每一問到,他會隨口說道:“呵,這都是命數。”
有人會撇著嘴,說:“你有啥資格這樣?你現在擁有的,哪一樣是你自己掙來的?不全都是因為你有一個有錢的老婆!”
老歪說:“你這是羨慕嫉妒。不是咱的魅力,這老婆能跟著咱過?”
那人不服氣,就找到他老婆,問:“老歪那吊兒郎當的樣子,你到底看中了他那一點?”
“善良,正直,不隨波逐流,”她又加了一句,“關鍵是他帥。”
那人學老歪老婆的語氣說這句話時,周圍的人似乎得到了心理上的平衡,態度有些曖昧地笑了,只有老歪,似乎聽不出話中的玄機,依舊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樣子。
去年,接上級通知,報社要由事業單位改為企業,這意味著所有的崗位,都將進行新的考核,而個人的收入,則與其崗位績效緊緊掛鉤。領導找到老歪說:“你的工作以往太輕松了,現在準備重新分配些新聞版面,由你來負責,你有什么想法?”
老歪說沒什么想法。他就真的擔起了那些工作,啥怨言都沒有。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許多,他經常加班到深夜才回到家里。不僅如此,以前上班不用打卡,實行崗位責任制,無論人在不在崗,只要把事情做完,就可以了。現在,所有人員,都得按時打卡上班,哪怕是加班到深夜,第二天仍然要依時到崗。
他的老婆看不下去了,在他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時,一邊為他準備宵夜,一邊嘟囔道:“你們領導,真是不通人情,你入職這五年,每年都給他捧回一個全國百佳副刊的獎牌,現在工作增加了,就應該多請些人來做。”
老歪說:“現在報社改為企業了,領導也要為企業的盈利考慮,增加人手,就增加了開支。每個人,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領導也是沒有辦法。”
他老婆說:“既然要考慮盈利,那就好說了,明天我去找一下你們領導,讓他們給你減些工作量。”
“那就不必了,現在這些工作,我還能應付過來。”老歪回答道。
第二天,他的老婆真就走進了領導辦公室。她是有這個能力讓領導改變想法的。同事們對此議論不已,認為老歪如果真減輕了工作量,而他又安然處之,那他真就是“吃軟飯”的男人了。
老歪并不理會同事們的議論,他快速地忙碌著,他知道妻子走后,領導就會找他談話,他要在領導找他之前,把當天的工作做完。
領導叫他時,同事們立即把目光聚集在他的臉上,他仿佛視若無睹,笑瞇瞇地走了進去。
領導有些哭笑不得,“你怎么從來就沒有提起過,你的老婆是我們幾個重要的廣告客戶之一?”
老歪說:“說了又能如何?畢竟,她是她,我是我,我的工作不可能由她來做的。”
“你這個人呀,真拿你沒辦法?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這么多,你就不抱怨?”
“有啥好抱怨的?對于這次調整,同事們大多有意見,可這仍擋不住改革的步伐。我們都知道,工作就是在不斷的妥協中進行的。”
“真是要被你氣死了。別人抱怨可能不見得有用處,你如果抱怨,我們一定會認真考慮的。”領導說,“其實,跟你實話說了吧,我們一下子加重你這么多工作量,是別有用意的。我們希望你吃不消,跑來發牢騷,這樣就可以理所當然地把你調回記者崗位了。你不知道,一名金牌記者對報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要不,你認真考慮一下?”
“我看沒有必要了,目前的狀況,我挺知足……”
老歪的工作量始終沒有減少。
不就是多一點工作,經常免費加班嗎?別人能夠做下去,我怎么就做不下去?面對妻子的質問,老歪理直氣壯地說。
一個單位,無論工作分配多么不合理,但總體工作量是確定的,一個人多干,另一人就會少干。每個人都明白,老歪的工作量如果減了下來,他們中的某個人就會增加工作量。只是,我們在暗笑老歪有些“傻”的同時,也在暗暗慶幸自己有了這么一位“傻”同事。
可是,他真的傻嗎?如果他傻,又怎能一次次在不同的崗位上,取得同事們所無法企及的成績?只是,能不讓自己這么累時,仍選擇了加班加點的繁重工作,這不是傻是什么?
我們發覺,老歪這個人,似乎越來越不可理解了。
老歪依舊埋頭工作,有空時,依舊會同我們打牌,會同一幫文學青年聚會,逛公園,桑拿,或者侃大山。
只是,我們悄然發現,在做完所有的這些事情,他一個人休息時,他會捧著一本書閱讀。在我們的報社圖書室里,他出入的頻率之高,更換圖書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不過,若你因此而認為老歪是一個沉默無味的男人,除了工作與閱讀、該有的應酬之外,回到家里會像大部分中年男人那樣,坐在沙發上,霸占著電視,卻不怎么對老婆孩子講話,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他的骨子里有一種別樣的浪漫。不加班及沒有應酬的時候,晚飯后他會陪著老婆、女兒到公園里散步,陪她們玩游戲、捉迷藏。
一進入陽春三月,深圳的各個角落,都開滿了鮮花,空氣里充斥著一種好聞的芳香。老歪就會休假一個星期,陪著妻子帶著女兒,游遍深圳每一處值得去的地方。
在他編輯的副刊上,第一次出現他的作品,是一首這樣的詩:
牽著她的手,我們在冰封的原野中穿過
從深圳的這端到那端,一只紅蜻蜓
逗留在常青藤上
再也不希望有突然發生,不希望
一只手離開另一只手
我們向前走著,風掀起
姑娘們的裙子,奇怪的是,它
從不驚擾那只紅蜻蜓
已經很久了。有些人已經遠去
熟悉的木質把手,無人再來轉動
我的愛人,請不要擔心
那只紅蜻蜓,那溢滿空氣的花香
會陪伴著你,帶著你經歷
更多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同事們因此而調侃他。每次見到他,都戲稱他為“大詩人”,他依如平常,淡然一笑,便走開了。
或許,在自己負責的版面上,刊發自己的作品,多少有點以公謀私,有點讓人不恥?
只是,誰都想不到,這是他唯一一次在自己的版面上發表作品。在他進入報社的第六個年頭,他向領導遞交了辭呈。
他離開了深圳,帶著女兒,還有他的那個帆布背包走了。
他去了哪里,沒人知道,報社里傳出了各種各樣的猜測:有的說他的妻子給他帶了綠帽子,他忍受不了,只有選擇離開;有的說,他本就一無所有,老婆是大戶人家的千金,肯定在一起不長時間,不被甩才怪;還有的說,他一定是不甘心“吃軟飯”了,離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有的猜測,無一例外地把矛頭指向了他的妻子,把老歪看成了弱者。只有我們幾個牌友,才真正了解,在他的這段婚姻中,老歪才不是弱者呢。但我們沒有一個人出來為他解釋,我們認為,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可不是,他悄然離去,不同任何人說一聲,不是也認為沒有必要嗎?
兩個月后,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裝有一張卡片,用一張照片制成的。照片上,老歪與一幫衣服上帶著補丁的學生,在一個破舊的木頭籃球架前,坐在坑洼不平的操場上。他們的臉上都帶著笑容,那種笑容是發自內心的,因為我看到了他們眼睛中的清澈。照片上,有老歪的親筆題字:本性。
卡片的背后,是手工繪制的圖案,從那笨拙的筆畫與顏色不一的筆跡上可以看出,這幅圖案是多人共同完成的,只是,令我驚奇的是,圖案上顯示的卻是一個溫暖的三口之家!
一個念頭進入腦海,我猛然間如觸電一般。迅速打開電腦,登錄支教網站,在上面我查到了想要的信息:老歪與他妻子的名字都赫然在列,而且是去往同一所學校,某貧困山區小學……
所有的猜測都不攻自破。領導得知此事,意欲組織人員前去探望慰問,然而,信上卻沒留地址。領導打電話到支教中心,對方以保護個人隱私為由,也沒有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慰問這件事,最終只好不了了之。
只是,在報社內部,老歪的故事重新流傳開來,這一次的版本,充滿了不少神秘與傳奇色彩,雖然我們都知道,老歪所有的選擇都如他在卡片上的題字一樣,是出自本性,然而,對于傳頌這樣的故事,卻樂此不疲。
[作者簡介] 阿北,本名張傳奇,1982年生,河南鄲城縣人。曾就讀于中山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深圳大學作家研究生班。90年代開始詩歌寫作,2009年嘗試小說創作,目前,出版長篇小說《易翔的王國》《心理咨詢師》,詩集《流塘·小事件》等。中短篇小說散見于《山花》《大家》《天津文學》《北方文學》等刊物。廣東省作協會員,現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