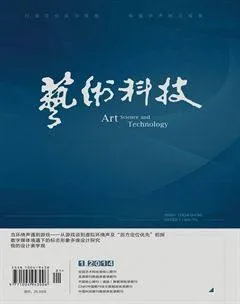《菲羅克忒忒斯》的政治道德與其教育意義
郭叢叢
摘要:古希臘悲劇具有鮮明的教育作用。《菲羅克忒忒斯》展現了共同體需求與個體生命經驗之間的矛盾,索福克勒斯提出了共同體生活中的政治道德:共同體應尊重個體生命經驗,而個體也應自覺維護共同體利益。這樣的道德勸誡在當今社會仍有現實意義。
關鍵詞:索福克勒斯;菲羅克忒忒斯;古希臘悲劇;政治道德觀看悲劇是古希臘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悲劇創作與演出不僅僅是文學審美活動,更是教育、團結民眾的政治活動。因此,在古希臘,進劇院看悲劇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可以得到戲劇津貼。通過觀看戲劇這樣一種審美的形式,民眾感同身受地體驗到在現實生活中不太可能發生的極端境遇,對劇中人物的悲慘遭遇產生憐憫之情,并對神意的莫測、人生的苦難感到恐懼,從而使靈魂得到凈化,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覺的復制并執行著劇作所傳達的價值標準與道德規范。
作為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人之一的索福克勒斯非常重視城邦生活,他在劇作中探討英雄、法律、倫理、道德等難題,展示出城邦生活可能面臨的種種困境,并在一系列激烈的矛盾沖突中表達自己的觀點。索福克勒斯是雅典民主城邦制的維護者,是溫和的民主派,經常在作品中委婉的勸誡統治者以及廣大民眾致力于維護城邦共同體的長期繁榮,得到民眾的普遍歡迎。他本人也在希臘各城邦中都享有極高的聲譽。
本文選取索氏晚年的劇作《菲羅克忒忒斯》為對象,對劇中人物糾葛、情節沖突進行細致分析,旨在探明作者的立場與態度,揭示本劇對于政治共同體與個體成員雙方的教育意義。
1共同體生活的困境
《菲羅克忒忒斯》共有五場,“進場”部分的主要人物是奧德修斯與涅奧普托勒摩斯,其中奧德修斯占據主導地位。在這一部分中,奧德修斯介紹了事情的原委及此行的目的與自己的計謀,并在此過程中顯示出自己的立場與處事原則:當年為了希臘聯軍共同體的利益拋棄菲羅克忒忒斯,如今又是為了共同體的利益來接回他,為了達到目的,不惜采用欺騙等可恥手段,要求涅奧普托勒摩斯為了“共同的目的”而服從他。“第一場”的主要人物是菲羅克忒忒斯與涅奧普托勒摩斯,菲羅克忒忒斯占據主導地位。他從與奧德修斯不同的、個體的角度補充說明了十年來自己所受的苦難,也暗示出自己的立場:信奉英雄主義的行為準則,崇尚正義、武力,鄙視玩弄語言計謀者,要求重視個體尊嚴榮譽與身體經驗,絕不回到特洛伊戰場,屈服于昔日的敵人奧德修斯,并要求涅奧普托勒摩斯出于正義、憐憫而送他回家。
在這兩場中,涅奧普托勒摩斯作為情節線索,見證了本劇的主要沖突:奧德修斯所代表的 “共同體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與菲羅克忒忒斯代表的要求個體經驗得到尊重的生命原則。這種沖突中至少包含著兩個不同層面上的基本問題。
從共同體的維度來看,是否可以用“共同體利益至上”的原則對待成員?也就是說,是否可以像使用棋子一樣利用共同體中的成員,沒有用的時候立即拋棄,有用的時候再拿來用,完全不顧個體的利益與感受?索福克勒斯的答案當然是不能,奧德修斯的失敗說明了一切。他不能說服菲羅克忒忒斯,也無法用武力強迫他,最終甚至失去了涅奧普托勒摩斯這個盟友——共同體的另一枚棋子。為了共同體利益而忽視個體經驗的行為最終又反轉過來危害到了共同體的利益(此時的希臘聯軍需要菲羅克忒忒斯,但是他們之前的行為導致菲羅克忒忒斯不想滿足他們的需求),甚至可能導致共同體的瓦解,這是索福克勒斯苦心經營展示出來的、統治者及每一個共同體成員都必須明白的悖論。
那是否意味著個體的生命體驗可以得到無限放大與極度推崇,在面對共同體的時候取得壓倒性勝利?這個問題是面向共同體成員的,也就是在問他們,共同體需求與個體經驗發生沖突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完全不顧集體,只追求個體利益的獲得與尊嚴的滿足?索福克勒斯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在劇作的退場部分,菲羅克忒忒斯不肯回到特洛伊的堅持取得暫時性成功,個體生命經驗得到尊重。但在這時候,等待他的命運是不再成為希臘聯軍中的一員,也就是退出共同體。這樣的人不再是政治人,不再享受政治權利,不再是希臘城邦中的“公民”。這意味著自我毀滅。所以,最終的結果不能是這樣。英雄赫拉克里勒斯出場,說服菲羅克忒忒斯回到特洛伊,表明了詩人的立場與態度。
在這兩個否定性問題的解決過程中,暗含著詩人的建設性意見,暗含著索福克勒斯的政治道德觀念——共同體應該如何對待成員?個體面對共同體時又該采取何種態度?
2共同體對待個體成員的政治道德準則
菲羅克忒忒斯是共同體成員的代表,征服他的過程也就是掌控共同體成員的過程。首先,奧德修斯的徹底失敗表明“共同體需求至上、忽視個體感受”原則的破產。隨后,又有兩個人試圖說服菲羅克忒忒斯——涅奧普托勒摩斯與赫拉克勒斯,其中,赫拉克勒斯取得成功。他成功地掌控了共同體成員,使之為共同體利益服務,這正是有效共同體的追求。在赫拉克勒斯說服菲羅克忒忒斯的行動與語言中,共同體至少可以學到以下三條對待成員的政治道德準則:
(1)奉行英雄式的行為準則。赫拉克勒斯能夠說服菲羅克忒忒斯,最首要的原因在于他的身份:他是英雄中的英雄,最終成為神。他與被菲羅克忒忒斯所鄙視的奧德修斯完全不同,擁有光明磊落的天性與強大的武力,重視正義與榮譽,這一切正是菲羅克忒忒斯的人生信條,能夠得到他的尊重。索福克勒斯認為,共同體內部也應該奉行英雄式的行為準則。
(2)尊重個體生命經驗。赫拉克勒斯在說服菲羅克忒忒斯的時候提出的第一條理由是:菲羅克忒忒斯要走一條與他相同的道路,歷經種種苦難后成為英雄。赫拉克勒斯表明,他是菲羅克忒忒斯的朋友,與菲羅克忒忒斯有著同樣的經歷,對他的苦難感同身受。這是劇作中第一次有人能夠對菲羅克忒忒斯所有的十年苦難做出心理補償。菲羅克忒忒斯不肯回到特洛伊的重要原因就是不肯與昔日的敵人結為同盟,如果回去,那他的十年苦難就白白承受了,他在心理上沒有得到安慰與補償。涅奧普托勒摩斯曾經把菲的十年苦難歸咎于“神意”,這顯然不能說服菲羅克忒忒斯。“神意”與奧德修斯倡導的“共同體需求”一樣高高在上,完全忽略個人感受。赫拉克勒斯將菲羅克忒忒斯的苦難定義為成為英雄之前必須經受的歷程,并許諾他一個光明的未來,使得他的十年苦難有了價值與意義。菲羅克忒忒斯的個體需求(成為英雄)得到了滿足,所受的委屈與屈辱(十年苦難)也得到了同情與尊重,因此他愿意重新回到共同體。
(3)成員間的聯結關系。最后,赫拉克勒斯要求菲羅克忒忒斯與涅奧普托勒摩斯相互扶持,像“一對同行同止的獅子”[1],實際上是提出了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聯結的新方式。菲羅克忒忒斯與奧德修斯的聯結紐帶是利益,這種關系最終破產;而與涅奧普托勒摩斯的連接紐帶是相互尊重,或者說友誼,這也是菲羅克忒忒斯與赫拉克勒斯的關系中的重要層面,是維持共同體長期存在的重要因素。
3共同體中的個體成員應遵守的政治道德
索福克勒斯是城邦生活的維護者,發現共同體與個體的矛盾困境之落腳點還是要更好地鞏固發展共同體。在劇作中,菲羅克忒忒斯是悲劇的中心人物,通過對他的性格命運進行剖析,索福克勒斯也對共同體生活中的個體成員提出了兩點要求:
(1)對神的虔敬。在古希臘,神祇是城邦生活的維系者、城邦利益的保護者,同時也是約束英雄個人主義過分膨脹的力量。神是人類的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的力量與智慧,非凡人可比。神的意志是難以捉摸的,人類對神必須虔敬,否則就會受到懲罰。在索福克勒斯的劇作中,時常可以看到因冒犯神靈而受難的英雄,如埃阿斯,因過分狂妄自大而惹怒雅典娜,最終走上自殺的道路;菲羅克忒忒斯之所以經受這么多苦難,最初的原因也是冒犯了島上的女神。最終,矛盾的解決依賴于帶來宙斯旨意的赫拉克勒斯,反映了菲羅克忒忒斯最終皈依于神的意志而得到救贖。菲羅克忒忒斯的悲慘遭遇足以引起觀眾的恐懼之感,從而有意避免自身犯同樣的錯誤,達到教育勸誡的目的。
(2)自覺維護共同體利益。乍看之下,這一政治道德勸誡似乎與前文的“共同體需尊重個體生命經驗”相矛盾。共同體需求與個體自由意志確實是一對永恒存在的矛盾,索福克勒斯在劇作中并沒能解決這一難題。只要存在共同體,這一類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且無法解決的。它們代表著一組關系的兩級,人類生活就是在這兩極間展開,不斷沖突碰撞。索福克勒斯只是把這一困境展示出來,而后分別對雙方提出若干政治道德原則,以促進共同體良性發展。從成員層面來看,索福克勒斯要求他們自覺維護共同體的利益。在“第二哀歌”中,歌隊與菲羅克忒忒斯的對話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詩人思想的端倪。菲羅克忒忒斯堅決不回特洛伊,因喪失了自己的弓而咒罵奧德修斯,這時歌隊說:“在許多人之中還只有奧德修斯,接受了這個差事,按大家的委托,為朋友們的公益出力。”[1]隨后,歌隊強調,擺脫不幸的主動權掌握在菲羅克忒忒斯自己手里。涅奧普托勒摩斯也表示,像他這樣“固執的給自己制造不幸”,是“不可能有人正當的同情和憐憫他的”。[1]雖然歌隊與涅奧普托勒摩斯說服菲羅克忒忒斯的砝碼不夠,但至少代表了極端個人主義的反面可能性。最終,赫拉克勒斯出現,他也要求菲羅克忒忒斯回到希臘聯軍中,使戲劇沖突達到高潮。赫拉克勒斯勸說菲羅克忒忒斯的言辭仍是從個人角度出發的,但最終達到了維護共同體的作用,顯示出索福克勒斯的價值取向。
4結語:索福克勒斯的當代意義
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創作在多個層面上觸及雅典民主城邦制面臨的困境與難題,這些問題都是不好解決的。索福克勒斯站在溫和民主派的立場上,嘗試揭示出問題雙方所處方位,并對之進行道德勸誡,以此來維護城邦的長期穩定與團結。在《菲羅克忒忒斯》中,索福克勒斯展現的是共同體需求與個體自由意志之間的矛盾,并提出若干政治道德原則:共同體應尊重個體生命經驗,個體成員也應虔敬神靈,自覺維護共同體利益。這樣的勸誡在當代政治生活中也是有意義的,比如,該如何對待共同體中的弱勢群體?共同體成員繁復紛雜的個體利益與要求該如何協調?統治者運用何種手段才能鞏固對于政治成員的掌控力?正如莎士比亞一樣,索福克勒斯也是屬于所有時代的偉大劇作家,可以不斷地為人類生活提供智慧與靈感源泉。參考文獻:
[1] 索福克勒斯(古希臘).索福克勒斯悲劇[M].張竹明,王煥生,譯.譯林出版社,2007:714,600,706.
[2] 魏鳳蓮.略論古希臘戲劇的宗教性[J].齊魯學刊,2004(01).
[3] 於榮.略論古希臘悲劇的教育功能[J].教育與考試,2008(02).
[4] 梁俊敏.悲劇作品中的情感美教育[J].文學教育,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