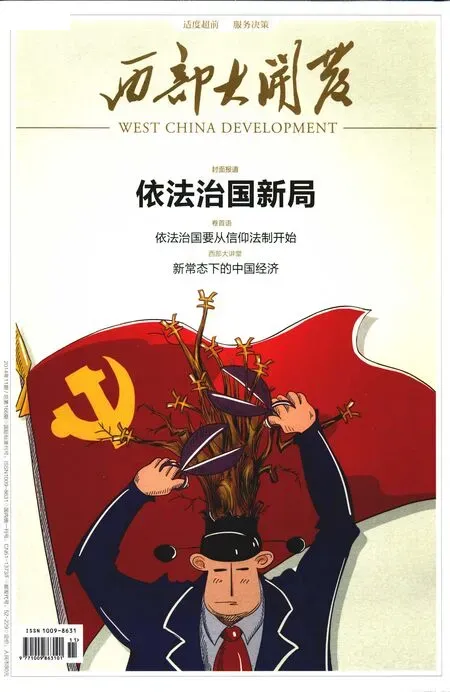在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中不斷加強基層建設(shè)
●文/丁偉
在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中不斷加強基層建設(shè)
●文/丁偉
編者按:
隨著社會利益結(jié)構(gòu)、社會組織形式以及社會關(guān)系的變化,傳統(tǒng)固化的“單位人”逐步為“社會人”和“個體人”所替代,社區(qū)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社區(qū)也成為了具有多重功能的社會場所,反映人們的心態(tài)體驗、表達不同的利益訴求、折射社會矛盾和風(fēng)險的幅度,從而標(biāo)刻出社會秩序體系的有效性和穩(wěn)定性。因此,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xiāng)社區(qū),社區(qū)服務(wù)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chǔ)就實了。社區(qū)治理作為一個重要的實踐探索領(lǐng)域,正在尋求中國社會建設(shè)和社會管理的創(chuàng)新和突破。
當(dāng)前,必須變革過去那種以單位為主體、以行政權(quán)力和資源壟斷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動員和命令來開展活動的傳統(tǒng)基層治理方式,以推進基層治理現(xiàn)代化為突破口,為社會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礎(chǔ)。
我們將會看到更多來自基層的驚喜和智慧。本期就“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shè)”展開筆談,從專家的獻言建策中,從北京、寧波、上海的實踐案例中,為基層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基層社會建設(shè)提供理論支撐、治理支撐和經(jīng)驗借鑒。(蘇惠芳)
在多元化的社會治理體系中,基層是社會的單元細胞,基層同時又是我們黨的執(zhí)政之基、力量之源。基礎(chǔ)不牢,地動山搖,因此,社會治理的關(guān)鍵在于夯實基層基礎(chǔ),在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中不斷加強基層建設(shè)。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diào),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關(guān)鍵在體制創(chuàng)新,核心是人,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會安定有序。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xiāng)社區(qū),盡可能把資源、服務(wù)、管理放到基層,使基層有職有權(quán)有物,更好為群眾提供精準(zhǔn)有效的服務(wù)和管理。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xiàn)的是系統(tǒng)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總書記關(guān)于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的重要論述,對于我們準(zhǔn)確把握社會治理的重心、社會治理的有效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同時也彰顯了中央決策層已將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作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重要突破口。
基層是社會的單元細胞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積極適應(yīng)新形勢下我國社會結(jié)構(gòu)、社會組織形式、社會管理環(huán)境發(fā)生深刻變化的需要,提出了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新要求,并將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確保人民安居樂業(yè)、社會安定有序作為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的重要目標(biāo)。社會治理的對象是社會關(guān)系,而社會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體,是人類相互聯(lián)系、互相合作形成的群體,社會和諧最主要的標(biāo)志是人與人和諧相處,因此,社會治理的核心無疑是人。
在多元化的社會治理體系中,基層是社會的單元細胞,是人作為社會成員參與社會活動最基本、最直接的載體,捕捉和傳輸社會需求最敏感的觸角,也是產(chǎn)生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的“源頭”、協(xié)調(diào)利益關(guān)系和疏導(dǎo)社會矛盾的“茬口”,基層同時又是我們黨的執(zhí)政之基、力量之源。基礎(chǔ)不牢,地動山搖,因此,社會治理的關(guān)鍵在于夯實基層基礎(chǔ),在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中不斷加強基層建設(shè)。為此,中共上海市委審時度勢,積極、主動應(yīng)對上海經(jīng)濟社會快速發(fā)展及基層建設(shè)中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將“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shè)”這一事關(guān)上海當(dāng)前改革和未來發(fā)展的全局性大事作為今年上海市委頭號調(diào)研課題,在調(diào)研重點上突出以問題為導(dǎo)向,集中力量、充分調(diào)研,力求結(jié)合上海實際,研究提出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shè)的目標(biāo)、思路和框架體系,形成清晰明確的頂層設(shè)計。這是上海切實貫徹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堅持源頭治理,標(biāo)本兼治、重在治本,扎實推進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的戰(zhàn)略性決策。
社會治理模式的全面變革
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系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確立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總目標(biāo)相呼應(yīng),是我們黨總結(jié)、傳承多年來的成功經(jīng)驗后對于社會建設(shè)更具科學(xué)性、開拓性的新提法。是我們黨深入分析社會發(fā)展階段性特征后得出的新結(jié)論、也是引領(lǐng)社會進步的新標(biāo)志。社會治理與傳統(tǒng)的社會管理雖一字之差,但內(nèi)涵卻發(fā)生了深刻變化,標(biāo)志著社會治理模式的全面變革,即治理主體從依靠政府為主走向全社會共同參與,治理手段從依靠行政手段為主走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治理內(nèi)容從以“管”為主走向管理與服務(wù)的有機結(jié)合,治理目標(biāo)從治標(biāo)為主走向源頭治理、標(biāo)本兼治。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指出,推進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要注重運用法治方式,實行多元主體共同治理;健全村務(wù)公開、居務(wù)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發(fā)揮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wù)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這一社會建設(shè)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chuàng)新要求我們積極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制,有效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tǒng)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相結(jié)合,進一步激發(fā)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guān)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quán)責(zé)、依法自治,建立健全有效預(yù)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體制和公共安全體系。顯然,強調(diào)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系,不僅顯示了我們黨對社會發(fā)展和社會建設(shè)規(guī)律認識的新飛躍,同時也彰顯了執(zhí)政黨領(lǐng)導(dǎo)思維的跨越、執(zhí)政理念的升華和治國方略的轉(zhuǎn)型。
把治理納入法治軌道
社會治理體制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huán),是一個復(fù)雜的系統(tǒng)工程,涉及經(jīng)濟、政治、社會等諸多領(lǐng)域的制度建設(shè),必須采用切實有效的治理手段。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biāo),并且明確將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
將法治化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于法治化手段具有其他治理手段無法比擬的一系列優(yōu)勢。首先,法治化手段崇尚法律至上的理念。與其他社會規(guī)范相比,法律具有權(quán)威性、普適性、穩(wěn)定性等固有特征,體現(xiàn)了國家意志,是確保社會有序化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的決定性力量,建立在法治基礎(chǔ)上的治理體系是實現(xiàn)政治清明、社會公平、民心穩(wěn)定、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其次,法治化手段強調(diào)治理體系的全局性、整體性、系統(tǒng)性。這一治理體系貫穿立法、執(zhí)法、司法、守法整個過程,具有系統(tǒng)性、整體性、協(xié)同性的功能。
再次,法治化手段凸顯治理過程的民主性、公開性、回應(yīng)性。在社會轉(zhuǎn)型、矛盾凸顯的新時期,法律已成為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規(guī)范行為、消除矛盾、彌合分歧、維護秩序、實現(xiàn)和諧的“最大公約數(shù)”。公眾在了解和通曉法律的同時,必將牢固樹立法律信仰,自覺地將法律要求內(nèi)化為自己的行動準(zhǔn)則,國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將越來越強,社會治理體系的基礎(chǔ)將越來越堅實。
最后,法治化手段具有可預(yù)期性、可問責(zé)性、可救濟性的明顯優(yōu)勢。法治與人治相對而言,其最基本特征是法律至上、權(quán)利平等、權(quán)力制約,強調(diào)對公共權(quán)力的合理配置和依法制約,把權(quán)力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里,把治理納入法治軌道。強調(diào)以法治化手段推進社會治理,要求我們善于用法治精神引領(lǐng)社會治理、用法治思維謀劃社會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會治理難題,把社會治理納入法治軌道。
(作者為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法學(xu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