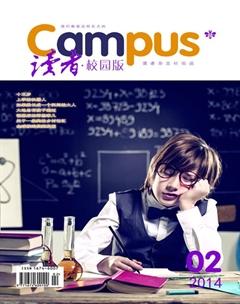關于一條狗的鄉村記憶
袁靜帆
幾年前,二舅從西安帶回兩條小狗,把公的送給了三舅。
三舅家在農村,和舅媽在服裝廠里工作,姥姥一般住在三舅家,三舅還要供兩個哥哥上學,生活并不寬裕。那條狗雖說不是農村的那種土狗,卻也沒有被當作寵物,甚至連名字也沒有,它只是一條看門狗,再普通不過。平時三舅只給它一些剩飯剩菜,它卻長得很快,兩年過后,它立起來時就和上高中的表哥差不多高了。但它一直很瘦,總能清晰地看到它肋骨的凸痕。
表哥從來不拴著它。村子里其他的狗嫌它是外來品種,總是與它為敵,所以它也不常亂跑。姥姥總說這狗十分精明。有一次,它竟然與家中的貓聯合起來,偷吃了二姨給姥姥買的燒雞,姥爺訓斥了它一頓,我和弟弟卻因此更喜歡它了。
我總要在假期回老家住幾天。看著村里的孩子騎著自行車在鄉村公路上疾馳,我也開始學起了騎車。學會之后還不太熟練,我總是騎得歪歪扭扭。之后有一天我獨自練習的時候,路旁的院子里突然竄出兩條兇猛的狗,朝我這邊沖過來,我嚇得大叫,卻沒有一個人出現,我不知從哪兒來的力氣,瘋狂地蹬著自行車,完全沒了初學者的生疏。我想甩掉這兩條狗,沒想到這兩只“四輪驅動”的動物跑得還確實快,流著口水的嘴離我越來越近,好像是想把我的小腿給當作午餐!我騎了一路尖叫了一路,最后筋疲力盡打算聽天由命的時候,舅舅家的狗卻不知從哪里沖了出來,將那一黑一黃兩個家伙咬得狗毛亂飛,最后它們狼狽地逃走了。我驚魂未定,恍恍惚惚地從自行車上下來,腿都軟了,過了半天才意識到,那個大家伙救了我!我帶著狗回家,把火腿腸分了它一半,它好像也很高興,跑到院子里扒出一只幼蟬吃掉了。
之后幾天,我騎車時總讓它跟在我的身后,再也沒有狗企圖咬我了。有時它跑進旁邊的田地里,歡快地跳著,一身褐色皮毛在陽光的映襯下閃閃發亮。玉米苗高得淹沒了它,它就這樣在一片蕩漾的碧綠之中起起伏伏,白色的小蝴蝶在它爪子的撲閃間飛舞。
我們一起買燒餅,一起在雨天滑倒,一起在鐵路旁看著運煤的老火車呼嘯而過。它總想霸道地躺在沙發上,但每次都在被姥姥訓斥后,繞一圈又躺在涼席上。我們哭笑不得地看著它時,它卻已經自在地睡著了。
對于那個遙遠夏天的記憶,只因一條連名字都沒有的狗,變得簡單、純粹而又清晰。
很久之后的一天,三舅打電話來說狗被賣了。當時我和弟弟正在吃午飯,我們一聽都愣住了,思緒好像在那一刻凝固,遲鈍到無法運轉,緩過神來后,我們便止不住地哭起來,淚水好像灑進了我的碗里,以至于那頓飯吃起來又苦又澀。
三舅說,狗不小心抓傷了一個小孩,于是被他們拴了起來,后來狗又咬了那個住在東邊的叫“郝妞”的老太婆。郝妞很生氣,坐在門口的青石板上不停地罵狗。三舅本來因為狗就賠了別人不少錢,鬧了許多不愉快,讓她這么一罵,只好狠下心賣了狗。
我不敢想那個買狗的人是干什么的,我不敢想狗在籠子里看著漸行漸遠的村子是什么樣的眼神,我不敢想它是不是成了別人的盤中餐、腹中肉,我只是不停地將碗里的飯送進嘴里,希望飯菜可以讓我的思緒停滯,止住我的眼淚。我寧愿相信它還能快樂地生活。
后來又回到老家,郝妞家門前開了幾朵很大的花,媽媽客套地說她的花好看,我和弟弟卻一直在一旁作嘔吐狀,發出很惡心的聲音。誰讓她害了我的狗!
再后來,那輛自行車也老了,鈴鐺發出的聲音不再清脆,鉸鏈還會時不時罷工,有些地方也已經生銹,失去了昔日的光澤。我知道那段時光已經永遠離開我了。
每次回去,我都要去看看那片玉米地,默默地想念那個曾在這里跳躍的身影,和那幾只飛舞的白色蝴蝶。
(本文作者系我刊校園通訊員,河南省鄭州市實驗外國語中學九年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