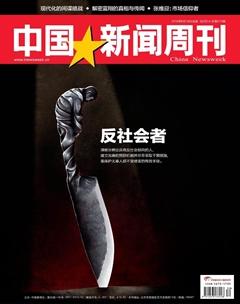以弗所:歷史與大海的相遇
周琦

旅行第11天,仍舊在土耳其的版圖里,卻已有點亞歐莫辨,南北不分。
土耳其的大巴是奔著航空標準去的。除了提供飲料、小食,每個座位前還有多媒體屏幕,WiFi隨時刷,和國內完全是天涯若比鄰。坐在我們左前方的土耳其大嬸把耳機連上屏幕,聽著音樂逍遙地織著杯墊。我在想,這就是土耳其版的C'est la vie吧。
某個鄉(xiāng)間小站,大嬸下車,對一個十幾歲的男孩(目測是她的孫子)抱了又抱,親了又親,又和一位白發(fā)蒼蒼的老先生(應該是他的丈夫吧)久久相擁。我隔著車窗看著這溫情一幕,只覺得看不夠。
胖胖的服務員一路殷勤地端茶送水,車入休息站時還非趕你下車去喝一杯土耳其紅茶。快到目的地時,又奉上咖啡。知道咖啡燙,車速又快,所以倒半杯,任其只晃不灑。
就在咖啡的濃郁醇香里,塞爾丘克到了。
如果說伊斯坦布爾有點像北京和上海的綜合體,那么卡帕多其亞像敦煌,安塔利亞像廈門,棉花堡像黃龍,我實在說不出來塞爾丘克像中國的哪里。
才幾步路的距離,就從汽車站走到了主城。城門的殘垣在昏暗燈光的映照下屹立不倒,仿佛在訴說著前世的榮光。愛琴海邊的塞爾丘克,因近郊著名的以弗所古城而享譽的“歷史與大海相遇之地”,在我們到達的這個夜晚,顯得如此安詳靜謐。
提著行李兜兜轉轉找到了事先預定的客棧。客棧老板微笑著帶點嗔怪地說:“怎么不事先發(fā)個郵件或者打個電話來?可以去汽車站接你們。我們這里都是石板路,拖行李很受罪吧?”
待我們卸下行李收拾停當,老板又送來了地圖和茶點,熱情洋溢地介紹起了塞爾丘克的林林總總,并為我們設計了翌日的線路。得知我們想去銀行換點土耳其里拉,他讓我們這么晚了別出去了,跟他換就行,按即時匯率算。
第二天早上,老板開車送我們去了以弗所。
在塞爾丘克,所有的游客都是奔著以弗所而來。以弗所距塞爾丘克中心城區(qū)3公里,有“土耳其的龐貝”之稱,但龐貝瞬間毀滅,以弗所卻更像是原住民撤離后的空城。
以弗所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大最完好的古希臘、羅馬城市。公元前11世紀,古希臘的愛奧尼亞人來此殖民,初建以弗所,后逐漸成為古希臘的工業(yè)和文化中心之一。此后,以弗所飽經(jīng)戰(zhàn)火蹂躪,先后被波斯、馬其頓、帕加馬和羅馬所占領。很長一段時間內,它是羅馬帝國中僅次于羅馬的第二大城市,被譽為“亞洲第一個和最大的大都會”。到中世紀,以弗所漸趨衰落,終成一片廢墟。
以弗所也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中心。天主教認為,圣母瑪利亞終老于此。傳說她因猶太人迫害而逃離巴勒斯坦,使徒約翰遵守對耶穌之承諾,將她迎接至此地奉養(yǎng)。
今天的以弗所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館。進入以弗所景區(qū),只見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團從一輛輛大巴車里魚貫而出,成群結隊,熙熙攘攘,好似大都會時光重現(xiàn)。有白發(fā)蒼蒼的耄耋團,也有齊刷刷熱褲上陣的少女團,一排頎長的腿,倚靠在潔白光滑的大理石邊,任憑時光翻轉錯亂。
和之前在土耳其其他城市遇到的導游不同,以弗所的導游,無論男女長幼,都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站在圖書館后面的山坡上,一位中年女導游遙指著兩公里外的某處說:“請閉上眼,想象一下,眼前就是大海……”
以弗所曾經(jīng)是繁忙的港口,無數(shù)的觀光客從各地慕名而來,一如今日。發(fā)達的貿(mào)易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經(jīng)濟實力的增強使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人口逐年增加。最強盛的時期,以弗所城里的人口達到了30萬之多。海面帆影點點,港口萬船待發(fā),大街小巷車如流水,馬似游龍。然而,隨著愛琴海的泥沙淤積,海水褪去,港口不再,城市也被遺棄。
如今的以弗所遺址,只發(fā)掘了一部分。其中,塞爾瑟斯圖書館是保存最完好的建筑。周圍的壁龕里,曾藏有萬卷圖書,正面從左到右排列著四個代表美德的雕像,分別是仁慈、思想、學識和智慧。壯美的圖書館面東南而建,使得人們可以充分利用早晨的光線閱讀。
依山勢而建的梯田式大劇場,由幾十米高的石墻環(huán)繞著,音響效果極佳。埃爾頓·約翰和多明戈都曾在這里開過演唱會,今年的主角則變成了麥當娜。雖說現(xiàn)代劇場或體育場無一不是古羅馬斗獸場的翻版,但試想一下,置身于一座真正的古代建筑,于星光斑斕里放歌,依然讓人覺得震撼。在大劇場的石階上小坐一會兒,沒有任何遮陽設施,5月天的紫外線已然要將人曬化。在大劇場幾百米之外,就聽到詠嘆調的回響,大約是有專業(yè)基礎的游客興之所至高歌一曲,美妙無比。看來古人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jīng)懂得利用高保真音響的環(huán)繞原理了。
公元前400年前的以弗所,排污管敷設在大理石石板下面,街燈掛在廊柱上照明,主干道兩旁商鋪林立,地面上至今可見被馬車軋過的車輪印記。在一處名為Terrace House的室內遺址里,房間里鋪著地磚(依據(jù)電腦合成圖復原的),淋浴設施完備。公共廁所設施看上去比當今中國很多落后地區(qū)的蹲坑還要現(xiàn)代化。
以弗所古城最著名的建筑,當屬阿爾忒彌斯神廟。它被稱為世界七大奇跡之一,如今只余一根石柱,不在今日的以弗所景區(qū)內,而是寂寞地戳在塞爾丘克“城鄉(xiāng)結合部”的蘆葦叢中,人跡罕至,不收門票(在我們中國人看來,這才是最大的奇跡啊)。以弗所的人潮洶涌也好,大得駭人也罷,竟不如它給人的震撼多。
兜售圖書和明信片的小販興沖沖跑上來問我們:“Japanese?Korean?”見我們不答應,他似乎更來勁了:“那一定是Chinese!”算你猜對了好嗎,但一本盜版書20歐,搶錢吧?
賣書的小販一直跟我磨,從20歐到15歐到10歐,再到20個土耳其里拉(約合7.5歐)。他哀求我說,這已經(jīng)是虧本的價格了,太陽都快下山了他還沒開張,虧本賣給我只是為了轉運。我真為土耳其人民的幽默給跪了,成交!
在夕陽中,慢慢翻閱這本故事集。大約在公元前550年,以弗所人開始修建阿耳忒彌斯神殿,供奉被希臘人稱作阿耳忒彌斯的“以弗所女神”。然而公元前356年7月21日的深夜,這座壯麗的神殿在一場大火中變成了廢墟。后來以弗所人又在原址上按原樣重建了一座神殿,比原來的更加富麗堂皇,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大理石建筑。公元262年,神殿在哥特人入侵時遭逢了徹底毀滅的厄運。
這本有趣的書就像一個歷史的魔術——蓋上透明彩頁是前世的繁華似錦,翻開則是今生的孤獨一柱。這根石柱是考古學家用發(fā)掘出的大理石拼成的,以提醒世人此地曾經(jīng)發(fā)生的神跡。站在這根巨大的石柱前,“滄海桑田、海枯石爛”這八個字,幾乎伸手就可觸摸得到。
帕慕克說:“我們一生當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帶領我們檢視自己出生的環(huán)境,我們何以在特定的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這一角。我們出生的家庭、人生簽牌分派給我們的國家和城市,都期待我們的愛,最終,我們的確打從心底里愛他們。”
就像帕慕克愛伊斯坦布爾,愛它初冬傍晚時分光禿禿的樹在北風中顫抖、身穿黑大衣和夾克的人們穿過天色漸暗的街道趕回家去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憂傷”。就像古羅馬人愛以弗所,愛清晨在圖書館趁著熹微的晨光讀書,也愛黃昏時到大劇場放歌或觀摩角斗士們血淋淋的決斗。就像我,愛世界上任何一個美好的地方,但無論如何,卻更愛那個叫上海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