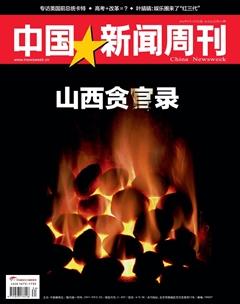聶春玉 呂梁漩渦里的“溫水”書記
韓永

因為兩人有頗多相似之處,聶春玉和杜善學經常被外界拿來相互比較。
他們兩人都先是在各自的系統工作了很長的時間——杜善學在財政系統工作了18年,聶春玉則在政研系統工作了19年;然后同時下到地市擔任行政一把手,并在幾年后擔任黨委一把手,這兩個職位的履職時間加起來,兩人都是8年。
另外,他們都在呂梁擔任過一把手,并先后在這一位置上被提拔為省委常委;他們都曾擔任省委秘書長;他們都在省委常委的位置上被調查,落馬的時間相隔不到3個月。
但與性格火暴、風格強勢的杜善學不同,聶春玉溫潤平和,喜怒不形于色,很少在公開場合批評下屬。
以穩見長
與杜善學在畢業后有個“高大上”的起點不同,聶春玉畢業于一個不起眼的學校——阜新礦業學院,專業是地質測量。畢業后,機會不多的聶春玉選擇回到老家侯馬,從宣傳干事開始了仕途生涯。
觀察聶春玉的從政經歷,會發現他畢業后前一個8年和后一個8年職務升遷的巨大差異:在侯馬市的8年,他從市委宣傳部干事,做到了公社的副主任,官拜副科級;從1984年進入省委政研室開始,他職務升遷的步伐開始加速。此后8年,他從一個副科級干部,升到了副廳級,官拜山西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這樣算下來,他每升一個級別的等待時間只有2年。聶春玉升至副廳的年齡與杜善學相同,都是37歲。
山西省一位與聶春玉相熟的副廳級官員,這樣分析聶春玉快速升遷的原因:聶春玉身上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性格很穩,能沉得住氣,不會輕易犯錯誤,也不會輕易得罪人。“你要給聶春玉提意見,他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不吭氣。不會跟人吵架,哪怕是很尖銳的意見,也不會發火。”
這位官員說,聶春玉對政策的動向非常敏感,善于從文件中琢磨上意,“大事不糊涂”,這對他的仕途大有裨益。
1985年,聶春玉30歲時,在《經濟科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土地收益遞減規律”的提法不妥》。這是一篇與人商榷觀點的文章。文章中引述了《資本論》《剩余價值學說史》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自然辯證法》的內容,看得出他在這方面的閱讀頗豐,多有積累。
但聶春玉從事政研工作19年,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并不多,真正有影響的觀點也不多。“能力不算突出,做成一件事的主動性不夠。”這是很多受訪者對他的一致評價。
多位受訪者認為,聶春玉以穩見長的性格,很適合做一個為領導服務的角色。而他19年的政研經歷,無論是在省委政研室還是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做的都是類似的工作。
“溫水”書記
2003年1月,聶春玉結束自己19年的政研生涯,前往呂梁,擔任該地區行署專員。呂梁撤地劃市后,他即出任該市市長。
此前的呂梁,被很多人稱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全市13個縣市,有9個在山上。經濟發展的一些基本條件——交通設施、水資源,都嚴重不足。而儲量豐富的煤炭資源,囿于價格偏低和交通條件,只能少量開采供本地消化。這個山西省最后一個撤地劃市的區域,留給外人的印象,除了呂梁英雄的傳說,就是貧瘠的山脈和連片的貧困帶。
1998年,呂梁的經濟總量在山西省叨陪末座;1999年,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出現負數;到了2000年,呂梁地區的財政收入只有10億元。呂梁市委一位前副秘書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在呂梁的一些貧困山區,老百姓一天只能吃上兩頓飯,一頓在上午9點多,一頓在下午4點多,其余的時間餓了,就只能硬扛。
從2002年開始煤炭價格上漲,給了這片掙扎在溫飽線上的土地以希望。呂梁市一位前縣委書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呂梁盛產熱含量較高的4號煤,在行情最好的時候,這種煤賣到了每噸1400元。以一個日產1萬噸的小煤礦為例,1天的產值就是1400萬元。
在這樣的背景下,呂梁的經濟就像久旱逢甘雨,逐漸洗去了往日的貧瘠。2000年,呂梁市的GDP是105億元,而到了2009年,則已經飆升至611億元,年均增長率12.6%;財政收入由2000年的10億元,增加到165億元,年均增長36.5%;城鎮居民和農民的人均收入分別增長了3.2倍和2.1倍。到了2010年,呂梁的經濟總量突破800億元大關,排名全省第四,增速排名第一。
與杜善學主政時期的長治一樣,呂梁在此期間的高速發展,大部分應歸功于煤炭價格上漲。而正是呂梁經濟的快速發展,客觀上助推了聶春玉的職位升遷。
上文提到的縣委書記說,與其性格有關,聶春玉在經濟發展中也傾向于求穩,任期內提出的有開創性的建議不多。他在經濟發展上最主要的一個思路,就是“三三戰略”。這幾乎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戰略,沒有很強的針對性,對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很弱,在實踐中往往蛻變為在招商引資中向大項目傾斜。
聶春玉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做每一個決策之前,都喜歡在很大范圍內征求意見,以尋求最大的共識。這樣做的好處是“眾人劃槳行大船”,但也同時讓決策變得沒有效率。接受采訪的呂梁市官員,大多對他曾做過什么事情印象模糊,但同時又認為這個人還可以,“沒有架子,待人比較熱情”。
雖說出身自政研系統,但聶春玉講話也沒有太多文人特質,平常也鮮有文章出爐,最多就是有人出書他給做個序,但也是別人把內容寫好,他修改下簽個名而已,“理論水平還算可以吧。”
上文提到的前縣委書記說,聶春玉在任期間,呂梁的社會治安總體上比較平穩,沒有大的案件發生,上訪的人也不是很多,這一方面與聶春玉較為溫和的執政風格有關,另一方面,當時的土地價格還沒有上漲到后來“寸土必爭”的地步。
買官賣官
呂梁經濟快速發展的動力,是作為該市經濟支柱的煤企快速發展,以及煤老板財富的快速積累。
與長治煤礦多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不同,呂梁的煤礦多掌握在個人手里。在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之前,呂梁有四十多家私人煤企,經過整合后,剩下的還有十多家。其中,今年3月份被查的邢利斌,以及8月份被查的賈廷亮、袁玉珠,都是在山西乃至國內有影響力的人物。
呂梁市一位煤企高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與北京的一位官員拉上關系,呂梁的一位老板蹲守北京,找到了該官員妹妹所住的小區,努力說服其對門的業主把房子高價賣給自己,并在該官員的妹妹回家時,故作巧遇說上一句話。這位煤企高管說,為了搭上與上層的關系,很多煤老板都不惜成本。
他向《中國新聞周刊》算了其中的投入產出比:對于煤老板來說,送禮的成本再夸張,也只占其煤礦收益很小一部分。“在煤炭行情看好的時候,一個日產1萬噸的小煤礦,一天的收益就有上千萬元。也就是說,就算送給官員1000萬元,也只動用了煤老板一天的收益。”
但官員手中的權力能給煤老板帶來的收益,就不是多少天的煤炭收益所能估量的。不管是煤礦開采資格的分配,還是煤礦整合主體資格的分配,都關系到煤礦所有權的歸屬。
官員對與商人之間關系的需求,主要在于買官的成本需要有人埋單。多位采訪對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呂梁甚至整個山西省,存在著一條實實在在的官商之間的利益輸送鏈條:商人向官員購買資源的分配權,官員再向上一級官員購買職位以期擁有資源的分配權。從煤老板處流出的賄賂款,從低級官員不斷流向高層級官員,客觀上造成的一個結果是,各個層級的官員都在直接或間接地為煤老板服務。
呂梁市多位受訪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聶春玉當政的8年,社會上關于買官賣官的輿論甚盛。每逢干部提拔的時候,這種輿論就達到了頂點。
聶春玉選拔官員,通常要通過考試設置一個門檻,越過這個門檻才有獲得提拔的資格。但越過這個門檻后,就會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最終的錄取者,通常都是那些財力雄厚者,而財力單薄者往往名落孫山。但這些在第一輪未獲提拔的官員,又往往會在第二輪得到提拔。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有一年,呂梁市選拔三位縣長,共有5人進入候選人名單。最后獲得提拔的三位,都是公認的財力雄厚者,而一位來自市委黨校的候選人,和另一位同樣囊中羞澀的候選人,則在3年后獲得了提拔。
“這當中的邏輯可能是:在同為候選人的前提下,優先提拔那些有所表示的;無力表示的,則會延遲一輪獲得提拔的機會。也就是說,有錢快一點,沒錢慢一點。”這位知情者說。
一位呂梁的前縣委書記還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講述了他所經歷過的一次縣委書記選拔。在這次選拔中,游戲規則是以民意測驗定輸贏,誰得票高提拔誰。參加民意測驗投票的共有40來位市級干部。結果,幾位候選人都給他們送了禮。這讓投票的干部們為難之極——到底該投給誰呢?而另一個讓他們為難的事情是,這些禮他們很難回絕。“如果不收,對方就會認為你肯定沒給他投票,這樣得罪人后,以后連個管飯的也找不著了。”
和杜善學一樣,聶春玉也是從呂梁市委書記任上提拔進入省常委班子。包括聶春玉和杜善學在內,短短半年以來受到查處的呂梁現任官員或有呂梁履職經歷的官員達到了六人,他們分布在三大班子。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足見呂梁的政治生態已然幾近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