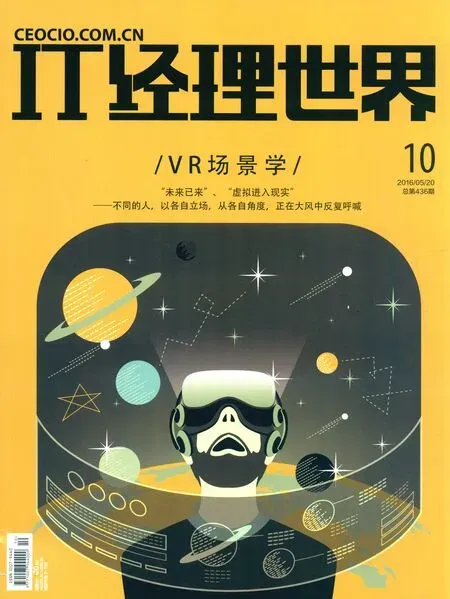經濟視角下,遲到5年的高教改革
劉西曼
中國經濟必須直面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不斷下降。按照中央智囊、社科院蔡昉教授團隊的研究,目前中國的長期增長潛力折合到GDP增速大約7.2%,未來3~5年可能下降到7%以下。主要的變數就在于人口紅利的逐步減少、并變為負利。
在這種背景下,最近政府正在啟動一次高等教育改革,這對于中國長期增長潛力的提升有重要的經濟學層面的意義:教育部副部長魯昕表示,中國高等教育將發生革命性調整,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將逐步轉型職業技術學院,也就是說,有將近85%的高校將面向職業教育。這是一個向德國學習的路線,德國只有20%的大學入學率,其他中學畢業后主要進行職業教育;即使這20%之中,也還有1/3是專業教育,而不是綜合研究性大學。
“數量型人口紅利”拐點
為什么說人的素質提升將成為中國未來經濟長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這需要我們先來認識一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所謂經濟潛在增長率,主要取決于幾個關鍵要素:資源紅利潛力、人口紅利潛力和勞動生產率潛力,以及由這幾方面共同作用,所得到的生產力提升。而其中的勞動生產率提升,進一步細分后,可以主要歸于技術紅利、制度紅利。
早在十幾年以前,中國的資源已經是“黑利”,大量的資源需要進口,就意味著國內創造的很多財富用來購買原材料,而不是消費,沒有直接提升生活水平。好在,中國工業化進程迅猛,在生產加工環節創造的利潤足以購買這些資源并形成順差。否則,就會像印度一樣,只有大量能源進口,而沒有制造業環節的盈利,糟糕至極。
至于制度改革、技術進步,我們很難直接衡量其貢獻率,假定未來中國的改革仍然會繼續、技術進步依然會保持,但是,其速度也沒有理由比過去30年更快,只是維系。
這種情況下,人口紅利可能是決定性因素。2013年中國勞動總人口達到9.2億,同比減少244萬,很多學者將其視為劉易斯拐點;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仍然沒有完成,每年可以提供1000萬左右,減去退休人口之后,總勞動人口依然增長了273萬,達到7.7億,所以,數量紅利將還會延續3~5年。但是,無論按照哪種說法,最遲2016年中國的人口數量型紅利都會消失;即便是這幾年看,其貢獻率也在下降。
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度高達20%~25%,相當于2個百分點甚至更高,而2013年預計這一比率僅為不足10%,相當于0.5~0.7個點的GDP,而且每年可能以0.05~0.1點GDP的速度在下降。
這種情況下,即使技術、制度紅利仍然存在,中國的GDP也會因此逐年下降約0.1個百分點,況且在資源方面的負利也會逐步增大,中國的出口潛力已經逐步透支。
人口素質紅利至關重要
這時候,放開二胎只是減緩之計,并不能導致人口的回升,畢竟日本、臺灣、香港等地方并沒有計劃生育,生育率也同樣很低。所以,關鍵是人口素質紅利。素質紅利體現在哪些方面?第一,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總比重;第二,則是教育人口的結構問題了。
中國經過20年連續不斷的大學擴招,當年入學人口從不足100萬上升到700多萬,大學毛入學率達到16%,應該說已經起到了很好的白領勞動力供給的問題。但是,早在2007~2008年,結構性就業難題就已經出現,藍領工人、高級技術工人稀缺,白領大學畢業生逐步過剩,到2012~2013年已經嚴重過剩。
換句話說,大學教育提供了過多的所謂“高級人才”,但是根本與市場需求不匹配,很多是“偽人才”,原來的所謂市場化只是市場化收費,而沒有適應市場化需求!這種結構性矛盾是非常嚴重的,以至于大眾普遍對高校改革持有負面態度。
筆者的看法更為中性:早期的大學擴招,對于迅速補充中國的白領市場利大于弊,但是,在市場供需矛盾出現嚴重問題的時候,已經弊大于利,難以滿足生產力提升的要求。嚴格來說,2008年前后就應該進行較大幅度的改革了,目前的改革至少晚了5年。大學教育已經成為中國教育最薄弱的環節,不得不改。
這次教育改革有兩大潛在意義,不可偏廢:對于85%的地方高校來說,主要面向校企對接,注重動手能力,以高級技工、工程師為訴求,主要面向的是德國、日本等競爭對手;而對于15%的研究型高校,應該更好地細分,將一般性研究和精英型研究分開,真正培育10~20所亞洲一流、3~5所全球一流的高校,向美國的產業鏈發起挑戰。畢竟,中國要想向高端進軍,美日歐已經是中國必須去面對的對手,人才不僅僅是紅利,還是必不可少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