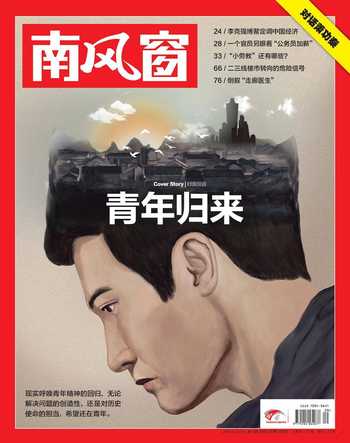二三線樓市轉向的危險信號
譚保羅

過去這些年,中國的“打房派”一直被城市中的“多數人”嘲笑,因為房價從來沒降過。而投鼠忌器的“調控”和房價上升的現實,更讓許多人的資產得以升值,久而久之,中國社會幾乎形成了一種對房價堅挺的篤定心理。
從財務學來講,土地是世界上少有的永不折舊的資產,但這只是指那些“好的土地”。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說明,由工業化推動的“自然城市化”過程中,中心城市的房價上漲是較常見的,遇到經濟周期則可能會波動或者調整。但由投資推動的城市化則是另一種邏輯,它會讓那些沒有價值的土地變得充滿泡沫。
實際上,一些二三線樓市的樓市泡沫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其繁榮時光得益于體制內外的多重“保險”的支撐,比如政府投資的決心和能力、行政體制的地區分割以及外部投資者對中國城市化的信心。但泡沫天生的價值缺陷就如同巨人的一雙泥足,決定了危機將在這些“保險”松動之時發生。
最近各地樓市接連發生的事情,讓人看到了二三線樓市轉向的危險信號。
破壞“規則”
連續上演的“房鬧”事件,其對樓市的“調控”意義很可能超越一次紅頭文件的頒布,樓市劇變或許不再是“打房派”的信口之詞。
3月底,港資老牌地產商九龍倉在成都的一處高端樓盤突然大幅降價,引發數百名業主圍堵售樓部。降價前,位于成都二環路的該樓盤均價在1.1萬至1.3萬元/平方米之間,而降價后最低只售8000左右。有購房者怒稱,一個月前買的公寓,一個月時間便折價“蒸發”了30萬。
地產商的降價策略取得了成功,一天之內,數百套降價房售罄。但一些成都購房人被激怒了,他們打出標語,群情激奮。在售樓部外,裝備著頭盔和盾牌的保安一字排開,這讓不少網友誤以為成都又有大事發生。
在中文的網絡百科中,“房鬧”被定義為,“已購房的老業主由于對新開或新推盤價格低于其購房時的價格不滿,而發生的集體與地產開發商鬧事的行為”。在樓市近20年的“調控”歷程之中,總有一些中小地產商資金不濟,進而降價銷售,引發“房鬧”反復上演。
但這一次卻有所不同。一家資金雄厚的龍頭港資地產商,在短時間內,密集地在幾個知名二線城市降價,不能不叫人遐想。除成都以外,在杭州和常州,九龍倉的降價幅度達到每平方米四五千元。
購房者情緒復雜。一方面,他們可能抱怨后來者運氣比自己好,買得便宜,這種“患不均”的憤怒,可以說是社會心態被樓市扭曲的表現。但更重要的是,樓盤價格的下降對應著家庭資產的縮水,而地產商更無情地踐踏了購買人的情感,焦慮和憤怒是人之常情。
一位川渝地產界的投資人士對《南風窗》記者說,在九龍倉該盤所在地段,其他內地地產商的盤有近10個,均價全部過萬。陸續開盤以來,銷售并沒有預期的好,但大家都扛著不降。而九龍倉突然就降了,其他的盤很被動。
九龍倉似乎也意識到了問題。4月初,九龍倉在上海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其副主席周安橋表示,在同行都有機會降價的情況下,自己可能“先下手為強”。但他也不忘表達了對內地樓市的信心,認為滯銷和降價只是部分地區的“階段性供應過剩”。有解讀稱,這種公開表態是九龍倉的對行業的“補償”。
《南風窗》記者查閱九龍倉近年財報發現,隨著內地投資的加碼,其負債凈額(不包括碼頭等附屬公司)近年一直在上升。2010年末為233.76億港元,2012年末為492.01億港元,而2013年年中為462.75億港元。也就是說,3年的時間內,其負債翻番。而九龍倉在內地大舉擴張正是發生在2010年前后。
不過,這樣的財務狀況依然健康。近年來,九龍倉負債額與總權益的比率一直穩定在20%左右。對比而言,內地地產商的這個比率超過100%幾乎是常態。而一些拿地激進的中小地產商還可能超過800%,換言之,即一家公司借的錢是公司股東投資額的8倍,等于是在財務上“踩鋼絲”。
可以看出,和中小地產商降價銷售不同,九龍倉并非短期內缺錢,因此必須降價以回籠資金。降價而不選擇“捂盤”,其深層原因極可能是并不看好這些樓盤的前景,以及對自身內地擴張策略的調整。
一直以來,港資地產商最推崇的經營法則一是財務的穩健,二是對地段的篤信。在財務上,和記黃埔、九龍倉等都屬于綜合性巨頭,即可以用公用事業、基建和港口碼頭等利潤不高,但現金流穩定的板塊來對地產板塊進行資金支持。因此,對外負債不多,抗風險能力強。
而在地段上,“上策”是選擇已有最好地段,其次才是把“生地”培養為“熟地”,但這只是“下策”。與和記黃埔等港資同行相比,九龍倉在內地樓市算是“后進生”。由于一線城市土地成本較高和好地段越來越難找的原因,它選擇了“下策”。這幾年,九龍倉主要的十多個住宅項目多數都位于二線城市,即便在二線城市,不少項目也僅位于“次中心”。
地段選擇上“退一步”的策略,讓九龍倉的內地銷售額一路高漲,但擔憂也隨之而來。因為,“生地”要變成“熟地”的條件有兩個。一是地方政府必須在城市建設擁有強大的投資能力,二是和宏觀環境密切相關。簡而言之,就是必須背靠所謂的“城市化”大潮,倘若潮退,風險便會顯現。
“城市化”局限
這些年,“挺房派”對于中國樓市的樂觀態度,其論據主要來自于巨大的“城市化”潛力。在其看來,中國城市化率不足50%,而美國早在上世紀70年代便超過70%。除了農業人口要繼續進城之外,每年新畢業數百萬大學生也有意愿購房,所以住房的“剛性需求”貌似源源不斷。
結論很樂觀,但論據可能存在缺陷。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對《南風窗》記者分析,中國樓市其實已發生屬性“變異”,即房子已從消費品變成投資品。房子如果拿來居住,那么就是消費品,有存在“剛性需求”的基礎。但中國的房子很多都是作為“投資品”來買的,“剛性需求”的說法站不住腳。“有錢人在投資,房子空置沒人住,這能算剛性需求嗎?” 易憲容說。
“剛需”和“投需”的區別在哪里?這很容易理解。如果是“剛需”,那么不論房價漲跌,自住的房子往往是不會被拋售的,樓市有了穩定劑。而“投需”就像買股票,必然追漲殺跌,如果房價下跌,投資者必然“斷供”來止損,最終導致信心崩潰,全面下跌。實際上,從2009年開始,溫州、鄂爾多斯已斷供頻現。
除了“剛需”的脆弱之外,“城市化”過程本身也可能接近極限,這在二三線城市表現尤為突出。
“過去十多年,中國從事農業的青壯年已經很少了,到農村看一看便知。”海通證券副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南風窗》記者說,中國的實際城市化率極可能被低估,甚至可能被低估10%。舉個例子,中西部很多進城的務工人員可能沒有城鎮戶口,只是在城市打散工,但卻在城里買了房。“城市有關部門可能把人口控制作為政績,存在少報動機。”李迅雷說。
不難發現,在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歷程中,工業化是最根本的推動因素。紐約、芝加哥、倫敦、東京、巴黎這些城市,無不遵循著“先有產業,后有樓市”的演進路徑。但就中國而言,除了工業化的自然推動外,政府投資成為了另一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這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獨特的“雙輪”驅動模式。
獨特的“城市化”路徑也影響了中國地產商的行為模式。內地地產商最熟悉的投資模型被稱為萬科“PIE”,地產商是否拿地,必須看這個城市的“PIE”值。在模型中,P(population)是人口,I(investment)是基礎設施投資,E(employment)是就業即產業的發展。模型有很多種理解,但其中一種最深入人心:投資是核心,而人口和就業只是其延伸的雙翼。
“拿不拿地,要看當地政府對投資的驅動能力。” 某H股上市上海地產商的一位投資經理對《南風窗》記者坦言,很多二線城市根本沒什么產業,也沒有常住人口的就業,但政府官員和金融機構關系好,能借錢,所以樓市也會火。
他舉了一個例子,比如某個樓盤位于二線城市一個偏遠的角落,但只要政府在旁邊挖坑修路,那么地產商就肯定會投。至于這條路修起來做什么,有沒有車跑,一點也不重要。“我們只拿二線城市的中心地段,因為一旦地方政府換屆,‘城市次中心就變了。”該經理笑稱。
強大的“雙輪模式”意味著“城市化”的高效率,同時也蘊含著高風險。因為兩個“輪子”必須同時有力,否則馬車就有停滯乃至顛覆的危險。而事實上,投資這個“輪子”總會有其膨脹的極限。
對一線城市來說,兩個“輪子”相對平衡。以廣東為例,其在2007年,常住人口便達到約9449萬, 超河南而居全國第一。背后寓意是,盡管珠三角的“城市化”也有投資驅動的因素,但產業發展更解決了更為關鍵的常住人口就業問題。但對很多二三線城市來說, 投資只帶來了“臨時工作”,即建筑工程業的流動務工增加,而本該作為常住人口的大學畢業生只能“逃回北上廣”。樓市“剛需”,從何說起?
“常州這種地方很少有外來人口,本地有錢人都去上海買房了,市場能有多大?”以上川渝投資人士認為,九龍倉下一步還可能在其他二線城市降價。
在一些缺乏工業化或者說產業化推動的二三線城市,政府投資充當了樓市繁榮的“內部保險”。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政策的轉圜空間仍然存在。李迅雷認為,低回報的投資,總有結束之時,必須看地方政府是否還能借到錢,是否還可以用各種理由要求中央財政給予轉移支付。
外部“保險”
形象地說,中國樓市很難用供需關系這類傳統框架來解釋,這個市場講求的是一種“勢”,而“勢”又時常被簡化為信心。當信心缺失,繁榮便可能成為無“米”之 炊。簡而言之,樓市的“米”包括兩種錢,一種是政府的錢,即投資推動的錢;另外一種是政府之外的錢,這些錢或投給地產商用作開發,或投資到物業以期升值。后一種錢來自于民間及海外,而海外資金尤其具有信心風向標的價值。
近年來,人民幣“升值”越來越被看成是內地樓市的“保險閥”。較普遍的看法是,當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那么在內地樓市逐利的錢將會大規模撤走,進而導致房價下跌。目前,國內“挺房派”和“打房派”的爭論焦點之一,也正在于此。
在海外資金的流動中,地產商在香港的發債息率具有標桿意義。目前,除少量原先國資背景較重的地產商之外,內地一線民營地產商幾乎都是香港上市公司。數據公司Dealogic的統計顯示,自2010年以來,外國投資者通過美元債券和以人民幣計價債券的形式分別向中國房地產企業提供了480億美元和60億美元的資金。考慮到地產商的融資量往往有著強大的“乘數效應”,因此可以說,海外資金是推動中國樓市投資的重要發動機之一。
為何海外融資火爆?原因主要在于成本較低。一般而言,企業從內地銀行貸款,利率加上“操作費用”,高者年化成本可能超過10%,但香港發美元債可能只要6%。
但數據反映了變化。《南風窗》記者查閱近年的公開數據發現,2009年之前,內地房企在香港發行美元債的年息率一般保持在5%左右,而2012年之后,這個數字經常超過8%,一些項目還超過了15%。盡管不同地產商、不同項目、不同時間的息率會有波動,但整體上升趨勢明確。2014年開年以來,該趨勢尤為明顯。
息率為何上升?一是內地地產商負債率升高,風險也升高,一些大型地產商之前以4%融資,但現在升到了10%,因此其負債率也上升了兩倍。另外,更多的項目開始位于那些外國投資者從未聽說過的城市,自然要求更高的風險貼水。
除了項目本身的風險外,息率上升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人民幣貶值的預期的隱現。上述H股地產公司投資經理分析稱,海外投資者的收益來自于兩方面,一是息率收益,二是在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務投資中的人民幣升值的收益。匯率變動的收益加上息率,海外投資者的收益相當可觀。但問題在于,如果人民幣貶值,那么收益就必須要減去匯率變動的損失。因此,投資者也必然要求融資方承受更高的息率。
該投資經理還認為,九龍倉這樣的港資地產商一直把資金成本看得很重。在“危險地段”速戰速決既可避免風險,也能讓財務結構更好看,融到成本更低的錢,好去開發一線城市更有把握、更加擅長的商用項目。
債券融資的“截面”無疑說明了信心的微妙轉變。事實上,當物業從“消費商品”異化為“投資品”之后,中國樓市早已變成一個“信心市”,這在二三線樓市表現尤甚。當信心潰散的扳機被扣動,事情發展便可能超乎想象。與此同時,既然GDP增速已從2010年的10.4%下降至2013年的7.7%,自然有人要為這樣的變化埋單。
換個角度看,在一些二三線城市,低效的投資也必然意味著尋租,權力階層的灰色收入和外地炒房團的資金成為了樓市繁榮的金融基礎。這樣的樓市,有什么理由堅挺?王石說,反腐是樓市最大的調控,個中深意,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