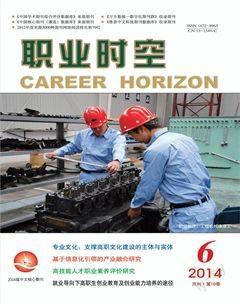“賢妻良母主義”與女子師范教育
趙司堯 朱峰 邢雪
摘要:清末民初,“賢妻良母主義”作為政府對待女性問題的指導思想,深刻影響著女子師范教育。從課程設置上看,清末的女子師范學堂集中體現了培養“賢妻良母”的目標,辛亥革命后的課程改革則兼具進步與保守成分,特別是袁世凱執政時期,由于社會需求的增加和觀念的落后,傳統女性觀出現了強勢反彈,致使民國初年的女子師范教育仍舊停留在傳統框架中。
關鍵詞:女子師范學堂;女子師范學校;課程設置;賢妻良母主義
早在中國古代傳統的家族觀念中就體現了對“賢妻良母”的認同,《女則》、《內訓》等著述深刻影響了女子在傳統社會的角色和定位。到了近代,“賢妻良母主義”在中國正式提出,其標準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1]
女子師范教育對提高女性素質有顯著效應,因而是清末政府和民間興辦女學的排頭兵,反映著社會對女子教育的重視。當時人們認為女子師范教育是在女學中確立家庭教育為本的正本清源之道,其性質和功能對于傳播“賢妻良母主義”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對1907-1916年女子師范教育的課程設置及其變革進行考察,探求“賢妻良母主義”在女子師范教育中的角色及其成因。
一、“賢妻良母主義”與初期課程設置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頒定了《女子師范學堂章程》(以下簡稱《章程》),標志著女子師范教育被正式納入國家教育體系。《章程》在開篇就明確指出,女子師范學堂“以養成女子小學堂教習,并講習保育幼兒方法,期于裨補家計,有益于家庭教育為宗旨”,[2]著重強調了女子所接受的師范教育應在很大程度上為家庭生活服務,從而奠定了“賢妻良母主義”教育的基調。總要共計十條,其中一、二、四各條系關于訓育者,與男子師范絕然不同,[3]它們突出了晚清政府對傳統女德、婦道的重視,并進一步說明了女子師范教育應達到的目標——培養賢妻良母。如第一條總要規定:“今教女子師范生……務時勉以貞靜、順良、慈淑、端儉諸美德,總期不背中國向來之禮教與懿媺之風俗……至于女子之對父母夫婿,總以服從為主。”[2]
在教育宗旨與總要的指導之下,《章程》還具體規定了女子師范學堂開設的學科以及四年間每星期的課時。就學科設置而言,女子師范學堂共開設修身、教育、國文、歷史、地理、算術、格致、圖畫、家事、裁縫、手藝、音樂、體操等13門,較之男子初等師范,家事、裁縫、手藝等科目獨屬女學,且修身課只重女教。而就此來看,其實質完全屬于賢妻良母的培養模式,以期使女性養成傳統女子之德性,于夫畢恭畢敬、完全遵從,于子溫柔慈愛、教導有方,于家勤勉節約、心靈手巧。同時,我們從《章程》所規定的課時數中也會發現,上述幾門課所占的比例是比較高的,四年均超過了四分之一。總之,在課程方面,《章程》一方面反映出晚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實行的是男女差異化對待,開設了一些適合女性學習與掌握的實踐型課程;而其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希望女子的學習重在傳統德行與家事技能的養成,女子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培養一批批合格的“賢妻良母”。
除此之外,《章程》在女子師范學堂的管理以及對學生的要求上也體現了“賢妻良母主義”教育的內容。如“選女子師范生入學之定格,須取身家清白、品行端淑、身體健全,且有切實公正紳民及家庭為之保證,方收入學”“學生當一律布素(用天青或藍色長布褂最宜),不御紈綺,不近脂粉”,[2]這就從入學條件及在校著裝方面對學堂的女生做出了極具傳統傾向的要求。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學部奏遵議設立女子師范學堂折》中依舊重申女子師范教育要“務期遵照臣部《奏定章程》……語言行事力戒新奇,即一切服飾皆宜恪守中國舊式,不得隨俗轉移。并責成國文、修身教習選取經史所載烈女嘉言懿行,時時與之講授,以培根本”。[4]
《章程》是女子師范學堂設立的法律性文件,既代表著政府對女子師范教育的整體設想,同時也決定著各地女子師范學堂的設立與運行。總的來看,晚清時期的女子師范學堂,無論是其立學總義、教育要旨,還是學科設置、課程目標,抑或是對學生的要求和管理,都特別注重為女、為母、為婦之道,希望用一種形式來約束女子的思想行為。[3]晚清女子師范學堂充斥著傳統的女子教育內容,是典型的“賢妻良母主義”教育,其實質就是要使女性以家庭為中心,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行,著力塑造一群符合傳統儒家文化要求的賢妻良母。
二、進步與保守并存的改革
民國建立后,所有女子師范學堂更名為女子師范學校,并多次調整了課程設置。1912年1月,《呈報并咨行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及課程標準》規定:“師范學校之學科目為修身、教育、國文、外國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理化、法制、經濟、習字、圖畫、手工、音樂、體操。”[5]同年12月出臺的《師范學校規程》指出:“女子師范學校本科第一部之學科目為修身、讀經、教育、國文、習字、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圖畫手工、家事、園藝、縫紉、樂歌、體操。”[6]1916年1月頒布的《修正師范學校規程》做出了進一步調整和細化:“女子師范學校本科第一部之學科目為修身、讀經、教育、國文、習字、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圖畫、手工、家事園藝、縫紉、樂歌、體操。”[7]
通過具體的課程設置,可以看出民國初年女子師范學校所奉行的教學理念同清末相比存在一定的差異:
從科目類別來看,民國初期的女子師范教育在保留“賢妻良母”所必須的家政、園藝、裁縫等家事類課程的基礎上,增加了外語、理化、博物、法制與經濟等富有現代特色的理論課程。這些整改體現了對女子文化水平的進一步重視,同時改革還更科學地適應了師范類學校的育人目標。對于未來的小學和幼兒園教師,專業技能的培訓不可或缺,如增設習字科便考慮到了板書對教師和教學的重要性,內容為“端正姿勢,及執筆、運筆之法,習楷書、行書及草書,并練習記錄與黑板寫法,兼課教授法。”[8]此外,一些“隨意科”的出現進一步賦予了女師教育更大的彈性和更多樣化的選擇,比如1912年1月,《呈報并咨行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及課程標準》規定:“視地方情形得加設農、工、商業之一科目。”[5]12月的《師范學校規程》也補充:“視地方情形,得加英語或世界語,為隨意科。家事園藝科之園藝得缺之。”[6]
在具體學時的數量和比例上,清末到民初,女師的總課時數基本沒有變化,但各科的份額卻存在較大差異。清末與“賢妻良母”密切相關家事類課程的學時占總體的27.9%。民國時期,1912年1月以上科目的比率為12.9%,同年12月有了明顯上升,達到了20.2%(算入外語為18.5%)。1916年即便增設了讀經科,其所占比率(20.6%,算入外語為19%)也沒有超過清末。民國初年家事類課程比例相對較低的原因在于習字、博物、法制經濟等其他課程的增設,同時家事類課程在課時上有所收縮,而國文、體育等的課時則略有增加,如表1所示。
表1 平均每周課時數變化對比表
從表1可見,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家事類課程的影響減弱,女子師范教育更加注重全面發展。雖然這一時期的課程設置有了顯著改觀,但從1912年9月到1916年,隨著袁世凱統治地位的鞏固,其推行“尊孔復古”的反動政策使“賢妻良母主義”出現了回潮,這一點在課程設置上也有鮮明的體現。
首先,重啟儒學和讀經科。民國伊始,教育部對清末的學制、課程做了大刀闊斧的整改。1912年1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9]1912年5月,教育部又下令廢止了師范、中、小學的讀經科。7月召開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蔡元培再次強調:“普通教育廢止讀經,大學校廢經科,而以經科分入文科之哲學、史學、文學三門,是破除自大舊習之一端”。[10]但袁世凱上臺后,重新將落后的封建倫常奉為圭臬。1914年3月,教育部長湯化龍在飭令上公然鼓吹道:“孔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微言大義亦多散見群經之內,則于學校教科書中采取其言行之切于倫常日用者,發揚吾國民固有之秉彛而示以懿德,庶國民教育對于國民模范人物,本良知之信仰乃益顯其效能”。[11]同年12月政府頒布的教育令上也指出:“中小各學校修身國文教科書,采取經訓,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前已由部呈請注重道德教育,擬于中小學校修身及國文教科書內采取經訓,務以孔子之言為旨歸……”。[12]
到1915年,經學更成為獨立的科目。政府下令:“各學校均應崇奉古圣賢以為師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學均加讀經一科,按照經書及學校程度,分別講讀由教育部編入課程,并妥擬講讀之法,通咨京外轉飭施行……”[13]并犧牲其他課時設置了“讀經時刻”,直接同畢業掛鉤。這一系列做法貌似是為了維護國粹,敦化風俗,但在當時對于啟迪民智,特別是女性的思想解放摧殘甚重。官方要求:“講經宜先就《論語》、《孟子》全文中之合于兒童心理及其學年程度簡明詮釋。”[7]在師范學校重啟讀經科,表面是為了滿足小學讀經課程的講授工作,但這也就意味著在師范學校就讀的女學生不僅要學習這些經書的要旨,更要諳熟其教授之法,無形之中致使本應該成為女性旗手的她們,反到成了封建倫理的傳播者和衛道士。
其次,增加了家事類科目的課時。從其本身來看,家事類科目的設置說明“國民政府重視家教知識的學習,將與家庭在生活中直接相關的工作加以科學技術性的教育”,[14]對于將傳統生活技藝的系統理論化和傳承有很大幫助。但根據前文的統計,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家事類課時在袁世凱上臺后大量增加,其所占比率相比于1912年1月增長了近一倍。這些變化標志著“賢妻良母主義”的回潮,而且與當時的社會狀況有著重要聯系。
三、“賢妻良母主義”的回潮動力
“賢妻良母主義”何以在辛亥革命不久后就驟然抬頭?這一反彈可以從當時社會的觀念和需求兩個角度考量。
從觀念來看,作為獨裁者的袁世凱首當其沖。他在女子教育思想上極其保守,認為女子應“勉為賢妻良母,以競爭于家政”。[15]1914年12月教育部提出:“(女學)標示育成良妻賢母主義,以挽其委瑣齷齪或放任不羈之陋習。”“使知從事于教養……注重體育及初等小學之訓練教授各方法,嚴定管理規程,修養其心身……要旨在發揮其特性,俾能以致密之理想、耐勞之習慣指導兒童,積漸誘進,以盡教育家之天職。”“使知從事于職業……以家政為重,兼及手工圖畫刺繡造花各科,養優美之本能,知勞動為神圣,一掃從前褊隘恬嬉之弊,庶家庭社會兩受其益。”[12]
隨著儒學禮教的滲入,修身、國文、讀經無不充斥著濃厚的封建氣息。上行下效,女子師范學校的教育和管理越來越僵化而迂腐,時任女子師范學校校長的吳鼎昌就是代表。時人記載:“吳課甲班修身必令學生一個一個站起,站起后吳斜視良久,上至頭髻,下至裙履,覽之殆遍,乃令坐下,點名畢已耗十五分鐘(學生僅十余人)。……蓋吳所實行之政策,在于禁錮學生之言論,閉塞其智識,干涉其行動,使之腦中眼里皆含有校長之權威,而后操縱愛憎,惟一人所左右。”[16]
同時,社會對女子教育的認識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改變。辛亥革命后,女子在社會中的客觀地位仍然沒有本質變化,民眾對女性的獨立人格缺乏認同,在教育領域也有人認為:“女子認識幾個粗字,懂得一點兒裁縫烹飪,以供家庭之驅遣足矣”。[16]可見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注定會對男女的社會角色進行區別對待,而且女子的身份選擇和活動領域明顯要更加狹隘。
從需求來看,社會對于家事類課程的教師需求量增加。1914年6月教育部文件指出:“目前女子中學師范之教員,所最缺乏者,不外家事、縫紉等科。茲由本部酌訂家事技藝專修課程表一紙,仰即斟酌施行。”[18]女子師范學校先后新設了小學教員講習科、保姆講習科、家事技藝專修科等課程,以求迅速彌補人才缺漏。
而從政府的意圖來看,女子師范學校對于宣傳“賢妻良母主義”還有特殊意義。這一點可以通過對比普通女子中學的課程設置窺見其意。從1913年普通女子中學課程設置(1913年3月)[18]與前文中女子師范學校課程設置(1912年12月)[6]、女子師范學校課程設置(1916年1月)[7]的比較可以看出,在總課時相差無幾的前提下,女子師范學校的課程設置中,縫紉、圖畫手工的課時要比普通女中多出近一倍,并相應減少了國文、歷史、地理和外語的課時。這一現象也反映出社會對家事類課程教師的需求。而更深層次地看,作為國民教育之母的師范教育,其學生不僅有“成己之責”,更有“成人之責”,對中小學有十分重要的引導和模范作用。于是,政府便意圖將女師范生打造成賢妻良母的典范,使得她們也能在之后的工作中培養出更多的賢妻良母。因此,當局既對女子教育有十分明確的定位:“女子教育注重師范及職業,并保持嚴肅之風紀。”[12]同時,也對師范教育有極其嚴格的要求:“師范學生采嚴格訓育主義,俾將來克盡教師之天職。”[12]
但這些政策的出臺,與其說是政府對女子師范教育的重視,不如說是女子師范學校的特殊性質使然——師范教育的傳播功能恰好契合了政府推廣“賢妻良母主義”的需求,因而相比于普通女子中學,家事類因素在女子師范學校的課程設置上更加突出。在這種模式下,女子師范教育兼具了制造和傳播兩重意義——既是培養模范式的“賢妻良母”的溫床,又肩負著將“賢妻良母主義”普及推廣的使命。
四、結 論
從清末到民初女子師范學校的課程變化來看,“賢妻良母主義”在其中的地位呈現出由高降低再抬頭的趨勢。民國初期的教育改革讓女師學生解除了大量負擔,擁有了更多學習其他知識的機會,為她們擺脫“賢妻良母”的桎梏創造了可能。然而,落后勢力的回潮讓女師重新染上了封建倫常的色彩。究其原因,無論是觀念還是需求,都是基于對女子的片面認識,其本質依然與“賢妻良母主義”密切相關。可見此時社會對于女性的定位仍然從屬于家庭,政府也更側重讓女性從事與“妻”、“母”相關的工作,將其活動限制于居家勞動和教育兒童。
然而這種教育本就帶有很強的局限性,因為它在認識女性時先入為主地將其臉譜化,從身份而非人格出發,導致了“妻”與“母”的角色吞噬了女子的個性,女子的家庭身份決定了其社會身份,教育家葉圣陶對此深惡痛絕,他曾批評道:“‘良母賢妻又是女子的大教訓。近時開了女學校,至標這四字做施教的主旨,這豈不是說,女子只應做某某的妻、某某的母,除了以外,沒有別的可做了……人格完全的人,他總不把‘做某人的某人算究竟,他總要做社會上一個獨立健全的分子。女子被人把‘母、‘妻兩字籠罩住,就輕輕把人格取消了”。[19]
綜上所述,盡管女子師范經歷了從學堂到學校的一系列變革,但很快伴隨著政治步入低潮,至少在課程設置上,民國初年的女師教育仍舊偏向保守,這也為五四新文化時期的新學制和婦女解放埋下了伏筆。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梁啟超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495.
[2] 女子師范學堂章程[A]//璩鑫圭,童富勇,張守智.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實業教育師范教育,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597-604.
[3]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1895-1945)[M].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1989:34-37.
[4] 學部奏遵議設立女子師范學堂折[A]//璩鑫圭,童富
勇,張守智.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實業教育師范
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795.
[5] 呈報并咨行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及課程標準[A]//[日]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民國編),臺北:文
海出版社,1976:571.
[6] 師范學校規程[A]//璩鑫圭,唐良炎.中國近代教育
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688-693.
[7] 修正師范學校規程[J].中華教育界,1916,5(2).
[8] 師范教育令[J].教育部編纂處月刊,1913,1(3).
[9] 普通教育暫行辦法[A]//[日]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
教育史資料(民國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571.
[10] 蔡元培.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J].教育雜志,
1912,4(6).
[11] 湯化龍.飭京內外各中小學修身及國文教科書采取經
訓務以孔子之言為指歸文[J].教育公報,1914,1.
[12] 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J].教育公報,1915,8.
[13] 大總統特定教育綱要[J].中華教育界,1915,4(4).
[14] 雷良波,陳陽鳳,熊賢軍.中國女子教育史[M].武漢:
武漢出版社,1993:288.
[15] 大總統頒定教育宗旨[A]//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
料(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1933:110.
[16] 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最近大風潮聞見記[J].婦女時報,
1913,(9):50-54.
[17] 批女子師范學校女子高等師范未設以前暫準該校附設
專修科[J].教育公報,1914,2.
[18] 中學校令施行規則[A]//璩鑫圭,唐良炎.中國近代
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682.
[19] 葉圣陶.女子人格問題[A]//葉圣陶,葉至善,葉至
美.葉圣陶集(第五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