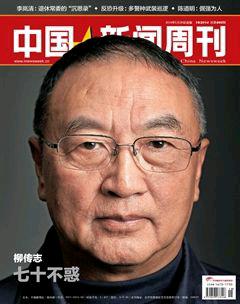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馬光遠
5月上旬,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首次以新常態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國經濟。
應該說,“新常態”這種提法并非新詞。近幾年,面對中國經濟增速的持續下滑,國內的很多經濟學者都試圖從理論和參與決策的層面論述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征和表現。但對于新常態究竟是中國經濟危機后的各種不穩定表現,還是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常態的周期,學者之間的分歧很大。而習近平這次站在決策者的角度,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并從經濟發展戰略的高度提出“新常態”的概念,則屬首次,其勢必對中國未來的宏觀政策選擇具有方向性的影響。
新一代決策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并通過“新常態”透視中國宏觀政策未來的選擇,絕非“一時興起”,而是深思熟慮之舉。事實上,自2010年中國GDP規模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之后,中國經濟出現了明顯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自2010年至2012年經濟增速連續11個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連續兩年低于8%。對于經濟增速的持續下滑,理論和政策層面對此分歧很大。一部分學者認為,2010年以來經濟下滑是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一旦這些因素消除,中國經濟會恢復快速增長;而絕大多數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近幾年增速下滑的原因是趨勢性的,是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舊的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經濟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很顯然,兩種觀點不僅僅是理論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蘊含的宏觀政策的導向完全不同:如果認為中國經濟的減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則意味著目前的經濟增長是低于潛在增長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為;如果認為中國經濟的減速是內在因素所致,則意味著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是潛在增長率下降,宏觀政策對此應該保持必要的克制和包容。
事實上,新一屆管理層對中國經濟的減速和先前模式的不可持續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去年換屆之后,習李二人在很多場合都為盲目追求GDP增長的行為和理念降溫,多次表示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到新的中高速增長階段,中國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追求遠在速度本身之上,中國不會追求有后遺癥的速度等等。這種將對速度的簡單追求保持強烈克制的執政思維在2013年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盡管全年穩增長壓力很大,但外界概括的“李克強經濟學”的精髓之一——不刺激的政策方向貫穿全年,這在換屆的第一年,的確讓外界看到了管理層推動改革和發展方式轉型的決心與魄力。
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習近平關于“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提法與外界所概括的“克強經濟學”在理念和內在邏輯上幾乎是一致的。按照我的理解,“新常態”至少應該包含以下幾方面:一是經濟增速正式告別8%的快速增長,潛在增長率在2020年前后回落至7.5%左右;二是宏觀政策告別常態的調控和刺激,如果經濟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區間,不會采取非常規的刺激措施;三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悄然轉換,政府投資讓位于民間投資,出口讓位于國內消費,創新驅動成為決定中國經濟成敗的勝負手;四是在推動新型工業化使命的同時,強力扶持服務業,經濟結構避重就輕;五是告別貨幣推動型增長模式,控制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泡沫和債務杠桿優于經濟增長本身。
如果上述“新常態”的理念在政策層面得到貫徹,幾乎意味著:面對當前經濟下滑的壓力,管理層絕不會輕易啟動以前動輒救市的模式,容忍甚至聽任經濟下行可能引發的一些風險,比如企業債務和房地產泡沫。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遺留的產能過剩、債務杠桿以及房地產泡沫的確極為痛苦,但這是倒逼中國走上真正的改革正道,推動經濟轉型的唯一正確的選擇。這是個套餐,要選擇改革,就必須真誠面對過程中的痛苦和必須的代價,羅曼蒂克式的、田園牧歌式的改革從來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中,就現實而論,改革和轉型的過程是極為痛苦的。
我一直堅持認為,中國還處在極為珍貴的戰略機遇期,但這種機遇能否兌現,取決于我們能否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對經濟減速保持寬容,對調整中的風險不再回避和拖延。更直接一點說,能否借房地產調整的時機,痛下決心,刮骨療毒,擺脫對房地產的危險依賴,這是中國經濟未來能否再次勃興的關鍵。如果輕易啟動救市模式,再次推高已經高高在上的泡沫,屬于中國的機會就會漸行漸遠。且行且珍惜。